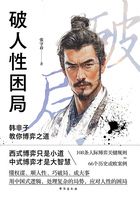
第5章 有度:用人技巧
1 识人要靠主见,不是他见
原文
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
作者智解
(君主经常的做法是,听臣子们对某个人的称誉或非议,来决定提拔和斥退谁,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根据下属赞誉谁来提拔谁,那么臣子就会结党,民众都忙着结交朋友、搞关系而不求依照法令了。谁被称誉得最多就提拔谁,被诋毁得最多就惩罚谁,那么人们就不顾公法,而私下用术,互相结党比周。臣子都忘了君主的利益,跟别人结交来推荐自己的党友,下面人替君主着想的就太少了。
延伸论据:李林甫的美名——征求意见要谨慎
如果领导对待下属的进退,都靠听别人的毁誉(毁指批评,誉指赞誉),那么就会发生偏差。
按现在的观念,领导在用人时,要听听群众的意见,但韩非子对征求意见持不赞成的态度。这是因为当臣子们都结为朋党的时候,他们的毁誉是基于私人集团的利益,所以,越是征求意见,越是被蒙蔽。可以举两个例子:
李林甫是唐玄宗时候的奸臣。他原本是皇族的远亲,但是没有什么学问。有一次,李林甫的表弟生了一个儿子,他写信道贺:“闻有弄獐之庆。”此处应为“弄璋”。璋为一种玉器,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獐则是一种没有角的鹿。客人看到后都捂着嘴偷偷笑话他。
李林甫的贵人是他的情人——大名鼎鼎的武三思的女儿。武氏想让自己的情夫李林甫当宰相,请高力士向玄宗推荐李林甫。高力士没敢说。武氏又帮着李林甫去巴结宰相韩休,韩休因此很喜欢李林甫。宰相韩休在唐玄宗面前高度赞扬李林甫,说他有宰相之才,于是唐玄宗很快把李林甫提拔为黄门侍郎,作为韩休的副手。过了几年,韩休下台,李林甫顺利当上了宰相。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李林甫能当上宰相,就是因为一些贵人在皇帝面前推荐保举他,而他通过情妇跑通了这些贵人的关系,实际上他也没有什么文化,这就是领导听从别人的毁誉(指赞美或毁谤)而任用人,结果选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李林甫的人品也不行,号称口蜜腹剑。所以,韩非子说选人要通过考核,而不是身边的人说谁好谁坏。
李林甫能当上宰相,是因为皇帝听从身边人的胡乱赞美。韩非子说“君主经常听臣子们对某个人的称誉或非议,来决定提拔和斥退谁。如果根据下属赞誉谁来提拔谁,那么臣子就会结党”,总之,向别人征求意见和评论是最不建议的做法。别人能老老实实地说实话吗?聪明的领导者通过实践考察来判断,而不是向左右人去打听某人好不好。
2 小团体利益与君主利益相悖
原文
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
作者智解
臣子互相交结,相好的人多,内外构成朋党,即便他干了大坏事,也有人替他罩着、捂着。所以忠臣无罪却落得死,坏人得利还没事。这样,群臣都不按法办,都行私。人们都跑去党魁(强臣)的门下走关系,没有去看望君主的。都考虑对自己私家的好处,没有替国君考虑的。官员数量虽然多,也没有替国家做事的。国君虽然有人主之名,实际权力却落在了私家那里。各私家都务求互相帮忙,增加各自的财产,没有忙着使国家富起来的;大臣们互相提升、巩固彼此的地位,没有忙着尊抬国君的;小官只在乎自己拿多少工资,而不在意官事干得怎么样。
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君主没有一切以法来断,而信下面的人称誉谁或诋毁谁。
延伸论据:三人成虎、劫持君主——上位者怕“结党”
臣子一旦结党,就会异口同声地非议某个人。君主听了,肯定会把这个人罢免。关于这个,可以讲三人成虎的故事。
庞恭陪伴太子去邯郸做人质,临走前对魏王说:“假如有一人说农贸市场有老虎,您信吗?”魏王说:“不信。”庞恭说:“如果两人说有虎呢?”魏王还说不信。庞恭说:“三人说有虎呢?”魏王说:“那我就信了。”庞恭说:“农贸市场明摆着没有虎,但是三人说有虎,就成了真的有。邯郸离这里更远,非议我的人可能超过三个,希望大王明察。”
等庞恭从邯郸回来的时候,国君竟不肯见他了——他还是被人在国君面前诬陷,而且国君信了。这就是三人成虎。臣子结党,异口同声地说某人坏话,听得多了,再贤明的君主也会被蒙蔽。
下级拉帮结派,是上级最怕的事情。
张仪和惠施两个人在魏惠王面前争论,一个主张魏国跟秦国结好,另一个主张魏国跟齐国结好。其他的魏国大臣都发言赞同张仪。魏惠王狐疑了半天,打算按张仪说的办。
等魏惠王一退朝,惠施赶紧跑进内宫求见。魏惠王说:“先生不要再讲了。我已经决定了结好秦国,听张仪的,这是对的,而且一朝之臣尽以为然。”
惠施展开逻辑,劝说魏惠王:
“朝士尽以为然反倒有问题了。按照客观规律,小的事情,说可和不可的人应该各占一半,何况是大事呢?结齐还是结秦,是大事,但群臣都认为可,不知是因为这种可,是如此明显,还是群臣的智术,如此一样。其实这件事的可,并非如此的明显,群臣的智术,也应该是不尽相同的,那就是有一半人的真实意见被堵塞住了。所谓‘被劫持了的君主’,就是失去那一半人的真实意见的君主啊。”
魏惠王还是转不过弯来,糊里糊涂地让惠施带着他的逻辑先走了。
惠施这里说的,其实就是结党的问题。在讨论大事时,应该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现在群臣异口同声的都是赞同,那就说明他们结党了——也就是跟张仪结为一党了。这时候,君主就算是被他们劫持了。这些人统一口径一起忽悠魏惠王。
君子避免下属结党的办法,就是使用法度,而不是听大家称赞谁和否定谁。具体来讲,就是韩非子接下来说的内容。
3 任法不任人
原文
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作者智解
明主用法来选择提拔人,不主观挑选;用法来度量这个人的功业大小,不自己主观度量。能者不会埋没,差的也不会虚伪地自饰,大家都称誉的人(交结党友的党魁)不会被提拔,大家都非议的人(不肯同流合污的)不会被降职。这样就判断准确了,所以君主一切要依照法。
延伸论据:齐威王的单独考核——“火力侦察”拿到真情报
韩非子这里说,避免下级结党的办法就是君主一一地考核这些人,从而判断出谁好谁坏。如果是听大家的口头称赞和诋毁,那么好人也会被说成坏人,坏人也会被说成好人。我们说一下齐威王的故事。
齐威王善于用这种办法去检查下属,而不是听左右亲信们的毁誉。齐威王派人调查阿大夫的地盘,发现这个公认的优秀者所管辖的阿县却是田野不辟,人民冻馁。他开会告诫大家:“我们必须根治虚假,你们要常下去看看。好吧,今天杀一儆百,先把虚报成绩的阿大夫烹了。”于是,鬼哭狼嚎的阿大夫当着各级地方领导的面被烹了,平时交口称赞阿大夫的人,也一同入锅当了作料。
显然,阿大夫就是靠着贿赂齐威王身边的人(这些人都替他说好话),把他装扮成好官,才得了好评。但是,齐威王一下去考核,就避免了被蒙蔽。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君子以法和考核来明察臣子,而不是听别人的口头毁誉。
领导和奸邪的人博弈时,后者会释放假情报,判断真假的办法就是进行“火力侦察”。考核就是一种火力侦察。别人的评价和意见可能是被这人操纵和扭曲的,盲从的上级就成了“盲聋”的人。任法不任人,信息情报收集要把握在自己手中,这样才能避免误解和偏差,小人失去了从中捣乱的空间,自己也避免了决策错误。未经验证的信息,都是不能接受的。
4 一个人怎么与多人博弈
原文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崄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禁过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作者智解
贤良的人臣(干部),向国君效忠,没有二心,遇上事情不推诿,打仗不因为害怕而推辞,顺着上面的要求,遵从主上的法,虚心等待命令而不惹是非。好的人臣,就像手一样,向上去保护头,向下去保护脚。
现在,大家都看轻爵禄,轻易就换地方,另择一个主子(跳槽),这样的臣子都不算是廉(古文“廉”指不看重财物)。胡说八道,违逆法令,背离主子进行强谏,这不是忠;对别人施惠,求得大名,这不是仁;隐居起来,非议君上,这不是义。
对外出使诸侯,对内消耗国家,趁着国家危险就吓唬自己的主子:“这些外交危险除了我没有人能解决了。”国君就听他的了。他自己捞了好处和利益(如今做业务的,也有这么干的。制造市场困难,回来跟总裁要好处,说自己能解决,从而拿奖金),这都是乱世的特点。从前治世不是这样的,当时大家都奉公法,废掉图私的心术,专意一行,准备好接受任务。
人要是靠自己察验百官,那么时间和精力都不够。你用眼睛来察看,下面的人就装饰自己的外观;你用耳朵来听,他们就修饰自己的声音;你用思虑来查看,他们就美化自己的言辞。这些都不足以,所以应该舍掉自己的能事(主观检查判断)而一切遵从法数,审定赏罚。
(这里说的法数,后文《扬权》的第二节中有详细的讲解,就是用任务考核,来判断他的好坏。)
掌握这个简单的要领,就不受侵害了。他独制四海之内,聪明的人不敢用诈来骗他,险躁的人不敢用佞蒙来蔽他,奸邪的人无所依托。朝堂群臣都把自己单独的力量汇集给君主,不敢越官交结(指不同职务的人串通)。
人臣侵夺他的主子,是渐渐扩及的,叫人主慢慢丧失权柄而不自知。所以明主使唤群臣不要超出法的范围,也不要在法之内随便施恩,一切行动依托法(这些法,指广义,也包括组织内的规矩)。对方犯错了,绝不宽贷,持法权柄也要单独握在君主手里。所以说,巧匠靠着目意也能中绳,但一定要先以规矩为度。
即便聪明的人做普通的事,也需要依照方法规则。绳子直才能把歪的木头砍掉,标准平才能把突出的部分砍掉,权衡(秤砣)有了才能定出轻重。所以以法治国,就是把标准放上去而已。法不阿附贵人,就像绳子不绕过曲的木头。法所加的地方,聪明的人也无所辞避,勇敢的人也不敢相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问责下面的邪辟,把乱的搞清楚,把民众统一到一个轨道上,莫如用法。治理官和民,把淫殆的人斥退,莫如用刑。刑罚重,则上面的人尊高而下面的人不敢侵上。如果人主放弃法而用私,则上下无别了。
延伸论据:李林甫——利用信息不对称,打掉竞争者
君主用法这种客观工具来度量,而不是私下的主观判断,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上文的主要意思。
李林甫做宰相时,同做宰相的还有李适之。李林甫口蜜腹剑,想害李适之,以便自己独揽大权。李林甫告诉李适之:“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皇上还不知道这件事呢。”李适之赶紧报告给唐玄宗。玄宗问李林甫,李林甫却说:“我早就知道这个,但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王气所在,开凿它不合适,所以我没敢提这个事。”
唐玄宗听了以后,认为李适之考虑不周,更加亲近李林甫,还把李适之批评了一顿。后者又遇上几次类似的事,李适之干脆饮药自杀了。于是,李林甫成为独揽大权的权臣。
李林甫作为宰相,嫉贤妒能,又搬弄是非,把一些有潜力升为宰相的优秀官员,如户部侍郎,都罢免乃至害死,以免威胁到自己。在这过程中,唐玄宗依旧是听他的口头评论,来决定这些人的进退。如果唐玄宗能客观考察那些人,就能留下其中有用的,用来制衡李林甫。
这就是韩非子说的,“应该舍掉自己的能事(主观检查判断)而一切遵从法数,审定赏罚”。口头评价会有很多误解和信息损失或扭曲,人听了,容易萌生猜疑,所以必须以事实来验核。过于信任一个人,而不加查验,怎么算是明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