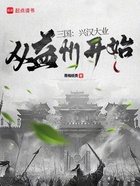
第88章 大势下的声音
夜色如墨,大将军府外。
月光隐去,只留一片深沉的暗色。
何进身披朝服,快步踏出府门。
未等行出几步,两道身披铠甲、手执长剑的身影猛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袁绍面色凝重,曹操眼神锐利,二人齐声高呼:“大将军,此番切不可进宫!”
何进眉头微皱,不悦地问道:“为何?本将军亲胞妹召唤进宫,难道其中还会有隐情不成?”
袁绍急忙上前劝阻,解释道:
“大将军,太后必定是受张让等宦官所惑,将军此去必有祸灾啊。大将军矫诏召外兵入京,此谋已泄,其事已漏,此时进宫,岂不是自投罗网?”
曹操沉声附和道:“大将军,本初所言极是。若要进宫,也当先让张让之徒出宫,确保万无一失才行。”
何进不以为意,大笑一声:“孟德啊孟德,你又在讲笑话了。我掌天下之权,张让之徒又能奈何?莫非他们这些无能之辈还敢图谋大臣不成?”
曹操知道自己的劝言对何进无用,索性便将心中打好的腹稿继续存放于心,退于一旁不再说话。
袁绍不死心,苦口婆心道:“大将军,切勿轻敌冒进。若一意前往,可让我与孟德调城门兵引甲相护!”
何进有些不耐烦,但见是袁绍相劝,他也只好压下火气,摆了摆手说道:“好了,本初无需多言,本将军自有分寸。”
言罢,何进转身走向早已备好的马车,快步登车,驱使车夫迅速进宫。
袁绍和曹操目送着马车远去,心中皆是忧虑重重。
曹操眯着眼冷哼道:“大将军如此不听忠言,宫城之中必生危难。”
袁绍叹了口气,声音颇为无奈:“孟德,事已至此,你且快去调城门营兵相护大将军,以避免途中不测。”
曹操拱手作别,转身快步向城门营奔去,心中暗自祈祷此番何进能够平安回来。
否则,一旦董卓领外兵成功入京后,将无人遏制其乱来,大汉天下内外加剧的危乱也将会随之开始。
到时大汉的臭虫又真会像沈稻所说的那般倾巢而动吗?
对此,曹操不得而知。
……
……
中平六年,十二月。
益州,巴郡,汉昌县内。
郑度拿到雒阳那边快马送过来的秘信后,当即起身快马赶到汉昌亭候的封地,四处张望寻找从雒阳回来后便专心种田的主公。
大树底下,百姓们围堵得水泄不通,官兵们手拿手阻挡,努力的维持着现场的秩序。
“亲爱的各位乡亲父老,开春在即,今天我带来了汉为的黄金豆,大家也可以因其种在土里而叫做土豆。”
沈稻一身青衫,手拉折扇,站在人群中央,手里拿着一颗土豆,面带微笑地向周围的百姓们介绍。
百姓们听后,纷纷露出好奇和期待的神色。
“沈亭侯自从你来了汉昌县,除匪患修陂池,又借给乡里人官府的牛,还白送农具,亭侯说种土豆,我们乡亲们哪有不种的!”
“对对对!沈亭侯才是我们汉昌县的众望所归!亭侯让我们有了好日子过,让我娶到了婆娘,沈亭侯叫种啥我就种啥!”
“八月田里干,是沈亭侯制水车引护城河的水来浇淋老汉我的田。现在亭侯说种土豆好,信他的,准没错!”
“……”
润物细无声,沈稻回到益州后的一系列无心之举,让朴实的当地百姓牢牢记在了心头。
汉昌亭侯身上的这些善意,是他们这群底层小人物从没在大人物身上看到过的。
围过来看热闹的百姓越聚越多,有的人甚至开始高呼起来,数百十人的齐声高呼,让沈稻产生了一种想要演讲的冲动。
“我们需要种植新的农作产物,它的生长必须迅速,必须忍耐干旱,忍耐土地的瘠薄。现在它来了,土豆就种在来年的春耕!”
“来年春耕种下的土豆,将带领我们汉昌县的百姓走向温饱,远离灾荒之年的饥肠辘辘!”
沈稻的声音充满了力量,他的双手激动的在胸前不断比划。
在场的百姓没人知道来年的春耕会是怎样,但他们却仍是坚信不移的欢呼起来,响应着沈稻的号召。
待人群稍稍退去些许,沈稻方才在亲卫队的护送下退于一旁的别院之中。
在场目睹完沈稻的所有言行,郑度近前打趣道:“主公真可谓是一呼百应,眼下雒阳传信来说,校尉曹操刺董失败,同袁绍矫诏天下,现时机已至,实可行大事也!”
沈稻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从回到益州的这段时间里,沈稻时不时的就会从雒阳那边知道一些他已经知道的事情。
诸如大将军何进身死宫中、董卓废帝乱京城、吕布弑父掌控并州军、袁绍的剑未尝不利……这些消息全部都来自雒阳的汉为酒楼。
不过比起这些已知消息,沈稻更好奇吕布有没有认董卓为义父,袁绍真的那么有种,曹操逃亡的路上有没有杀吕伯奢一家之类的。
沈稻沉默了一会儿才问道:“我之前问的问题,奉孝他可有在信中回答啊?”
郑度抚须没好气的说道:“郭嘉先生回信告之,骑都尉吕布并没有拜董卓为义父,再者袁绍与董卓堂中拔剑对峙确有此事。”
沈稻哦了一声,不再说什么。
郑度竭力抑制着内心的激荡,以沉稳而含蓄的语调言道:“亭侯,吾等何时挥师进发雒阳,与四方诸侯之联军并肩,共谋伐董之大计?”
“这是一个让我头疼的问题,”沈稻轻轻叹了口气,“目前李铁收招过来的兵卒不过三千,其中大半数还是没上过战场的新卒,如何能起兵过董?”
郑度闻言差点没忍住破口而出。
诸侯联军讨董,这是何等的名扬天下的机会?
匡扶汉室的必行之事,沈稻却告诉他这是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在郑度看来如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又怎能因战卒不足而错失?
郑度毕竟是个谋士,他有智者的战略定力,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想了想,事实也确实如沈稻所说。
沈稻去雒阳的时候,将手中的能战之兵尽数交给了刘焉,如今能余下一千的可战之兵已是不可多得的极限。
不过,郑度眼珠一转,很快就想到了解决方法,沉声说道:“亭侯,吾等可借匡扶汉室之名,向益州牧刘焉借兵五千。”
刘焉虽有野心,然已是暮年,行事谨慎,不过一守土之辈。吾等以家国大义相责,晓以利害,刘焉定会碍于名分,不得不借兵给我们。”
沈稻看了看郑度,满脸的赞赏。
想当初临走时,他交给刘焉三千战卒,如今自己回来了,郑度这家伙竟然要连本带利的道德绑架对方拿出五千战卒!
能主动给汉为集团投简历的,不得不说都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狠人啊!
郑度这位益州谋士,沈稻打心底地很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