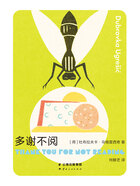
文学梦
在市场主导文学的文化环境里,无产阶级,也就是我们作者,是最痛苦的。所有作者中,又以东欧作者最令我同情,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批声名狼藉者中的一员。
美国与西欧作家曾长期嘲讽他们的东欧同行尸位素餐,说他们看牙不要钱,住房不要钱,度假上免费的作协度假屋(dom tvorchestva),偶尔竟还能住到独栋房子(dacha)。但他们狡猾地对自己的尸位素餐守口如瓶,比如他们创作的自由,他们靠写作获得的奖金、资助,他们为写作设立的基金会、举办的活动,比如他们出书有国家补贴、有外国译介,还能以艺术家之名免费入住度假别墅(作家之家)。如今,西欧作家依然享有这些权益;而东欧作家的权益已全数归零。
我必须承认,这个零让我脑壳疼。每天晚上我都做噩梦,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斯拉夫了,就像情景喜剧《艾伦秀》里说的那样(我感觉自己脾气大、心情差、情绪低迷,整个人都斯拉夫了!)。
比方说,我梦见一个很大的露天集市,我们一大群农民都在集市里卖自己种的菜。我的摊子上可怜巴巴地摆着三个甜菜头。伟大的俄国作家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在我面前停步。“你的甜菜长得真好,”他说,“与其说是甜菜,不如说更像土豆。”
我还梦见自己的牙齿一颗颗地掉了出来,变成了我尚未写出的作品集里的一本本书,书名分别是:《门牙》《槽牙》《犬牙》……
我又梦见自己是某小部落的一员,部落坐落在西伯利亚森林里,我奉命修书,要记载整个部落自有文字以来全部的文学,正往一块西伯利亚驯鹿鞣革上雕刻部落文学的开头。
我梦见自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不仅奇迹般地复活了,而且还能看得见东西。他碰了碰自己的眉毛,变成了保罗·科埃略。
总而言之,我的梦都很吓人。不久前我还梦见自己被战争犯拉多万·卡拉季奇[1]捉住,他为了折磨我,要我在男女老幼面前朗诵他的诗歌,甚至逼我背诵,而且每天都要抽查。
我也梦过自己是欧洲南部一个叫克罗地亚的小国里最伟大的作家,该国主席给我颁了一块奖。
“祝贺你!芬基尔克劳[2]先生!”主席一边把奖牌挂到我脖子上,一边说,接着,他展示出国家领导人的风范,亲了亲我的嘴。
“可我不是芬基尔克劳!”我惊恐万状。没有人听见我的喊叫,大家都在热烈鼓掌。
我还梦见自己是琼·柯林斯,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准备去斯德哥尔摩时的受奖辞。梦中我浑身冒汗、体似筛糠,很难说我究竟在怕什么:是获奖紧张呢,还是因为琼·柯林斯居然也能获奖?虽然在梦里,时年六十有余的我看起来只有三十岁,但这也没能给我什么安慰。
在另一个类似的梦里,我变成了伊万娜·特朗普,并被选为国际笔会主席。这个梦比诺贝尔奖那个好多了,因为任命完毕后我们就去了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所有作家都在那里点到了18.99美元一位的下午茶。
我梦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老是从他的坟里出来给我打电话。
“Ah, koleshka, ty moja koleshka...[3]”他叹息着。
“我又不是你的同事!你为什么总是来烦我?”我嚷道。
听筒那边陷入死寂。
在最近的一个梦里,我变成了萨尔曼·拉什迪,我把自己赚到的所有钱都捐给了一个致力于保护阿尔及利亚作家和所有其他受威胁作家的基金会。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梦叫我特别心烦,我就去找心理咨询师。
“你为什么不干脆改行?”
“什么叫干脆?是彻底不写了吗?”
“干吗不呢?重塑自己!”心理咨询师好心地劝我。
我还真的听了劝告。在一家葡式餐馆找了个女招待的工作。有个同事有时下班后会一边喝红酒一边背佩索阿给我听,那段时间,我与文学的接触仅止于此。我再也不做文学噩梦了。我的梦变得令人神清气爽。比如,我梦见自己是一个飞着为顾客送餐的葡式餐馆女招待;一个超人女招待。客人们走前将小费抛向空中,而我彬彬有礼地接住,引起在座食客的一片掌声。
1996年
[1]Radovan Karadžić(1945— ),原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1995年因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起诉,此后一直在逃,直到2008年被捕。逃亡期间,他化名德拉甘·达比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家私人诊所做心理医生。2016年被判处四十年监禁。自1968年来,他曾多次出版诗集与小说,其诗作被誉为“充满了人道主义和斯拉夫精神”。
[2]Alain Finkielkraut(1949— ),法国哲学家、作家、公共知识分子。
[3]俄语,意为:啊,科列什卡,你是我的科列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