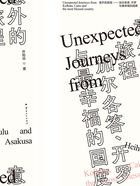
世界的鸟巢
加尔各答的乌鸦
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那是俄国人在1963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都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他赞扬过日本,期望过中国,俄国人如今则激起他最慷慨的钦佩,在两周的旅行中,他保持了一贯的高产,写下十四封信。在最后的两封信中,他的乐观开始消退,感到了苏联实验的另一面:“我还是觉得,他们不能正确地划清个人和社会的界限。在这方面他们同法西斯分子相类似。他们忘记了,削弱个人,不可能加强集体,如果束缚个人,那么集体也不可能获得自由。”
这最后两封信,没出现在苏联官方出版的泰戈尔文集中,他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表达出的相似忧虑,直到1986年才被刊登出来。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与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一片连绵的建筑,则是一所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它的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经过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博物馆中,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
无处不在的,是泰戈尔的形象。英俊的、椭圆的面孔,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都被包进了浓密、垂下的头发和白胡须中,还有那袭白色长袍,如果他再晚生一些年,必定可以直接出演《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这一形象曾风靡世界——一位神秘的东方智者,了解拯救世界危机的智慧。这个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当我看到照片中他少年时瘦弱、敏感的样貌,多少有些不适应,似乎他理应一出生就老去。他是那个由报纸、摄影、电报、杂志构成的媒体革命中的全球偶像,他的外表与内涵同样至关重要。能与这个形象媲美的,可能只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天才的头发如宇宙爆炸般展开,一脸孩子式的心不在焉。他们还会过面,在1930年的柏林,他们共同谈论科学、美与真。“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瞭望台就不再美了吗?”爱因斯坦问。泰戈尔说:“是的。”
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里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他的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一样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在地板上走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迦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它是泰戈尔1916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地批评了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认为那是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2008年的春天读到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试图邀请过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当时中国境遇更糟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泰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为印度赢得了另一种自尊,他的诗歌征服了欧洲,他还四处宣扬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一定给予了一些中国人某种鼓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亚洲价值观”的前身。
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都出自他笔下。不仅泰戈尔,甚至整个南亚大陆在我脑中都是一片空白。谈论亚洲时,我想起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那是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也激不起我们的任何兴趣。我们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等级意识,当我们谈论世界时,世界仅仅意味着发达的、白皮肤的欧洲与美国,他们意味着财富、权力、教养。相较之下,我们对于黑色、棕色皮肤主导的地带兴致寥寥,即使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权力中心东移、中印崛起的神话。
“别乱吃东西,只喝瓶装水,要打防疫针。”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去印度,警告我说。在全球经济中刚刚大放异彩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的印度形象,压不过那个“失败”的印度形象——连车厢顶上都站满了人的火车、满街的垃圾、路旁睡着的人群,“红头阿三”的印象也偶尔冒出,他们天生是做苦力的。印度宗教与文化中的神秘色彩从未让我产生兴趣,虽然美国的诗人、英国摇滚乐手,还有无数的嬉皮士都曾对印度流连忘返。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人产生的短暂兴趣来自电影,《流浪者》感染了一代中国人。他们既在其中感受到期望的自由,又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愤怒:一个法官的儿子就一定是法官,一个罪犯的儿子就一定是罪犯吗?像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子生来是坏蛋”的另一种控诉。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歌舞片,为那个单调的中国带来了乐趣。但这些形象,都压不过印度在物质建设上的失败。
当我到达加尔各答时,这种失败感的确扑面而来。这个城市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修建过新的建筑,最雄伟与漂亮的建筑都是英国人的遗产,但它们都在可悲地衰败。红色的作家大楼,白色的邮政总局,连成一片的银行、律师楼,它们曾是大英帝国的象征,都曾闪闪发光,如今全部年久失修,褪色,墙皮脱落。
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出现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们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其不意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猩红的牙龈。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般纠缠在一起,竟然仍在运转。
奈保尔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来过加尔各答,那是1962年,印度获得独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尼赫鲁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尚未消退,但奈保尔看到的则是一个可怖景象。殖民者早就离去,民族主义者们无力管理从英国手中要回的一切。原本能容纳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又拥进四百万人口,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管理的崩溃。他们该住在哪里,水源与食物在哪里,有足够的医院、警察局、公共汽车与厕所吗?“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1960年的一期《孟买周刊》这样形容加尔各答。奈保尔曾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在首次的印度之旅中,最令他震惊的是印度人对苦难的无动于衷,它还发展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蒙蔽,他们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国家,否则必定会被眼前的悲惨逼疯。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加尔各答仍像是“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我从未见过贫困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在城市的中心。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而我们在泰戈尔故居周围问路时,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既不敏感也没兴趣。
我对印度的理解深深烙上了奈保尔的印记。在这位特立尼达的印度后裔眼中,印度是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所有的辉煌历史都掩饰不了它眼前的困境。他要毁掉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幻想与同情,他又知道自己与这个国家撕扯不断的内在联系,印度是他洗也洗不掉的身份认同。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着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看到了自己。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同胞们自我蒙蔽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