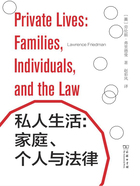
五
美国现代婚姻家庭领域的选择同另一个法律区域——隐私——相竞合。隐私作为法律概念约在19世纪晚期才出现,有两重含义:一是指隐私侵权之诉,即针对“侵入生活中人们有权隐藏之空间的一种诉讼”;二是指被赋予宪法权利性质的现代隐私权,即人们可以不受干预地选择有关性爱、避孕和堕胎等亲密事务的权利。这两种隐私都关乎家庭,因为家庭既是私人的安全空间堡垒,又是亲密关系的唯一合法场所。故近百年的隐私叙事是“一个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注13
首先,弗里德曼阐释了第一类隐私——侵犯隐私之诉。19世纪晚期,一些社会精英惊骇于媒体放肆披露亲密关系,发起了关于隐私侵权的学术讨论,主张创设一种新的侵权,认可一种新的权利:静默无闻、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由此诞生了弗里德曼所称的“维多利亚式的隐私”,它旨在保护体面的人们的私人生活免受媒体的窥探。该隐私的特点在于,为私人生活的某些领域拉上一道帷幕,使其成为私宅以外的禁忌,远离公共议程。尽管精英呼吁对法律实践的影响并非立竿见影,但各州逐渐出现了隐私侵权诉讼,一些维权者获得了胜诉。从20世纪30年代起,由于大众传媒和名人文化的兴起,第一类隐私迅速衰落。所谓“名人”是一个颇为广义的概念,凡受媒体关注(过)的公众人物或新闻人物,无论是政坛领袖、文体明星、企业成功人士,还是轰动社会的大案犯罪分子和受害人,甚至是任何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均可称为名人。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系列案例表明,名人的隐私很难以侵权之诉或其他条款获得法律保护。在新闻自由、公众知情权和名人隐私权之间,法院始终无法划定清晰的界限;唯一清晰的是,媒体自由的领地不断扩展,挤压隐私空间。至20世纪末,隐私侵权之诉所保护的隐私几乎丧失了法律生命力。
其次,第二类隐私作为一种宪法性权利的确立,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实质是“不受公共干预地做出基本生活选择的权利”,与家庭生活和性亲密相联。该类隐私权的发展,有赖于现代家庭居住条件的改良,使个人拥有私密空间(并在私人空间亲密)成为可能。其内容要点可分解如下:一是避孕节育的权利。一系列案例(如1965年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使禁止个人避孕的法律归于无效。联邦最高法院提出《权利法案》存在权利的“半影”和“放射”区域的观点,成为宪法性隐私权的法律依据。二是妇女自主堕胎的权利。1973年罗伊诉韦德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所有禁止堕胎的法律,宪法性隐私权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三是同性恋的权利。20世纪最后十几年见证了美国同性恋的合法化运动。各州废止了禁止鸡奸法,同性恋性行为不再是刑事犯罪,最高法院肯定了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公众对性少数派的态度也大为宽容。若干同性恋者公开恋情,公开伴侣生活,公开收养子女,甚至获得了民事“结婚”权。四是变性人的权利。21世纪初,有几个州法院开始对变性人的新性别身份和权利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变性及使其成为隐私权的想法再度证明了选择观念的力量,它以极端化的方式展现了表现型个人主义的边缘景观:可塑性身份的个人选择。
再次,关于隐私权的意义与诟病,弗里德曼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一方面,两类隐私权的演变均显示,美国法院在不断地将表现型个人主义纳入宪法文本,私人生活的选择领域持续扩大。在隐私的护栏下,人们愈益广泛地获得了自由选择个人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权利,包括过去被认为是越轨、耻辱甚至犯罪的模式和方式。另一方面,隐私一直饱受争议。两类隐私——将个人私密生活和世界隔开意义上的“隐私”与公开自由选择生活方式意义上的“隐私”——有些自相矛盾。隐私权的勃兴,加之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促发了“性革命”。媒体对名人隐私(尤其是亲密关系)的饕口咂嘴膨胀了人们窥探他人隐私的欲望——美国俨然成为“偷窥之国”,同时亦刺激了他们保护自身隐私、实现个人生活选择权的渴求。宗教信仰上的指斥、道德伦理上的批判和科学技术上的两刃效果,会持续困扰隐私权问题。
最后,隐私与选择的关系,是本章主题的落脚点。实质上,隐私本身是选择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人们既可选择保守隐私——持守平静无闻的生活,也可选择公开隐私,像名人那样“生活在一种玻璃鱼缸里”注14。由于电视、互联网等传媒的惊人发展和各种窃听、监视技术的入户式侵扰,使第一种隐私日益变得不可能。大众媒体的广告式鼓动,则使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选择让渡隐私,进入聚光灯下富有知名度的袒露世界。或许正是窥探的眼睛刺激了人们对第二类隐私权的强烈主张。而两类隐私的一个共同向度是,人们希望隐私成为一种可自由选择的“消费品”:由个人选择消费多少、何时消费以及如何消费隐私。新媒体“老大哥”式的全面在场下,捍卫隐私、力争消费隐私的斗争,或许将成为选择共和国“国民”的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