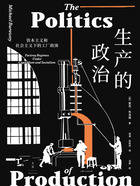
序言
本书缘起可回溯至1968年,其时我担任赞比亚铜业服务局(Zambian Copper Industry Service Bureau)的研究员。【1】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目睹了两个跨国矿业公司对四年前建立的赞比亚政体的反应。我能够观察管理层所做出的与工会和政府有关的决策;我还能够研究在铜矿本身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是在我与作为面试官的赞比亚人事官员一起对劳动力开展大型社会调查之际。随后我前往赞比亚大学,在那里用两年半的时间进行研究,形成本书第五章的经验基础。到1971年夏季,阿贝尔·潘达瓦(Abel Pandawa)、纳特·唐波(Nat Tembo)和托尼·斯姆索克维(Tony Simusokwe)加入了我的工作。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又在工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我称之为“联合”(Allied)的跨国公司引擎分部充当机械操作工。虽说管理层知晓我的研究旨趣,但仍像对待任何其他工人一样对待我。这是在1974年,我掌有这份工作达十个月之久。我告诉我的工友我在此务工是为了撰写博士论文,但是他们既不在意也不相信。这确实不合乎他们关于大学教育的想法。
由于偶然的机缘,我得以追随一位在芝加哥大学度过岁月的、最为机敏和富于经验的田野工作者的步伐。唐纳德·罗伊(Donald Roy)在三十年前曾是同一间工厂的摇臂钻床操作工。他关于吉尔公司(Geer Company)的研究不仅是比较的基础,而且是对我的研究的一种激励。罗伊在1980年去世,正值他将三十年来在北卡罗来纳州关于工会组织的研究汇聚起来之际。他是为数不多的设法横跨产业工人世界和学术界的社会学家之一,虽说付出了大量的个人成本。我自己的研究与罗伊的研究的比较在《制造同意》中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2】在这部书的第三章中,我更注重将我的研究与另一位和工人阶级具有紧密关联的工业社会学家进行比较。汤姆·卢普顿(Tom Lupton)的《车间里》(On the Shop Floor)是一项关于曼彻斯特两间工厂的研究,对英国的工业社会学至为重要,恰如唐纳德·罗伊的著作之于美国的工业社会学。
我对匈牙利的兴趣最初是由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著作激发的,其英文的题目是《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与唐纳德·罗伊和我自己一样,哈拉兹蒂也是一个机工,1971年是布达佩斯红星拖拉机厂(Red Star Tractor Factory)的一个机床操作员。他的书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生动地捕捉到一位新机械操作员的艰辛痛苦。但是那本书却产生了一个悖论:红星工厂里的生活比唐纳德·罗伊、鲁普顿和我在车间发现的生活都更为专制得多。这与苏联社会关于工作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在苏联,没有严重失业,难以解雇工人,共同利益将工人和管理者捆绑在一起对抗中央管理部门,这些势必会在车间形成更宽松的节奏。我曾经去过匈牙利,以探寻哈拉兹蒂描述的体系如何可能以及有多普通。1983年秋季,我在一家香槟酒厂和一家小纺织厂工作;1984年夏季,有两个月我作为摇臂钻床操作工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其类似于在联合和红星的工作。我在此的经验充实了本书第四章我关于哈拉兹蒂悖论的结论。
本书论文起步于工厂内部的工人阶级经验。作为一个将时光奉献于车间之后就重返大学的学术人,要解释这些经验并非总是容易的事。若没有乐意让我进入其生活并给我展示窍门的工人们,接下来的叙说绝无可能。我不能说我的车间生活是永久的欢乐,但是由于我的同伴们的社交创造力,它尚可忍受,有时还很有趣。
在工厂和矿场之外,我也欠了很多人情。亚普·范·韦尔森(Jaap Van Velsen)除了导引我进入人类学和社会学之外,还是头一个让我牢记研究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而非假设乌托邦的重要性的人,在此种乌托邦中,所有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恶魔全都神奇地消失了。在芝加哥,我有幸与友善并博学的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kski)持续对话。无论好坏,他都把我的法农(1)式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更可敬的结构主义。自回到伯克利以后,我对结构主义的主张日渐生疑。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思潮,【3】其源于玛格丽特·塞卢洛(Margaret Cerullo),在第一章中是颇为明显的。但无论何时,当我在人本主义方向上走得太远时,埃里克·赖特(Erik Wright)总是及时出现,试图将我重新推回到科学轨道上来。过去六年间,他一直是经久不衰的鼓励和批判的泉源。他阅读和评论过本书所有部分,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伯克利的学生们不得不容忍许多。很多人容忍了我将马克思主义化约为一种沉默——一种关于生产政治的沉默。毫无疑问,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都已写进本书。尤其是汤姆·朗(Tom Long),他在最近八年里一直是我在理论和哲学上的耐心导引者。在1982至1983年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变迁项目”中的讨论让我获益良多。三家机构赞助了我的研究:1980年,耶鲁的“南非研究项目”向我提供了一个学期的支持;1983年,伯克利国际研究所资助我完成了为期半年的匈牙利—波兰之旅;在匈牙利,我是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访客。在那里,拉斯洛·切赫-松鲍蒂(László Cseh-Szombathy)、埃莱梅尔·汉吉斯(Elemér Hankiss)、洛齐·布鲁斯特(Laci Bruszt)、乔鲍·毛科(Csaba Makó)、亚诺什·卢卡奇、彼得·高尔希(Péter Galsi)和加博尔·凯尔泰希(Gábor Kertesi)使我在匈牙利的逗留变得富于成果和饶有兴味。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和罗比·曼琴(Robi Manchin)启动了这一切,并且持续地给予鼓励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导引。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人评论了本书的不同部分:大卫·普洛特克(David Plotke)、露丝·米尔克曼(Ruth Milkman)、雷奥纳德·汤普森(Leonard Thompson)、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阿米·马里奥蒂(Amy Mariotti)、科林·利斯(Colin Leys)、马哈茂德·马丹尼(Mahmood Mamdani)、杰夫·豪伊度(Jeff Haydu)、卡罗尔·哈奇(Carol Hatch)、斯蒂夫·弗伦克尔(Steve Frenkel)、薇姬·邦内尔(Vicki Bonnell)、伊萨克·科恩(Isaac Cohen)、雷吉·泽尔尼克(Reggie Zelnik)、查克·蒂利(Chuck Tilly)、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莫里斯·蔡特林(Maurice Zeitli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约翰·迈尔斯(John Myles)、里奥·帕内奇(Leo Panitch)和沃利·戈德弗兰克(Wally Goldfrank)。我很感激他们所有人,感激格蕾琴·富兰克林(Gretchen Franklin),其政治批判从未妨害完美无瑕的编辑和誊写。我还要感谢《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匿名审稿人,以及《政治与社会》(Political and Society)和《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的编辑委员会。最后,我应该向已故的阿尔文·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致敬。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与他的《工业官僚制模式》(Patterns of Industrial Bureaucracy)的延伸对话。虽说我从未见过他,但他比任何其他当代理论家都更加激发起我对社会学的兴趣。无论我的研究通往哪一个方向,我总会发现他都已走在我的前面。[1]
(1) 弗朗茨·奥玛·法农(Frantz Omar Fanon,1925—1962)是20世纪中期法国著名的作家、心理分析学家和革命家。法农关于殖民主义的理论在当时曾发挥巨大影响,主要著作如《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已有中文版出版(译林出版社,2002/200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译者注(如无特殊说明,星号注释均为译者注,下同)
[1] 一篇阐述与哈拉兹蒂对立观点的民族志文章《计件工资:匈牙利方式》(“Piece Rates, Hungarian Style”)将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1985年1月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