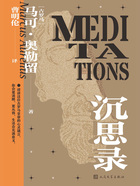
译者序言
把每一天都当作此生最后一天来活。
把任何事都当作此生最后一件事做。
在这个世界,真值得去做的唯有一事,那就是在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做事不可拖泥带水,说话不可语无伦次,思维不可含混不清。既不要萎靡不振,也不要得意扬扬。让你的生活有那么点优哉游哉。
你不可能活上千秋万岁。死亡随时都会降临,所以趁你还活着,趁你还有能力,就好好做人。
若非义举,切莫出手;若非真话,切莫出口。
人都是为彼此而生。所以要么相互习惯,要么彼此宽容。
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就经常在想,如果是偶然且分别读到以上这类箴言,一般读者会相信这些话是出自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位罗马皇帝的手笔吗?但确凿无疑的是,以上七段箴言的确是白纸黑字地依次摘抄自这本《沉思录》的卷七第69节、卷二第5节、卷六第47节、卷八第51节、卷四第17节、卷十二第17节和卷八第59节。
《沉思录》的作者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不仅是古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在位期161—180),而且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皇帝”出身于贵族世家,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据他在本书卷一中所记述,他祖父教给他宽容与温良,生父传给他正直与刚毅,母亲传给他虔诚与慷慨;教他绘画的家庭教师狄奥涅图斯鼓励他亲近哲学,而另一位家庭教师鲁斯蒂库斯则让他在年少时就读到了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谈话录》一书[1];此书对奥勒留影响极大,他由此把自己的兴趣从修辞学转向了哲学,尤其是对斯多葛学派哲学的研究,最终成为晚期斯多葛学派三个代表人物之一。
公元一至二世纪的罗马帝国被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那个时代的五位罗马皇帝则被称为“五贤帝”。奥勒留位居“五贤帝”之末代,当时帝国的繁荣趋于停滞,经济开始衰退,其威望也开始衰减。这位哲学家皇帝在位那二十年正值罗马帝国内忧外患的时期,内有洪水、地震、瘟疫、叛乱等天灾人祸,外有东方和北方异族部落的侵扰。对内,奥勒留励精图治,试图改善奴隶和穷人的生存状态;对外,他经常御驾亲征,戍边卫国。从168年到180年这十二年间,他很少待在罗马,大部分时间都征战在帝国北部边境(多瑙河以北的中欧和东南欧地区)。但其间他并未停止研修哲学,思考人生,这册《沉思录》就是他在戎马倥偬间偷闲写下的私人日记和哲学笔记。
说到哲学,有些读者可能会望而却步,因为他们以为哲学就是抽象概念之堆砌,是脱离实际的玄思,是深奥晦涩的学问。其实这是没有真正接触过哲学者的一种偏见。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指出:“哲学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凡有社会生活的地方就有哲学,或者说凡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哲学。不过“哲学”这个概念起源于古希腊,表示这个概念的古希腊语词是Φιλοσοφία。这个词本身的意思是“爱智慧”(爱知识),而热爱智慧者和具有智慧者在希腊语中则被称为Φιλóσοφος。这与我们古汉语中的“哲”字可谓完全对应(如《诗经·大雅》中的“既明且哲”之哲和“靡哲不愚”之哲),所以最早传播西方哲学的东方学者便将这两个希腊语词分别翻译成了“哲学”和“哲学家”。知道了这个渊源,哲学也许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读者可以自问:凡神志正常者有谁不爱智慧,不爱知识?而稍有生活阅历之人,谁没有思考过(或者说想过)天地自然、生死苦乐、善恶是非等问题?若换种说法,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哲学教科书上常说的有关世界的本质与真理的问题、有关我们如何认识自然或认识真理的问题,以及有关生命的意义与道德实践的问题。再换言之,这些问题所追问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人在很多时候都想过这些问题,只是要么想得不那么深刻,要么因偷懒而没有记录下来罢了。而这册《沉思录》就是作者记录的他对这些问题的想法。
关于人与自然(古人心目中的自然亦包括神祇)的关系,《沉思录》写道:
神之造物皆充满神意。命运之作并不独立于自然,其纺织编排之成形依然受神意支配。万事万物都来自那个世界,其他因素亦是整个宇宙之必需和利益之所在,而你只是那其中之一部分。自然之每个部分都受益于维持那种状态的宇宙整体性,受益于保持那种性质的万物所产生之结果,而宇宙秩序同样由各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不断变化而维持。(卷二第3节)
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沉思录》写道:
要是你见过被砍掉的手脚或脑袋躺在其躯体旁边就好啦——因总有人会尽其所能做类似的事,那就是在他不接受自己的命运,将自己与社会割开,或者实施某种反社会行为的时候。假若你让自己成了自然统一体的一名被驱逐者,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本来天生就是其中一员,现在却斩断了自己与统一体的联系。不过对你来说还有件奇怪的事,那就是你可以重归统一体。神没给予其他被分离部分这种特权,其他物体之部分一旦与整体分离,就永远被切割开了。想想神对人类的宠爱和恩惠吧!神首先让人有权不被逐离整体,而有人若与整体割裂,他还有权回归,重新融入整体,恢复其作为一名成员的角色。(卷八第34节)
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除上文摘录的“人都是为彼此而生。所以要么相互习惯,要么彼此宽容”之外,《沉思录》还写道:
请早上一睁眼就对自己说:我今天会遇上好管闲事者、忘恩负义者、惹是生非者、背信弃义者、心怀恶意者、性情孤僻者。这些人之所以不幸积下此类恶习,皆因不辨真善与真恶。然我已知悉,善之本即公平,恶之根乃不义;而且我每每想到,有恶习者之本性与我的本性同源——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而且还分享同一种心智,同一种残留的神性。故而,我不可能被他们中任何人伤害,因为谁也不可能让我染上他们的恶习。而我对这些同胞也不会怒目相向,不会深恶痛绝。我们天生就需要协作,犹如手足之左右,眼睑之上下,牙之上排与下列。所以,上下左右对着干乃悖逆自然,而彼此怨恨和排斥就是作对。(卷二第1节)
如以上抄录的片段所示,《沉思录》字里行间经常出现第二人称“你”字。读者当然可以把这个“你”理解为作者在对你说话,但同时别忘了《沉思录》是作者的私人日记和哲学笔记,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或曰作者在与自己的内心(灵魂)对话,所以这个“你”字其实是作者对自己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讲,《沉思录》可谓一位罗马皇帝的心路历程,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无意间留给世人的一册智慧之书、生命之书。
说“无意间留给世人”,是因为作者当初记录下自己这些思想时并未想到要将其公之于世,世人直到公元350年才从希腊修辞学家忒弥修斯(Themistius,约317—约388)的演讲录中得知有这样一部手稿。手稿用古希腊语写成,原本并无书名,除卷一之外,其余各卷各节(尤其是分段)也极有可能是由后人编排划分。最初的全抄本出现于1559年,书名为《写给自己的书》(To Himself)。其后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英译本最终将书名约定俗成为Meditations(《沉思录》)。据梁实秋先生考证,截至1908年,仅在英国出版的《沉思录》版本就达196种之多。拙译主要依据的英译本由翻译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英国古典学者马丁·哈蒙德(Martin Hammond,1944— )于2002年前后翻译,由英国企鹅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发行;部分章节的翻译对照参阅过早期的英译文。
我翻译此书是应人民文学出版社冯娅女士之邀。接到邀约电话时我曾纳闷:“你们咋知道我想翻译此书呢?”我之所以为此纳闷,是因为当时我刚译完十九世纪英国学人卢伯克的《生命之用》(The Use of Life)和《生命之乐》(The Pleasures of Life)二书,那两本书恰好引用了《沉思录》中的许多片段,而那些精彩的片段已经让我萌生了为《沉思录》新添一种中译本的想法。因我在翻译那些片段时发现,坊间刊行的数种中文版《沉思录》之译者都认为其所据的英译本语言“朴实无华”“近于拙朴”或“相当朴拙”,而我在读过相距一百多年的两种英文译本后,非但没有他们那种感觉,反倒与杜克大学古典文学教授迪斯金·克莱(Diskin Clay)的感觉相似。克莱教授在为哈蒙德译本写的导言中说:“若想从此书了解一位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坚韧的意志和朴素的生活,读者当然不会失望,但他们也会惊于书中那些读起来像现代诗的散文语言,惊于作者那些生动的例证和形象的描述。”为证明自己的论断,克莱教授列举了他认为既含哲理又富诗意的三个段落,即卷三第2节、卷八第51节和第57节。其实这种既含哲理又富诗意的段落在《沉思录》中可谓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诸如:
谈及芸芸众生,应恍如居高俯瞰凡尘俗事——成群的牛羊、对垒的大军、田畴与农家、结婚与离异、出生与死亡、法庭之喧嚷、荒漠之寂静、异邦之民族、喜庆与出殡、商贾与集市;看看这个世界之混杂熙攘,想想正反事物之有序关联。(卷七第48节)
一般人会寻求离群索居,隐于乡野、海滨或山林。你也非常渴望这样的生活,但这种隐居通常乃俗人所为,因为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选择大隐于市,归于你心中独善其身。若要找能避开纷扰的清静之处,天下没任何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内心,尤其是,若你胸中自有万千想象和记忆,只需对其凝神观照,即刻便可感到湛然宁静;所谓宁静,我是指一种井然有序的生活。所以,要经常让自己这般退隐,不断让自己获得新生。你内心参照的宗旨原则应简明扼要,足以一次就消除你所有的痛苦,使你在重新面对必须要面对的生活时能摆脱不满和怨恨。(卷四第3节)
总而言之,正因为作者将自己吾爱众生的道德承诺、万物统一的哲学理念,以及天人融合的坚定信仰付之于“既含哲理又富诗意”的语言,才使得这册《沉思录》自问世以来不仅成了研修哲学者必读之经典,也成了修身养性者喜爱的读物,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各国普通读者。我相信,有缘翻开此书的读者多少都会对生活、事业,乃至生命本身有所领悟。
曹明伦
壬寅年中秋于成都公行道
[1] 参阅本书卷一第7节(1.7节)相关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