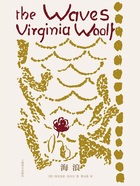
译本序
海浪拍岸声声碎
用太阳或海浪的升起和沉落比喻人的一生,描述人的生命由生到死的过程,这对一般有一定文学素养的人来说丝毫也不足为奇。但是,在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中,使文本自身运行的节奏,使人物的情感、意识、思想、言说脉动的节奏,统统伴随着太阳或海浪的升起与沉落的节奏而起伏、张弛、生灭,从而形成某种完美和谐的对应,却是非常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事情。这种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事情便发生在上个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海浪》之中。与伍尔夫同时代的英国作家E.M.福斯特曾经赞叹这部作品写得恰到好处,说它:“略少一笔,则将失去它所具有的诗意;略增一笔,则它将跌入艺术宫殿的深渊,变得索然无味和故作风雅。”的确,复杂深奥的内容,精美别致的结构,臻于化境的艺术技巧,全都融会在这部充满实验色彩的作品中,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伍尔夫最完美的创作。
《海浪》是一部高度诗意化、抽象化和程式化的实验作品。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故事,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性格饱满的人物。它将人生的全部岁月与一天的时间结构互相对应起来。从文本构成来看,它就像一部由九个乐章组成的音乐作品;每个乐章分为引子部分和正文部分。每个引子部分都是一篇精致的散文诗,它们按照太阳在一天的不同阶段在空中运行的不同位置——从晨光熹微,太阳初升,到太阳升高、当空而照,再到太阳西斜、落低、沉落,分别描写了同一景色在不同时间段的种种变化。构成这景色的有:运行在不同位置的太阳的光线,海边的一座房屋,海潮的阵阵涨落,鸟儿和花朵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状态,房间里的种种物体随着光线的变化所呈现的种种形态,等等。对这景色的种种变化的描写在富有音乐变奏的同时,又像是一幅幅富于变化的印象主义绘画,它们构成了整部作品中形象最为生动、诗意最为浓厚的部分。
跟在每个引子后面的正文部分是六个人物在相应的人生各个阶段——从儿童时代,学生时代,青春时代,中年时代,直到老年时代——的瞬间内心独白。这是六个没有姓氏的、形式化的人物,他们分别是伯纳德、苏珊、奈维尔、珍妮、路易斯和罗达。除了作品的最后一个正文部分是由老迈的伯纳德一人面对一个就餐者的独白,总结他们六位的一生之外,前面的八个正文部分全部是由这六个人物交替进行的瞬间内心独白所构成。每篇正文部分的内容与引子部分的基调均形成互相映照的关系。晨光熹微,太阳初升的时候,花园里的鸟儿唱着单调的歌曲,而处于孩提时代的六个孩子的意识和言辞犹如这单调的鸟鸣一样显得既简单、又跳跃。太阳升上来时,阳光洒下越来越阔大的光斑,读书时代的六个儿童的意识也在成长,开始对周围的一切做出初步的反映。随着太阳已经升起,六个人物步入青春时代,他们的意识、情感就像海浪和海岸上的景色一样全都变得明亮、复杂起来。升起的太阳垂直地俯瞰着波涛起伏的海面,阳光像尖锐的楔子射进了房间,六个人物的个性意识也终于成形并显露出来;他们聚在一起为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就要前往印度饯行,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其实就是一场成人仪式。太阳升至中天后,阳光下的景物没有秘密,全都被清清楚楚、细致入微地暴露出来;与此相应,成熟起来的六个人物开始听到死亡的信息——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在印度死了,世界和生命开始笼罩上了阴影。接着,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射下来,浪潮在海岸上留下片片积水,搁浅的鱼儿在那里扑打着尾巴,六个人物刚刚步入中年,他们尝试着越出自我,寻求爱情。太阳落得越来越低之后,花园里的花朵开始凋谢,六个人物开始意识到时间无可挽回的流逝,意识到生命的局限。太阳沉落时,如同坚硬岩石般的白昼碎裂了,收割后的庄稼只剩下一片片残茬,海岸上的阴影开始蔓延开来,日近黄昏,历尽沧桑的六个人物又一次聚在一起,充满绝望和幻灭感地回忆他们的人生历程。太阳完全沉落之后,黑暗的潮水淹没一切,唯一还活着的人物伯纳德面对即将走完的生命历程,开始总结他和他的朋友的一生。随后,能够听到的只剩下——“海浪拍岸声声碎”。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总结。这种潮生潮灭的海浪形象构成了人的生命、意识、感觉的永恒象征。
在《海浪》的正文部分,六个人物的独白就像一个乐章的六个声部,轮番交替地呈现出来,它们有时候互相独立,有时候又存在一些对位关系。这六个人物按照太阳的运行,海浪的起落,以程式化的独白语言描述着他们从幼年到老年的人生体验。六个声部所呈现出来的不是具体的、实在的个人化声音,而是被提炼到了很纯粹、很抽象的层次上,远离了原质生活的静默的声音。不仅如此,六个声部之间还基本上没有相互对话。并且,在同一个章节中,六个声部的独白不是在同一个时间水平上进行的,而是递进式地展示着时间、生命、人生的进程。就是说,时间的演进,生活的变化,无不是随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瞬间独白而呈现的。当六个人物都还是小孩子时,时间和生活是清晰、简洁的;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时间和生活就像成人们的世界一样失去了可以把握的秩序。这种变化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言说方式上,因为他们独白的言辞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愈来愈复杂起来——从早期简单的跳跃的言辞,到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的越来越复杂的言辞——句式由短变长,由简单到繁复。六个人物的性格轮廓也随着这些变化逐渐由模糊不清变得相对清晰、饱满起来。然而,六个人物在整个作品中又并不具备鲜明的、活灵活现个性,他们每个人的性格特征均呈现为程式化的、抽象化的、类型化的。比如说,伯纳德像个热爱生活的作家,他相信言辞的力量,喜欢用各种各样的辞藻来描述世界;奈维尔崇尚理性精神,追求严谨的知识;路易斯心理自卑,但又深受传统的影响,具有极强的进取心;苏珊厌弃都市,向往自然,像个贤妻良母;珍妮憧憬社交生活,具有敏锐的肉体感受力;罗达羞怯而神秘,她总在说自己没有面孔,试图遗忘自己的存在,而凝视彼岸的世界。六个人物仿佛代表了人的生命的不同侧面。将六个人物凝聚在一起的是一个神秘的、始终沉默,但又像影子一样始终存在于每个人的意识和独白中的人物,这就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珀西瓦尔——一个与英国十五世纪作家托马斯·马洛礼爵士编写的《亚瑟王之死》中寻找圣杯的骑士名字相同的人物。珀西瓦尔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衡量生活意义的标尺;同时,对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珀西瓦尔又是一个不同的人,代表着他们各自的隐秘愿望。
在六个进行瞬间内心独白的人物中,伯纳德是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历历在目的人物。孩童时代的伯纳德曾经说过:“我们通过辞藻互相融入了对方。我们的边界模糊不清。我们组成了一个虚幻飘渺的王国。”在大学时代,他曾经在不同的阶段把自己认同为各式各样的角色,如哈姆雷特、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某个主人公,还有拜伦等。他终生信仰词语的魔力,在一生中他不断地记着各式各样的笔记。通过词语的编织,他像一张蜘蛛网似的把其他人的生活联结在了一起。尤其是在《海浪》的最后一章,衰老、孤独的伯纳德的总结性独白,堪称一部可以独立成章的、将密度压缩到极致的长篇小说。这部分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它所揭示的人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一定程度上堪与《尤利西斯》那样的巨著相媲美。在《海浪》的前面出现过的所有人物的生活,全都通过伯纳德这生命最后一刻的长篇独白编织在了一起。不仅如此,他的总结还起到了使整部《海浪》的结构达到最完美的平衡的作用。
《海浪》出版于一九三一年,那一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已接近五十岁,正当创造力极为旺盛时期。在此以前,她已经在小说实验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在小说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富于创造性的独特声音,也已经使她成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的第一部实验小说《雅各的房间》发表于一九二二年。那是一个对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在那一年,诗人艾略特发表了他的长诗《荒原》,小说家乔伊斯发表了他的小说《尤利西斯》,英吉利海峡彼岸的普鲁斯特则告别了人世。那一年发生的文学大事自然对伍尔夫的文学观念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就个人的文学写作来说,伍尔夫称,在《雅各的房间》里“我(在四十岁时)发现了如何用自己的声音去说话”。而面对乔伊斯的那部对整个十九世纪的小说样式形成摧毁性颠覆的《尤利西斯》,她清醒地意识到它对于小说艺术的革新来说,“乃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突然剧变——无限地大胆,可怕的灾难”。不过她对《尤利西斯》并不是盲目地完全肯定。她认为乔伊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遵循着从前的小说道路,因为乔伊斯所运用的种种新颖的艺术方法无非是为了表现世纪初的都柏林社会生活。对于小说艺术,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要独辟蹊径,执著地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亦即以隧道掘进的方式充分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伍尔夫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纯粹的。她对外部现实世界抱有怀疑的态度,她所感兴趣的是一种所谓“内在的真实”,这种“内在的真实”就是积累在人的内心深处而又不断涌现到意识层面上来的种种感觉印象。在她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体验感觉的器官,从一个人的出生到死亡,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感觉体验的冲击。在那篇著名的文学宣言式的文章《论现代小说》(一九一九年)中,她写道:
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的印象——琐碎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生活并不是一副副匀称地装配好的眼镜;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环,生活是与我们的意识相始终的、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说的内在精神——不论它可能显得多么反常和复杂——用文字表达出来,并且尽可能少羼入一些外部的杂质,这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来追踪这种模式,不论从表面上看来它是多么不连贯、多么不一致;按照这种模式,每一个情景或细节都会在思想意识中留下痕迹。
《雅各的房间》是伍尔夫为使上述写作理想变成现实所做的初步尝试,其中散布着许多充满印象主义色彩的场景和感觉描写。这部小说在艺术上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是伍尔夫从这部小说的尝试中摸索到了创造一种新小说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她随后的两部小说——《达洛卫夫人》(一九二五年)和《到灯塔去》(一九二七年)中得到了圆满实现。这是两部极具英国式的严谨的现代主义小说,两部在意识流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作品。伍尔夫在这两部小说中娴熟地运用了诸如内心独白、感觉分析、主客观时间交错、象征等意识流小说技巧。《达洛卫夫人》像《尤利西斯》一样,小说中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压缩在从上午九点到次日凌晨的短短十五个小时里,展示了一位上层社会妇女在这段时间里的内心活动,并且通过内部时间与外部时间的穿插交错,清楚无遗地展现出她从十八岁到五十二岁的内在的生活体验。《到灯塔去》除了意识流技巧运用娴熟之外,在结构处理上也更为紧凑和诗意化。这部小说采用了三段式的音乐结构,第一部分“窗口”以拉姆齐夫人为中心人物,通过她的心灵之窗展示了九月的某个下午和黄昏的生活(音乐中的主题);第二部分“岁月流逝”则以时间、生命的流逝为主题,人世沧桑,小说第一部分中的许多人物已经去世(音乐中的副题);第三部分“灯塔”则以已经去世的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永恒存在于生者的心中为主题(音乐中的主题变奏)。伍尔夫采用这种具有浓厚象征意蕴的精巧结构,一方面是为了小说外部形式上的锐意创新,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则显然是为了与小说中人物关于生活、死亡、时间等人生问题的近乎抽象的反省、沉思达到某种艺术上的平衡。如果说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还在通过种种意识流手法试图表现出主人公个人内在的生活体验,那么到了《到灯塔去》她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这种表现,在一种浓缩的诗意化的结构形式中,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开那些具体的生活细节,试图写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抽象的、沉思默想的生活——其中裹挟着关于生命、时间、痛苦、希望、死亡等人生问题的思考。可以说,伍尔夫由此开始了超越对纯粹个人化的内在经验的描写,而转向了对人生经验的抽象本质的探索。但是,在《到灯塔去》中,对抽象的生活实质的描写还是受到了关于具体人物的叙述的限制。直到写作《海浪》的时候,伍尔夫才基本上摆脱了这种限制的束缚,随心所欲地进行全方位的实验。
伍尔夫属于那种把小说艺术研究与小说创作很好结合起来的作家。她一生中写了大量的作品评论,其中既有对古典文学又有对现代作品的研究。在写于一九二七年的小说理论文章《狭窄的艺术之桥》(原来的题目是《诗歌、小说与未来》)中,伍尔夫通过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诗剧、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浪漫派诗歌以及在文体上惊世骇俗的《项狄传》(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长篇小说),描述了她心目中的理想小说。她认为,那像饕餮一样的小说将会吞噬许多文艺形式:
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我们究竟将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它,这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的这种新颖的作品……
它和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从生活后退一步,站得更远一点。它将像诗歌一样,只提供生活的轮廓而不是它的细节。它将很少使用作为小说的标志之一的那种惊人的写实能力。它将很少告诉我们关于它的人物的住房、收入、职业等情况;它和那种社会小说和环境小说几乎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带着这种局限性,它将密切地、生动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然而,只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它将不会像迄今为止的小说那样,仅仅主要是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共同活动;它将表达个人的心灵和一般的观念关系,以及人物在沉默状态中的内心独白。
从最初酝酿到最后完成花了四年之久的《海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遵循着这种小说写作的理想而进行创作的。这部作品就像是一种写作的历险。它让纯诗一般的独白片断像无数生生不息的海浪一样我行我素、自由自在地生成,无须任何解释。它对小说写作的革新,使它完全超越了小说这种形式,变成了非小说。它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封闭式的结构,它没有传统小说中占中心地位的主人公。它让六个人物的内心独白如同季节和海浪一样循环往复,潮起潮落,而且关于这些人物没有任何客观真实的描述;他们只是一些没有躯壳的幽灵,一些抽象的、作者借以抒写生活感受和人生实质的传声筒。
为了让作品达到纯诗的高度,伍尔夫一如既往地重视对人生中的特殊瞬间的开掘和描写。她认为:“每一个瞬间,都是一大批尚未预料的感觉荟萃的中心。”(见《狭窄的艺术之桥》)在关于《海浪》的创作日记中,她曾写道:“我有了一个想法,现在我所做的一切乃是使每一个原子都达到饱和。我要把所有无用的、没有生气的或多余的描写统统剔除,全力以赴地去表现那瞬间,不管它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容。比如说,那瞬间是思想、感觉和大海的呼吸的组合。”所以,在《海浪》中,每个人物的独白均呈现为关于人生瞬间感受的独白。这些瞬间的感受在每个人物的生活中均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们被放大,被像科学解剖一样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出来。这使得《海浪》成为一部揭示人生瞬间的深层内蕴的作品。与此同时,伍尔夫又赋予每个人物的瞬间独白以戏剧性的力量,使他们各自的独白均呈现为相互独立的声音,从不同的视角描述着不同的人生经验。对此,伍尔夫在创作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海浪》正在转化为一系列戏剧性独白。关键是使它们随着海浪的节奏均衡地出现与消失。”这就是说,把人物置于大海的背景中,用海浪的节奏为作品赋予整体上的美感,亦即借助海浪的韵律,把纯诗性的描写与戏剧性的独白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
这就是《海浪》,一部将诗歌、戏剧,乃至音乐等多种文艺形式融入小说写作中去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许多人说它是诗化小说。但也有人意识到了它的戏剧化特征,比如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评述伍尔夫的著作中感叹地说:它“简直成了一首长诗。六个人物用变化的诗句讲着话,中间插入一些抒情的默想。是诗吗?更正确地说,是一部清唱剧。六个独唱者轮流念出辞藻华丽的独白,唱出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观念”。
针对伍尔夫所展示的这样一种创作形态,爱·福斯特曾经作过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我们可以借来作为本文的结尾。福斯特在一篇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演讲中说:“她属于诗的世界,但又迷恋于另一个世界,她总是从她那着了魔的诗歌之树上伸出手臂,从匆匆流过的日常生活的溪流中抓住一些碎片,从这些碎片中,她创作出一部部小说。……这就是她的问题所在:她是一位诗人,却想写出一部尽可能接近于小说的作品。”
曹元勇
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