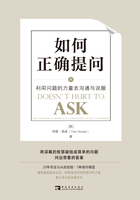
第一部分 开口前需了然于胸
第一章 确有愚蠢的问题
让人哄堂大笑的问题
谋杀案件让人忧郁,一个人失去生命,另一个人接受审判,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者更加严厉——被处以死刑。所以,可以想象,任何刑事审判都容不得半点马虎。然而,在我经历的第一场死刑判决现场,我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人说:“根本不存在愚蠢的问题”,那这个人肯定没去过2001年秋天斯帕坦堡县的庭审现场。
在那起案件中,一位便利店的收银员遭抢劫,遇害身亡,起因竟是微不足道的小钱。收银员工作卖力,为人善良,行事规矩,一辈子吃过不少苦。如果嫌疑犯开口要那点小钱,他也不会拒绝。
在大部分类似的案件中,只有两位目击证人,一位(也就是受害者)已经死亡,所以除了法医或实物证据,只能依靠被告的陈词、供述或虚假的辩驳。但在这起案件中,还有另一位目击者——抢劫、枪击发生时,他坐在一边玩电子扑克游戏。
每当有其他证人,律师总想提前与他们会面,了解他们会说什么,如何应对。在这起案件中,我与这位目击者见面多次。尽管他可能对在死刑审判中作证感到紧张,但是他态度真诚,所言可信,这对案件的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轮到他出庭作证了。先向陪审团描述案发现场十分必要:商店的格局如何,相对于收银台和收银员,这位证人坐在哪个位置,他是否有机会看到案件发生,当时有没有吸毒或饮酒,判断力有没有受到影响,另外还要预测陪审团可能会问到的其他问题。
“你与商店的正门之间有遮挡吗?”
“没有。”
“有什么遮挡你的视线吗?”
“没有。”
“当时开灯了吗?”
“开了。”
“屋里有烟雾吗?”
“没有。”
“你喝酒了吗?”
“没有。”
“这个问题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你当时服用了任何处方药物或其他药物吗?”
“没有。”
“嫌疑人从前门进来时,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嫌疑人进来时,商店里还有其他人吗?”
“只有我和收银员。”
“嫌疑人进来时,你的目光从他身上离开过吗?”
“没有。”
“你看清楚嫌疑人了吗?”
“看清楚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嗯,那个人走向柜台后面的收银员,掏出一把枪。”
“你能看见枪吗?”
“能。”
“你能向陪审团描述那把枪吗?”
“能。是黑色的,看起来像手枪,不是左轮手枪。”
证人表现很好,控制住了情绪,说话清晰、准确。但显然我不能让对话如此顺利地进行下去,我必须出击。
“先生,我注意到你今天没戴眼镜,你那天晚上戴眼镜了吗?”
“没有。”
“你视力好吗?”
“好。我右眼完全没问题。”
他在说什么?我的证人,你不是希腊神话里的独眼巨人!你有两只眼睛,我自言自语道。
我陷入了什么样的境地?我如何抽身?接下来该问什么或说什么?就此放过,希望陪审团没听见?或者希望陪审团没想起来人有两只眼睛?愚蠢如我啊,我得做些什么,不能这么悬在那儿。
“证人先生,你当然视力很好,当然视力很好。”我只能这么说。
“那你的左眼呢?”
(痛苦的沉默)
“是假的。”
“嗯,当然,证人先生,是义眼。”
“不,是假的。”他说。
我就这么一位证人,但我竟然和在场的其他人一样,刚刚才得知他是位独眼证人。
在上法庭之前,竟然没有问证人的眼睛状况。我慌乱了,多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给我报个名。我要躲到囚禁基督山伯爵的伊夫堡监狱!
情况不能比这更糟糕了,难道不是吗?诚然,很多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糟糕,而且在这起案件中,情况太窘迫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接着发问。
“嗯,嫌疑人手里提着个蓝袋子。”
“好,蓝袋子是什么颜色?”
法庭里爆发出一阵笑声,有一只眼睛盯着我,好像我失去了理智一般。
我想他可能没听清楚问题,所以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蓝袋子是什么颜色?”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发生了什么?为何这群人在死刑审判中笑了起来?就在我要第三次提出这个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愚蠢的问题时,法官满怀怜悯地对我说:“检察官先生,我想陪审团现在知道蓝袋子是什么颜色。你可以继续提问了。”
问题可以是肯定的。问题可以是为了真诚地寻求更多信息,也可以是为了证实已有的陈述。你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是陪审团里有人却未必,所以你利用提问来向他人传递信息,而不是把信息传递给自己。问题可以是为了控告或削弱对方的观点,也可以是出于防御,或可以让你重新组织、转移和引导别人的注意力,从而可以继续一时或一天的战斗。
也确实有愚蠢的问题。
问题有好有坏,相同的问题因提问情形不同,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如果开庭前几周,在办公室询问目击证人的视力,那可能是个绝好的问题。
公诉官办公室的同事给了我一张那场庭审的照片,那是当地一家报社的摄影师拍的,当时证人正在说:“我的右眼视力完全没问题。”同事之所以给我那张庭审照片,原因是当证人提及自己的一只眼时,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能让人察觉的反应,而内心深处,我却充满渴望。直到我错上加错,问起蓝袋子是什么颜色,陪审团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从第一个问题中幸存下来,但却问了第二个问题,白白浪费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