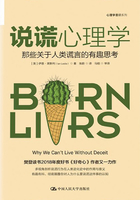
第4章 智慧因欺骗而来
这无关道德,只为生存。
摘自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1719年出版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鲁滨孙·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发现自己独自一人流落荒岛,他能不能顺利地活下去完全取决于他那快速学习其他技能的能力。他必须建造住所,收集食物,并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危险的伤害。于是他挖了个洞穴,用石头和木头制作工具,打猎,养羊,种玉米,甚至学会了制作陶器。在岛上的最初几个月,乃至几年里,他都孤身一人,身边仅有一只鹦鹉陪伴,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鲁滨孙从登岛的一群野蛮人手里救下了一个本来要被吃掉的野人,并称呼他为“星期五”,从此“星期五”就成了他的同伴,他教“星期五”英语,并使他皈依基督教,再后来他们两人一起营救了更多的被野蛮人囚禁的人,并开始建立一个小型社会。
近几年,科学家在试图解释与人类智力相关的问题时,也会讲一个与鲁滨孙这段神话般经历类似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版本中,人类驾驭了大自然,并为那些我们熟悉的物体(如石头等)赋予了新的用途,比如用来制作工具,或以新的方式运用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使得我们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壮和聪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进化让那些有能力适应这些新方式、新方法的人得以生存,同时我们的大脑也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你能明白这个故事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让我们人类看起来高贵、心灵手巧并且强大。作为人类,我们似乎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标签和定位,但是对于我们卓越的心智而言,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
纵观漫长的进化历史,人类的大脑可能是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是最为神秘的成就了。原始人的大脑容量仅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但是在大约150万到20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我们祖先的大脑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开始了扩展,而科学家一直无法确定其原因。我们的大脑实际上是一个能耗巨兽,它虽然只占了我们身体质量的一小部分,但却吞噬着我们身体五分之一的能量。更大的脑容量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又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更高的智商对人类来说似乎是一种极危险的奢侈品。当我们对大脑进行探究时,还有一个比较难理解的点,那就是人类的大脑比类人猿的大脑在体积上要大得多,但两者生存的环境是相似的,人类98%的基因也都与类人猿共享,那这种大脑体积的差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大脑的发展从某个时刻开始很突然地把类人猿抛在了身后。这就好像托比和莎拉的故事一样,这对能力相似的兄妹,在学校的头几年里,彼此成绩不相上下。但突然从某一个学期开始,托比领先了,他可以解出很难的问题,并且每一次的考试都考得还不错,有时候你甚至会怀疑托比是不是在作弊。
近几十年来,在对人类的高智商进行解释时,出现了一种以善于欺骗为核心的观点——欺骗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提出这个观点的科学家认为,在鲁滨孙荒岛求生这个世人皆知的故事里,我们漏掉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其他人,即鲁滨孙之外的“星期五”的出现。
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是现代学术界里面少有的全能型选手。他对人类大脑的功能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并始终认为任何学科之间都是可以交叉的,并且觉得烦琐艰苦的实证研究方法相当无趣。他有自己的一套学术研究方法,一般情况下,他会选择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然后针对现在该领域内研究者正在进行探究的问题重新进行构想,并在此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接下来,他并不会去针对此假设进行论证,提出之后就把自己的目标转向新的研究领域去了。但是假设已经提出了,那这个领域中的其他研究者,就有必要去论证这个假设,这些想去证明的研究者,就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证明汉弗莱所提出假设的正确性,并且往往到最后,结论还真的就如汉弗莱所假设的那样。
1976年,汉弗莱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人类进化的激辩中插了一脚。他发表了一篇名为《智力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Intellect)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针对“人类智力是在我们的祖先与自然的斗争中进化而来的”这个传统观点提出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假设。他认为:
我们之所以对智力抱持着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们一直对《鲁滨孙漂流记》这本书中所讲述的故事进行着错误的解读,我们一般都会认为鲁滨孙那段独自生活、完全依靠自己艰难度日的时光是他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光。但也许“星期五”的出现,才是那个真正给他带来巨大压力的转变。在长时间的独处之后,鲁滨孙必须学习(或重新学习)如何与另一个人相处,与和自己一样的高智力等级生物进行交流与合作。“星期五”在整个故事里对鲁滨孙都非常忠诚,这是他们交流与合作的其中一个前提。但是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鲁滨孙并不信任作为自己同伴的“星期五”呢?那这个故事中的鲁滨孙可能就真的要时刻保持警惕了。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另一种假设,就是如果故事中出现的不止一个“星期五”呢?同时还出现了叫“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三”或“星期四”的另外几个男性或女性同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鲁滨孙的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很难相信我们的祖先进化出如此卓越的智力,仅是为了去应付那些生存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当然,制造出一个工具确实需要一点头脑,就像当捕食者朝你冲过来的时候,你要记得爬到树上躲避一样,但是这些并不一定需要创造性。当某个物种中的某一个成员经过努力或者是很偶然地发现了这样的技术,这个物种中的其他成员接下来所要做的其实就是机械地复制它。但是还有一些物种,尤其是我们人类自己,其实是具有惊人的预见和创新推理能力的,这种能力被汉弗莱称之为“创造性智力”。我们可以想象出很多新奇的场景,并以此为基础去计划我们的反应;我们甚至可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预见”它们,然后,如果足够幸运的话,这种预见会成为现实。人类所展现出的这种想象力从何而来?汉弗莱认为,这也许是从旧石器时代那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挑战带来的。
人类及其直系祖先所生活的群体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庞大,也更加复杂。更大的群体在带来更多安全感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流言蜚语和更加激烈的竞争。虽说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要依靠他人的帮助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但在争夺食物和配偶的过程中,每个成员又都必须学会如何去利用和超越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或者至少要学会如何避免被别人利用和超越。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变成了一场战术游戏,而在这场游戏中,你必须提前进行思考,并把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牢记每一张你见过的脸,必须知道今天早上或上周谁对你做了什么、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这还意味着,你需要去预估你的行为可能对别人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的行为可能对你的影响,你必须在混沌不堪且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完成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事情。
汉弗莱认为,人类在社会中苟活比与大自然打交道需要更多的智慧。毕竟,树木不会四处乱窜,石头也不会设法骗走你的食物。当我们的祖先离开森林来到开阔的大草原时,他们复杂的社会生活需求与新环境所带来的挑战融合到了一起,这就好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从背后猛地推了我们的祖先一把,这一推,智力进化突飞猛进,智人由此诞生。
动物有趣的欺骗行为
这观点看上去就很“汉弗莱”。多年来,“社会智力”假说一直都因为缺乏证据而固步于争议漩涡的中心,汉弗莱的论文就像是向生物学家发出的挑战一样。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安德鲁·怀特(Andrew Whiten)决定迎战之前,这篇论文和其中提出的观点都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伯恩和怀特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两位年轻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他们希望通过对汉弗莱所提出的假设的验证来为自己正名。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把研究目光投向了社会行为的一个特殊方面——欺骗。这两位踌躇满志的研究者先是在简·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相关研究中找到了黑猩猩实施欺骗的例子,之后又在南非德拉肯斯堡山的实地考察中,亲眼目睹了狒狒所做出的欺骗行为:
一只年轻的狒狒因为攻击群体中的另一只狒狒而与几只年长的狒狒发生了冲突,这其中也包括了它的母亲。当这只年轻的狒狒听到年长的狒狒们发出咄咄逼人的吼叫声,并越过山丘冲过来准备教训自己时,它突然做出了一个观望的姿势:用后脚站立,凝视着远处的山谷。因为它的这个姿势,那些冲过来准备教训它的年长狒狒们停了下来,因为这个姿势让它们认为远处有捕食者或敌人正在靠近,于是也无一例外地朝那个方向看去。虽然最后证明远处的山谷里什么也没有,但那些咄咄逼人冲过来的年长狒狒,也因为分心去观察远方莫须有的敌人,而忘记了它们最初跑过来的目的。
对黑猩猩的观察,也发现了类似的行为模式:
两只年轻的黑猩猩在地上疯狂地刨着,试图寻找一些被埋藏起来的食物。当它们察觉到有一只年长的黑猩猩靠近时,它们会立刻停下来离开刚刚刨的地方,并在附近走来走去,抓耳挠腮,看上去就好像它们无所事事一样。但是,当年长的黑猩猩走远后,它们立刻就会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挖刨,取得食物。
让我们再来看一只狒狒的行为模式:
一只成年雄狒狒将一只雌狒狒推搡出了觅食的区域。这只被赶出去的雌狒狒似乎并没有对此表现出抗议或退缩,而是立刻望向雄狒狒,邀请它与自己一起去攻击和驱赶一只在附近独自觅食的无辜狒狒,这个邀约很顺利地得到了雄狒狒的支持。在雄狒狒冲上去攻击和驱赶无辜的年轻狒狒的瞬间,雌狒狒就回到了她自己的领地内,继续进食。
很多人会把这些现象当成茶余饭后谈论的轶事,但伯恩和怀特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严重怀疑这些灵长类动物故事的背后潜藏着一套逻辑。他们一开始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就意识到灵长类动物尤其是类人猿(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都是说谎的惯犯,而这个意识结果,又反向推动着他们对智人进化的过程进行着思考。在我们祖先所处的生存环境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定律,即你越善于预测自己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人的行为可能对你自己产生的影响,你就越有可能生存下来。基于这个定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判断,就是那些更擅长说谎和欺骗的人,在远古生存环境中,会享有更多的生殖繁衍优势。因为他们更擅长用这样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生存目的,比如骗取本不属于自己的食物等。当然,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那些更善于发现谎言的人也更容易生存,因为他们能够比较轻易地避免被他人欺骗。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利文斯通·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所说的:“在一个处处是谎言的世界里,谁拥有测谎仪,谁就能占优势。”在物种进化的阶梯上,每上一个台阶,我们就会变得更加擅长说谎和欺骗,也更擅长甄别谎言,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进化的“军备竞赛”。可能所有的物种,包括我们人类,都会进化得更善于记忆、更善于预判,也会在这种看似微妙的游戏中,进化得更善于思考别人下一步会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研究初期,伯恩和怀特发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思考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很难公开发表。因为,说谎和欺骗在人类进化中的作用并不是他们两人所处的领域中绝大多数人会去认真对待的一个话题。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科学家其实也有自己的偏见和知识盲区。所以,当一个如此不符合我们自我形象的观点被提出时,遇到如此大的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你深信,我们人类是通过各种独创技术和诚实的努力所进化而来,那你就必然很难接受伯恩和怀特的发现和所提出的观点。
但是,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并不会因为诚实而对我们有所偏袒,所以依旧存在很多的物种,把欺骗作为一种生存的必要手段去践行。举个例子,东方猪鼻蛇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选择通过翻滚、散发恶臭和吐信子来装死。又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附近水域发现的拟态章鱼,可以随意伪装成至少15种不同的海洋生物,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吸引猎物或抵御捕食者。鸟类中也不乏善于欺骗者,比如鸻鸟。当捕食者靠近时,雌性鸻鸟为了将捕食者引开,会主动从巢中飞出,并假装自己的翅膀断了,以此把捕食者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而不是巢中的幼鸟。其实不只是动物,甚至在植物中也存在善于欺骗者。比如,北非的镜兰就会开出一种特殊的小花来吸引潜在的授粉者。这种小花并没有花蜜,但它会用一种特殊的诡计来吸引那些粗心的授粉者,蓝紫色花蕊像极了一只正在休息的雌黄蜂的翅膀,而厚厚的红色长须则很像雌黄蜂腹部的绒毛,乍看上去,俨然就是一只雌黄蜂,这对于那些好色的雄蜂来说,无疑是无法抗拒的诱惑。
1982年,一本同时吸引业界学者及普通读者注意力的新书,为伯恩和怀特这种看似危险的想法带来的一些新的动力。这本扣人心弦的作品正是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所写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这本书描写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动物园中一群被圈养的黑猩猩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读起来就像黑帮题材电影的剧本一样,其中有联盟的形成、瓦解和重组,有被操纵的个体,有预谋的暴力行为,甚至还有针对雌性的争夺和诱惑。德瓦尔基于他的结论,针对人类的政治活动也提出了些许意见,并且在书中还引用了尼克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所著的《君主论》(The Prince)中的名言:“既然人是不守信用的、可怜的、低等的生物,那作为统治者,就必须知道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说谎者和骗子。”
伯恩和怀特无一不对德瓦尔的作品着迷,尤其是书中那些对谎言与欺骗赤裸裸的描写:
一只名为普伊斯特的成年雌性黑猩猩正追着一个和她有竞争关系的雌性对手到处跑,她追上对手并且绕到了前面,却很神奇地什么也没做,僵持了几分钟后,隔着一段距离的普伊斯特向她的对手伸出一只张开的手,看上去似乎是在示好。这个时候,那只年轻的雌性黑猩猩变很犹豫,一边环顾四周,一边慢慢地靠近普伊斯特,她显然不确定普伊斯特是什么意思,所以脸上还带着那种因为紧张而产生的不自然的微笑。但普伊斯特看上去却很坚定,那只似乎预示着友好的手也一直悬在半空,伴随着年轻雌性对手的靠近,普伊斯特开始轻轻地喘气,这种动作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在黑猩猩亲吻对方之前。但是,并没有什么亲吻发生,普伊斯特这个时候突然扑了上去,抓住对手,紧接着就是狠狠的一口。
德瓦尔把黑猩猩的这一举动称为“具有欺骗性的和解提议”,任何去过游乐场或看过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行为感到陌生的。
《黑猩猩的政治》这本书的成功,给围绕灵长类动物欺骗行为进行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合理性基础,伯恩和怀特也终于在1988年出版了他们合著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Machiavellian Intelligence )一书(书名也是受德瓦尔德启发所起)。在这本书中,伯恩和怀特对他们发现的所有关于欺骗的例子进行了收集和再分类,划分为戏弄、假装、隐藏和分散注意力等几个主要类别,并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但又非常有力的论点,即我们的智力始于“社会操纵、欺骗和狡猾的合作”。《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这本书的出版,可谓他们二人的高光时刻,书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不仅在进化理论领域,而且在包括了从心理学到经济学的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极具影响力。
欺骗能力与智力的关联性
伯恩和怀特认为,智力和欺骗能力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并找了很多的例子来佐证这一论点,使其可信度更高,但依旧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补足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仍然缺乏确凿的证据来对这个论点进行支撑。正在他们二人对此一筹莫展之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这位来自利物浦大学的人类学家,为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邓巴同样也受到了汉弗莱提出的社会智力理论的启发,他指出,尽管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有与其体型相关联的体积较大的大脑,但生活在大群体中的狒狒的大脑却显得格外地大,而生活在小群体中的黑脸狒狒的大脑,相比之下却显得异常地小。基于这一发现,他想去弄清楚一个问题,即灵长类动物是否需要一个更大的大脑来处理更大社会群体所展现出的那种复杂性。假如你处于一个五人小团体中,那你就可能需要去掌握10种不同的关系,以便你自己可以在团体中成功地驾驭各种社会动态。也就是说,你需要知道谁与谁是结了盟的,哪些人值得你花些时间去多关注一下,哪些人又不值得你这么做,仅是这几点,听上去就已经够难的了。设想一下,如果你正处于一个20人组成的团体中,那就意味着,你有多达190种双向关系需要去掌握,其中19种涉及你自己,171种涉及团体中的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种关系在团体扩大时进行的等量级增长。当这个团体扩大到近四倍时,这些需要掌握的关系的数量以及掌握它们所带来的智力负担,已经悄然增加了近20倍。
邓巴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各地关于灵长类动物的数据海洋之中,去寻找动物大脑大小和其通常生活的社会群体大小之间可能存在的统计学关系。他用物种大脑外层的新皮层的体积作为代表物种大脑大小的单位,而我们有时候也将这个部分称为负责大脑“思考”的部位,因为它所处理的是抽象、自我反思和前瞻性规划等工作,而这些又被汉弗莱认为是应对混乱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另一方面,在200万年前突然开始快速成长的也正是灵长类特别是人类大脑的这个区域。
通过研究,邓巴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显著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非常显著,我们甚至可以仅通过对一个物种大脑新皮层大小的了解,就非常精确地预测出这个物种所处种群的大小。他甚至对人类所能应付的社交群体大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即根据我们大脑的大小,我们所能应付的社交群体大小应该约为150人,但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找150个人去社交,这些人最起码得是那种你愿意和对方喝上一杯聊一聊的人。邓巴并没有停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梳理和研究,他随后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并且得到了一个足以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结果,他发现许多人类社会群体的粗略平均数:从狩猎采集社会到现代军队以及公司部门,都正好是150人。
受到邓巴研究结论的鼓舞,理查德·伯恩与一位名叫纳迪亚·库柏(Nadia Corp)的年轻研究员合作,开始了一项有关欺骗行为和大脑体积之间关联性的论证研究。伯恩和库柏的研究围绕着野生灵长类动物欺骗行为的一系列观察结果展开,这些观察结果的数量已经比伯恩和怀特提出他们开创性假设的初期多了很多。伯恩和库柏研究后发现,一个物种中欺骗行为出现的频率与这个物种大脑中新皮层的大小成正比。夜猴和狐猴的新皮层体积相对较小,所以它们可以称得上是所有灵长类里面最坦荡的了;相反,包括类人猿在内的那些称得上最具欺骗性的灵长类动物,则有着体积最大的新皮层。这个发现印证了最初的理论观点,欺骗的手段越高明,或者说越精通欺骗之道,相对应的大脑体积就会越大。
但是,伯恩并没有试图去测量智人这种拥有最大新皮层体积的动物的欺骗能力,某种层面上来说,根据研究所发现的关联性,就可以准确地推断出智人欺骗能力的等级,也确实不需要再多此一举。至于哪个物种会卫冕欺骗之王,可能所有人心中都已经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答案了。
人类是天生的骗子吗
19世纪中叶,美国娱乐大亨和美国马戏团创始人菲尼亚斯·泰勒·巴纳姆(Phineas Taylor Barnum)收购了位于纽约的美国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收藏了一批在当时来说非常奇特的人和动物的标本,其中包括长着胡子的女人、一头大白鲸和一对引起巨大争议的连体婴。开放展览之后,反响异常火爆,但同时巴纳姆意识到一个问题,用现代零售业的话来说,就是“通路流量”的问题。由于展览太受欢迎,人们在一个展览点前面驻足的时间越来越长,场地随之变得越来越拥挤。巴纳姆为解决这个问题,找了一个极其生僻、晦涩的表示出口的术语,搭配上一个“出口”的标志,贴在了展览的必经之路上做指引。参观者一眼看上去,以为这个标志是下一个奇特标本的指引,就很兴奋地跟着标志指示一直走,结果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走出了博物馆。
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引申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针对谎言的定义,即谎言是带有欺骗意图的虚假陈述。在了解这个谎言的定义后,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如果我告诉你巴黎是比利时的首都,即使你知道我在说谎,一般也不会指责我骗人。你可能会认为我说错了,或者我是在开玩笑。也就是说,如果说假话的人相信自己所述属实,那说假话的人其实就不算是在说谎。但是如果听的人明确地意识到说假话的人是知道巴黎并不是比利时的首都,并且知道说假话的人这么做是以利己为目的(比如想让你输掉常识问答游戏)时,听的人就会把这种说假话的行为定义为撒谎。
正如巴纳姆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人可以通过说出真相来撒谎,也可以通过撒谎来给出真相。比如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墙》(The Wall)中,当被法西斯分子判处死刑的囚犯巴勃罗·伊比埃塔(Pablo Ibbieta)被卫兵问及他的战友拉蒙·格里斯(Ramon Gris)的下落时,他误以为格里斯此时应该和他的表兄弟们躲在一起,为了给自己的战友拖延更多的时间,他告诉卫兵格里斯藏在墓地。然后,在卫兵发现被骗之前,他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好好地想想自己被处决的事情。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在黎明破晓时发生了,格里斯已经搬到了伊比埃塔向卫兵报告的藏身处,随后格里斯在墓地被捕,伊比埃塔反而因为告发了自己的战友被释放。在这个故事中,伊比埃塔的本意是向卫兵撒谎、欺骗他们,但实际上,却无意间把真相告诉了他们。
谎言是狡诈且变化多端的东西。我们会为了简化一个复杂的故事或保护自己的隐私,或者为了摆脱不太喜欢的社交场合去撒一个小谎,比如,“周四吗?很抱歉,我那晚要去上一节低音管演奏课”。有些人也会为了掩盖不端行为或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去撒一些弥天大谎,比如那些存在于违法犯罪行为及对他人的操纵行为中的谎言。我们甚至还可以将谎言分为作为与不作为的谎言。作为的谎言指的就是很主动地去撒一个明确的谎,比如谎称自己是一名警察;不作为的谎言则是避重就轻,比如和对方诉说自己激情似火的情爱生活却没有提到和自己约会的是对方的妻子。另外,我们有时候也会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而说谎,比如:“我钓到了一条非常大的鱼,但我把它放了”,或者是一位士兵对自己英勇行为所做出的异常夸张的描述等。甚至,还有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身体或精神伤害而说出的谎言。
还有另一种说谎的类型,就是我们可能都遇到过那种纯粹为了好玩而说谎的人,他们通常会用虚构的情节去修饰他们所讲的故事。这么做的原因,只是这会让他们在别人面前显得更加有趣。“我是你一生中见过的最精于此道的骗子。想想就觉得太可怕了!”这句话出自《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中14岁的英雄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Holden Caulfield)之口,他接着说:“如果我在去商店买杂志的路上,遇到某个人问我去干什么,我可能会非常自然地说我正要去看歌剧,这是多么可怕的行为啊。”
在本书中,我会经常交替使用“欺骗”和“谎言”这两个词,但这并不是我的无意之举,交替使用是因为这两个词之间确实有所区别。伟大而古怪的美国魔术师杰里·安德鲁斯(Jerry Andrus)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从不说谎。尽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他的魔术效果呈现和所有其他魔术师一样,都需要依赖对观众进行视觉上的欺骗去达成,但是安德鲁斯通过对自己魔术的设计,使得表述上的诚实和手法上的欺骗在自己的魔术中达到了共生。就比如,他会在把某张特定的牌从一整副牌中变出来之前告诉观众“这看起来好像是我把牌放在了这副牌的中间”,而不是说“我把牌放在了这副牌的中间”,注意他的这个话术。这个话术增加了他魔术表演的难度,因为他在魔术开始之前就提醒了他的观众,即将要表演的这个魔术很可能存在着欺骗,但无论怎么说,这是安德鲁斯给自己设定的挑战。我们可以从定义上对谎言和欺骗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欺骗是囊括了任何形式的、具有误导意味的企图,它可能是一种语调、一个微笑、一个伪造的签名或一面投降的白旗;而谎言则主要指的是言语上的东西,它是一种特别的口头欺骗形式。
事实上,我们人类所具有的在适应旧石器时代社会生活需求过程中所习得的掩藏真实动机的能力,也同样随着语言的出现得到了加强。虽然学术界对这种变化发生的时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推断,从5万年前到50万年前都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变化将交流与行为分离开来,并因此为欺骗的发展带来了一次巨大的飞跃。当我们不用明确地指着食物让对方知道食物在哪里,而是可以通过言语来引导,让对方自己去寻找的时候,欺骗也就随之变得无限多样和复杂起来。
当我们去阅读那些描写灵长类动物欺骗行为的故事时,很可能会有不适与钦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袭来。感到不适是因为这些故事似乎在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欺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特质;而同时,我们又会对这种狡诈、创造力和智慧感到钦佩。与之类似的完全不同且对立的反应,几乎贯穿于我们对待说谎的态度中,而且无论态度怎么变化,这种对立的感觉就在那里。在我们对自己能够编造不真实的谎言感到震惊的同时,又对自己所展现出的创造力叹为观止;不安于我们对虚假之言淡然处之的同时,又确信某些谎言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说谎无疑是一种让人深恶痛绝的恶习,”16世纪的哲学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写道,“如果我们意识到说谎的可怕和严重性,我们就会发现说谎这个行为比其他犯罪行为更应该被处以火刑。”其实,从奥古斯丁时代开始,神学家就已经对说谎开始了严厉的谴责,并把说谎定义为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伊曼努尔·康德曾经说过,并不存在善意的谎言,在任何情况下,说谎都是不正当的。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些并不认同上述观点的思想家。这部分思想家认为,“我们可以或应该没有欺骗地生活”,这个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只有一个世界,”尼采说,“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残酷的、矛盾的、误解的、无意义的……我们需要谎言来征服这个现实,征服这个‘真相’,我们需要谎言来生存”。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则用了和尼采完全不同的轻松风格对谎言进行了阐述。他说,撒谎是人们用来逃避现实生活中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闷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显然非常受欢迎,只是撒谎本身确实需要一些技巧。之后,他哀叹道:“谎言作为一种艺术、一门科学和一种社会乐趣正在衰落。”康德和蒙田可能会同意《伊利亚特》(Iliad)中的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话,他说:“心口不一的人,我恨之入骨。”然而在《奥德赛》(Odyssey)中,荷马(Homer)却将阿喀琉斯与“凡人骗术大师”放在一起进行了一番对比。这种对比的结果是,让奥德修斯(Odysseus)这个在战争和爱情中熟练地运用骗术并引以为傲的人成了更有吸引力、更人性化的英雄。
关于说谎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我们开始交谈以来,谎言就一直是我们七嘴八舌与窃窃私语的一部分,几乎包含了一切,如我们对自己生物性的认识、成为一个好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其他人到底在谈论我们什么,等等。虽然囊括众多,但有一点始终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欺骗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谎言往往很自然地就到了嘴边。文学评论家、人文主义哲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说过:“人类说谎的能力对于人类意识的平衡和人类在社会中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我们都是天生的骗子。
说谎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