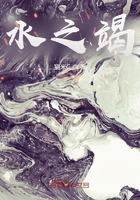
第104章 张不疑(1)
出了长沙后一连走了数日,每一天都是晴空万里,仰头见一排大雁滑翔而过,郁结于胸的紧张感随之烟消云散。这些年来中原战火云集,家家户户都闹得鸡犬不惊,好不容易熬到新朝建立,又恰逢干旱时节。而这偏远的荆蛮之地,虽说亦不富裕,却显得安定祥和,难怪许多中原人不惜放弃几代留下的家业远迁于此。如今正值秋收时节,沿路是成片金灿灿的稻田,果园里种满了各色的水果,枝头被大而饱满的果实压得直向下坠。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灿烂的丰收景色,不由惊叹得东张西望,步伐也慢了下来。辟疆更是瞪大了双眼,眨也不眨一下,生怕错过什么。若不是我一直把他硬按在马背上,只怕他早就跑得不见了踪影。这小鬼自打学会走路后,两条小腿就没有消停过。真不知为什么义父一定要他跟来,明明只会添乱而已。
出了长沙境内,村庄逐渐稀疏,无人修整的野草高得几乎淹没了马腿,道路也愈发难走。就这样走走停停,终究还是错过了宿头。天已几近全黑,我们却还逗留在荒郊野外。最近的村落望不到踪影,往回走更是不可能,只好下马硬着头皮摸黑走下去。好不容易前面林子中隐隐透出建筑的影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废弃的庙宇。
辟疆缩到我身后,冻得冰冷的小手紧紧地攥着我的袖子。夜幕下,庙宇破碎而狰狞的剪影透着森森冷气,像是千百年都没来过人了。
眼下也没什么可挑剔的了,好歹有了个挡风的地方,总比露宿野外要好。我踢开挡路的碎木块,领着辟疆小心翼翼地来到庙门口。正要推门时,发现落满灰烬的木门上留有一个小小的手印,突兀之极。
我和辟疆对视一眼,顿觉毛骨悚然。这手印如此新,主人很有可能还在门内。观其大小,却似孩子的手印。这深更半夜的,谁家的孩子会没事跑到偏僻古旧的破庙里来?
脑海中回响起义父讲过的关于鬼婴的故事,我迟疑了一下,一咬牙还是推开了门。陈旧的木门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没发现什么异常,便叫辟疆进来。借着从碎墙间隙透进来的月光一起清理出一片空地,再将附近干燥的废木收拾成一堆,拿出随身的打火石生火取暖。
石块相碰,撞出一片火花。在一瞬间的火光映照下,有黑影在不远处的石像附近闪了一下。我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拿着火石的手僵在半空,双眼紧紧盯着那个辨不清面目的石像,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刚刚是错觉。虽然流浪街头时什么地方都住过,但对于黑暗的恐惧我一直无法克服。记忆中也是在类似的夜晚,那晚风大屋漏,我怕冷,走到爹的病榻前,却发现爹已然没了气息。那彻骨的寒意至今仍残留在我身体里。
为了驱逐从脚底蔓延上来的寒气,我继续用力敲击着火石。直到柴火被点着,噼里啪啦越燃越旺,我才舒了一口气。下一口气还没接上来,一个小孩的影子就出现在了辟疆身后。
这回是真真切切看到了。我大叫着跳起,猛地跨过火堆,随手拾起一根燃着火的木棍,朝黑暗处挥去。
对方反应也快,几乎同时朝后退去。躲过了火棍后也不跑走,站在原地和我对峙。火光下,我终于看清了他的样子,是个脏兮兮的黑小子。我僵直的身体放松下来,只要是活物就好。我再不济,摆平一两个小鬼还是不在话下。
谁知这小子却先一步挑衅起来,单手叉腰,指着我的鼻子喝问道:“你是谁?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方才被他吓得叫出了声,我自觉失了面子,没好气地回道:“小爷管你的!门匾上又没写名字。说是你的,莫非上面供着的是你不成?。”
闻言,他便如被踩了尾巴的猫一般窜了起来,眼睛瞪得溜圆,尖声叫道:“臭小子话倒是不少,今个就让你知道话多的坏处!”说罢,抡圆了胳臂冲了上来。
三句不合就要动手吗?这小子脾气也太爆了。我一时间来不及反应,下意识抬手护头。辟疆见状连忙跑了出来,拉住了那小子的衣服。黑小子见来了个小孩,立刻收了力道,把辟疆拽到面前,问道:“你这小孩又是谁?”
“他是我弟弟。辟疆,这边来!”我唤道。
谁知辟疆却不理我,而是可怜兮兮地对那小子说:“姐姐,我们走了一天了,真的好累哦。阿兄他不懂事,你可不可以原谅他,别赶我们走?求求你了……”
我震惊得身形都不稳了,指着那黑小子对辟疆道:“你瞎说什么呢?!这小子怎么可能是女……”话未说完,一块木板打着转朝我飞来,幸亏我反应快,一猫腰躲了过去。
辟疆回过头来,以四岁小孩绝对不可能有的神态对我叹了口气。那黑小子……哦不,黑丫头白了我一眼,弯下腰摸摸辟疆的脑袋,柔声道:“你叫辟疆啊?”
辟疆扬起小脸甜甜地应了一声,黑丫头也被感染得露出笑容,道:“辟疆乖,和姐姐到里面休息吧。至于你这臭哥哥……就让他一个人在这里吹风吧!”辟疆听话地点了点头,两人如亲姐弟一般拉着手绕过石像,走进庙堂内殿,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大呼小叫。
所以人们才说,小孩养大了都是白眼狼。我忧伤地长叹一声,往被过堂风吹得快要熄灭的火里添了些柴火,缩着脖子坐在火边生闷气。过了一会实在闷得慌,便掏出随身青铜剑,自娱自乐地练起义父教我的招式。
平刺、斜刺、上挑、急退、挺身直进、回身斩……
“哇!”盯着距离自己鼻子不到一毫的剑尖,黑丫头吓得直对眼,猛退了几步,差点被身后的碎罐子绊倒。
“你出来干嘛?辟疆呢?”我板着脸问道。
“睡着哩,我可没害他。”丫头绞着手指,咬牙道,“喂,小子。这剑法是谁教你的?”
我白了她一眼:“怎么?想学啊?”
她愤愤地跺脚道:“谁稀得学啊!我只是觉得你出招的方式和我平时见过的不大一样,又不像是野路子来的……”
我收了剑,怀疑道:“你还懂剑?”
她哼了一声,道:“我偷看过不少大户人家的少爷练剑……更何况我有将军之血,天赋很高,看一遍就会了。”说罢,她照着我刚刚的样子凭空比划了几下,竟当真丝毫不差。见我瞠目结舌的样子,她得意地一挑眉,“如何?”
这几招可是我练了半个月才练会的。当下对她增了几分敬意,问她道:“你说的将军之血是什么?”
听我如此问,一直气势汹汹的丫头收了剑招,安静下来。她眼睛里闪着光,却并非火焰或月色映出来的,而是来自眼底漆黑璀璨的光。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她问我。
“张不疑,用人不疑的不疑。”
“不疑,辟疆……”她喃喃念了一遍,而后道,“我听人说,小孩的名字都来自于命名人的期望。这说明给你们起名的人有远大的志向且意志坚定。”
脑海中浮现出爹即使重病在床仍手不释卷时双眉紧蹙的样子,多年过去了,他的面孔清晰如故。我点头:“是的。爹常说,男儿在世,该做出一番事业来。只可惜……”
“你阿爹是个伟大的人。”她对我说,“我大父也是。我大父……是楚国的将军。”怕我误会,她又解释道,“并非楚霸王的西楚国,而是故芈楚的将军。”
七国大将的故事我听爹讲过不少,顿时来了兴趣:“你大父叫什么名字?”
谁知她却摇头道:“我娘没告诉我,她不喜欢我问过去的事。娘只提过大父是随国破而亡,我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而起的。虽然我没见过他……”说着说着,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呓语,“不过,我了解他。”
手心一暖,我低下头,见她将半块破碎的玉佩放进我的手心,上面刻满繁复的蟠螭纹和楚文,裂口处已被磨得光滑。做工虽不精细,却是温润至极。黑暗中,她的声音如铜币坠地,清脆而果决。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碎玉」,是我的名字。”
月光从屋漏处照射进来,是柔和的浅黄,与她眼中的坚毅相互映衬。碎玉的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胸口,另一只手附在我的手掌上,我们的手掌间是那片破碎的玉佩。之后的日子里,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的心口便会不自禁地发紧。自那天起,这个时而如钢般坚强,时而像玉般脆弱的女孩开始和我们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