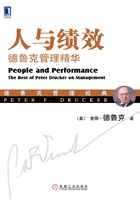
第3章 管理:回顾与展望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是19世纪的一位管理先驱,时至今日,他的深刻洞察力,他对自己信念的无畏勇气,仍然独树一帜。他还是最“进步的”管理者(150年前,他在新拉纳克做了一次实验,在短短几年里把一家破产的苏格兰纺织作坊变成了极为成功的企业,并成为人力关系和工厂组织的榜样),堪与如今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一较高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跟欧文同时代的法国人圣西门,他首次意识到企业家作为财富创造者的重要性。到了19世纪的后半叶,日本人赶了上来。虽然他们需要超越西方的技术和经济,却仍希望保持自己古老而丰富的传统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于是,日本人第一次认真思考起了管理者的社会责任和职能。最后,到19世纪末,美国人亨利·汤开始强调知识创造财富的贡献,以及分享管理经验的重要性。
这些先行者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肯定的是,欧文远远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以至于没人仿效他的做法。新拉纳克引起了轰动,却并未变成榜样。有几年,当地成了热门的旅游景点,许多大人物都曾去参观,但笔者从未听说有哪一个商人跑到那儿考察欧文做了些什么。
对比来看,圣西门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直到今天,欧洲大陆的基本管理哲学和结构都留着他的痕迹,强调“企业家”(承担财务风险)和管理者之间的差异。汤对美国管理和企业的基本结构有着同样深远的影响,他或许只是对既有做法进行了修订,但直到今天,美国的管理结构显然仍反映了汤提出的概念:企业的职能是利用系统化知识,创造经济价值。最后,在所有早期思想家当中,日本人或许有着最重要的影响。他们将一个非西方国家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时仍保持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和文化。他们不仅打破了西方在经济和技术进步上的垄断地位,还为当今经济爆炸式发展奠定了根基。从很多方面(尤其是构造上)来看,现代世界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不过,这些都是管理的史前时代,无法列入正史。因为所有这些先驱人士都缺乏一样东西,即认识到“管理”是一个独特的领域,“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工作,“管理者”是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独特的职能。如今我们读到他们的真知灼见,不免为之惊叹。但我们知道一些他们那时不知道的事情,我们从他们的作品里读到了一些他们本人并未意识到的东西。这些先驱者里的每一个都找到了大块的纯金,但没等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就又将之扔到了一旁。
管理的七个基本主题
1910年前后,对管理的新见解、新概念突然出现。在1910~1920年这10年里(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0年),管理的每一个大主题都鸣响起来。管理研究和管理的七种基本方法,每一种都是那时提出的。而自那以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时间上,都只是这些主题的变体和延伸。
管理,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作为一种特定的工作,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和经济职能,几乎是在过去50年发展起来的。
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出现于1911年。一年以后,他到国会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证词,把这种技术变成了一种研究工作及其合理组织方式的系统化、有组织化、可教学的方法。几乎在同一时间,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重组了美国军队;亨利·法约尔重组了法国矿业公司,确立了一种与泰勒(他研究的是劳动队伍执行的单个任务)恰恰相反的方法。他们对组织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以确定组织需要执行什么任务。也是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以施马伦巴赫为代表的德国人,建立了“经营学”,即对构成企业整体经济结果的个别交易进行系统化研究。
这三种方法都是孤立地看待企业及其管理。但就在1910年的下一年,我们又首次发展出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考察企业及其管理的方法。1911年,也就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原则和方法》(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问世的同一时间,奥地利的熊彼特(Schumpeter)出版了《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第一次提出了管理者在当代不断发展的经济中的职能问题,这本书甚至预见到了创新、市场营销和长期规划等新近的“发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德国的瓦尔特·拉特瑙首先注意到了大型组织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当代社会的管理责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美国的亨利·甘特(Henry Gantt)再一次重复了特拉瑙关注的问题。
工厂群体以及产业组织中的个体问题,属于第一批出现的管理主题——也是罗伯特·欧文最关心的事情。然而,它却是现代管理思想最后才动手处理的问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才由当时仍在澳大利亚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再度卓有成效地提了出来。
自此以后,这些主题就成为管理的重大主题:
·对工作的系统化研究;
·对组织的系统化研究;
·对努力和成果的系统化研究;
·管理和企业经济学;
·管理分析,即管理会计;
·管理的社会地位和责任;
·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工业社会中的位置。
新主题
这些方法中的每一种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讲,它们如今也都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它们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在过去10年。
这些不同的方法还能够维持更长时间吗?又或者,我们会很快达到迄今为止尚未达到的地步:将管理统一成一门学科?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将这些不同的方法看成同一套工具箱里不同的工具,每一种都是完成工作所必需的东西,而不是将之看成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观点。
所以,每一名管理者,以及每一名渴望成为管理者的学生,最好是学会使用所有这些管理方法。
但如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任务,先驱们开发的工具不够用,甚至不再适合。这些任务是哪一些呢?我们可以将之概略地做个分类。
高层管理的问题:开始探索
首先,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的现状:将高层管理视为理所当然,却知之甚少。
其实,有关我们对高层管理的认识,即我们对企业及其管理的统一、判断和决策机构的认识,是更加混乱的。传统方法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中企业的职能(即特拉瑙对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关注,或熊彼特对管理和企业经济学的关注),它唯一看得到的东西就是高层管理。实际上,它甚至把企业本身看做高层管理的延伸。如今我们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哪怕是一家小企业的组织,也远远不止是高层管理的延伸。例如,我们知道高层管理决策职能的基本问题,不是作决策本身,甚至不是得到有关决策的“事实”,而是如何让决策在组织上下贯彻始终。
但另一方面,孤立地解决企业和管理的方法,即可追溯回泰勒、法约尔和施马伦巴赫的方法,又完全看不到高层管理。这些方法是静态的,就像是把玻片里夹着的静态细胞组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一样。当然,这些方法由此获得了强大的分析力。但这也意味着它们无法区分什么相关什么不相关;不知道事关企业生死的决策有些什么区别,也不知道哪些决策与边际效率有关系。这些方法非常正确地指出,极小、极难以观察到的操作故障会让哪怕是十分健康的组织倒闭。但它们完全忽视了一点:就算是其他所有功能完全正常的组织,若是没有一套独立的、有效的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存活,更不可能正常运作。换句话说,它们没有看到高层管理。
企业顶层人员的职能、组织和工作,在管理上尚是一片未开拓的大陆。
与此同时,它又是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中要面对的最关键的问题。毫无疑问,对我们知识现状感到不满是有着充分理由的。至少,据我所知,在任何地方,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东方,大型组织的高层管理无一不对我们当今的所知所为不断重组、不断质疑、不断感到不满。
高层管理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如何选拔现任高层管理人员的接班人。正是因为管理的巨大成功,这才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成功,大公司的高层管理才成了一种社会和经济资源,有着远超具体公司的权力。这些问题牵扯到的东西,远远比股东的红利、股票的价格甚至公司员工的工作更多:谁会接替现任的最高管理者?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由什么人来选拔接任者?使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样的流程来选拔?如果发现继任者不合格,谁对他们负责?谁来撤他们的职?面对这些问题,不管是在管理实践还是管理理论中,恐怕没有任何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
内部问题
接下来的一类任务解决的是企业和管理的基本内部问题。首先,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是否具备管理性”的问题。
很有可能有些企业规模太大、太过复杂,超过了管理的极限。企业的信息组织和决策系统、系统化的业务研究、大企业内部自治小单位的系统化组织等新发展或许能将这种极限推得更远些,但最终的极限恐怕还是存在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种活动、每一种业务都真正属于大企业?
企业只是现代社会下成长起来的诸多权力中心的一支而已。现代政府和工会早就是主要的权力中心了。但企业不同的地方在于,有大大小小诸多单位同时存在、运作和竞争。
这显然是一种独特的优势:有助于维护社会的自由,实现一个不因大多数赤贫者与极少数暴富者之间必然爆发的阶级战争而破灭的社会。但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样的活动最适合在大企业内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交给小企业更合适。这同样是一个“是否具备管理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到目前为止也只能提出问题,但无法确定地定义它,更不可能回答它。
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决策。过去30年,决策已成为管理研究和思想的核心焦点。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相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做出理性决策。最起码,我们可以定义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了。
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个问题,一个无法用任何传统管理方法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决策”之间进行区分。我们不会把“2+2=4”说成是决策,而是叫它“正确的答案”。在现代决策理论(尤其适用于管理决策)中,我们说到“决策”的时候,都指的是只存在唯一正确答案的情况。如果要做的工作就是恢复或维持预设水平上的运作,这种答案是合用的。这些就是常规决策,这些我们都懂。但我们之所以理解它们,正是因为它们并非决策。
接下来的一类决策,我会称为管理决策,因为它们涉及现有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分配。这里没有正确答案。换句话说,这类决策存在风险。但这里仍存在一定范围内的最佳解决方案,有着确定或平衡的风险。显然,所有关于库存水平或库存分配的“决策”,是量化“管理科学家”最喜欢的练习题。这些决策同样并非真正的决策。通常,它们也不是事关企业生死的决策。
对于最后一类决策,也就是企业决策,我们了解得很少。这里显然没有正确答案。它甚至没有一定范围的最优解。它只与承担合适风险的能力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创新的能力,改变趋势而非紧跟趋势、预测趋势的能力。它同样要求严格谨慎的精神纪律。但它也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决策,需要非常不同的“事实”,有着与常规决策或管理决策非常不同的影响。它是唯一真正关键的决策,其目的不是消除风险,甚至不是将风险最小化,而是让企业能够承担更大的合适风险。
最后,就在企业基本内部任务这一领域,我们还必须将涉及事情的“管理科学”与涉及人的“管理科学”结合到一起。除非我们能把对客观事物(即物理或经济现象)的认识,以及对人及其发展、需求、渴望、尊严和个性的理解与关注,融入同一种分析过程、同一套思想概念、同一种决策行为,否则管理这门学科就无法成立。我们不能再将两者分开,不考虑是什么人在应用数据、为什么而应用,就直接把数据输入电脑。反过来说,不参考经济上的客观贡献和表现,我们不可能透彻地思考个人在组织中的作用、职能和位置。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把两者结合起来,两种方法仍然是独立的,甚至互不兼容。
社会和政治问题
企业与管理的社会及政治问题提出的全新重要任务,需要一套统一的方法。
过去30年,亨利·汤在一个世纪前的深刻见解(即知识是创造财富的资源)孕育出了果实。在每一个地方,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不管从成本、数量还是贡献上看,成为了真正的“劳动力”。过去的“劳动者”(也就是欧文首先给予关注的群体,泰勒最先对其工作进行了分析)正迅速成为现代工业的过去式。工作,正越来越多地由高学历人士完成,他们贡献自己的知识,靠自己的头脑来干活。
我们仍然倾向于认为,工业社会存在两个阶层:“管理者”和“工人”。这个想法不光危险,而且还正迅速走向彻底荒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大多数人在本质上是专业人士,他们工作时虽并非管理人员,但也绝非体力劳动者。他们是受雇的中间阶层,认为自己是“管理层的一部分”,对上没有“管理者”,对下没有“工人”,他们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无产者”,更不认为自己受了“剥削”。
这是20世纪的社会现实,也是它的社会问题。从经济上看,这些人已不再成问题。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克服了19世纪的“社会问题”。至少,我们知道,19世纪的社会问题,用19世纪的任何处方都解决不了。但通过20世纪独特的经济发展处方(对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用于工作的人进行高度投资),它可以得到解决。
然而,对这些人的位置,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他们,就是说,怎样让他们把知识、努力和贡献有效地完全发挥出来。管理学的奠基之父们几乎没人预见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出现在他们大获成功之后。成功带来的问题往往比他们解决过的问题更为艰巨,至少是更为微妙。
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还带来了一个同样重要的后果。“生产力”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含义,要求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和概念。尤其是在过去15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过大量的“生产力中心”。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更多的“效益中心”:也就是有组织地努力让新型工人、知识工人、受雇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发挥出全部的效率和生产力。
这也是一项对工作进行分析、仔细研究的任务。但这里的“工作”与从前不同,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必然改变。体力劳动者的生产力,靠的是对其任务和动作加以组织,提高单位小时(或单位成本)的产量。可对“知识工人”来说,问题不完全在于他们生产了多少,更在于他们是否将注意力放在了正确的“产品”上。知识工人的经济贡献,特点是效益而非效率。而且,知识工人的效率,不仅是让一个人做更多的问题,更是要让整个群体做得好。这些都是新的东西。到目前为止,不管是美国人、俄罗斯人还是欧洲人、日本人,都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点。
面对工业社会里典型的、特征性的、创造财富的工作,我们眼下所处的位置,正如泰勒之前人们面对体力工作一样。我们需要一位新的泰勒(当然,他得是一位相当不同的泰勒,不再用工程师的思维把人类看成精心设计的机械工具,而是“系统思想家”,把群体内的人看成整体里活生生的有机结构,从而实现整体的效力),着眼于有效地去做真正重要的事,而不是把时间和精力消磨在对绩效与成果无所助益的事情上(无论做得多好、多高效)。这是我们的一条重要前线。
管理职权的问题
接下来是管理合法性的政治大问题。管理的职权是以什么为基础的?管理并不以剥削和压迫为基础,也无须如此。但领导团队仅是不剥削、不霸占还远远不够,它的权力需要有立足的基础。它需要一套责任准则,并以问责为焦点。
现代工业中到底所有权和控制权是分裂的,还是所有权在实质上仍享有控制权,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管理作为一项职能,已经与法定的财产所有权脱离了。不管企业是个人所有、政府所有,还是数百万匿名的股东所有(通过保险政策或未来的养老金分摊持股),管理都必须站在企业而非业主的利益上专业地、客观地履行职责。管理层到底有多大的权力也并不相关。毫无疑问,哪怕在最严谨的管理职权和责任阐释中,管理层也必须掌握可观的职权才能履职。
这种权力必须始终扎根在社会价值、道德概念和理性问责当中,才能成为在社会和政治上具备合法性的权力。我们需要管理,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我们也知道,管理层只是现代社会中一群拥有权力的人,这与30年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管理界的共同看法是,管理层应该也能够是“权力精英”。
但我们不知道,管理的职权应该怎样扎根,怎样加以限制,又如何确定这些限制。这是一项有待管理专业的学生们去解决的核心任务。从本质上看,这项任务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但若是不掌握充分的管理知识,不理解它的关注点、职能、经济、组织和哲学,就不可能解决它。
管理界的宇宙大爆炸
70年来,我们一直采用独立而分离的方法研究管理。为什么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下去了,或者说,再这么做下去是徒劳无益的呢?这里有一个完全不同但或许更令人信服的理由。管理成为了世界性的现象。而最需要管理的,恰恰是没有管理传统的国家,也就是“欠发达”国家(以非西方传统、非欧洲人口的国家为主)。
在西方,管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较晚发展起来的职能和机构。自然,对这种职能的意识,以及“管理者”领导群体都出现得很晚。然而,在欠发达国家,管理是发展的核心资源,管理者是发展的核心动力。
管理作为一种超越国家的职能和学科,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60多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矿业工程师变成政治家的美国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以及从哲学-历史学家变成政治家的捷克人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携手创办了国际管理运动(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Movement)。
但从本质上说,直到最近,人们仍把管理视为只存在于“发达”国家的一种现象。而且,基本上除了日本,管理似乎仅仅局限在“西方”世界,就是欧洲各民族居住的国家。
自不待言,今天的情况早已不是这样。这或许是管理短暂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情。它也对我们的管理知识、对管理人员的专注提出了极大的需求。
过去70年,是管理问世的最初70年,在此期间,我们发展出了对这门学科、这一职能和这份工作的认可,确立了培养理性认识和专业能力的第一批方法。还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发展出了管理教育。事实上,第一所叫做“工商管理学院”的学校,即哈佛商学院,马上就要迎来自己70岁的生日了。
至此,管理的童年和青春期到了尾声。不出意外的话,人类期待会不断上涨,吞没整个世界,由此带来的巨大挑战要求我们将管理的方法统一起来,发展出一种可以学习、传授,以及更重要的,供人敬仰、给人鼓舞的东西。
“管理”是促成经济和社会快速自由而有尊严发展的催化剂。但与这种发展相对的,不再是不曾发展、偶尔才能窥见人类自由与尊严的原始社会,而是通过恐怖、通过暴政、通过把人贬低成庞大社会机器里的无名小卒,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
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呼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衡量管理的成就。这一成就也改变了管理,改变了管理要履行的任务。人们现在需要的,光靠卓越的技术已经无法满足了,但光靠人际关系的道德责任同样无法满足。从现在起,“管理科学”“科学管理”“管理经济学”和“人际关系”,必须在理论上成为整体,也必须在管理的实践中成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