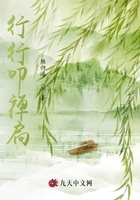
第24章 梨花酿(10)
人群中传来哄笑声,我一下子稳定了心神:“阎王哄骗你呢!小丫头可莫信啊,几个叔叔都是闹着玩儿的,还望你不要当真。”
但此刻我觉得像个傻子,杵在那里不是,出去也不是。
严崇明看我上当受骗,露出不经意的一笑。
我立马跪求到几位大佬的面前,假惺惺挤出几滴眼泪,红着眼眶向十王指控阎王的恶行:“请各位大人为小女做主,小女本想游览完人间后再转世轮回,谁知地位崇高的阎王殿下竟光天白日之下强抢民女,小女不从,便教唆黑白无常对我使用酷刑,您看小女的脖子,就是被他们勒成这样的。”
几位为之动情,而严酷冷漠的阎王却抓着牌不做声,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我揭开衣领,掐准大腿的肌肉,“啊”的叫出声来:“可怜我小小贱命,竟被地府高官戏耍,简直是草菅人命啊,我来地府后,整日被关在阎罗殿,不见一日光明,三餐虽由下人负责,但小女着实怕里面有毒啊!请各位大人为小女调查此事,还小女一个公道!”
阎王气得七窍生烟,指着我正要破口大骂。
我又连滚带爬拖住了阎王的脚,他吓得手里的牌混作一谈,他嘴角抽筋,此时怕是想将我扒皮,做成一副好骨架了。
早就听说十王脾气不好,阎王在场,他们怕是也不好发作,何况这事本是我冤屈,再怎么着他们也不敢先问我的罪。
此时战局一度僵化,呷茶的蓝袍汉子憋不住了,看向严崇明:“你不是有张十世镜吗?”
我料定此局五五平,怕是棋高一手的阎王也无力回天。
他镇定道:“被本王的下属弄丢了……”
他的眼神却带着点仇恨。
我梨花带雨,赖在地上不起,甚至还觉得阎罗殿还有点儿凉快,最起码……比三伏道行浅。
“那就没有法器勘测过去了吗?”
白袍大汉叹息道。
法器,法器,这一天到晚就是法器。严崇明那个仇恨值啊,快要被十王拉满了,现在洞悉真假的就只有我和阎王两人,我就不信他凭一面之词翻天?
哼哼,一切都在我料定的范围内有序进行着。
他的声音永远沉着稳重,仿佛世间万物都如过眼烟云:“你说本王苛待你,那为何会将你亲自带来地府悉心培养?”
我支支吾吾辩解道:“那是你……别有用心!”
他不紧不慢地揭破了我的谎言:“好,你既然说本王别有用心,那本王问你,在你被山魈抓伤时谁救了你?又是谁从黎氏兄弟手下饶恕你?本王带你回地府应职,可曾有一丝苛待?若是本王委屈了你,你尽可不必留在这里。”
我没有回答他。
十王用看戏的眼神老实磕瓜,就等着我出丑,但话锋一转,阎王还是把利刃收了回来:“我知你是无心之举,若是以后在地府行事,遇到不平皆可向我报告,就算是黎氏兄弟来犯,也不能畏惧。”
我懵懂地点了点头。
他的指尖敲了敲桌面,身上笼罩着一层柔软的暖光,带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今日本是子虚乌有,秋娘同为地府人员,一同为天庭着手,自当和和气气,不要发生内部矛盾才好。”
十王都抿着唇不说话,看样子,是严崇明决意护短了。这种场面,他们就不打紧了。
而我,莫名其妙的对阎王增加了几分好感。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还有些自责,虽然事情上没错的太离谱,但是顶撞上司这个事还真不好讲,毕竟十几个人压本,太大的情绪不好发挥。
严崇明这个家伙,还怪好心地替我做主,很显然给到我压力了,但那这一番话振聋发聩,让原本对地府内部福利不满的几个老员工,都通通征服了,看来他这个震慑力是给的够够的呀。
我搓了搓冒汗的小手,正准备说两句应承话,找个称心如意的借口离开,严崇明突然又笑了一笑,缓和气氛道:“本是去给她办理入职的,没成想半路又到了这里,没想到让新人等急了,既然时候已经不早,不如就此散场,也让十王早点回去休息吧。”
十王纷纷赞同,而我也在一片纷扰中,跟着严崇明回洞。
严崇明在前走着,步调缓慢,声音低沉,带了点斥责:“下次不要这么胡来了,地府很大,说不定哪天遇上一个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上司,或者迷路撞个头破血流,到时候就不是本王能预测的结果了。”
而我在身后不发一言。
“十王的脾气乖张,这次是我在,下一次呢?你自己能应付得过来吗?”
他的眉峰间带着狠戾,我难以捕捉,也无意触及,只是回想在人间的遭遇不免心猿意马,思绪一下就回到了街边五铜板的臊子面,那是和峨眉每日晨起的每个平凡瞬间,一边拿着冰棍跑一边给等等报讯,夕阳下的投影,是两双奔跑在田野间游戏的丫头片子。
可惜这一切恍若云烟,而我也终究成为地府人员,再也不能无拘无束地去人间游玩,而每次都是带着无比艰难的任务。
不知道是不是被阎王抓回来的缘故,我总感觉没有填完心愿就不算巾帼英雄,而且带着遗憾带着记忆游荡,也膈应的很。
严崇明见许久都没有听见回声,转身看身后,我正在那里一遍一遍苦恼未来的生活,就迎面撞上了他的胸膛,一头埋进那件宽大的袍子里,他身上带着助眠的兰香,让人不自觉陶醉其中。
而他的心跳声是那样的明显,呼吸上下起伏着,双手摊开一时不知所措,仿佛已经能洞察面具之下的那张脸是红扑扑的,是因为含羞带怯,还是刹那的心动,一瞬也分不清了。
而我下一秒好像就要抱紧他,头顶上却传来一声疏离的警告:“躺够了没有?等下教你新人手册,背下来默写三遍,抽问错一个字罚你抄书。”
我赶紧从他怀里抽身,悻悻冲到最前面:“我可不想接受第二次的惩罚了,殿下大人有大量,还是饶过小女吧!”
他嘴角勾起一丝得逞的微笑。
由于地府的地形类似,我只能靠标准的建筑物记住路程,比如说转角的烛火,门上的八卦阵,天顶上的洛书,还有女人的第六感,所以我很快就找到了原本的路。
但是当我抵达最前面的岔路口时,我酝酿着向阎王炫耀一下魂之超速,严崇明慢悠悠的赶来,嘴唇却异常苍白。
他甚至还扶着墙就要往后倒,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
这么短的时间,他去跟谁干架了?
我自打没趣地晃晃手,一脸担忧他的状况,毕竟这么久以来他也有意无意帮了我好几次的忙,我要说落下这个救命恩人,那岂不是真正的冷漠薄情?
我才不套背负这么多恩恩怨怨呢,只愿他只是装出来的,我能安心上任。
可我妄图想从那双眼睛读懂他的孤傲时,那丝丝缕缕的慌乱,失措,竟是如此也遮掩不住的。
我拉住他的臂膀,双手轻拍着他的后背,他抬起头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却充斥着仇恨与厌恶,弯起的嘴角不知是上火还是皲裂开了,裹挟着不能平息的愤怒,使劲抽搐了几下。
“你……没事吧!”他实在不是我记忆里的严崇明了,在我的刻板印象里,他一直克制而理性的,刚硬中不失柔和,而现在的他,好像恨不得把一切都吞噬,一切都是他罪恶的种子。
而他甩开我,强撑着身体往前走了几步,脚步却浮夸得像个买醉的痞子,我下意识扶住他的臂膀,他却踉跄走了两步,最后倒在地上躺平。
由于我并不知他的卧室在哪里,只是大抵知晓办公的地方叫做书房,就是用孟婆教给我的瞬移咒术,伴着他去了那个最初的房间。
我好不容易把他扶上胡床,他这辗转反侧的,可谓是比普通的病人还要难照顾,不仅梦呓一些天马行空的东西,而且老是在我换水的时候把上衣全扒拉开,额头上的湿毛巾就“唰”地一下掉下来。
胡床不大,是容不下这么大个男人横躺在上面的,顶多是一个我这样的骨架稍微小点的女子,坐在主位读书识字是恰好的。
许是他这个人念旧,桌子上的漆掉落,也不舍的换一张新的。而桌上的册子摞得高高的一叠,有多少是他不愿动手的,有多少是因为闲玩耽误的,咱也不知该不该批啊!
再者说,这厮醒来后,会怎么处分我,还是挨批?又是一回事了。
他躺着稍微舒服点时,屋子里关上窗户就闷热,让原本凉快得穿两件中衣的地府,都蒙上了夏天该有的皮囊,他闷热得浑身冒汗,气色是比刚刚好上不少,就是抓着被子,嘴里念叨着“不要走”这一句话,这个毛病真得改改。
我来来回回跑了很多趟,还差点在八张门外面迷路了,替他擦了无数次汗,很多次都想揭开面具看一看究竟,最后还是犹豫了,任着汗滴顺流而下,还是没有打开这最后的隐私。
事后我后悔,如果看一看他究竟是不是我认识的人,是否就能安心许多,或许我就能承认输在自己人手上,也没什么遗憾的了。
但如果这时出于好奇,他会不会醒来蹦起来暴打我一顿,或是将我逐出地府,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肯定还不如黑白无常的锁灵囊舒服,一觉睡到自然醒,还不用担心外面会出什么事。
于是简易搭了张桌子,搬上小板凳就开始趴在那里睡,一开始我并不知情哈喇子流在桌子上,只是有一下没一下感受到这股没由来的湿润,任凭它撇来撇去。
梦中又全都是人间的美食,这样的梦境,就别说笑得开花,就算是垂涎三尺,也不足为奇。
强烈的兰香味袭来时,那时我还是换个姿势接着睡,他刚往我的肩上一放大氅,我就揉着眼醒来了。
“怎么不多睡会儿?”我与严崇明同时脱口而出,他说这话的目的很明显是带着惦念,而我则是关切。
我们俩说完之后,纷纷把头别过去,严崇明神色异常,好像始终不愿面对我,我也没提出来留下的想法,于是找借口离开:“你的病还好,我去给你熬碗药吧!”
他一双冷漠至深的双眼终于回暖,坚毅中带着柔软,一把拉住我,对视许久:“我这是旧病,你不要去。”
我面上一热:难道……他这是在恳求我留下?
接下来我就明白自己想多了。
“出了这扇门,自己循着路标去找地藏菩萨的府邸,金乔会收留你的,你刚来暂时不能承担渡化的重任,先让你从底层扫地僧做起,顺便可以在扫地的同时学习一下是如何让怨灵诚服的。”
我哑口无言,没想到这个一毛不拔的阎王,会想到这么蹩脚的注意。不过也是,我对他意义不大,留在这里也是添乱。
“我知道了。”严崇明这家伙,里外不是人,像个石头一样难捂热,我又何必去他跟前找存在感?
倒不如自己寻个开心,也算是了却在人间的一桩心愿。
随着石门的移动,我按着按钮看了最后一眼,紧接着便在四通八达的洞穴四处寻找。
……我突然有些迷茫了。
然而在我走后,严崇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似是想起了曾经的一些痛苦的记忆,竟蹲在地上抱头大哭,嘴里还呜呜的叫着,那叫声听起来钻入人心,只觉他也是个可怜人一个。
前来报道的赤羽飞来,落在他的桌面上,梳理着沾满灰尘的破碎羽毛,它是一只出生于地火的尖喙小雀,从地府诞生以来,便一直存世。它虽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却在千百年的进化中,感知到人类的悲喜,并为其分享一二。
很显然,这次主人遇到了大麻烦。按照神仙的语言来说,这就是命中的劫数。
它不能参与记忆,却可以消弭一二,不多时,它便施展法术强行把这些难过拔除掉,可内心有个声音也在呼唤它,它的法术太薄弱,是能依靠天帝帮忙。
而当它飞去给天帝传信时,天帝却只回了一句简短的话:这是留住记忆的惩罚,赤羽你务必不要插手。
为了能留住记忆,甘心为地府服务千年,值得吗?
赤羽扪心自问,可它心中也没有答案,它只能默默倾听着来自主人的痛苦,那段像从深渊里涌出的火焰,合眼间就要吞没清醒的记忆。
这夜,严崇明的梦中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体弱多病的自己,年少相识的恋人,求佛拜神,担忧身体的爹娘,没有一个玩伴的童年,以及一段灰色的人生。
他好像一个初开混沌的生命,睁开疼痛难忍的双眼,撕裂一切不规则的黑暗,那未知终于在眼前清明:他倒在大雪纷飞的小院里,嘴角吐着猩红血沫,身上的白鹤大氅披在肩,而他半阖着眼,看屋檐上的落白,天地间的粉尘,在一瞬飘散的,飘散的是过去那些美好,夹杂着些许辛酸的回忆,而他就这样静静离去,等到下人发现时已经冰凉。
爹娘感叹白发人送黑发人,一夜之间竟哭哑了嗓子,乌发也白了许多,他们把他埋葬在靠南的一处悬崖,那里长满了临云的松柏,借此正好可以俯仰天地,后来听人们说,他们变卖了祖宅,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生活,还有人说,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一场场的离别,都昭示着结局的悲惨。世事如苍狗,生命终凋零,也许本该如此,他本该薄命,拥有过的也终将消散。漂泊不羁的灵魂,开始在人世间徘徊,当七魄散去,有人拿起手中的工具修补他的三魂时,另一个他就重生了。
严崇明回想着过往,梦中的画面好不真实,无论他如何想摆脱现实,都无力回天。
这就是天帝口中的惩罚,人间所说的报应。
地府很大,像蜘蛛精住的盘丝洞,千奇百怪之间掺杂着一丝华丽,比如说长廊尽头点起的莲花灯,屋顶上的北斗七星阵,都挺有玄机的。
地府很冷,来自枫杨树下的风灌进来,吹落一地沙沙的树叶,枯枝没有完全掩住洞口,反而成了一个很好的庇护所。所以尽管是大暑,也凉意袭人。
地府很暗,尽管点了无数盏莲花灯,没有那种置身洞穴的压抑感,但还是会有一刹那就要失明的错觉,大概是莲花灯照的太亮,时刻提醒着地府工作者,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视觉冲击。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回收着每扇门后面传来的声音,杂乱无章令人心烦意乱,经久不衰的凉意却一下冲散了这股莫名上来的火,说不上很奇怪,但每次都想按下按钮瞧一瞧,但一想到阎王的忠告,脚就顿在了门口。
“还是少管为妙。”我讪讪离开,走了这么久竟然一点都不渴,看了眼种满绿植的角落,盆栽里散漫的一串水珠呈直线形,挥洒在植物的根部。
我在十里春生茶馆当掌柜时,都是峨眉帮我记账,钱多多少少也进过她的口袋,但对于写在纸上的东西,我是一概不知,只是当年跟着等等在墙角下听过几堂教书先生的国语课,剩下的字就只能依靠别人说起,依靠脑袋去记。
所以压根我就不知道,水雾遇空气成气体的原理。
心里只道神奇,神奇,却不知是这个理。
正当我发愁上哪去找地藏菩萨时,一扇门忽然开了。
里面没有火球从里面滚出,也没有千丈的寒冰深渊,只是类似于普通寺庙里那种结构,房梁全部由凹凸不平的乱石凿成,周围点着千万盏莲花灯,照得整个殿宇灯火通明。
里面有几个僧人打扮的仆人正在干活,有修剪枝叶的,有扫地上灰尘的,有擦拭桌椅的,虽任务闲散,脸上却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仿佛他们的主人交给他们的任务,都是重中之重。
也说不上来,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包裹住了我,好像这里就如同我的另一个家一样,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不沉闷也并不无趣,总是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做。
这些僧人见大门开了,只当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我逐渐被里面的事物吸引,缓缓踱步走到大厅,顺手给他们关上门,这才发现里面另有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