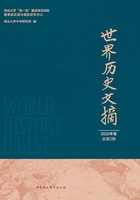
惠特拉姆政府与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的开启
汪诗明[1]
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党政府时期是澳大利亚土著政策的转折阶段。工党政府既承担了为土著立法的责任和义务,又在与土著有关的很多领域出台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政策或措施。这些政策或措施推动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且开启了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与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和解之路。废除“白澳政策”俨然从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构建扫除了障碍,为种族和解进程的开启创造了必要条件;“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组建体现了政府决策层面的民主化趋向,有利于在土著澳大利亚人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作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人权法案,《种族歧视法》的颁布不仅维护了“白澳政策”被废除的成果,而且成为种族和解事业前行的一个法律保障;土著土地所有权问题被纳入联邦政治议程,正视了种族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使得这一问题受到此后历届政府的持续关注。当然,土著问题本身的复杂与敏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种族和解理念及其实践活动尚处在初步探索阶段。
关键词:戈夫·惠特拉姆 多元文化主义 土著土地权 《种族歧视法》 种族和解
种族和解不仅是现代化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后现代社会研究中常常提及的话题。澳大利亚是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如今已步入后现代社会,但殖民时期所产生的土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意味着种族和解仍是澳大利亚今后所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和期待实现的政治目标。
从国内学术界来看,种族和解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是与陆克文总理分不开的。他于2008年2月13日首次以政府或议会的名义向土著民族尤其是“被偷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s)[2]表示了正式道歉。[3]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学界应有的关注,出现了若干研究成果。[4]但这些成果的视点大都放在作为新工党代表人物——陆克文身上以及此次道歉的原因、路径和影响方面,而对于种族和解的起点的探讨则付之阙如。
从国际学术界主要是澳大利亚学界来看,“白澳政策”期间,由于受到英国学界的影响,澳大利亚主流或传统学界通常是在宏大的帝国叙事背景下来界定殖民时代以及那个时代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5]及至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的学术生态有了较大改观,这主要是因为“白澳政策”的退场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登场。[6]这种新的政治生态对学术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土著问题纳入广泛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范畴中;二是以种族和解为视角或主题来研究土著问题。坦率地说,与种族和解有关的学术成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多。通过梳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类似于口述史学的成果。通过对幸存的“被偷的一代”的采访,让世人知晓他们曾经不堪的遭际,进而呼吁人们支持种族和解事业。这方面的代表作当属珍妮弗·萨比奥尼(Jennifer Sabbioni)等人主编的《澳大利亚土著之音》、彼特·里德(Peter Read)的《心灵之殇如此之深——被偷的一代的返乡》和米歇尔·戈登(Michael Gordon)的《和解之旅》。[7]二是具体探讨种族和解的路径或种族和解的模式等。这方面的成果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面世,如米歇尔·格拉顿(Michelle Grattan)主编的《论澳大利亚种族和解》就收录了包括澳大利亚政治家和知名学者在内的四十余篇演讲稿或主题论文。[8]三是把某一特定事件与种族和解进程联系起来考察。比如达缅恩·肖特(Damien Short)的《种族和解与殖民权力——澳大利亚的土著权利》就以专题形式对种族和解进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如“威克裁定”(Wik Judgement)、“被偷的一代”等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及其处理过程和结果对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9]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彼特·H.拉塞尔(Peter H.Russell)的《对土著土地权的承认——马宝案件和土著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抵制》[10]等。不难看出,上述成果聚焦在如何实现种族和解这一带有现实关切的问题方面,至于种族和解进程起源于何时以及由哪个党派开其先河,大都语焉不详。殊不知,要想对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及其成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厘清种族和解进程的起点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因为如果对这一事件的起点都不甚了解的话,何以对其进程进行梳理与考察,又何以对其成果做出总结与评判?通过对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土著政策的全面透视,我们发现,一个重要转折点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即以戈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1972—1975年在位)为首的工党政府时期。这一转折点不仅基于这一时期的土著政策或措施较之前有诸多革命性变化,而且在于对后世的持久影响方面。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种族和解的必要条件、种族和解的理念、重要途径、法律保障以及焦点问题等方面来剖析惠特拉姆政府是如何开启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的。
一 “白澳政策”的废除——种族和解的必要条件
“白澳政策”是一种体现盎格鲁—撒克逊人优越感,并以法律和政策来维护白人种族权益且把澳大利亚打造成一个纯白人国家的种族歧视政策。[11]这一政策维护了白人种族在澳大利亚的优越地位及其特殊权益,却给土著民族的命运及其种族关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并给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带来损害。“白澳政策”的废除表明通过法律或政策来维护某一特定种族的地位与权益而歧视其他种族的做法在现代国家里是行不通的。澳大利亚需要一种反映时代变迁以及种族关系新内涵的新的理念和政策。
“白澳政策”始于英国殖民时期,表现为殖民者对土著生命的漠视以及对其世代所有的土地的肆意侵占。1901年联邦成立后,这种政策发展为对有色人种移民的限制或排斥,以及对土著的忽视或歧视。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或措施的出台,“白澳意识”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白澳政策”成为立国之本;白人文化成为同化包括土著在内的有色人种的唯一官方文化。[12]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下,同化土著成为官方土著政策的不二之选,土著因此沦为澳大利亚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种族,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
首先,同化土著的政策是一项种族灭绝政策。
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曾对土著实行过屠杀和驱赶、保护与分离等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名目多样,但其目的或宗旨始终如一,那就是减少土著人口乃至最终让土著民族从地球上消失。[13]联邦成立后,土著成为一个被遗忘、被忽视的群体,甚至联邦人口统计都将土著排除在外。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同化”政策的大旗被高高擎起。[14]对土著的同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混血土著的同化,“偷走政策”是其主要手段。这场同化运动的另一面就是尽力阻止纯血统土著与混血土著之间通婚,而支持混血土著女性与其同样肤色的男性或白人结婚,作为在人工繁殖中消除肤色的一种手段。[15]第二阶段则是对所有土著的同化。这一政策意味着纯血统土著和混血土著将不得不放弃他们原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被迫去过白人那样的生活。[16]这一政策的设想是:假以时日,土著以及混血土著对其历史、文化和语言将一无所知,土著问题亦将不复存在。[17]所以,对土著来说,同化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政策。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斯图亚特·麦金泰尔(Stuart Macintyre)对此一语中的:“白澳政策是对这个国家土著居民的一种否定。”[18]
其次,同化政策使得土著与白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对立和僵化状态,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人为撕裂。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特征显著的民族或种族,土著厌弃同化政策。第一个抗议政府的同化政策的团体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悉尼,被称为“澳大利亚土著进步协会”(Australian Aborigines Progressive Association)。[19]此后,反对歧视土著的同化政策,要求获得与其他澳大利亚人同等公民权的运动就没有止歇过,并在6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20]比如,在土著坚持不懈的斗争以及白人有识之士的同情与支持之下,澳大利亚于1967年5月举行了旨在废除联邦宪法中歧视土著条款的全民公决。[21]虽然参与投票的人中有高达九成支持修改宪法[22],但全民公决后,土著并没有看到期望之中的变化,自由党联合政府仍自得于其在土著问题上惯常的“懒政”风格。在澳大利亚著名政论家、思想家唐纳德·霍恩(Donald Horne)看来,这可能是由于种族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自由党联合政府在土著政策方面的意识麻木以及缺乏想象力,他们甚至不明白缺乏政策在其本质上就是一种政策。[23]到了60年代末,为应对日益凸显的移民问题和土著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试图用“一体化”(integration)政策来取代“同化”政策。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一体化”政策仍是“同化”政策的翻版或变体,因为“一体化”政策并不意味着种族和文化的多元性被澳大利亚社会吸纳,相反,它意味着多元性的某些方面不会对主导文化和社会秩序带来困扰和威胁。[24]由此可见,只要“白澳政策”不从官方政策中涤除,那么任何有关有色人种的法律、政策或措施就无法不受其羁绊,土著与白人的关系因此就不可能出现好转。比如在昆士兰,一位年迈的土著就把欧洲人描述为“聪明绝顶、冷酷无情以及彻头彻尾的大骗子”。土著领导人丹尼斯·沃克(Denis Walker)则用更加政治性的术语说:“这个国家的压迫——尤其是在‘新法西斯的昆士兰州’——是一种对全人类的犯罪,最受压制的是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25]
1972年1月,为表达对政府有意忽视土著土地权政策的不满以及希望引起国内外对澳大利亚土著处境的关注,一帮土著青年在堪培拉国会门口大厦前的草坪上竖起了几顶帐篷[26],取名“土著大使馆”(Aboriginal Embassy),寓意土著是在澳大利亚土地上的外国人。土著青年采取这种激进的方式让威廉姆·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1971—1972年在位)政府处境尴尬[27],也让澳大利亚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28]“土著大使馆”事件暴露了自由党联合政府在土著问题上缺乏同理之心,同时给在野二十余年的工党看到了成为执政党的希望,以及在土著问题上有所作为的历史性机遇。在1972年的联邦大选中,工党许下承诺:将“对曾经引以自豪的土著民族遭到严重伤害和打击的那一段剥夺、不公正以及歧视的历史”予以匡正[29]。1973年,惠特拉姆政府毅然决然地废除了“白澳政策”。
众所周知,“白澳政策”曾经是土著澳大利亚人与非土著澳大利亚人之间构建平等关系的一大观念性和制度性阻碍因素。“白澳政策”的退场意味着土著澳大利亚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建立在新的观念和制度之上。这种新的观念和制度必须反映澳大利亚社会自“二战”以来就在悄然发生的移民结构的变化[30];必须把长期视而不见的土著问题置于政治议程之中并给予合理关切;必须以国际视域来审视国内的土著问题,履行相应的国际义务。无疑,澳大利亚需要一种反映时势变迁以及诠释种族关系新内涵的带有民主、平等、和谐意识的种族政策,即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或思潮是从加拿大借鉴过来的,旨在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方式,对“二战”后几十年间由于大量移民涌入而在本国出现的种族的“文化多样性”以及20世纪60年代逐渐放弃种族限制性移民政策做出反应。[31]在马克·洛佩兹(Mark Lopez)看来,“‘多元文化主义’一词具有互换的两个含义。它可以用来指代一个经验主义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事实: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语言多样的社会。它也可以用来表示澳大利亚社会被组织或应该被组织的方式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的概念。如果有意把客观事实的重要性注入意识形态/规范化的概念中去,那么它常常被用来指代上述两个方面的含义”[32]。洛佩兹对“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的界定与释义对澳大利亚社会的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意义。
土著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在几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历史长河中[33],土著民族生生不息,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本土文化。土著视文化为其生存的目的或意义的观念以及与自然共生一体的理念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建设舍弃不得的文化与精神财富。[34]从澳大利亚的历史嬗变、社会文化伦理的延续以及国家或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看,土著及其文化在正在构建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只有将土著及其文化纳入其中,使之成为多元文化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建立起来[35];反之,一个不包括土著及其文化的多元文化社会在其理论建构中是不完整的,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
接受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就意味着所有种族及其文化都应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从政策层面来看,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包容性政策,它首次作为公共政策所指涉的就是文化的多样性。当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个针对“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政策提出时,外来文化(包括土著文化)中的语言、传统、遗产和习惯就应得到尊重。“白澳政策”的摒弃,虽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动摇澳大利亚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却在理论上承认了其他非主流文化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为包括土著文化在内的其他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为“接受文化多元主义就是承认没有哪个群体生活在真空中——每个群体都是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36]曾担任惠特拉姆政府首任移民部长的A.J.格拉斯比(A.J.Grassby)就把“多元文化主义”形象地比喻为“民族之家”(Family of the Nation)。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强求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在观点或行动上的统一性(也可理解为“同一性”),这些成员也无必要为了一个表面上的、不近人情的统一性而否定各自的个性和特点。[37]1972年12月14日,惠特拉姆宣布,政府将对白人管理土著教育的体制进行改革,其目的是拯救正在消失的土著文化。在这一方案下,土著社会的初级教育将用土著语言授课,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土著的传统艺术和技艺也将受到重视,比如树皮画、舞蹈以及游戏等不再受到鄙视。这与同化政策时期只重视英语教育和白人文化有很大的不同。[38]此外,联邦政府还责令教育部要对所有特殊教育包括北领地区的土著成人教育承担责任。[39]
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文化社会,意味着联邦政府有义务去解决土著的实际民生问题。这是种族和解的一项重要内容。
多元文化主义不仅仅指文化的多样性,还有着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多元文化社会构建以前,土著人数以及包括健康指标在内的其他数据都是模糊不清的或缺失的。[40]1972年8月,由罗纳德·亨德森(Ronald Henderson)领衔的“亨德森贫困调查委员会”(Henderson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Poverty)[41]提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说:“与其他澳大利亚人相比,土著婴儿死亡率较高,土著寿命要短得多。他们易患一些澳大利亚白人中很少见的疾病,且发病率很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很多,包括生活贫困、住房条件差、卫生设施不到位、水供应欠缺、营养不良以及种族歧视。现有的医疗服务无法满足土著的健康需求。”为此,工党政府重视对土著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42]当然,土著也可自愿参与各种与己有关的福利机构中。[43]在重视土著健康的同时,土著的居住条件也在逐步改善。鉴于自由党联合政府时期的经验教训,工党政府从实际出发,制定不同政策来改善土著居民的住房条件。[44]
“白澳政策”持续了一百多年,它对形塑澳大利亚白人与包括原住民在内的有色人种的关系起到了制度性、结构性和基础性作用。“白澳政策”的废除意味着澳大利亚必须重新建构后殖民时期的种族关系乃至国家属性,而这种建构的指导原则和方针就是种族平等。对澳大利亚政治家来说,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让土著不再感到他们是澳大利亚社会的“他者”,而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5]惠特拉姆政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去审视和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并把解决土著民生问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后来的种族和解进程一再证明,惠特拉姆政府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理念以及对土著民生的关注实际开启了种族和解的一种模式——象征性和解与实际和解的有机和辩证的统一。
二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种族和解的重要机构
种族和解不是哪一方的独角戏,不是一个强势一方施压而弱势一方屈从的过程,而是一个有关各方加强沟通与了解、缩小分歧直至取得共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决策者或管理者必须倾听民意,了解土著社会的诉求。否则,政府的决策就有可能违逆土著社会的意愿而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土著社会一直认为,做出有关他们生活的重要决定而事先不与其磋商,这是不公正的和不民主的”[46]。因此,工党政府在倡导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同时,希望在土著社会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以便政府了解相关决策信息,并为土著社会实现“自决”或“自治”创造有利条件。“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borigi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47]
1973年4月6日,惠特拉姆在阿德莱德召开的联邦和州土著事务部长会议上致辞时说:“我的政府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恢复澳大利亚土著人民失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方面的自决能力。”[48]6月,成立咨询委员会的选民登记工作开始,拟定于9月29日结束。11月5日,筹备委员会向工党政府内阁提出建议,就成立“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给予经费支持。[49]11月10日开始选举,选民们将从195位土著候选人中选举41名土著正式代表。
为了动员更多的土著参与此次影响他们自身前程的选举,惠特拉姆总理于11月23日晚发表了电视动员讲话。惠特拉姆在讲话中对此次选举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肯定:“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明天将要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史无前例的选举。澳大利亚所有土著居民都有权利去投票。你们将投票选举‘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将在促进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事业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所有土著将行使其手中的权利并担负其肩上的责任,参与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和民主化的进程。”[50]12月,“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在堪培拉如期成立。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是在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由政府倡导、土著参与并起主导作用的一个有关土著事务的咨询机构。这一机构的成员构成、性质与功能决定了它必然对联邦政府有关土著政策的决策程序和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其对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的意义和影响不容小觑。
首先,成立由土著参与并主导的咨询机构是对土著社会应有的尊重。
早在1968年2月,土著领袖们就开始商讨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土著代表组织。新组织的目标就是让全国范围内的土著参与进来,使其成为一个名实相符的土著代表机构。[51]1973年2月,惠特拉姆政府首任土著事务部长戈登·布莱恩特(Gordon Bryant)不仅到土著社区走访,而且约请80名土著社会精英赴堪培拉就成立一个由土著代表参加的咨询机构进行磋商。[52]考虑到土著社会对白人操纵的咨询机构抱不信任态度,布莱恩特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明确而坚定:咨询机构的成员应从土著以及混血土著中遴选。与之前一个由白人所组成的类似的咨询机构相比,这是一个迥然有别的变化。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首次让备受压制和歧视的种族在影响其自身利益的官方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53]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选举中有26名土著妇女候选人,且最终有两名妇女当选[54],须知在当年的联邦议会中也仅有两名女议员。布莱恩特的继任者詹姆斯·卡瓦那(James Cavanagh)对此不无得意地说:“这是一个‘新的部落聚会’,我们的全部希望就是给澳大利亚土著及岛民带去被我们的社会长期剥夺的正义、尊严和地位。”[55]
其次,该机构将承担向联邦政府提供与土著事务有关的咨询功能。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向政府提供有关土著事务的独立建议”[56]。这也是工党政府成立这一机构的初衷或动机。正如惠特拉姆本人所言:“现在,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恢复土著拥有对其生活方式的决定权。土著事务部已经在把管理社区事务的责任由政府主管们和经理们转向土著本人。我们相信‘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建立是这一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希望该委员会成为土著表达意见的一个平台。我们希望在土著和联邦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健康的双向联系。”[57]该委员会建立后不久就肩负其责,并就改善土著民生等问题向土著事务部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而政府方面也开始发现在制定与土著事务有关的政策或措施方面,忽视该委员会的存在将会遇到更多的阻力。作为土著事务部的掌门人,詹姆斯·卡瓦那有时不得不出面澄清正在发生变化的联邦土著政策。1974年7月11日,他在议会发言时说:“帕金斯[58]先生说我们应该把管控土著的事务完全委予土著,我的部门以及我本人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我们正在通过组建城镇委员会、福利组织、住房协会以及发展工业来建立土著对每一个土著居住地和每一个传教站的控制,这样他们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加以推进。土著事务部最终在土著事务中将扮演次要角色,成为咨询者以及可能成为为建立很多产业而拨款的财政机关。”[59]总之,无论是惠特拉姆所提倡的“双向联系”,还是卡瓦那所预见的土著事务部将变成一个为发展土著产业而掏腰包的机构,均说明“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将在土著政策建议以及土著事务管理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组建展现了土著精英非凡的组织能力,并为土著自治埋下伏笔。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是一个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的土著事务咨询机构。该委员会从酝酿成立到选举落幕,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有资格参与此次投票的土著选民约5.3万人,实际投票人数为36338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举行如此成功的全国性选举,这在本质上是对参与并组织此次选举的土著精英能力的一种考验和肯定,此前在澳大利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60]这就用事实确证:白人社会能够做到的事情,土著社会同样能够做到。这是对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有力回击。这也成为种族和解的基础和动力之一,因为忽视、轻视乃至鄙视土著社会的管理与自治能力是白人社会的惯常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维系并强化了白人与土著之间的不平等交往方式,并致相互关系疏离、隔膜甚至对立。土著在此次选举中所显示出的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令白人政治家不得不予以正视与反思,这有利于纠正他们对土著群体的偏见。而偏见一旦消解,土著就有可能在相对平等的环境下主导自己的事务,距离他们所追求的自治目标也就不会太远。[61]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在其运作期间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比如该机构高层领导间的嫌隙以及与联邦土著事务部之间的互不信任等。[62]但这些问题与挑战最终以妥协的方式得以化解。这进一步说明:种族和解事业的开启与推进不能仅依政府的一厢情愿,土著社会的积极参与以及与政府的有益互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惠特拉姆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与尝试对于后来历届政府为推进种族和解事业而建立的诸多由土著参与的咨询或其他功能机构而言,既树立了榜样,又提供了动力,如马尔科姆·弗雷泽时期的“全国土著会议”(National Aboriginal Congress)[63]、鲍勃·霍克(Bob Hawke,1983—1991年在任)时期的“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64]都是受政府之命而成立的土著事务咨询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名称各异,但建立的背景和希望发挥的功能大抵一致,由此可见“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影响之一斑。
三 《种族歧视法》——种族和解的法律保障
“全国土著咨询委员会”的创建是澳大利亚政府在有关土著事务的决策程序层面向民主化和平等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利于渐次消除土著澳大利亚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以及白人社会对土著社会的歧视,是朝着种族和解的目标而迈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步。但要在根本意义上推动种族和解,澳大利亚就必须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有所作为,让种族歧视不仅在道义上受到指摘,而且为法律和制度所不容。1975年颁布的《种族歧视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就体现了这方面的本意,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和维护了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的成果,而且成为种族和解进程持续推进的一个法律保障。
在“白澳政策”下,澳大利亚的种族歧视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种族歧视给澳大利亚社会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社会分化严重、政治割裂加剧以及被国际社会所诟病等等。对种族歧视给予道义上的抨击是最基本的反应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对散布种族歧视言论以及制造种族歧视行为的人起不到震慑作用。摈弃“白澳政策”在理论上消除了建立种族平等社会的一大观念障碍,但只破不立难以剪除旧的不平等观念和树立新的平等意识。因此,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对种族歧视言论和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就必须成为一种治理常态,为由种族平等走向种族和解创造有利条件。
工党政府反对种族歧视的立场是较为鲜明的,因为“对工党改革家来说,平等是一个具有中心意义的概念”[65]。在惠特拉姆任职的头一年,联邦司法部长尼奥内尔·莫菲(Lionel Murphy)就衔命草拟了种族歧视法草案。然而,出台一部反种族歧视的联邦法律并非坦途。莫菲于1973年11月、1974年4月和10月先后三次向参议院提交《种族歧视法案》(Racial Discrimination Bill),但均告失利。[66]他的继任者凯普·恩德比(Kep Enderby)于1975年2月做了第四次努力。围绕这部法案的舌战折射了工党政府与反对党之间的歧见。当修订的法案在众议院二读时,为避免或缩小党派之间的分歧,恩德比重申了澳大利亚在《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下的义务。[67]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没有人会公然支持种族歧视。参议员戈登·迈克因托什(Gordon Mcintosh)在5月22日的议会辩论时指出,“我了解反对党原则上将支持这部法案,并且会取消一些修正条款……在一个进步的社会,真正的社会进步只能通过人口中的多数对少数群体的态度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来衡量。这部法案有利于保护人们在就业、住房、出入公共场所以及使用公共设施方面免遭种族歧视”[68]。6月2日,联邦众议院最终通过了经过参议院修改的《种族歧视法案》。10月31日,《种族歧视法》正式生效。
《种族歧视法》是落实多元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因此,它的条款中既有对“种族歧视”概念的严格界定[69],又有对具体领域的种族歧视或种族冒犯行为的清晰阐释,更有授权建立维护法律生效所需的基本运作机制。
在一个视种族歧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中,诞生一部从根本上否定这种传统观念或习惯的法律,其意义可谓彰明较著。
首先,《种族歧视法》是澳大利亚联邦历史上第一部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被视为澳大利亚第一部人权法案,是政府希望推动的对新的多元文化社会认可的一部分。它在理论上或原则上实现了土著与白人之间的平等。
190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联邦宪法颁布。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不是一部有关人权的法案,而是主要涉及联邦体制、政府或国家管理机构及其权限、财政与贸易等方面的文件。在这些方面,它是模仿美国宪法的产物。澳大利亚联邦宪法注意到了土著群体的存在,但与很多国家宪法对少数族群提供某些专门保护和优惠待遇不同的是,它只是确认对土著的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法》把平等的公民权扩大到所有公民而不论其种族、肤色、族群或民族背景,弥补了联邦宪法有关人权保护条款的缺失。正因为如此,惠特拉姆本人视它为一个对偏见和歧视的胜利。就在《种族歧视法》颁布的当日,在司法部总部大楼举行的社区关系专员办公室揭牌的简短仪式上,惠特拉姆重申了《种族歧视法》问世的意义。他说:“新的法律条款将坚定地写进我们的法律体系之中,即澳大利亚事实上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土著人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遗产能够在此找到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根据这部法律的精神而制定的教育和发展规划将确保这种现实转化成影响我们国家生活方方面面的实际举措。”[70]从惠特拉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工党政府希望通过法律这一手段来保护非白人群体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应有的地位与尊严。《种族歧视法》的拟定虽不是专门针对土著这一特殊对象,但土著是澳大利亚社会中最受歧视、地位最低下的一个群体,因此,它对土著基本人权的保护有着现实而又独到的意义。
其次,在实践意义上,《种族歧视法》是推进澳大利亚种族和解事业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种族歧视法》并不只是一部有关某一领域的具体立法,还是反对种族歧视的各种原则精神的归纳与总结,是其他立法行动的基础与指南。因为“就人权、土著澳大利亚人权利、澳大利亚少数族移民权利以及种族歧视等将被澳大利亚议会认定为不合法的激进概念而言,《种族歧视法》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重大的立法进步。然而,这不是一个旨在提出来去赢得选民支持或迎合政治测验专家的孤立条款,也非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即‘每个人’都给予同意,民意测验予以支持,它就因此能够成为法律,也不是基于这样的概念:一旦获得通过,它就只‘呆在那里’,作为‘伟大与美德’的证明,而不付诸实践”[71]。从这个角度来看,《种族歧视法》的意义绝不仅限于保护一般意义上的人权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还有着极为广泛的政策含义,比如在教育、医疗、法律援助、文化发展等领域,澳大利亚各级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去反对包括对土著在内的有色人种的歧视政策,即倡导所有种族、所有人在社会领域的平等相待。这一法律颁布的实际意义就在于给澳大利亚各级政府以如下提醒:种族的区别对待不再是任何政策决策的背景或前提,社会公正则既是任何政策的出发点,又是其目的或归宿。
《种族歧视法》被实践证明既是澳大利亚反对种族歧视的一部基础性法律,也是其履行《消除所有形式的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一部法律。因此,不管是哪个党派执牛耳,这部法律都会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科姆·弗雷泽政府不仅不加修改地予以袭用,而且下令检查该法在各地、各行业的落实情况;鲍勃·霍克政府设立“种族歧视专员”(Race Discrimination Commissioner)、建立“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以及对司法领域歧视土著的现象展开全国性调查[72],从而为《种族歧视法》的落实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73];保罗·基廷(1991—1996年在位)政府更是在《种族歧视法》下启动了对“被偷的一代”的调查。[74]正因为《种族歧视法》在反对种族歧视以及均衡种族关系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该法自颁布以来,有时因为联邦政府为在土著社会尤其是北领地区推行某些特殊政策而有被搁浅的现象[75],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国内外舆论合流夹攻之下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恢复《种族歧视法》的局面。[76]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验证了如下推论:只有土著的实际权益建立在《种族歧视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或政策的保护之下,土著人民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们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所拥有的尊严和地位,当然也就有了作为澳大利亚公民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唯有如此,土著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改善。
四 土著土地权——种族和解的焦点之一
种族和解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这个系统中,既有联邦、州或领地层面的决策机制的民主化问题,又有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法律保障问题,更有涉及土著的民生以及福利待遇等实际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就其性质或属性而言都不会在根本上危及白人社会的既得利益。土地所有权问题就不一样了。土地所有权牵涉殖民化、土著在澳大利亚历史中以及现实国家中的社会地位等敏感性话题。所以,二战后长期执政的自由党联合政府在土著要求取得土地所有权问题上的态度要么是不管不问,要么是消极应对。对主张改革和倡导种族和解的工党来说,沿袭前自由党政府的一贯做法是极不明智的,只会让种族关系变得更糟。但另一方面,工党政府也非常清楚,处理土著土地所有权问题将会面临来自白人社会的阻挠或责难。鉴于此,在不广泛触动白人社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选择土著较为集中的北领地区进行土地权的改革与立法试点,就成为工党政府一个明智而有意义的抉择。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60年代末,土著通过包括请愿甚至诉诸法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来争取土地所有权。[77]除少数州外,多数州的政府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如南澳大利亚州于1966年就出台了《土著土地信托条例》(Aboriginal Lands Trust Act)。该条例将为失去土地的土著提供“某种形式的可能补偿”。1970年,维多利亚州政府颁布《土著土地条例》(Aboriginal Lands Act),同意将特莱斯湖(Lake Tyres)和弗拉姆林汉姆(Framlingham)的保留地归还给土著居民。这是保留地内的土地第一次回归其原住民。[78]但是,由于担心土著会提出更多的土地权要求,1972年1月,威廉·麦克马洪总理重申了联邦政府先前做出的对土著提出的土地权要求予以拒绝的政策。[79]这意味着土著收回保留地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发誓要上台的工党政府则被寄予了厚望。
在发起竞选活动时,身为工党领袖的惠特拉姆毫不掩饰其在土著土地权问题上的鲜明立场。1972年11月13日,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就阐述了以他为首的工党对土著澳大利亚人所做的承诺。他说:“我们试图设立一个单独的土著事务部长,在所有法庭所有诉讼程序中,为土著支付所有法律费用;为联邦管辖的领地内的土地进行立法,联邦管辖的领地是保留给土著使用的,并且对建立在传统的氏族以及其他部落组织权利之上的土著占有制度是有益的。根据此项立法,把这块土地给予土著社会;将为重要的持续存在的土著社会建立‘土著土地基金’(an Aboriginal Land Fund),未来十年内每年为该基金拨款500万美元;禁止种族歧视,批准所有重要的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sation)的协定,制定和解程序来推动土著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之间的谅解和合作;使得土著社会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目的进行联合。”[80]惠特拉姆的此番言论并非政治家取悦选民的一种政治诱饵,而是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以及对现实发展的考量而做出的一种情理皆合的承诺。因为忽视土著在澳大利亚历史中的独特地位并且听任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既不能避免土著通过各种途径或方式开展维权行动,也让澳大利亚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道义责任,给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与地位带来不利影响。[81]值得注意的是,惠特拉姆在讲话中首次提到了和解程序问题。[82]这说明“种族和解”不只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还是工党政府破解土著问题困局的良策以及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1973年2月8日,工党政府成立了以大法官A.E.伍德华德(A.E.Woodward)为专员的“土著土地权委员会”(Aboriginal Land Rights Commission)。该委员会的主要使命就是调查北领地区土著土地权纠纷以及就承认和给予土著土地权的路径提出具体建议。[83]伍德华德法官临危受命,他的调查范围被限定在北领地区,因为联邦政府在那里拥有直接管辖权。[84]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伍德华德向联邦政府提交了内容翔实的报告。报告不仅充分肯定了土地权之于土著社会在物质和精神生活层面的重要性,阐明了土著土地权问题的解决与促进一个更加广泛的澳大利亚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之间的重要关联,而且提出了给予土著土地权的具体策略或路径。
1974年7月2日,惠特拉姆宣布,联邦政府原则上接受伍德华德在最终报告中所提出的一些主要建议,并且授权有关部门进行立法。[85]但是,这一建议立马遭到乡村党的反对,也引发白人对工党政府的土著政策的强烈不满。[86]1975年10月,根据伍德华德报告拟定的《土著土地权议案》(Aboriginal Land Rights Bill)由土著事务部长莱斯·约翰逊(Les Johnson)提交给联邦议会讨论。约翰逊在申明这部议案的意义时说:“在土著事务领域,这无疑是迄今为止提交给联邦议会最重要的立法。”[87]然而,该立法议案在当年联邦议会参议院被搁置待议,原因是反对党因工党政府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案未获议会通过而提出不信任案,工党政府的任期提前结束了。[88]
工党政府的意外折戟,使得土著土地权议案未能走完最后一程,令人遗憾,但不能因此而低估这部提案的意义与影响。
首先,这是联邦层面首次尝试对土著土地权进行立法。这一方面说明土著土地权问题开始在联邦政治议程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另一方面印证了工党政府是在切实履行1967年全民公决的精神。从土著在立法中的地位来看,他们第一次在联邦层面成为立法的保护对象,也因此由澳大利亚社会备受歧视的“他者”变成由政府提供某种程度保护的“我者”。这一法律身份的变化使得处于弱势一方的土著在种族和解中有了政治层面的对等意义。正如克里斯托弗·斯韦尼(Christopher Sweeney)所言:“从法律和心理来看,第一次给予土地权的方案将会是一个主要步骤。”[89]
其次,该议案在实现北领地区的土著对土地权的诉求方面还是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因为这部议案在两种法律制度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并为北领地区的土著获取土地提供了基础。1975年11月,重回执政宝座的自由党联盟在本质上并不反对土著土地权法议案,只是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做了修改。这说明在土著土地权问题上,两党共识基本形成。[90]1976年12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总督正式签署了《土著土地权(北领地区)法》(Aboriginal Land Rights(NT)Act)。次年1月26日,该法正式生效。[91]当土地被视为“土著族群意识的一个重要象征,以及与古老的传统、值得尊敬的和令人自豪的历史保持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92]时,颁布这部法律的意义就不证自明了。对于北领地区的土著来说,一个最实际的成果就是获得了国家对他们土地权益承认的一个程序,并且据此拥有部分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无疑是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的一个非凡事件或重要成果。
第三,北领地区的土地权立法议案具有由点及面的推广意义。在惠特拉姆政府的工作计划中,北领地区只是一个先行试验区,这项计划最终惠及全国才是他的政府的理想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战略抱负。马尔科姆·弗雷泽时期,在《土著土地权(北领地区)法》的影响之下,其他各州在解决当地土著土地权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93]这就为出台一部全国性的土著土地权法律铺展了必要的基础。鲍勃·霍克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发起了全国土著土地权立法工作,并且认为土著拥有对其土地不可分割的自由持有权。[94]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权立法运动因种种原因而夭折,联邦政府只得通过其他举措把部分土地所有权给予其传统所有者。[95]迨至保罗·基廷时期,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土著土地权法》(Native Title Act)终于问世,[96]而约翰·霍华德(1996—2007年在任)政府于1998年又对《土著土地权法》进行了修订。这说明由戈夫·惠特拉姆政府所启动的土著土地权立法工作受到了其后历届政府的持续关注。
总之,在惠特拉姆政府之前,土著拥有土地权益是一个联邦成立以来历届政府从未予以重视的问题,更枉谈从法律层面建章立规。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土著土地权立法是一个既激进又务实的举措,因为工党政府在此方面所做的有益探索让后任政府在土著土地权方面都不敢掉以轻心,并且使土地权问题一直成为联邦政府一项主要的政治议程以及澳大利亚种族和解进程中的一个焦点,[97]这委实是惠特拉姆政府所开创的土著土地权立法工作的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之所在。
结束语
土著问题是澳大利亚社会长期存在的一个难题,种族和解是破解土著问题的一个路径或战略目标。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党政府时期之所以被视为澳大利亚种族和解的起点,是因为这一时期出台的关涉土著权益的诸多法律、政策或措施具有转折性和指向性意义。不过,由于土著问题积久年深且又复杂敏感,这一时期的土著政策或措施虽具有改革甚至革命性特征,但种族和解的理念及其实践活动仍处在探索阶段。
所谓的转折性意义是相对于以前历届政府所持的冥顽不化的土著政策而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工党政府责无旁贷地为土著承担立法之责。1967年全民公决前,联邦宪法并没有把有关土著事务的立法权赋予联邦政府,换言之,为土著立法是州或领地政府的事务。全民公决的结果正式宣告联邦宪法有关土著的歧视性条款成为历史,联邦政府也因此在理论上由一个土著事务的旁观者变成土著事务的管理者和立法者。但自由党联合政府均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角色变化。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1966—1967年在任)总理甚至做出这样的辩解:“联邦现在处在一个制定法律和容易与州发生冲突的位置,联邦并不寻求不必要地闯入这个领域,或介入一般由州处理的活动领域。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同,土著需求差异大。正因为如此,如果使土著管理工作行之有效,那么它就得以地区或州为基础。”[98]显而易见,此时的自由党联合政府是不准备承担管理土著事务责任的,而与时俱进的工党政府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性机遇。[99]保罗·哈斯拉克(Paul Hasluck)总督在1973年联邦议会开幕式上对土著事务管理机制的上述转变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他说:“我的政府承认澳大利亚土著人民遭受了最严重的社会不公、贫困和健康问题。在努力消除这个国家这方面的耻辱时,我的顾问们寻求与州政府合作。然而,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州政府或州机构去阻挠澳大利亚人民的清晰愿望,这一愿望在1967年全民公决压倒一切的表决结果中得到了体现,即国家政府应该为土著及托雷斯海峡岛民承担宪法责任。在主张和建立在此方面的全国意愿时,我的顾问们在使用澳大利亚人民所赋予的这些充分的宪法权力时不会踌躇不决。”[100]如果说1967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在理论上提供了联邦政府管理土著事务的权力,那么惠特拉姆政府不仅在决策理念中认识到了联邦政府插手土著事务管理的重要性[101],而且在实践中找到了联邦统筹土著事务的有效路径或方式。这是澳大利亚土著事务管理以及土著政策制定的一次重要转向。二是将种族平等的理念注入土著政策的拟定之中。此前连续执政二十余年的自由党联合政府将“白澳政策”视为治国之圭臬,把维护澳大利亚白人国家的纯洁性视为己任。通过一系列歧视性的法律、政策或措施,一方面尽可能地同化土著,另一方面使土著问题变得无足轻重。但工党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废除了“白澳政策”,把土著问题纳入多元文化社会建设的轨道,而且把发展土著教育、保护土著文化以及解决土著实际生活问题当作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且取得了方方面面的成就。[102]正如1973年2月惠特拉姆对一些土著代表所展望的那样:“如果我的政府有一个高于一切的抱负,如果有一项我希望应该被铭记的成就,如果有一项未来的历史学家向我们致意的事业,那就是:我所领导的政府消除了我们国家荣誉的一个污点,还土著人民以公正与平等。”[103]
而指向性意义预示这一时期的土著政策对后世的影响。澳大利亚是一个政党制国家。政党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所有党派尤其是主要党派在一些重要或棘手问题上并非一个声音说话。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种族关系史的演进表明,尽管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及其联盟在国家治理的很多问题上的立场往往南辕北辙,但在土著问题尤其是种族和解问题上的立场通常是共见大于分歧。[104]具体来说,无论是工党或是自由党联盟,它们都不再遮掩或回避土著问题,都支持白人与土著实现持久和解,均认识到种族和解之于澳大利亚国家或民族认同以及澳大利亚在国际社会地位的提升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在与种族和解有关的很多政策领域,比如土著事务咨询机构的建立、土著土地所有权立法的出台以及检视和落实《种族歧视法》等方面,历届政府在立场与政策方面保持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或连续性。[105]这说明由“土著问题”或“种族问题”演化而来的种族和解问题已在澳大利亚高层政治中形成较广泛的共识。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党政府为解决土著问题找到了一条正确之径。所以,贝恩·阿特伍德(Bain Attwood)和安德鲁·马库斯(Andrew Markus)认为,1972年,“以戈夫·惠特拉姆为首的澳大利亚工党赢得选举是土著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接下来承诺在他们的土著政治途径中进行主要变革的连续几届联邦政府中的首届”[106]。无独有偶,克莱姆·劳伊德(Clem Lloyd)也给予类似评价:“惠特拉姆为日后十多年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规划了政治和政策议程。”[107]
既然20世纪70年代初的工党政府开启了种族和解进程,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鲜明的印记:一是种族和解的概念尽管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实施路径,但基本上还是被包容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或理念之中。换言之,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是“白澳政策”废除后工党政府的一项主要的现实任务,种族和解是在这一背景下衍生出的一个概念或理念,但有其独特的政治内涵和实践维度。二是这一时期工党政府的土著政策或措施主要还是基于长期延续下来的“土著问题”而提出来的,并不涉及种族和解事业中的一个本质性问题,即土著在澳大利亚宪法中的地位。这无疑是惠特拉姆政府较为顺利地出台很多有关土著事务的政策或措施的原因之一。三是工党的土著政策既遭到在野党和既得利益阶层不同程度的反对,有时也会引起土著社会的不满。前者的反对是在意料之中,因为他们当中谁也不愿意既得权益受损;而后者的不满也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工党的土著政策让身处绝境中的土著看到了希望,而失望与希望总是相伴相随。[108]上述方面的特点既应和了种族和解处于起始阶段的历史本质,又反映出种族和解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这是我们在界定、认识和剖析澳大利亚种族和解的起点时必须予以注意的问题。
(原载《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
[1] 汪诗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授。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60年代,为了让混血土著孩子尽快同化到澳大利亚社会,一些州或领地政府差人把他们从其父母身边强行带走,并把这些孩子放在欧洲人居住区的孤儿院或白人家中抚养。有人估计,这一期间澳大利亚全境约有1/4的土著孩子被偷走。参见Peter Read,A Rape of the Soul so Profound-The Return of the Stolen Generations,Allen & Unwin,1999,pp.ix-xi;Richard Broome,Aboriginal Australians:A History since 1788,Allen & Unwin,2010,p.215;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8 October 1996,p.5945.
[3] 陆克文说:“对于被偷的一代,作为澳大利亚总理,我要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政府,我说声对不起;代表澳大利亚议会,我说声对不起。”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13 February 2008,p.170.
[4] 韩锋:《从澳大利亚总理向土著人致歉说开去》,《中国民族报》2008年2月22日;李辉:《陆克文道歉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2月16日;汪诗明:《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向土著居民致歉的原因探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汪诗明:《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道歉与种族和解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汪诗明:《论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向“被偷的一代”表示道歉的路径选择》,《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等等。
[5] 很少有学者对“白澳政策”表示异议。从1901年《移民限制法》(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的通过到1962年“移民改革小组”(Immigration Reform Group)出版《移民:种族控制或种族歧视?》(Immigration:Control or Colour Bar?)期间,只有两本著作对“白澳政策”持批评态度,它们是E.W.科尔(E.W.Cole)的《白澳是不可能的》(White Australia Impossible)和E.W.弗克萨尔(E.W.Foxall)的《种族恐惧症:白澳谬误的暴露》(Colorphobia:An Exposure of the White Australia Fallacy)。参见David Walker,“Race Building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White Australia”,in Laksiri Jayasuriya,David Walker and Jan Gothard,eds.,Legacies of White Australia,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2003,p.33.
[6] Will Sanders,“Indigenous 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A Review”,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ume 50,Number 4,December 2015,pp.679-680.
[7] Jennifer Sabbioni,Kay Schaffer and Sidonie Smith,eds.,Indigenous Australian Voices:A Reader,Rutgers Unversity Press,1998;Peter Read,A Rape of the Soul so Profound-The Return of the Stolen Generations;Michael Gordon,Reconciliation-A Jour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2001.
[8] 政治家演讲稿有保罗·基廷(Paul Keating)的“雷迪芬公园演讲”(“The Redfern Park Speech”)、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实际的和解”(“Practical Reconciliation”)等;主要论文成果有迪昂·芒迪耐(Djon Mundine)的“协商共存”(“Negotiating Co-existence”)、迈妮萨·卡斯坦(Melissa Castan)的“和解、法律和宪法”(“Reconciliation,Law and the Constitution”)、古斯塔夫·诺萨尔(Gustav Nossal)的“种族和解潮流中的象征主义与物质”(“Symbolism and Substance in the Surge Towards Reconciliation”)和P.P.麦吉尼斯(P.P.McGuinness)的“种族和解是一个双向道”(“Reconciliation is a Two-way Street”)等。参见Michelle Grattan,ed.,Essays on Australian Reconciliation,Bookman Press Pty Ltd.,2000.
[9] Damien Short,Reconciliation and Colonial Power-Indigenous Rights in Australia,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8,pp.31-86.
[10] Peter H.Russell,Recognizing Aboriginal Title-The Mabo Case and Indigenous Resistance to English-Settler Colonialism,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rated,2005.
[11]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15 November 1901,pp.7331-7362;A.T.Yarwood,ed.,Attitudes to non-European Immigration,Cassell Australia,1968,pp.70-101.
[12] Paul R.Wilson,Immigrants and Politic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3,pp.1-2;Statutory Rules from 1901 to 1927 Made under Commonwealth Acts and in Force on 31st December,1927,Vol II,The Govern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1927,pp.1609-1621.
[13] Donald Horne,The Lucky Country,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64,pp.124-126.
[14]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5 September 1973,p.1453.
[15] 杨洪贵:《澳大利亚对混血土著的“血统改造”》,《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7—133页。
[16] “Representations by the Australian Board of Missions re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for Aborigines”,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A):A452,1962/7391,p.9;Craig McGregor,Profile of Australia,Hodder and Stoughton,1966,p.299.
[17] Malcolm Fraser,Common Ground-Issues that should Bind and not Divide Us,Penguin Books,2003,pp.196-197.
[18] Stuart Macintyre,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44.
[19] Bain Attwood and Andrew Markus,The Struggle for Aboriginal Rights-A Documentary History,Allen & Unwin,1999,pp.58-59.
[20] 汪诗明、王艳芬:《1920—1960年代澳大利亚土著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第91—93页。
[21] 联邦宪法中有两处涉及土著的条款,均是歧视性的。宪法第51条第26款规定:“为了维护澳大利亚联邦的和平、秩序以及良好的管理,联邦议会将依据宪法拥有对各州除土著以外的任何种族的居民制定特别法律的权利,而这被认为是有必要的”;宪法第127条规定:“在统计联邦或州或联邦其他地方的人口时,土著居民不得计算在内。” 参见“Referendum,1967:Constitution-Writ”,NAA:A406,E1967/30 PART B,p.42.
[22] “Referendum,1967:Constitution-Referendum Results and General Returns”,NAA:A406,E1967/30 PART K,pp.1-50.
[23] Donald Horne,The Lucky Country,p.127.
[24] Adam Jamrozik,Cathy Boland and Robert Urquhart,Social Chang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ustra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95;Phillip Lynch,“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in Hew Roberts,ed.,Australia's Immigration Policy,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1976,pp.4-7.
[25] Harold Throssell,“A Black Upsurge Down Under?”,Guardian,Oct.2,1973.
[26] Julian Burger,Aborigines Today,Anti-Slavery Soceity,1988,pp.17-20.
[27]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15 August 1972,p.6.
[28] William W.Bostock,Alternatives of Ethnicity-Immigrants and Aborigines in Anglo-Saxon Australia,Corvus Publishers,1981,p.93.
[29] Phillip Knightley,Australia:A Biography of a Nation,Jonathan Cape,2000,p.267.
[30] Charles A.Price,“Overseas Migration to Australia:1947-1970”,Migration Today,Number 16,Autumn 1970,pp.38-47.
[31] Laksiri Jayasuriya,“Multiculturalism and Pluralism in Australia”,in Richard Nile,ed.,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Race in Australia and Britain,University of London,1991,pp.82-97.
[32] Mark Lopez,The Origins of Multiculturalism in Australian Politics 1945-1975,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0,p.3.
[33] 澳大利亚著名人类学家W.E.H.斯坦内(W.E.H.Stanner)认为,土著在澳大利亚大陆生活有一万年的历史;著名历史学家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认为有三万年的历史,而较为一致的看法则是四万年。参见 Max Griffiths,Aboriginal Affairs-A Short History,Kangaroo Press,1995,p.12.
[34] Charles Perkins,“Self-Determination and Managing the Future”,in Christine Fletcher,ed.,Aboriginal Self-Determination,Aboriginal Studies Press,1994,p.37.
[35]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13 November 1979,p.2181.
[36] John L.Sherwood,“International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in Margarita Bowen,ed.,Australia 2000:The Ethnic Impact,The University of New England,1976,p.57.
[37] A.J.Grassby,A Multi-Cultural Society for the Future,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3,p.4.
[38] Robert Trumbull,“Australia Acts to Save Aboriginal Culture”,New York Times,Dec 15,1972.
[39] Prime Minister,“Responsibility for Aboriginal Education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Press Statement,No.51,12 February 1973,p.1.
[40] 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Th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Aborigines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ir Sacred Sites:Second Progress Report from the Senate Standing Committee on Social Environment,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74,pp.10-16.
[41] 该委员会于1972年8月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调查包括土著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的贫困状况。
[42] “1974/1975 Aboriginal Affairs Program-Decision 2517”,NAA:A5915,1197,p.2.
[43] “Aborigin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Welfare Activities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Decision 2871(WEL)and 2911”,NAA:A5915,1342,p.2.
[44] 一是住房协会方案。该方案允许土著社区在使用部门拨款方面可以制定自己的预算。二是发放住房贷款。政府根据土著的个人住房建设或修缮申请,给予申请人一定的低息贷款。三是土著旅社计划。1973年6月,作为一项旨在为土著提供紧急住房之需的公用事业,政府建立了“土著旅社有限公司”(Aboriginal Hostels Ltd)。至1975年末,该公司修建旅馆74个,提供床位1677个。参见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Penguin Books of Australia Ltd,1985,p.473.
[45] Official Year Book of Australia,No.61,1975 and 1976,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1976,p.1085;Damien Short,Reconciliation and Colonial Power-Indigenous Rights in Australia,pp.156-157.
[46] “National Aborigi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Decision 1479,1508(WEL)and 1525”,NAA:A5915,690,p.5.
[47]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Aborigi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Submission No.690)”,NAA:A5931,CL782,p.26.
[48] “Aboriginals and Society”,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the Hon.E.G.Whitlam,Q.C.,M.P.,Circulated to a Conference of Commonwealth and State Ministers Concerned with Aboriginal Affairs in Adelaide,Press Statement,No.74,6 April 1973,p.1.
[49]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Aborigi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ubmission No.690 refers]”,NAA:A5931,CL782,p.8.
[50]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468.
[51] Bain Attwood and Andrew Markus,The Struggles for Aboriginal Rigths-A Documentary History,pp.239-240.
[52]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p.467-468.
[53] Robert Trumbull,“Aborigines Begin Vote in Australia:Poll's Justness Disputed Estimate”,New York Times,Nov.25,1973.
[54] “PM to Speak on Aboriginal Part”,Sydney Morning Herald,November 23,1973.
[55] Press Release by Senator The Hon.J.L.Cavanagh,Comments Concerning the Declaration of the N.A.A.C Poll on 13/12/73,Canberra,12 December 1973.
[56] “Department of Aboriginal Affairs Funds for National Aboriginal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Departmental Consultations with Aboriginals Decision 2515”,NAA:A5915,1190,p.2.
[57]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468.
[58] 查尔斯·帕金斯(Charles Perkins)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土著社会活动家。
[59]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11 July 1974,p.79.
[60] Press Release by Senator The Hon.J.L.Cavanagh,Comments Concerning the Declaration of the N.A.A.C Poll on 13 /12 /73,Canberra,December 12,1973.
[61] 为推动土著对其事务的自我管理,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 Fraser,1975—1983年在位)政府加快了北领地区自治条例的拟定进程。1978年7月1日,《北领地区自治条例》(Northern Territory Self-Government Act)终于问世。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 June 1978,pp.3029-3057.
[62] Kenneth Randall,“Aboriginal Official in ‘Racist Storm’”,Guardian,Feb.25,1974;“Future of Aboriginal Council in Doubt”,Sydney Morning Herald,February 11 1974.
[63]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4 March 1977,p.578.
[64]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8 May 1990,p.25;Lois O'Donoghue,“Keynote Address:Australian Govern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in Christine Fletcher,ed.,Aboriginal Self-Determination,pp.10-11.
[65] Margaret Bowman & Michelle Grattan,Reformers-Shaping Australian Soceity from the 60s to the 80s,Collins Dove,1989,p.22.
[66]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31 October 1974,pp.2192-2193.
[67] 1965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69年6月4日生效。澳大利亚于1966年10月13日在该公约上签字,但是,自由党连续三任政府都没有批准该公约。参见Gough Whitlam,“Human Rights in One Nation:The Keating Government and the Whitlam Legacy”,in Hugh Emy,Owen Hughes and Race Mathews,eds.,Whitlam Re-visited:Policy Development,Policies and Outcomes,Pluto Press Australia limited,1993,p.120.
[68]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22 May 1975,p.1793.
[69] 《种族歧视法》的核心内容是第9条第(1)款。该条款对“种族歧视”做了如下界定:若有下列行为,就是不合法的:“当一个人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而施行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是取消或损害政治、经济、社会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行使。”参见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An Act Relating to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and Other Discrimination)”,NAA:A1559,1975/52,p.9.
[70]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 1972-1975,pp.505-506.
[71] Jocelynne A.Scutt,“Revisiting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 1975:Precision,Scope and the 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Subverted”,in Jenny Hocking and Colleen Lewis,eds.,It's Time Again-Whitlam and Modern Labor,Melbourne Publishing Group,2003,pp.115-116.
[72] 汪诗明:《论鲍勃·霍克政府对土著监禁致死的调查》,《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74—181页。
[73]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28 November 1986,pp.2972-2973.
[74]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8 October 1996,p.5944.
[75] 为解决北领地区儿童受虐问题,2007年8月,自由党政府采取了一揽子“干预政策”(intervention)。为了使这一计划付诸实施,联邦政府中止了《种族歧视法》在北领地区的实施。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14 August 2007,pp.41-78.
[76] 在多方压力之下,2010年6月21日,联邦议会通过了恢复《种族歧视法》的修正案。修正案意味着《种族歧视法》不再被中止,但又规定,限制利用《种族歧视法》去挑战联邦政府在北领地区的各种政策或措施。参见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The Senate),Hansard,21 June 2010,p.3634.
[77] Gordon Briscoe,“The Origins of Aboriginal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Aboriginal Embassy,1907-1972”,in Gary Foley,Andrew Schaap and Edwina Howell,eds.,The Aboriginal Tent Embassy-Sovereignty,Black Power,Land Rights and the State,Routledge,2014,p.51.
[78] Fay Gale,Urban Aborigin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72,pp.56-57.
[79] Robert Trumbull,“Aborigines in Australia Given New Land Rights”,New York Times,Jan 26,1972.
[80]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p.466.
[81] Paul Keating,Engagement:Australia Faces the Aisa-Pacific,Pan Macmillan Australia Pty Ltd.,2000,pp.264-266.
[82] 1968年,澳大利亚主教会议建立了“天主教公平与和平委员会”(Catholic Commission for Justice and Peace)。该委员会对土著在澳大利亚社会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关注,并且倡导种族和解。在多米尼克·奥·沙利文看来,“对于教会来说,虽然和解是一个宗教概念,但其一般原则作为可能的政治方案的基础已经变得重要起来。”参见Dominic O'Sullivan,Faith,Politics and Reconciliation-Cathol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ndigeneity,Huia Publishers,2005,p.143.
[83] Robert Trumbull,“Rulling that Land isn't Theirs Angers Australia Tribe”,New York Times,May 8,1971.
[84]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5 November 1910,pp.6875-6876.
[85] Prime Minister,“New Land Deal for Northern Territory Aboriginals”,Press Statement,No.281,2 July 1974.
[86] Kenneth Randall,“Whitlam Backs Aboriginal Land Reform”,Guardian,May 9,1974.
[87]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16 October 1975,pp.2222-2223.
[88] Gough Whitlam,The Truth of the Matter,Penguin Books Ltd,1979;Paul Kelly,The Unmaking of Gough,Angus & Robertson Publishers,1976,p.346.
[89] Christopher Sweeney,“Aborigines may Get Rich Lands”,Washington Post,Dec.1,1974.
[90] Tim Rowse,Indigenous and Other Australians since 1901,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2017,p.296.
[91] 汪诗明:《论〈土著土地权(北领地区)法〉的颁布》,《史学集刊》2018年第6期,第98—108页。
[92] Bain Attwood and Andrew Markus,The Struggles for Aboriginal Rigths-A Documentary History,p.229.
[93] “Aboriginal Land Rights”,Sydney Morning Herald,May 9,1978.
[94] Amanda Buckley,“Canberra Set for War over Landrights”,Sydney Morning Herald,December 9,1983.
[95] Bob Hawke,The Hawke Memoirs,William Heinemann Australia,1994,pp.592-593.
[96] 汪诗明:《“马宝裁定”与澳大利亚土著土地权立法》,《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171—174页。
[97] Verge Blunden,“NT Land Rights Claim Challenged”,Sydney Morning Herald,June 16,1982.
[98] Margaret Ann Frankin,Black and White Australians,Heinemann Educational Australia Pty Ltd,1976.
[99] Keith McConnochie,David Hollinsworth and Jan Pettman,Race and Racism in Australia,Social Science Press,1988,p.142.
[100]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7 February 1973,p.14.
[101] 惠特拉姆本人在1972年曾这样精确地自我描述:“我在工党内的角色是一位改革者……我的风格是渐进的,我的本质是最革命的……我是这届议会中第一位提议联邦政府行动在处理所有国内事务中有着重要意义的议员。”参见Margaret Bowman & Michelle Grattan,Reformers-Shaping Australian Socieity from the 60s to the 80s,p.18.
[102] Helen Friedman and Harold Friedman,“For Australia's Aborigines,a Better Life”,New York Times,Oct 22,1977.
[103] Gough Whitlam,The Whitlam Government,1972-1975,p.468.
[104]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25 August 1988,pp.402-405.
[105]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Hansard,8 May 1990,p.25.
[106] Bain Attwood and Andrew Markus,The Struggle for Aboriginal Rights:A Documentary History,p.276.
[107] Clem Lloyd,“Edward Gough Whitlam”,in Michelle Grattan,ed.,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s,New Holland Publishers(Australia),2000,p.325.
[108] Harold Throssell,“Black Doubt Whitlam”,Guardian,Nov.14,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