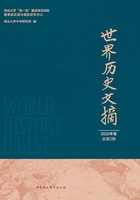
麝香之路:7—10世纪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
沈琛[1]
摘要:本文通过对伊斯兰史料与藏汉文史料的梳理,结合青藏高原的考古发现,对吐蕃与中亚的商贸往来进行研究。吐蕃输往中亚的商品主要是麝香,因而这条商路又被称为麝香之路。动物皮毛、盾牌、盔甲、金银器等吐蕃商品也在伊斯兰世界非常知名。中亚输往吐蕃的商品包括金银器、织锦、香料等。吐蕃与中亚贸易路线主要有海上和陆上两条,前者须通过西北印度到达印度洋港口提 ,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陆路经拉达克、大小勃律,经大食之门到达呼罗珊、粟特、阿拉伯。粟特商人、大食商人、犹太商人都曾活跃于麝香之路上。
,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陆路经拉达克、大小勃律,经大食之门到达呼罗珊、粟特、阿拉伯。粟特商人、大食商人、犹太商人都曾活跃于麝香之路上。
关键词:麝香之路 吐蕃 大食 粟特
关于吐蕃与中亚的贸易往来,伊斯兰史料中保存了诸多史料,但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白桂思在《吐蕃与欧亚大陆中世纪早期的繁荣——吐蕃经济史初探》一文中对吐蕃与东西方的贸易进行了简要梳理[2],张云先生在《丝路文化:吐蕃卷》一书中专辟一章对吐蕃与中亚的经济与文化交流进行讨论[3]。麝香在吐蕃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Anna Akasoy等人将吐蕃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交流路线概括为麝香之路,并且将其视为丝绸之路的支线[4],我们也遵从这一作法。总体来看,关于吐蕃麝香之路的研究还很薄弱。近年来,更多伊斯兰史料得到翻译,新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不少实物的证据,通过结合各语言文献与考古发现进行研究,可以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以下笔者将从吐蕃进出口商品、商人及路线等方面对吐蕃的麝香之路进行探讨。错谬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吐蕃输往中亚的商品
吐蕃对外出口的主要物品有麝香、动物皮毛、犀牛角、盾牌、盔甲等。《世界境域志》对于吐蕃各地物产与贸易的记载最为详细,“吐蕃有金矿,并出产大量麝香、黑狐、灰狐、黑貂、银鼠与犀牛角”[5]。其中麝香、锁子甲与吐蕃盾牌知名度较高,11世纪以后的伊斯兰史书《珍宝与稀奇之书》称6世纪萨珊波斯库思老一世筑成达班特(Darband)长城时,曾收到来自吐蕃、中国和印度西部国王的贺礼。吐蕃可汗进贡了100件铠甲、100件镀金圆盾、4000囊麝香[6]。这一记录当然不可靠,6世纪雅隆河谷的吐蕃文明尚在形成阶段,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但是这反映了后期吐蕃麝香、铠甲、盾牌在伊斯兰世界的声誉。以下对这三种典型的吐蕃产品进行简要梳理。
(一)麝香
关于吐蕃的麝香贸易,学界关注不少[7],Anya H.King所著的《天国花园之香:麝香与中古伊斯兰世界》一书更是对吐蕃与伊斯兰麝香和香料贸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8],我们仅作简要交代。
在伊斯兰史料中,吐蕃常常被描述为麝香之国。例如928年左右成书的古达玛(Abu'l-Faraj Qudāmah b.Ja‘far)的《税册及其编写》记载,亚历山大东征时,吐蕃人曾经送给亚历山大4000维格尔(Wiqr)的赤金和麝香[9],虽然这是出于杜撰,但能够反映黄金和麝香在吐蕃对外商品输出中的地位。
311年左右的粟特文古信札2中提到粟特人往撒马尔罕贩卖的商品中就包括了大宗的麝香,这是最早的关于麝香长途贸易的记录[10]。5—6世纪时,麝香已经在萨珊波斯广为人知,这一时期麝香由波斯湾传入阿拉伯地区。约在4—5世纪的笈多王朝,印度也开始使用麝香。大食的征服战争推动了物质文化的交流,麝香、樟脑、龙涎香等香料开始大量传入近东地区[11]。
麝香最早被认为产自印度,最晚到9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已经认识到麝香产自吐蕃和中国,黑衣大食的宫廷御医伊本·马萨瓦(Ibn Māsawayh,777-857)在他的文章《基本的香料》(Kitab jawāhir al-tib al-mufrad)中对于麝香有明确的记载,在这篇文章中,他将麝香列为五种主要香料之首,其他四种是龙涎香、芦荟、樟脑和藏红花,详细介绍了麝香的产地、贸易路线:
麝香,根据其品质优劣有很多种,最好的是粟特麝香,从吐蕃运到粟特,被驮卖至其他地区。其次是印度麝香,从吐蕃运到印度,然后到达提 (al-Daybul),再通过海路运输,由于海上运输其品质劣于前者。还有中国麝香,由于在海上贮存的时间较长故其品质劣于印度麝香。也有可能其优劣差别是由于最初的草地不同之故。最好的麝香是产自于一种名为al-kandasa的草地中,分布于吐蕃或者箇失密。次优的是产自于调香师所用的甘松的草地上,分布于吐蕃。最次的产于名为“苦味”(murr)的草地上,这种植物的味道与其根部(aṣl)是麝香的味道,但此种麝香味道要更加燥烈[12]。
(al-Daybul),再通过海路运输,由于海上运输其品质劣于前者。还有中国麝香,由于在海上贮存的时间较长故其品质劣于印度麝香。也有可能其优劣差别是由于最初的草地不同之故。最好的麝香是产自于一种名为al-kandasa的草地中,分布于吐蕃或者箇失密。次优的是产自于调香师所用的甘松的草地上,分布于吐蕃。最次的产于名为“苦味”(murr)的草地上,这种植物的味道与其根部(aṣl)是麝香的味道,但此种麝香味道要更加燥烈[12]。
此外,文章中的次要香料之首为甘松,也主要来自于吐蕃,“次要香料。甘松,有许多种,最好的是印度甘松……这是一种从印度购来的草,它长于吐蕃的土地上”[13]。但是阿拉伯人对于麝香来源并不清楚,认为是采自瞪羚。我们可以由此确知吐蕃麝香销往西方的两种途径,其一是粟特商人从陆上运输,其二是经由印度的港口提 从海路运往中东与近东。
从海路运往中东与近东。
粟特商人在麝香的陆路贸易上的重要性也见载于其他地理学著作,10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al-Iṣṭakhrī)的《道里邦国书》(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提到:“粟特人拥有产自吐蕃和黠戛斯的麝香,从此地运往其他大都市。”[14]
1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人对吐蕃麝香的产地有了更清晰地认识,10世纪初的阿布·赛义德(Abū Zayd al-Sīrāfī)在《中国印度闻见录》(Akhbār al-Ṣīn wa-l-Hind)第2卷对吐蕃麝香的产地和采集方法做了清晰的说明:根据一位在中国经商的撒马尔罕麝香商人描述,汉地与吐蕃产麝香鹿之地毗邻,但吐蕃所产麝香质量更佳,有两个原因。一是两边麝香鹿的食材不同,吐蕃麝香鹿吃的是甘松,而汉地的麝香鹿以其他草木为食。其二,吐蕃人将麝香留在麝香鹿的腺囊之中,汉人则否,且汉地麝香自海路运输容易受潮变质。其质量稍逊。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学者失哈不丁·奴瓦叶里(Shihāb al-Dīn Ahmad bin' Abd al-Wahhāb al-Nuwayri,1279-1333)编著的百科全书《博雅技艺之终极目标》(Nihayat al-arab fī funūn al-adab)中引用了980年左右写成的《新娘的颜色与灵魂的芳香》(Jayb al-‘arūs wa-rayḥān al-nufūs)一书,其中提到:“麝香有很多种类,最好的麝香是产自于朵思麻(Dhū samt,即藏语‘mdo smad’的音译),然后被带到吐蕃,中间两个月路程,之后被运到呼罗珊(Khūrāsān)。”[15]
麝香作为吐蕃的主要商品,对于大量使用香料的大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通过海陆与陆路分别运往西方,这条麝香之路成为吐蕃与伊斯兰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渠道,由此产生了跨越帕米尔与喜马拉雅山的人员流动与知识交流,对于吐蕃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的意义重大。
(二)盔甲与盾牌
吐蕃的盔甲与盾牌不仅仅在唐蕃战场上令唐人生畏,也在伊斯兰世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据《塔巴里年代记》,苏禄在729年围攻卡玛尔加(Kamarju)时就是因为吐蕃锁子甲而得以在大食射手的近距离攻击中幸存。可见吐蕃锁子甲曾流入突骑施,并在战场上得到了检验。
《通典》明确记载:“(吐蕃)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弓矢弱而甲坚。”[16]关于吐蕃的盔甲的来源,劳费尔最先指出,吐蕃的锁子甲应该是从波斯传来,吐蕃并未实现盔甲的本土制造[17]。戴密微分析了萨珊波斯的雕像与文献中的锁子甲的形制,将其与汉文史料、考古发现和敦煌壁画中的吐蕃铠甲进行比对,指出萨珊波斯的库思老二世(Khosrow II,590—628年在位)浮雕中的锁子甲与吐蕃锁子甲形制完全一致,皆用长条金属片竖排连缀而成、唯露双眼、人马俱披,确证吐蕃铠甲源自波斯。但他同时指出吐蕃的金属冶炼业十分发达,吐蕃在6—7世纪引进之后就能自行制造[18]。戴密微的这种看法是令人信服的,吐蕃向外界购买铠甲以支撑其数十万军队是不可想象的,《册府元龟》记载“(吐蕃)惟以淬砺为业,罕务耕耘”[19]。吐蕃曾向唐朝进贡金甲、金拂庐等形制奇异的冶金制品,也曾在南诏一带铸造漾濞铁桥、神川铁桥等难度极高的铁索桥,其冶炼技术是毋庸置疑的。《贤者喜宴》《西藏王统记》中记载吐蕃雅隆王国第8代赞普布代贡杰时茹莱杰( )“炼铁石为金、银、铜、铁”[20]。而《柱间史》则称是27代的赞普囊日松赞发现了金银铜铁[21],当然这些吐蕃先王的历史并不可靠,但吐蕃在雅隆河谷时已经学会了金属冶炼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炼铁石为金、银、铜、铁”[20]。而《柱间史》则称是27代的赞普囊日松赞发现了金银铜铁[21],当然这些吐蕃先王的历史并不可靠,但吐蕃在雅隆河谷时已经学会了金属冶炼技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弟吴宗教源流》记载松赞干布划分桂(军户)、庸(民户)之时(实际为禄东赞划分),庸户中包括六匠人( ):“舞者卡约、鞍匠噶如、弓匠瑟拉、箭匠览铄、铠甲匠甲瓦、画师宗次。”[22](
):“舞者卡约、鞍匠噶如、弓匠瑟拉、箭匠览铄、铠甲匠甲瓦、画师宗次。”[22](



 )[23]这里的六匠人之中铠甲匠与制造弓、箭、马鞍的匠人都是与作战有关,这体现了吐蕃手工业的优先发展方向,也印证吐蕃的兵器制造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在《弟吴宗教源流》等书中都提到了这一时期吐蕃征服的四个王,其中苏毗王被称为苏毗铁王(
)[23]这里的六匠人之中铠甲匠与制造弓、箭、马鞍的匠人都是与作战有关,这体现了吐蕃手工业的优先发展方向,也印证吐蕃的兵器制造技术是非常发达的。在《弟吴宗教源流》等书中都提到了这一时期吐蕃征服的四个王,其中苏毗王被称为苏毗铁王( )[24],说明苏毗是吐蕃重要的铁矿区。这一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2008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呷拉宗(
)[24],说明苏毗是吐蕃重要的铁矿区。这一记载也为考古发现所证实,2008年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呷拉宗( ,意为“铁匠铺”)遗址发现一座吐蕃时期的炼铁炉,其年代为7世纪,其自然鼓风的冶炼技术以及“竖井式”的炉型与汉地的冶炼技术有明显区别,应是源于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系经印度传入吐蕃东境[25]。该地应是属于吐蕃孙波茹的辖境,与“苏毗铁王”的记载可相印证。
,意为“铁匠铺”)遗址发现一座吐蕃时期的炼铁炉,其年代为7世纪,其自然鼓风的冶炼技术以及“竖井式”的炉型与汉地的冶炼技术有明显区别,应是源于南亚地区的斯里兰卡,系经印度传入吐蕃东境[25]。该地应是属于吐蕃孙波茹的辖境,与“苏毗铁王”的记载可相印证。
吐蕃的锁子甲一直延续到近代仍然继续使用,许多15—16世纪的吐蕃锁子甲保存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学者借此对吐蕃铠甲的制作工艺进行了更为详尽的研究[26]。吐蕃时期在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绘制的毗沙门天王像基本都是吐蕃铠甲武士的形象,郭里木墓地出土的吐蕃棺板画中也绘有披锁子甲的武士[27],结合近来古格等地出土的吐蕃盔甲,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直观和深入的认识[28]。
同样著名的还有吐蕃的盾牌,伊本·豪卡尔的《大地之形象》在988年写成,书中比喻布哈拉的城堡就像吐蕃盾牌一般[29]。伊本·法基赫(Ibn al-Faqīh)902年写成的《诸国志》两次提及吐蕃盾牌,列举世界各地的特产时就有吐蕃的盾牌[30],并且在叙述呼罗珊时说到,“在呼罗珊,人们可以获得各地的特产,包括吐蕃的麝香和皮革盾牌”[31]。汉藏文史料中对吐蕃盾牌的记载不多,刘元鼎出使吐蕃入赞普金帐时,“中有高台,环以宝楯。赞普坐帐中,以黄金饰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结朝霞冒首,佩金镂剑”[32]。布达拉宫中有吐蕃时期的武士铠甲、盾牌、枪等武器,系17世纪时仿制而成,可以一窥吐蕃时期武器装备的面貌[33]。
(三)金银器
众所周知,吐蕃有发达的金银器冶炼技术,除了向唐朝进贡大量的金银器之外,也作为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如吐蕃曾赠送南诏金印、金片告身等等。735年唐朝在葱岭抓获吐蕃潜通突骑施的使者,一同缴获还有“所送金银诸物”[34],突骑施可汗苏禄不知唐朝已经将其送还吐蕃,曾致书玄宗索要,张九龄代写的《(唐玄宗)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中云:“所有蕃书,具言物数。朕皆送还赞普,其中一物不留,可汗亦以此为词,谓言朕留此物。且蕃中贫薄,所见不广,银瓶、香子将作珍奇,黑毯、赤縻[35]亦为好物。我中国虽在贫下,固不以此为贵。”[36]这里的香子就是指麝香,黑毯应是狐皮或貂皮制成的毯子,“赤縻”不知何物,银瓶指的就是吐蕃的镀金银瓶,唐朝史料中称之为“银胡瓶”。
吐蕃的黄金为西方所熟知,《世界境域志》在总述吐蕃特产时首先提到“吐蕃有金矿”,在下文记述吐蕃各地的特产时,记载Rang rong(即象雄, ),“据说山上有金矿,山中发现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在记述N.zvān地方时云,“是吐蕃一个富足的地区,物产很多,该地有一部落名为Mayūl,吐蕃诸王皆出于此……物产很多,如黄金、皮毛、羊以及其他许多货物与用具”[37]。此处应该指拉达克一带的
),“据说山上有金矿,山中发现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在记述N.zvān地方时云,“是吐蕃一个富足的地区,物产很多,该地有一部落名为Mayūl,吐蕃诸王皆出于此……物产很多,如黄金、皮毛、羊以及其他许多货物与用具”[37]。此处应该指拉达克一带的 。吐蕃以金银为货币,以金银器作为最经常使用的国礼。吐蕃延请印度的法师寂护、莲花生等译师都是以黄金作为束脩。相传11世纪初古格国王益西沃为葛逻禄所绑架,要求吐蕃以等身金赎回[38]。
。吐蕃以金银为货币,以金银器作为最经常使用的国礼。吐蕃延请印度的法师寂护、莲花生等译师都是以黄金作为束脩。相传11世纪初古格国王益西沃为葛逻禄所绑架,要求吐蕃以等身金赎回[38]。
霍巍先生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对海内外现存的吐蕃金银器皿进行了梳理,是目前对吐蕃金银器最为全面的研究成果[39]。这些金银器的冶炼技术和纹样虽然受到了波斯、粟特乃至唐朝的强烈影响,但是许多都是在吐蕃制造。虽然学界对于大多数的吐蕃金银器的来源都有争议,但是有不少金银器都带有藏文铭文,包括金杯、镀金银杯、镀金银瓶、银盘、银箭筒等等,都可以确认为吐蕃所造[40]。但是目前尚未在中亚发现有藏文铭文的吐蕃金银器,吐蕃金银器的对外输出主要停留在贡赐贸易的层面,其规模并不大。
不难想见,吐蕃以金银器冶炼技术自豪,因此金银器与吐蕃特产麝香、皮毛等被作为国礼,送与唐、南诏、突骑施、葛逻禄、突厥乃至大食等政权,这种以吐蕃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是吐蕃对外贸易的重要补充。
二 中亚输往吐蕃的产品
吐蕃从西域进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包括金银器皿、波斯锦和青金石等。
(一)金银器
吐蕃金银器技术的发展受到了萨珊波斯与粟特系统金银器的诸多影响,尤其是在器型和纹饰上最为明显,这也使得判定吐蕃金银器的产地变得非常困难。吐蕃目前所发现的金银器绝大部分都不是通过正常的考古发掘所获,而是通过私人买卖流散于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这又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目前可以确定为粟特输入的金银器数量并不多,我们梳理如下:
1.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舍利容器的镀金银饰片。当时通行的镀金工艺有两种,一种是粟特的火镀金工艺,是将金箔捶揲在银表面,然后直接加热。另外一种称为汞镀金( ),其方法为溶解金粉于水银中,涂于器物表面,加热后水银挥发,后者为吐蕃常用的镀金方式[41]。吐蕃都兰墓地中出土的舍利容器的镀金银饰片正是用火镀金与捶揲法制作,其纹饰也与粟特金银器一致,许新国先生据此判定是粟特系统的金银器[42]。
),其方法为溶解金粉于水银中,涂于器物表面,加热后水银挥发,后者为吐蕃常用的镀金方式[41]。吐蕃都兰墓地中出土的舍利容器的镀金银饰片正是用火镀金与捶揲法制作,其纹饰也与粟特金银器一致,许新国先生据此判定是粟特系统的金银器[42]。
2.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金高足金杯。霍巍先生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一文中提到了这件金杯,“上为杯体,平面呈圆形,深腹,圜底,高足,高足的中部有‘算盘珠’式的节。口沿部在长方形的分格内饰动物纹样,腹饰缠枝花草,在缠枝纹样当中出现龙、独角兽等动物,柄部上方和器足上饰联珠纹样一周。展品说明文字称其出土地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代为吐蕃时期(7—8世纪)”,这件高足杯应是民间收购而来,其图片并未刊布,霍巍先生指出:“唐代发现的高足杯多为银器,而少见金器,此外从纹饰上看,过去见诸注录的唐代银高足杯常见的纹饰有忍冬纹、三角纹、联珠纹、葡萄纹、狩猎纹、缠枝纹等,而很少见到像这件金高足杯上的动物纹样。”因此他认为这件高足杯来自中亚[43]。
3.日本东京古代东方博物馆藏的银碗。碗身有纹饰,包括六个几乎全裸的男人,三人持酒壶与碗,三个为仆人,中间以树隔开,枝头为孵雏之鸟与觊觎之蛇,碗底有水波纹与鱼纹。该银碗原系英国的David Snellgrove教授1961年在伦敦从原居拉萨的西藏上层家族获得,1985年拍卖给了日本东京古代东方博物馆[44]。Denwood曾对这件银碗的纹饰进行研究,指出该银碗的纹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情节,即奥德修斯所讲述的祭神时蛇吞食麻雀的预言[45],其水波纹与鱼纹则体现了萨珊波斯风格,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件产于巴克特里亚的银碗,7世纪时传入吐蕃[46],这一观点被其他学者所接受[47]。
4.另外一件是拉萨大昭寺的银壶。纹饰部分有鎏金痕迹,其上有胡人醉酒和反弹琵琶纹饰。对于其产地,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宿白先生根据器型和纹饰认为:“估计此银壶约是7—9世纪阿姆河流域南迄呼罗珊以西地区所制作。其传入拉萨,或经今新疆、青海区域;或由克什米尔、阿里一线。”[48]而阿米·海勒(Amy Heller)认为这件银壶是由吐蕃人制造,其纹饰虽为胡人,服饰却与吐蕃服饰类似,反弹琵琶则是唐朝特点,因此认为这件银壶融合了粟特、汉式与吐蕃的纹饰特点,与其他吐蕃金银容器一样,皆是由吐蕃人自行制造,其年代应为7世纪晚期到9世纪中期[49]。霍巍先生则指出该胡人醉酒图与青海郭里木棺板画上的吐蕃人醉酒图题材相同,因此认为其为“当时吐蕃人饮酒风俗的真实写照”,强调“它是由吐蕃人按照自身所习惯的生活方式自行设计、创作的这种可能性”[50]。这件银壶具有浓厚的西域色彩,根据目前的证据,仍然无法排除其出自于西域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仍然将其附列于此。
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中的射牛图中“有1人执壶,1人手捧盘子,盘中置有银杯3只”,许新国先生认为图中的壶“上端直接交在口上,颈部短粗,圈足粗矮,而且没有节状装饰,形制更接近粟特的产品,时代也相吻合,因此应是粟特银器”。对于盘中的高足杯,他认为与李静训墓、何家村出土的金银高足杯形制类似,应是源出拜占庭,但也有可能是通过萨珊波斯输入吐蕃的[51]。
(二)织锦
吐蕃本土的衣料主要是麻布和皮毛,“衣率毡韦”[52],“俗养牛羊,兼取毛为褐而衣焉”[53]。虽然吐蕃占领了河西与于阗,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掌握养蚕缫丝的技术[54]。但随着吐蕃对外交流的增加,唐朝与中亚丝绸贸易的盛行,也影响到了吐蕃,《通典》谓吐蕃“重汉缯而贵瑟瑟”[55],丝绸不仅成为吐蕃贵族的常用服饰面料,也成为吐蕃佛事活动中重要的装饰品[56],丝绸在吐蕃日益流行。
敦煌汉文文献中曾经出现“番锦”一词,吐蕃、归义军时期皆有出现,明显是一种贵重的丝绸,且经常用作丝织物的缘饰,姜伯勤先生提出有两种可能:“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的锦或沙州丝绵部落中吐蕃人主持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他又指出唐五代“番”字不仅仅指吐蕃,因此“‘番锦’也可能是‘胡锦’的同义词,即指周边部族制锦,有时也包括外国锦”[57]。吐蕃本土不产锦,敦煌文书中用“蕃”字称吐蕃较为常见,用“番”字者较少。而且敦煌文书P.2613中已经明确记载一件番锦的纹饰类似于联珠对狮锦[58],这里的番锦应该就是指“胡锦”,亦即中亚粟特或波斯所产之锦[59]。有的学者将番锦理解为“吐蕃番锦”,认为是阿拉伯占领中亚之后粟特人在吐蕃本土建立了丝织业,番锦即在吐蕃本土生产的丝绸[60],显然缺乏依据。
6—8世纪,源于萨珊波斯的联珠纹锦服饰风行欧亚大陆,东至日本,西至埃及,吐蕃也不例外。在7世纪初期,联珠纹锦就已经在吐蕃非常流行,《步辇图》中禄东赞即身穿紫红底连珠鸟纹团花长袍[61]。郭里木吐蕃棺板画上不少吐蕃贵族所穿的衣服都以联珠纹锦装饰衣袖[62],敦煌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中赞普即身穿联珠纹锦的袍子[63],即便是壁画中卧佛的枕垫都是联珠纹饰[64]。吐蕃西部的勃律和拉达克一带也有不少带有联珠纹锦的艺术品留存,吉尔吉特发现的715/716年间的佛陀铜像的坐垫以及供养人勃律王与王后的衣服都是联珠纹锦样式,拉达克阿奇寺(Alchi)、斯匹提的塔波寺以及西藏境内的托林寺都是属于古格王国在10—11世纪兴建的寺院,学者指出这些寺院壁画中都或多或少的出现了联珠纹锦的服饰风格[65]。
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青海都兰吐蕃墓葬群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中亚地区的胡锦。都兰吐蕃墓葬数量巨大,从1982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发掘都兰热水乡血渭一号大墓(M1),一直到1999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前者联合发掘热水乡原察苏河南岸4座墓葬为止,总共发掘了80多座吐蕃墓葬[66]。根据许新国先生统计,都兰热水墓中出土的丝绸“不重复图案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汉地织造,占品种总数86%,18种为西方中亚、西亚所织造,占品种总数的14%。西方织锦中有独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粟特锦,数量最多;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钵罗婆文字锦,是目前所发现世界上仅有的件确证无疑的8世纪波斯文字锦”[67]。这一条巴列维语题记后经释读为“王中之王,伟大的、光荣的”。巴列维语为萨珊波斯的官方语言,这条织锦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萨珊波斯王室[68]。
除了考古发现之外,国外的一些博物馆也收购了一些来自西藏的丝织品。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收藏了一件联珠对鸟含绶织锦的对襟小衫,一起入藏的还有一条唐朝风格的丝织裤子[69]。与之类似的是美国私人收藏的一件联珠对鸟含绶纹小孩裙衣(相片号80B-26A)[70],其余藏品还有一件联珠对鸟含绶纹的马鞍织物,霍巍先生曾对此做过调查[71]。瑞士阿贝克基金会博物馆入藏了3件吐蕃织锦。其中1件编号为5065,118×122 厘米,黄底红花,侧边有联珠纹饰,且有藏文题记。另外两件为联珠对狮锦,编号为4863b与4864c,藏文题记显示其为“停尸间之财物”( ),阿米·海勒指出这三件联珠纹锦是出自8世纪的吐蕃[72]。
),阿米·海勒指出这三件联珠纹锦是出自8世纪的吐蕃[72]。
虽然联珠纹锦的纹饰源自于萨珊波斯,但是其产地却很难确定,许新国先生对于含绶鸟织锦的纺织手法和纹饰的研究表明,都兰出土的这一类联珠纹锦的西方产地可以分为波斯和粟特两种,含绶鸟织锦是最受吐蕃人欢迎的西方织锦品种,《步辇图》上禄东赞所穿的就是含绶鸟锦袍[73]。此外,汉地也大量仿制了联珠纹锦销往西域等地,有的学者指出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许多联珠纹锦都是蜀地生产[74]。因此我们并不能将所有的联珠纹锦都视作来自波斯或者粟特,但也不能一概否定这些胡锦的西方来源,仍然需要专门的丝织品研究者对每一件丝织品的纺织手法和纹饰进行个案分析,或许有朝一日建立起吐蕃丝织品的数据库,我们就可以从每一件丝织品透视出吐蕃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线索。
除了这些商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各类的商品输入吐蕃,正如粟特商人将琳琅满目的商品输入汉地一样。关于吐蕃时期的名物列举最为丰富的要属敦煌医药文献,其中有不少来自于西域的物品。IOL Tib 56+57中提到饮用粟特酒( )可以治疗发热(第32—35行)[75],可见粟特所产的葡萄酒曾大量输入吐蕃。在另一件敦煌藏文医典P.t.127中提到燃烧大食纸(
)可以治疗发热(第32—35行)[75],可见粟特所产的葡萄酒曾大量输入吐蕃。在另一件敦煌藏文医典P.t.127中提到燃烧大食纸( )熏鼻可止住鼻血(第174行)[76],众所周知,造纸术至晚已在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传入伊斯兰世界,而吐蕃早在7世纪中期就已经从汉地传入造纸术,但大食纸依然被传入吐蕃,并用于止鼻血。同一件文书中提到用突厥锥针(
)熏鼻可止住鼻血(第174行)[76],众所周知,造纸术至晚已在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传入伊斯兰世界,而吐蕃早在7世纪中期就已经从汉地传入造纸术,但大食纸依然被传入吐蕃,并用于止鼻血。同一件文书中提到用突厥锥针( )放血可以治疗昏厥[77],反映了突厥医学传入吐蕃的信息。类似的物品还有硇砂(
)放血可以治疗昏厥[77],反映了突厥医学传入吐蕃的信息。类似的物品还有硇砂( )、密陀僧(
)、密陀僧( )、于阗糖(
)、于阗糖( )等等,假如对这些名物进行仔细的辨析,应该能够补充不少关于吐蕃与西域物质交流的新知识。
)等等,假如对这些名物进行仔细的辨析,应该能够补充不少关于吐蕃与西域物质交流的新知识。
三 商路与商人
吐蕃与西域的贸易路线分为陆上与海上两条,海上路线主要是从吐蕃运到印度,然后到达提 ,再通过海路运输。从吐蕃入印度有多条道路,《新唐书·箇失密传》云,“臣(箇失密王)与中天竺扼吐蕃五大道”[78],最常用的有两条,一条是吉隆入泥婆罗道,一条是从勃律至迦湿弥罗,西南行至印度河入海口的提
,再通过海路运输。从吐蕃入印度有多条道路,《新唐书·箇失密传》云,“臣(箇失密王)与中天竺扼吐蕃五大道”[78],最常用的有两条,一条是吉隆入泥婆罗道,一条是从勃律至迦湿弥罗,西南行至印度河入海口的提 ,即今巴基斯坦的Banbhore遗址。提
,即今巴基斯坦的Banbhore遗址。提 作为中古时期的印度洋的重要港口,是从南海与阿拉伯贸易的重要一站,麝香之路与海上丝路在此处会合。
作为中古时期的印度洋的重要港口,是从南海与阿拉伯贸易的重要一站,麝香之路与海上丝路在此处会合。
贾耽《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自广州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然后沿印度海岸西北行,“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至提 国……又自提
国……又自提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之阿巴丹)……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巴士拉南部之Obollah),……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79]。前述《新娘的颜色与灵魂的芳香》一书中记述了麝香从印度运往大食的道路:“比粟特麝香差一点的是印度麝香,源自吐蕃,被运输到印度,再到提
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伊朗之阿巴丹)……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巴士拉南部之Obollah),……小舟泝流,二日至末罗国(今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79]。前述《新娘的颜色与灵魂的芳香》一书中记述了麝香从印度运往大食的道路:“比粟特麝香差一点的是印度麝香,源自吐蕃,被运输到印度,再到提 ,然后海运至尸罗夫(Siraf)、艾顿(Aden)、阿曼(Oman)等地。”[80]对比《皇华四达记》的记载,可知这条海上麝香之路的路线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然后海运至尸罗夫(Siraf)、艾顿(Aden)、阿曼(Oman)等地。”[80]对比《皇华四达记》的记载,可知这条海上麝香之路的路线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关于陆上麝香之路的路线,从拉达克到吉尔吉特一线是吐蕃西出的最主要的路线,即便在吐蕃崩溃之后仍是如此。拉达克( )在8世纪时已经为吐蕃之领地,上文所述《世界境域志》中也提到此处的物产极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拉达克东部靠近班公错的唐泽(Tangtse)的岩壁上发现了25条粟特语铭文,其年代为9世纪,其中一条提到粟特使者出使吐蕃:“在210年(即841/842年),撒马尔罕的Caitra,与僧人奴失芬(Nōsh-farn)受命出使吐蕃。”[81]
)在8世纪时已经为吐蕃之领地,上文所述《世界境域志》中也提到此处的物产极为丰富。更为重要的是,拉达克东部靠近班公错的唐泽(Tangtse)的岩壁上发现了25条粟特语铭文,其年代为9世纪,其中一条提到粟特使者出使吐蕃:“在210年(即841/842年),撒马尔罕的Caitra,与僧人奴失芬(Nōsh-farn)受命出使吐蕃。”[81]
拉达克以西即同为吐蕃领地的大勃律,《世界境域志》第11章《吐蕃及其城镇》记载:“吐蕃勃律(B.lūrī Tubbat),吐蕃的一个地区,与小勃律(Bolor)接境,其民主要为商人,住在帐篷与毡房中,其国横向15日程,纵向亦15日程。”[82]大勃律商人众多,说明了大勃律在吐蕃对外商贸中的重要地位。小勃律则被置于第26章《关于河中边境及其城镇》之下:“勃律(Bolor)是一大国,其王自称太阳之子……他被称为勃律·沙(Bulūrī-shāh)。其国无盐,需从箇失密进口。”[83]这里说的Bolor是指小勃律,并未提到吐蕃人的存在,说明此时小勃律已经恢复了独立地位,而小勃律需要从克什米尔进口食盐的记录也与唐朝史料中“(小勃律)于箇失密市易盐米”的记载相印证。今天从大勃律首都斯卡都(Skardu)至吉尔吉特之间最便捷的道路是沿着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谷修建的S-1公路,但在中古时期需要翻越近3600米的圣古斯山口(Shengus Gali Pass),几乎不通行人。中古时期两地间最主要的道路稍往南部迂回,从斯卡都(Skardu)向南经由撒帕拉谷地(Sadpara Valley),西经德赛平原(Deosai Plains),然后向北经阿斯托谷地(Astor Valley)进入印度河谷经崩季(Bunji)到达吉尔吉特[84]。
大勃律也可以在进入印度河谷后顺流西南行到达契拉斯(Chilās),西北行可至朅师(即吉德拉尔,Chitral),天宝年间吐蕃军队勾结朅师“捉(小)勃律要路”就是沿此道进行的。契拉斯为印度河谷中的交通枢纽,北通大小勃律,西南可至印度河平原,东南可经至箇失密,既是小勃律东往箇失密购盐米的主要路线,也是大勃律西通朅师的必经之路,在契拉斯西到夏提欧(Shatial)这一带河谷两岸的岩壁上发现了600多条的粟特语和中古伊朗语题记,年代约在4—6世纪,足见其商贸地位之重要[85]。
吉尔吉特往西的道路分为两途,一途向西南行经过俱位(在马斯杜杰以西)到达朅师,再折向西北翻越多拉(Dorah)山口到达桑里希(Sanglich)。桑里希在《世界境域志》第26章中写作“S.NGLNG”,位于山脚下,山中有八达哈伤石榴石与红宝石……从该矿到吐蕃有一日半的路程”[86]。从桑里奇向北即到达泽巴克,再往西北就是大食之门,大食在此设卡收税。从大食之门向西北即八达哈伤的首府法扎巴德,再往西就到达吐火罗和粟特地区,往北则是骨咄、拔汗那和碎叶,此道从便捷性和安全性上来讲是吐蕃去往呼罗珊的最佳路线。朅师向南可至乌苌(今斯瓦特)、健驮罗(今白沙瓦)、高附(今阿富汗喀布尔)、迦毕试(今阿富汗贝格拉姆),经由此道也可以到达大食境内,但由此道前往吐火罗和粟特地区则较为迂回。
而从吉尔吉特向西北先到加古杰(Gahkuch),可由此地北经伊斯科曼谷地(Ishkoman)到达娑勒城(Sarhad);或者从加古杰往西沿着高仙芝伐小勃律的路线,先到达阿弩越城(Gupis),然后沿亚辛河谷北上,翻越坦驹岭(Darkot山口)后到达娑勒城。娑勒城在《世界境域志》中被称为“小撒马尔罕”,此地应是有不少的粟特商人存在,故有此名。也可以从坦驹岭以东的Ishkoman山谷到达娑勒城以东。从娑勒城沿婆勒川经昏驮多到达护密国都塞伽审。护密北与识匿接壤,《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载“彼王(识匿)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密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着也”[87]。从塞伽审西南即到泽巴克与南道汇合,向西入大食之门。
比这条道路更危险的道路是吉尔吉特北经洪扎河谷、明铁盖山口向北翻越葱岭至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从渴盘陀可以北至疏勒、雅儿看,与今天中巴友谊公路大体重合,渴盘陀向西可出护密、吐火罗。有学者指出由于喀喇昆仑山脉高寒缺氧,洪扎河谷水急而狭窄,这条路线使用频率并不高,商队更愿意从吉尔吉特向西经由伊斯科曼河谷或者吉德拉尔去往大食之门[88]。根据辛维廉的调查,洪扎河谷也发现了6条粟特语铭文,说明也有不少粟特商人活跃于这条道路上[89]。印度河谷下游的夏提欧发现的一条粟特文铭文更有说服力:“那色波(Narisaf)的儿子那你盘陀(Nanai-vandak)于第十(天)来到这里,并祈求好运于圣地K'rt之灵,我将尽快到达渴盘陀(χrβntn),并见到我兄弟健康快乐!”[90]这位粟特商人从夏提欧前往渴盘陀,最直接的路线就是经吉尔吉特、洪扎河谷,翻越喀喇昆仑山脉到达渴盘陀。
索格底亚那是大食与吐蕃陆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前文提到的粟特麝香正是大食人从粟特市场上获得的吐蕃麝香。马苏迪在930年代写成的《黄金草原》中记载:“我在呼罗珊还认识几个人,经过硇砂山道从索格狄亚那到吐蕃和中国。”[91]12世纪下半叶来自西班牙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在其行纪中记录了犹太商人至吐蕃贸易的路线:自巴格达至波斯、设拉子、加兹尼、撒马尔罕,“从彼处四天可至吐蕃,其境内的林中出产麝香”[92]。这也反映了商人群体的变化,在9世纪之前,粟特商人在丝绸之路和麝香之路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魏义天在《粟特商人史》中将粟特在中亚、中国和印度的商业网络进行了系统的阐述[93]。就吐蕃而言,粟特商人在吐蕃西境的角色要比在吐蕃东境更为重要。吐蕃东境与唐朝接壤,唐蕃边境多为战区,唐朝又有“诸蕃商胡若有驰驱,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的法令规定[94],因此粟特商人在东境难以施展。且相较于索格底亚那至青海道路途之遥远,粟特人从西境进入吐蕃更为便捷。粟特人跨越帕米尔与喜马拉雅山脉建立起囊括印度西北、吐蕃西境的商业网络,这一贸易网络的核心外销商品正是吐蕃的麝香、甘松和印度的龙涎香、沉香等大食需求量极高的香料[95],而粟特、波斯的织锦作为商品而不是货币输入吐蕃,贸易的主要货币是金银而不是丝绸,这些共同特点使得喜马拉雅和帕米尔地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贸易区。
而在9世纪之后粟特商人逐渐没落,大食商人与犹太商人渐渐崛起,众所周知,大食商人几乎垄断了印度洋的海上贸易,麝香从印度西海岸被大食商人运到尸罗夫、巴格达等城市。犹太商人的触角也到达了西域、印度和中国,除了上述犹太商人直接到达吐蕃的证据外,伊本·胡尔达赫比兹(Ibn Khurradādhbih,820-912)所著的《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记录了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拉赞尼亚(Rādhāniyyah)犹太商人的商道,这些犹太商人的经商范围西至法兰克,东至中国,“从西方贩来奴隶、婢女、娈童、织锦、毛皮、黑貂和宝剑等……从中国携带着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其他各地的商货返回红海”[96]。Anya King将其与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犹太-波斯语古信札联系起来,指出犹太商人在8世纪末已经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犹太商人或许就是《道里邦国志》中的拉赞尼亚犹太商人部落[97]。需要指出的是,吐蕃商人、箇失密商人、尼婆罗商人和印度商人在边境贸易中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些商人在吐蕃境内活动,将吐蕃商品交付给长途贸易的粟特人等商人团体,再将外来商品带到拉萨等地的市场上贩卖,是吐蕃国内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结论
7—10世纪吐蕃与中亚之间的商贸往来非常密切,这条商路被称为“麝香之路”。这条道路上的主要货币是金、银等贵金属,吐蕃的主要商品有麝香、动物皮毛等,粟特、波斯及大食向吐蕃出口的主要商品为织锦、金银器和香料。拉达克、象雄一线是麝香之路的主要陆上商道。吐蕃商品又经箇失密和泥婆罗商人贩卖到印度,最后并入印度洋贸易,可视为麝香之路的海上通道。粟特商人曾垄断了陆上贸易,后来犹太商人与大食商人崛起,控制了陆上与海上的贸易渠道。麝香之路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连接在一起,构建起吐蕃与印度、中亚之间独特的贸易网络。
(原载《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
[1] 沈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18ZDA177)阶段性成果之一。
[2] Ch.I.Beckwith,“Tibet and the Early Medieval Florissance in Eurasia:A Preliminary Note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Tibetan Empire”,CAJ 21,1977,pp.89-104.
[3] 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9—274页;同书改名为《吐蕃丝绸之路》再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9—248页。
[4] Anna Akasoy and Ronit Yoeli-Tlalim,“Along the Musk Routes:Exchanges Between Tibet and The Islamic World”,Asian Medicine,Vol.3,2007,pp.217-240.
[5] 王治来译:《世界境域志》,中华书局,1991年,第65页。
[6] Aḥmad Ibn al-Rashīd Ibn al-Zubayr,Book of Gifts and Rarities(Kitab al-hadāyā wa al-tuḥaf),tr.by Ghādah-Ḥijjāwī Qaddūmī,Cambridge,1996,p.62.
[7] Anna Akasoy and Ronit Yoeli-Tlalim,“Along the Musk Routes:Exchanges Between Tibet and The Islamic World”,pp.217-240;Anya King,“Tibetan Musk and Medieval Arab Perfumery”,in Anna Akasoy,Charles Burnett and Ronit Yoeli-Tlalim(eds.),Islam and Tibet:Interactions Along the Musk Routes,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1,pp.145-162.
[8] Anya King,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Brill,2017.
[9] 宋岘译:《道里邦国志》附《税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280页。
[10] 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in Philologica et linguistica:historia,pluralitas,universitas:Festschrift Jur Helmut Humbach zum 80.Geburtstag,Trier:Wissenschaftllcher Verlag,2001,pp.267-280.
[11] Amar Zohar & Efraim Lev,“Trends in the Use of Perfumes and Incense in the Near East after the Muslim Conquests”,JRAS,Vol.23:1,2013,pp.28-30;Anya King 2017,pp.93-146.
[12] Martin Levey,“Ibn Māsawaih and his treatise on Simple Aromatic Substanc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Vol.16,1961,p.399;King 2011,p.147.
[13] Martin Levey,“Ibn Māsawaih and his treatise on Simple Aromatic Substances”,p.403.
[14] The Oriental Geography of Ebn Haukal,tr.by William Ouseley,London,1800,p.233;Anya King,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p.237.
[15] Anya King,“Tibetan Musk and Medieval Arab Perfumery”,in Anna Akasoy,Charles Burnett and Ronit Yoeli-Tlalim(eds.),Islam and Tibet:Interactions Along the Musk Routes,Farnham & 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1,pp.149-150;Shihāb al-Dīn al-Nuwayrī,The Ultimate Ambition in the Arts of Erudition:A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from the Classical Islamic World,tr.by Elias Muhanna,New York:Penguin Books,2016,p.215.
[16] 《通典》卷190《边防典》“吐蕃”条,中华书局,1988年,第5171页。
[17] B.Laufer,Chinese Clay Figure,Chicago,1914,pp.253-257.
[18] 戴密微著、耿升译:《吐蕃僧诤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487—489页。
[19] 《册府元龟》卷961《外臣部·土风》,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137页。
[20] 黄灏、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21] 阿底峡尊者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22] Brandon Dotson,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Section on Law and State and Its Old Tibetan Antecedants,PHD Dissertation:Oxford University,pp.127-128.
[23] 《弟吴史记》中第6个匠人记为“皮匠宗次”( ),
), (皮匠)与
(皮匠)与 (画师)的区别在于
(画师)的区别在于 后是否有后加字
后是否有后加字 ,无法断定何者正确,见Brandon Dotson,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Section on Law and State and Its Old Tibetan Antecedants,PHD Dissertation:Oxford University,2006,p.132.
,无法断定何者正确,见Brandon Dotson,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Section on Law and State and Its Old Tibetan Antecedants,PHD Dissertation:Oxford University,2006,p.132.
[24] Dotson,Administr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pp.126-129.
[2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旅游局、炉霍县文化旅游局:《四川炉霍县呷拉宗遗址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 期,第15—28页;李映福:《四川炉霍县呷拉宗吐蕃时期炼铁炉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第5—13页。
[26] 关于对现存吐蕃铠甲的研究,请参Donald La Rocca,Royal Armouries Yearbook,Vol.4,1999,pp.113-132.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06年曾举办“喜马拉雅的战士”的展览,集中展出了西藏古代武器的藏品,参“Warriors of the Himalayas,Rediscovering of Arms and Amors of Tibet”,https://www.asianart.com/exhibitions/tibet-armor/intro.html;Donald J.La Rocca,“Tibetan Arms and Armor”,2007,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d/tbar/hd_tbar.htm.关于吐蕃武器的文饰,参Donald J.La Rocca,“The Decoration of Tibetan Arms and Armor”,2007,https://www.metmuseum.org/toah/hd/dtba/hd_dtba.htm.
[27] Amy Heller,“Observations on Painted Coffin Panels of the Tibetan Empire”,in Christoph Cüppers,Robert Mayerandmichael Walter(eds.),Tibet after Empire Culture,Society and Religion between 850-100,2013,pp.117-168.
[28] Amy Heller,“Armor and Weapons in the Iconography of Tibetan Buddhist Deities” in Donald LaRocca,Warriors of the Himalayas:Rediscovering the Arms and Armor of Tibet,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2006,pp.35-44;谢继胜:《榆林窟15 窟天王像与吐蕃天王图像演变分析》,《装饰》2008年第6期,第54—59页。
[29] Abū l-Qaˉsim Ibn Ḥauqal,Configuration de la Terre(Kitab Surat Al-Ard),Kramers,J.H.et Wiet,G.(trans.),Paris-Beirut,1964,p.454.
[30] Ibn al-Faqīh al-Hamadhān,Abrégé du livre des pays,tr.by H.Massé,Damascus,1973,p.62.
[31] Ibn al-Faqīh al-Hamadhān,Abrégé du livre des pays,p.308.
[32] 《新唐书·吐蕃传》,第6103页。
[33] 刘鸿孝主编:《布达拉宫秘宝》,中国民族电影艺术出版社,1999年,第251页。
[34]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1《敕吐蕃赞普书》,中华书局,2008年,第648页。
[35] 縻:熊飞据《文苑英华》将“縻”改作“麋”,今不取。《张九龄集校注》卷11,第637页,校勘记13。
[36] 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11,第637页。
[37] V.Minorsky,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London,1931,1970,p.93.
[38] 荣新江、朱丽双:《敦煌与于阗》,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43页。
[39]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89—128页。
[40] Amy Heller,“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Vol.1,2013,pp.259-291.
[41] Amy Heller,“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efacts”,p.263.
[42]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中镀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中国藏学》1994年第4期,第31—45页。
[43]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94、106页。
[44]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第322页。
[45] 王焕生译:《伊利亚特》卷2,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第17页。
[46] Philip Denwood,“A Greek Bowl from Tibet”,Iran,Vol.11,1973,pp.121-127.
[47]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110—111页;A.S.Melikian-Chirvani,“Iran to Tibet”,in Islam and Tibet:Interactions Along the Musk Routes,pp.97-99.
[48] 宿白:《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10世纪之前的陆上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新世纪出版社,1996年,第406页。
[49] Amy Heller,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7th-9th Century),Silk Road,Art and Archaeology,Vol.9,2003.http://www.asianart.com/articles/heller/index.html#5.
[50]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第109页。
[51] 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64—65页。
[52] 《新唐书·吐蕃传》(上),第6072页。
[53] 《唐会要》卷97“吐蕃”条,第2049页。
[54] 王尧:《吐蕃饮馔服饰考》,《西藏文史考信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290页。
[55] 《通典》卷190《边防典》“吐蕃”条,第5171页。
[56] Valrae Reynolds,“Luxury Textiles in Tibet”,in Jill Tilden(ed.),Asian Art,London,1995,pp.118-131;石硕、罗宏:《高原丝路:吐蕃“重汉缯”之俗与丝绸使用》,《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第89—100页。
[57]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207—209页。
[58]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与丝绸之路》,第208页。
[59]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第230页。
[60] 林梅村:《丝绸之路上的吐蕃番锦》,《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5—224页。
[6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86—289页;Heather Karmay,“Tibetan Costume,Seventh to Eleventh Centuries”,in Ariane Macdonald and Yoshiro Imaeda(eds),Essais sur I’art du Tibet (Paris,1977),pp.65-67.
[62] 许新国:《郭里木乡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69页;霍巍:《丝路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西北民族论丛》第1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4页。
[63] Paul Pelliot,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s de notes de Paul Pelliot,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s I,Collège de France,Paris,1981,p.64.
[64] Amy Heller,“Two Inscribed Fabric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ome Observations on Esthetics and Silk Trade in Tibet,7th to 9th Centuiy”,in Riggisberger Berichte,6 Entlang der SeidenstrasseI,Riggisberg,1998,pp.114-115.
[65] Valrae Reynolds,“Luxury Textiles in Tibet”,p.122;Amy Heller,“Recent Findings on Textil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in Regula Schorta(ed.),Riggisberger Berichte 9,Central Asian Textiles and Their Context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Abegg-Stiftung,Riggisberg,2006,pp.179-183,186-188.
[66] 其中仅有1999年发掘的四座墓葬公布了考古报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科学出版社,2005年。
[67] 许新国:《中国青海省都兰吐蕃墓群的发现、发掘与研究》,《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第139页。
[68]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第218页。
[69] James C.Y.Watt,Anne E.Wardwell and Morris Rossabi(eds.),When Silk Was Gold: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Textiles,New York: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1997,pp.34-37.
[70] 霍巍:《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第33—34页。
[71] 霍巍:《丝路入蕃:考古学的观察及其文化史意义》,《西北民族论丛》第13辑,第8页。
[72] Amy Heller,“Recent Findings on Textil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pp.175-188;Amy Heller,“Two Inscribed Fabric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Some Observations on Esthetics and Silk Trade in Tibet,7th to 9th Centuiy”,pp.95-118.
[73]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第213—232页。
[74] 许新国:《都兰出土蜀锦与吐谷浑之路》,《西陲之地的东西方文明》,第199—231页。
[75] 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23、205行。
[76] 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第29、222页。
[77] 罗秉芬:《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第29、222页。
[78] 关于“吐蕃五大道”,参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79]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53—1154页。
[80] Akasoy,2007,p.221;Shihāb al-Dīn al-Nuwayrī,The Ultimate Ambition in the Arts of Erudition:A Compendium of Knowledge from the Classical Islamic World,p.216.
[81] 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Inscriptions of Ladakh”,in Karl Jettmar,Ditte Konig and Martin Bemmann(eds.),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Vol.2,Mainz,1993,pp.151-163.
[82]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p.92.
[83]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p.121.
[84] Karl Jettmar,“The Paṭolas,Their Governers and Their Successors”,in Antiquities of Northern Pakistan:Reports and Studies,Vol.2,p.83.
[85] N.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London,1992;N.Sims-Williams,“The Sogdian Merchants in China and India”,in A.Cadonna and L.Lanciotti,eds.,Cina e Iran da Alessandro Magno alla Dinastia Tang,Firenze,1996,pp.45-67;辛姆斯·威廉姆斯著、毕波译:《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2—56页;K.Jettmar,“Sogdians in the Indus Valley”,in Beyond the Gorges of the Indus,Oxford,2002,pp.110-115.
[86] Ḥudūd al-’Ā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p.121.
[87] 慧超撰、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145页。
[88] Deborah E.Klimburg-Salter,The Silk Road and the Diamond Path,Los Angels,1982,p.33.
[89] N.Sims-Williams,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p.25,map 1.
[90] Y.Yoshida,“Sogdian Miscellany III,”in R.E.Emmerick and D.Weber(eds.),Corolla Iranica,Papers in Honor of Prof.Dr.David Neil MacKenzie,Frankfurt-am-Main:Peter Lang,1991,pp.237-244;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tr.by James Ward,Brill,2005,p.81.
[91] 耿升译:《黄金草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92] The Itinery of Benjamin of Tudela,tr.by A.Asher,London and Berlin,1840,pp.58-59 [p.82].
[93]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tr.by James Ward,Brill,2005.
[94]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第278页。
[95] Anya King,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Brill,2017,pp.59-65.
[96] 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第164页。
[97] Anya King,Scent from the Garden of Paradise:Musk and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Brill,2017,pp.25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