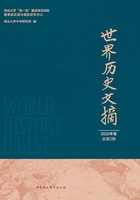
霍乱、面包与谣言
——论1832年巴黎的拾荒者骚乱
乐启良[1]
摘要:第一次全球性的霍乱危机肆虐巴黎长达半年之久,导致法国首都的死亡人数多达18402人。为了防止霍乱疫情的扩大,巴黎警察局领导开展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卫生政治运动,积极推动环卫承包制度的改革,要求更迅速、更彻底地搬运城市的生活垃圾,并由此和拾荒者产生了严重的利益冲突,致使他们发动骚乱。在骚乱期间,怀疑霍乱的存在并有人投毒的谣言纷纷四起,而且引发了不少袭击甚至虐杀无辜者的暴力事件。尽管拾荒者的骚乱和谣言危机只持续了一周左右,但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路易-菲利普政府主导的卫生运动和最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之间存在的巨大紧张。从某种意义上说,七月王朝在处理霍乱危机时所表现的无能强化了大革命以来法国社会病入膏肓的印象,促进了共和主义与社会主义等激进思潮的传播。
关键词:霍乱 巴黎 拾荒者骚乱 谣言
1832年3月26日,一场先后席卷俄罗斯、波兰、普鲁士、奥地利、比利时以及英国的霍乱,悄然侵入巴黎。霍乱在肆虐法国半年后,给巴黎留下了18402具面容枯槁的尸体。[2]突如其来而又病因不明的霍乱给七月王朝初期巴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对于第一场全球性的霍乱危机在法国的蔓延与消亡,[3]对于霍乱在巴黎引起的巨大恐慌,[4]由此揭示出来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5]以及政府机关与医疗机构采取的应对之策,[6]西方学者已经作过颇为详细的论述。然而,对于霍乱时期巴黎爆发的拾荒者骚乱,却很少有人予以专门的着墨。笔者试图通过考察1832年4月1—4月5日期间爆发的巴黎拾荒者骚乱,分析政府、环卫公司以及拾荒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牵扯和权力关系,借此呈现七月王朝统治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
一 霍乱前夕的卫生运动
霍乱是由于摄入的食物、饮料或饮用水受到霍乱弧菌的污染而引起的,它的主要症状是持续的呕吐和腹泻,并由此引起严重脱水、循环衰竭、脉搏微弱、心律不齐、神志不清甚至造成死亡。在很长时间内,霍乱只是一种区域性的疾病,仅仅局限于印度河谷地区,但伴随着殖民活动、军事征服、朝圣活动、商业贸易以及频繁的人员与船只往来,[7]它逐渐向周边扩散,最后演变成一场席卷全球的流行病。[8]
在1817年,霍乱首次超出了德干半岛,由于距离欧洲仍然太过遥远,关心它的欧洲人士屈指可数。当霍乱在1830年7月出现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的阿拉特斯罕,并迅速侵袭整个俄罗斯,在短短数月内造成数以万计的病患以及超高的死亡率后,才真正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和恐慌。不久,霍乱先后肆虐波兰、普鲁士、奥地利、比利时和英国。
虽然迟至1832年3月26日,巴黎才出现了首例确诊的霍乱病患,但路易-菲利普政权很早就开始密切关注外国疫情的发展情况,并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
尽管自1817年起,法国医学人士便注意到霍乱的存在,但对于它的病理机制、诊治方案、是否具有传染性、如何预防等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为了更好地认识霍乱并采取恰切的预防措施,路易-菲利普政权派遣多个医疗小组到俄罗斯、波兰、奥地利和普鲁士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要求他们及时向国内发回医学报告,供皇家医学院讨论。但是,由于在19世纪上半叶无人洞悉细菌学的奥秘,在霍乱的起源、诊治、是否传染、是否应当采取隔离措施等问题上,俄罗斯和波兰等地发回的报告以及巴黎的医学界得出了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的结论。
然而,几乎所有的考察报告都同意,霍乱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卫生状况息息相关。派驻俄罗斯的医生雅奇尼尚(Jachnichen)指出:“流行病主要出现在低等阶级当中,出现在低矮、潮湿与肮脏的住所,出现在人口拥挤的街区;酗酒、堕落、劣质食品、纵欲、寒冷、消化不良也是不可辩驳的因素。”[9]又如,杜布勒(Bouble)报告的结论认为,霍乱大爆发的主要原因有:忽冷忽热、潮湿、气候变化的频繁、人口拥挤、军队的安营与行军、饮食过度、堕落、肮脏、住所的低矮与潮湿、缺乏通风、人畜同屋、精神的剧烈变化、劣质的食物和饮料、难以消化与霉变的食品,等等。[10]此外,派驻波兰的医生布里埃尔(Brière)同样表示,虽然产生霍乱的根本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贫困,不卫生,住所的低矮与狭窄,街道的肮脏、阴暗与局促,气候的骤然变化,饮食,服装,习惯与恐惧”等因素都会助长疾病的传播。[11]时任驻英大使的塔列朗也致信法国医生说:“霍乱似乎集中在城市(即伦敦——笔者注)中人口最密集、最肮脏的地区:泰晤士河两岸。”[12]
实际上,巴黎的著名公共卫生学家路易-勒内·维莱梅(Lousi René Villermé)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人们的寿命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饮食和环境:“我们应当高度重视卫生或者不卫生、衣着、食物、酒水的影响;毋庸置疑,它们的好坏将决定着生命的长短。”[13]然而,尽管巴黎在19世纪上半叶经常被人誉为“文明世界之都”[14],但绝大多数街区的卫生状况可谓惨不忍睹。如勒·雅南如是描绘了当时巴黎的糟糕状况:“房屋昏暗,过道无风,到处都见不到阳光,窃贼横行于每条街道,狼群在各个城门前饥肠辘辘,焦虑无处不在,人们只能向上苍寻找希望,但上苍却从来不会让他们如愿……实际上,人们生活在一个哥特式的城市里,黑暗、阴森、粪便成堆、闷热,它是一个阴森、混乱、暴力、贫困与鲜血淋漓的城市。”[15]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路易-菲利普政权在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入侵的霍乱时,为什么会把搞好巴黎的卫生当作重中之重。巴黎警察局是当时环卫工作的领导机构,它负责组织和实施各种防卫措施。
首先,巴黎警察局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下辖12个区卫生委员会和 48个街区委员会,负责监督整个巴黎的卫生状况。中央卫生委员会的职能是向政府提供建议,同时接收和讨论各区和各街区的卫生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并提出必要的整改措施。区卫生委员会充当沟通中央卫生委员会和街区卫生委员会的中介,负责上传下达,没有什么实际的职权。相反,各街区卫生委员会由于有权向中央卫生委员会或巴黎警察局直接汇报,因而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的成员通常包括建筑师、警长、医生、药剂师以及地方显贵。街区卫生委员会的职责是参观各自辖区的公共场所(市场、剧院、学校、军营、医院、出租屋、阅览室、咖啡馆、墓地等),检查卫生死角,提醒居民定期打扫房屋,及时清理垃圾、粪便,维护公共道路的整洁,维持街道、广场、河岸、十字路口的整洁,确保生活用水(如喷泉、水井与运河)的干净。[16]
其次,巴黎警察局颁布各项条例,勒令各行各业做好饮食安全、药品安全与卫生防治。它禁止摊贩售卖变质的面包、禽肉、兽肉、羊肉、牛肉、猪肉和鱼肉,要求他们定期用氯水清洗砧板,禁止他们向公共道路抛撒垃圾。1831年10月29日,巴黎警察局向各区的区长和警长下令,禁止药剂师、药品商、草药贩、食品店主以及染料商在未经允许和登记的情况下,出售有毒的商品。同时,警察局还要求各个房东把房屋的墙壁刷白,命令他们及时处理自己家里或附近地区的粪池、水沟、水井、水坑、马厩、厩肥、垃圾站、沟渠、小溪等。[17]
再次,巴黎警察局印发了40000份《霍乱防治手册》[18],宣传防治霍乱的方法与措施。它提醒人们尽可能长时间打开门窗,保持家里通风;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多穿由羊毛或法兰绒制成的衣服,建议穷人要养成穿鞋的习惯,不要光脚丫走路;勤倒夜壶,不要积留尿液与粪便,不要随意将把生活污水排放到街道;保持家里卫生,每天用氯水冲洗水沟与厕所;利用排水沟和屋檐尽快排出雨水;生活作息要有规律,既要劳逸结合,避免过分操劳,也要饮食节制,避免暴饮暴食;尽量多吃煮熟、容易消化的肉制品、鸡蛋、面包,要吃成熟的水果;饮用水要干净,过滤水最佳;不要酗酒,不喝烧酒、啤酒、苹果醋,但可饮用少量的优质葡萄酒。
最后,1831年11月19日,巴黎警察局要求各个街区都应成立至少1个医疗救助站。医疗站每天都应配备至少6名医生、1名药剂师、6名医学院的学生、6名护工与2名护士;霍乱爆发后,他们应当立即赶赴病患的住所,及时给病人提供帮助。每个医疗站必须预留2间宽敞的病房,1间病房要配备6条凳子、2条长椅、3张制作精良的草褥、3个长枕、6条羊毛床单、1个铁炉并配有火铲与火钳,1个水壶、2个平底大口杯、2个夜壶;另一间病房则要提供6个椅子、2个靠椅、4张帆布床、4张床垫、4个长枕、8张羊毛床单、1把火钳、1把火铲、1个风箱、2个烛台、1张抽屉桌、1个墨水瓶、笔、纸、1个放药品与衣服的橱柜。此外,医疗站应当准备数量不等的芥末粉、洋白菊、拌胡椒的薄荷、大麦粉、葡萄酒醋、液态氯化钙、樟脑酒、匈牙利膏药、盐水、混合茴香与樟脑的氨水、硫酸醚、鸦片酊、树胶糖浆等各种药品与物品。[19]
毋庸讳言,巴黎警察局为整治卫生和防御疾病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但也需要指出,许多政府官员和医学精英仍然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霍乱有可能不会出现在法国,或者霍乱给法国造成的危害将会远远小于其他国家。巴黎警察局广泛分发的《霍乱防治手册》严重低估了霍乱的危害程度:“在欧洲最适合传播疾病的地方,感染的人数比例不超过1/75,有些城市的感染比例甚至还低于1/200。”[20]法兰西院士、陆军卫生委员会的成员拉雷(Larrey)男爵自负地认为,良好的地形、发达的医学、健全的卫生措施以及法国公民的节制,将有助于法国战胜甚至避免霍乱的灾祸:
法国的地形是如此有利,以至于人们无须担心霍乱病毒或其他鼠疫的入侵……人们不必担心它侵入国家的腹地,因为它会立刻得到所有法国医生都掌握的理性医学的阻遏和处理……1789年以来在整个法国得到推广的卫生法令和健康措施,已经造福于人民……如今,在地球上,除了英国,没有一个民族的文明、工业与实业能比我们更完善,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好地遵守卫生条例。防御各种疾病的卫生尤其是节制,是法国公民的首要品质。[21]
当时法国医学界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肯定会让民众掉以轻心,进而影响巴黎环卫工作的进展。夏尔勒·德·雷米扎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了霍乱爆发前夕巴黎民众的普遍心态:
在一年多以前,起源于亚洲腹地的霍乱,正流行于西欧。有人在谈论它造成的危害,有人提前告诉我们它即将来袭;我们充满好奇地听着,但并不惊慌。我们的历史学家谈论的重大鼠疫只属于中世纪。它们不可能再进入一个如此发达的社会:我们的气候、我们国家的整洁、我们的治安条例、科学的进步都能保护我们,免于受到它们的侵害。如何想象一个像巴黎这样伟大的城市,怎么会和东方的悲惨城市一样,遭到印度传染病的打击呢?[22]
二 拾荒者的骚乱
巴黎警察局采取各种卫生防御措施,目的是要在霍乱爆发时有效地遏制疾病的扩散,因而在本质上符合法国公众的根本利益。然而,如火如荼的卫生运动也让许多巴黎民众感到不适,甚至还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因为它不仅要求人民抛弃某些由来已久的陈规陋习,而且还威胁到了某些人群的生存条件。
面对随时可能爆发的霍乱,巴黎警察局加强了社会流动人口的监督与管理。1831年11月19日,巴黎警察局颁布法令,要求客店、旅馆、出租屋检查客人的护照、签证和居留证,登记他们的姓名、年龄、常驻地址和职业,在规定期限内向街区警长汇报。甚至,免费接待客人的普通市民也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定。该法令还规定,没有证件的外国人或者游客在抵达巴黎3天之内,必须向警察局申请居留许可证,否则将被移交法院处理。[23]1832年12月14日,巴黎警察局以“阻碍行人和车辆的自由流通、干扰商铺的经营并会制造经常引发骚乱的人口聚集”为借口,宣布自1832年1月1日起,取缔卖唱者、杂技演员、魔术师、小丑、管风琴演奏者等街头卖艺者的街头表演许可证,非法演出者将会被警察逮捕并移交法院处理。[24]巴黎警察局之所以颁布这两项法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排查、监督和控制流动人群,以降低霍乱传播的潜在风险。不难想象,其处境由此变得更为艰难的流民和乞丐们必然满腹怨气。
然而,巴黎环卫制度的改革催生了人数最多、仇恨最深的群体。1832年,巴黎十二个区总共拥有人口759135人,[25]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垃圾,巴黎市区每天需要运到郊区或乡村的垃圾总量超过400立方米。[26]所以,每天对巴黎进行打扫,并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是一项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金钱的公共工程,而且关系到每个巴黎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但是,巴黎的环卫体系虽然经过屡次改革,但其卫生状况始终难言令人满意。
1818—1827年期间,巴黎的环卫工作由拉巴尔特公司(Labalte)承包。巴黎市政府每年向拉巴尔特公司支付404000法郎。由于资金严重不足,拉巴尔特公司每年只能雇用93辆运输马车、200个扫地工、24个下水管道工以及38辆洒水车,无法维持“巴黎街道的表面整洁”[27]。而且,拉巴尔特公司并不直接负责街道打扫、管道清理和垃圾搬运等具体工作,而是将之转包给一批分包人。有鉴于此,巴黎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
1827年4月,复辟王朝的巴黎警察局对首都的环卫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它将承包费用提高到1100000法郎,并且不再和拉巴尔特公司续约,而是和分包人直接签订雇用合同,总共雇用216辆马车、352个扫地工、64个下水管道工以及56辆洒水车。[28]虽然承包费用以及雇用的人力与物力几乎增加了一倍,但巴黎的卫生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改善。[29]
1830年12月,路易-菲利普政权的巴黎警察局试图再次改革首都的环卫制度。巴黎警察局以塞纳河为界,把巴黎的环卫服务分成左岸与右岸,起草了两份标的分别是200000法郎和400000法郎的标书。巴黎警察局还制定了严格的考核与惩罚条例,授权政府官员以及警察对各个街区的卫生状况进行检查,对任何“没有打扫”或“打扫糟糕”的地方处以高额的罚金。[30]巴黎警察局的意图很明确,即要通过分开承包塞纳河两岸的环卫工作,引入竞争机制,并通过严格的考核制度,实现改善巴黎卫生条件的目标。但是,由于总承包费用的下降、考核制度过于严苛,并要缴纳高达60万法郎的巨额保证金,没有任何公司参加招标。
1831年6月,巴黎警察局重新起草标书。新标书吸取了前一次标书的失败教训,把保证金由60万下降到30万法郎,删除了苛刻的监督与惩罚条款。同时,新标书还提出了3项至关重要的新规定:
第一,要求承包商制作1匹马牵拉的小型环卫车辆。在此之前,巴黎多数的环卫马车由3匹马牵引,体积庞大。为了装满一辆垃圾车,经常要耗费很长时间,因而经常阻碍交通。而且,由于无法进入过于狭窄的街头巷尾,巴黎留下了许多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卫生死角。巴黎警察局希望通过推广更为轻便的马车,改善巴黎的卫生条件,同时改进首都的交通状况。
第二,赋予环卫公司垄断巴黎垃圾的权利。对未来的承包商而言,这一条款很有吸引力。据估计,假如能够垄断巴黎垃圾的分拣与出售,由此产生的利润将远远超过整个巴黎的环卫费用。[31]为了让新环卫公司尽心尽责地提供清洁服务,巴黎警察局两次颁布法令,重申了它对首都垃圾的垄断权利,禁止“乡村居民以及环卫公司以外的人员在巴黎的公共道路上拾捡垃圾或其他物品”,禁止巴黎居民“向街道抛弃杂物、垃圾、破布抑或旧家具,必须将之直接交给路过的环卫车辆”[32]。
第三,巴黎警察局改变环卫公司的工作时间表。在过去,环卫公司只在每天凌晨作业;如今,警察局批准环卫公司在凌晨和傍晚各作业一次。
巴黎警察局的改革,尤其是它赋予的垃圾垄断权使得首都的环卫工作变得有利可图。在1831年10月8日的招标活动上,雅各布公司(Jacob)以848442法郎竞标成功,价格远远低于巴黎警察局的预算(110万法郎),承包的年限是9年。[33]但是,由于缺乏实力,雅各布公司无法在短时间内建造出符合巴黎警察局要求的新马车,不得不在1832年3月20日,以270000法郎的总价,把巴黎的环卫服务转让给萨拉维特(Savalète)公司。[34]
对巴黎警察局和环卫公司而言,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巴黎警察局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有望借此改善巴黎的卫生条件,而环卫公司除了获取既定的承包费用,还能够凭借垃圾的垄断权,每年至少赚取50万法郎的额外利润。[35]然而,两个群体的利益却遭到了重创。一个人群是旧式垃圾车的主人,约有300人。撇开售卖垃圾的利润不论,每辆旧式马车每天能够赚取租赁费15法郎。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因损失巨大,反对的态度特别激烈。[36]另一个群体则是基数更为庞大的拾荒者。在1832年霍乱时期的巴黎究竟有多少靠捡垃圾(破布、纸张、骨头、旧家具)为生的拾荒者?巴黎警察局并没有为我们留下确切的数字。根据《国民报》的说法,1832年巴黎拾荒者的人数在10000—12000之间。[37]《国民报》可能夸大了拾荒者的数量,[38]但从事拾荒的人数及其行业利润却不容小觑。[39]毫无疑问,新式垃圾车的流通以及环卫公司对垃圾的垄断,将不可避免地威胁旧式垃圾车的主人和拾荒者的权益,甚至会直接导致他们的饥饿。
1832年3月26日,巴黎首次出现霍乱病例,并以很快的速度蔓延起来。[40]3月30日,中央卫生委员会(la commission central de salubrité)在《导报》发表公告,除了确认霍乱侵入巴黎的消息,要求各地及时救治病人和通报疫情外,还颁布法令,要求“特别打扫,清理垃圾”[41]。在政府部门的极力督促下,萨拉维特公司在1832年3月31日,开始使用第一批新造的小型垃圾车。消息传出后,拾荒者和旧式垃圾车的主人纷纷聚集起来,他们捣毁和焚烧了20多辆垃圾车,痛打车夫。同时,社会上许多不满者也加入了骚乱者的队伍。拾荒者向巴黎警察局局长提交抗议书,援引精英们所熟悉的权利话语,要求保护他们自古以来的神圣拾荒权利,痛陈拾荒者的艰难处境:
难道你不是在所有的报告中指出,霍乱尤其喜欢在贫穷中选择它的受害者吗?难道你不是说预防霍乱的唯一措施就是购买氯化物,让肚子吃饱,穿上法兰绒吗?我们和你一样相信,此举能够抵抗你们告诉我们的疾病,能够抵抗每天都在损害被匮乏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身体的所有疾病。所以,在你让一家新的公司剥夺我们从垃圾索取的面包时,请你给我们留下活路。你总是在毫无意义地强调,它的服务不会危害我们的行业,因为清扫工作只在白天进行。难道你忘记你的前任们禁止我们在子夜以后在大街上逗留了吗?因此,由于从日落到日出期间什么也不能做,导致我们在美好的季节,只能有3个小时工作![42]
在拾荒者起义后,人们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防范霍乱的蔓延和保障拾荒者的面包之间,应当做出如何选择?
共和派报纸《国民报》采取了某种折中主义的立场,认为政府一方面要“避免延误日常打扫和垃圾清理,防止增加流行病的威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拾荒者的生计,采取人道措施,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展开教育,让拾荒者认识到自己也有可能变成霍乱的受害者。[43]但是,更多的报纸以及巴黎的精英们倾向于强调整治巴黎卫生的迫切性,坚持拾荒者阶级应当以大局为重,为整个巴黎的安全做出牺牲。信条派的《立宪报》表示,“即便假定某个特殊阶级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要他们为所有人作出牺牲,乃是合理的、正当的做法”[44]。《法国信报》则抱怨说,拾荒者组织骚乱不仅对自己毫无裨益,而且会导致霍乱疫情变得更加不可控,“环卫服务的中断导致街道泥泞不堪,但拾荒者的资源并没有因此得到增加,却毫无意义地增加数百名病患”[45]。社会精英对拾荒者的普遍嫌恶,在旅居巴黎的德国诗人亨利·海涅(Henry Heine)身上尽显无疑。亨利·海涅怒斥拾荒者把少数人的权利凌驾于绝大多数人的安全之上,批评他们把“公共的肮脏当作私人的财产”[46]。
4月2日,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发表公告,呼吁巴黎民众尤其是拾荒者要为公共利益保持克制,避免被“公共秩序的敌人”蛊惑:“不要在一场偶然疾病所造成的困难外(你们安全的敌人夸大并加剧了困境),增添骚乱的威胁,从而破坏政府采取的预防措施,违反公共卫生的利益。要严厉打击那些反对社会,把一场暂时的疾病作为作奸犯科之工具的人。”[47]热斯盖派遣国民自卫军、警察、宪兵和骑兵驻扎各个重要的路口,严密监视事态的发展。对于不听劝告,仍然执意参加骚乱的拾荒者,他下令进行弹压,最后逮捕了225人。[48]
4月3日晚上,巴黎的秩序逐步得到了恢复。巴黎警察局长宣布继续推进清理街道的服务,但最终也向拾荒者做出了某些让步,承诺不会触动他们的拾荒权利。[49]于是,巴黎警察局废止了曾经授予环卫公司的垃圾垄断权利,并规定环卫公司的晚上作业只能限于偏僻的街道和郊区。[50]
然而,警察局长和稀泥的做法,导致整治巴黎的卫生运动取得的效果大打折扣。对此,一份杂志禁不住批评路易-菲利普政府的胆小怕事,“把街道当作私有财产之人的荒谬诉求有可能使人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警察对道路无法采取行动,也没有权力的国家”;它指责警察局长的不作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文明世界里,没有哪个首都会比巴黎更肮脏”[51]。
三 投毒的谣言
在拾荒者出现骚乱的同时,巴黎羁押政治犯的圣佩拉热(Saint-Pélagie)监狱也发生了暴动。4月1日,犯人们以霍乱威胁其生存为借口发动叛乱,虐待狱警,试图越狱;在外面,200左右的共和派从外部发动攻击。[52]接到暴动的消息后,大批警察前来救援。在镇压犯人的过程中,警察被迫开枪,并打死了1名犯人。暴乱结束后,政府决定给巴黎各监狱的犯人增加肉类和面包的供应,并释放了许多罪行并不严重的犯人。[53]
拾荒者和犯人的骚乱似乎并未让巴黎民众感到害怕,真正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周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者。根据《法国信报》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自从3月26日发现霍乱病患以来,患病以及死亡的总人数急剧攀升:
表1 霍乱危机初期巴黎的病患与死亡统计表[54]

4月初,霍乱的病患与死亡的人数远没有达到高峰,[55]但它在巴黎造成的巨大损失让对普通民众感到不寒而栗。尽管政府和报纸作过许多的宣传与报道,但还是许多人不相信霍乱的存在。几乎在拾荒者骚乱和圣佩拉热监狱暴乱的同时,否认霍乱存在,宣称有人投毒的谣言开始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传播开来,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某些报纸还煞有其事地报道了警察逮捕投毒者的谣言。[56]投毒谣言的传播是如此盛行,以至于《立宪报》指出“没有一个街区不为投毒的叙事感到胆战心惊”[57]。
伴随着投毒谣言的流传,有人开始把矛头指向政府,迁怒医生,认为霍乱不过是政府和医生的发明创造,用来消灭穷人。甚至,巴黎街头还出现了一些呼吁民众起义的《告人民书》。[58]
面对愈演愈烈的投毒谣言,尤其在巴黎民众把愤怒的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时,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不得不出面辟谣,并在4月2日给各区的警长下达如下的命令:
霍乱病毒出现在首都的事实,给所有良好的公民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和深深的痛苦,也给秩序的永久敌人提供了在民众当中散播反对政府的造谣中伤。他们竟然说,霍乱不过是政府代理人在投毒,目的是要减少人口,并转移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注意力。我获悉,一些坏蛋(misérables)携带小瓶或小包的毒药,在酒馆和肉铺附近晃荡,撒向喷泉、葡萄酒桶和肉制品,制造投毒的假象,或者让一些帮凶制止罪行,而后者谎称自己听命于警察,从而证明针对政府之可恶控诉的真实性。我只需向你们指出类似的过激事件,足以让你们认识到加强监督的必要性。[59]
4月4日,热斯盖又给巴黎各区区长发布了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命令:
社会秩序的永久敌人妄图为在此时此刻折磨着我们民众的灾祸寻找一个可耻的借口,以实现其经常谋划的阴谋。他们妄图利用我们的不幸,利用家庭的痛苦,诱惑民众。他们散布消息说,人们视为疾病受害者的不幸者只是……投毒的结果。他们竭力劝说民众中最不开明的阶级,霍乱并不存在;他们妄图打乱政府和医生给痛苦人类提供的救助;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这些卑鄙的阴谋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功。一些暴力和残暴的行为是他们诱惑一部分民众,使之误入歧途的结果。此种局势要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应当向有可能受到误导的公民说明情况,给他们提供明智的建议,提醒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公共利益,不要盲目相信坏人的诋毁和无耻的造谣,因为坏人只想恫吓民众,导致我们无法迅速摆脱正在肆虐首都的灾难。[60]
作为内阁总理佩利耶的密友,警察局长热斯盖或许认为帮助政府摆脱投毒的猜忌比消除谣言本身更为迫切,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给警长和区长下达急于推卸政府责任、把投毒归咎于“坏蛋”和政治反对派的命令。热斯盖的愚蠢做法让满腹狐疑的巴黎民众更加确信投毒事件的真实性。人们纷纷行动起来,在酒馆、水池、市场以及十字路口监视、盘查任何有投毒嫌疑的人,并由此导致巴黎街头出现了许多无辜者被怀疑、痛打,甚至被虐杀的血腥场景。亨利·海涅为我们描绘一幅幅令人不寒而栗的场景:
在刷上红漆的酒馆所在的街头拐角,人们自愿聚集起来;人们总是在这些地方寻找嫌疑犯;如果他们的口袋中藏有可疑的物品,他们就倒了大霉。人民会像一只野兽、一支愤怒的军队扑向他们。许多人由于自身的机智而逃过一劫,许多人由于在当天得到巡警的帮助而幸免于难;6个人遭到了无情地屠杀。没有什么场景比人民的怒火更为可怕,尤其当它变得嗜血、扼杀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时。在街头,人潮涌动,身穿衬衣的工人如同万劫不复者,如同魔鬼,如同相互撞击的白色浪花,他们无情地咆哮着、呼喊着。我在圣德尼街听到有人叫嚣:“吊死在灯柱!”……我看到其中的一个不幸者奄奄一息,年迈的妇女脱下鞋子,用鞋跟敲打他的脑袋,直至他死亡。他全身裸体,满身是血,浑身是伤;人们不仅扒光了他的衣服,也拔下他的眉毛、头发和鼻子;随后来了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用一条绳子绑住尸体的脚,在街上拖曳,并不停叫喊:“这就是霍乱病毒!”一位尊贵的美丽妇人,身体和双手都沾满鲜血,给经过的尸体重重一击。[61]
在谣言四起后,警察疲于奔命,从怒火中烧的民众手中保护和解救无辜者。同时,为了平息民众的怒火,他们还把葡萄酒、烧酒、果汁、水、面包、肉类、糖果等可疑物品送到医疗机构或者化学实验室检验。4月5日,各家报纸公开检验结果,宣布送检物品不含任何毒药,并发表检验医生的一封公开信,以证明投毒宣言的虚妄。[62]与此同时,主宫医院(l’Hotel-Dieu)的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发表声明,宣布对送进该医院的病人进行了全面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迹象。[63]确凿的医学证据,尤其是病患与死亡者的人数急剧攀升,让捕风捉影的投毒谣言很快消失。
结语
尽管拾荒者的骚乱和投毒的谣言持续的时间颇为短暂,但却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七月王朝初期乃至贯穿其始终的结构性矛盾。透过1832年4月初巴黎霍乱时期的拾荒者骚乱和投毒谣言,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路易-菲利普政权统治期间存在两种极为严重的矛盾。
一方面,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作为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言人,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在获悉投毒谣言时,他的本能反应不是遏制谣言,而是忙不更迭地撇清政府的责任,并指责保皇党是“幕后的主要黑手”[64]。共和派报纸《国民报》尽管批评普通民众的无知,批评投毒谣言及其催生的暴力体现了“罪恶的逻辑”[65],但强调民众之所以对政府抱有敌意,主要是因为七月王朝忽视、愚弄与镇压人民所致:
自七月革命以来,他们给群众做了什么好事呢?他们对群众的痛苦作了怎样的关心呢?……至少为了阻止一场不可避免的疾病,为了减少它的危害,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为什么从昨天才开始采取卫生防卫措施呢?为什么要等到出现死者之后,佩利耶和热斯盖才表达善意,才维护生者的健康呢?既然你们在格勒诺布尔、里昂、卡尔卡松侮辱了民众,为什么你还希望它会在巴黎信任你呢?这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玩弄真相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安慰群众,因为假如要安慰群众,就永远不要欺骗他们。[66]
另一方面,法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在霍乱爆发不久,医学院很快指出霍乱的受害者更多来自贫困阶级,“疾病首先打击住宿恶劣、衣着褴褛、饮食糟糕,并被各种劳作折磨得筋疲力尽的人”[67]。1832年4月初广泛传播的一份《告人民书》则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贫困人口所深切感受到的无奈、绝望和愤怒:
穷人并不是死于霍乱,而是死于饥饿!富人很少遇到威胁,因为他们逃跑了。不幸者拥有更少的劳动成果与面包。人们禁止死者的亲朋好友进入医院。为什么让胆小鬼、利己主义者携带生存资料,逃离边境,却让人民生活在巴黎?……疾病肆虐人口稠密的街区,因为它们既肮脏又拥挤;有人却抛弃了疾病不会侵入的干净而宽敞的房屋,它们空荡荡的;但医院却人满为患,穷人之悲惨与狭窄的居所却在吞噬奄奄一息者。啊!让这些毫无用处的公馆接收除了臭气熏天的大街却无处居住的不幸者!既然富有的主人抛弃了它们,那么就让人民去居住![68]
巴黎穷人的直观感受也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证实。[69]
尖锐的政治矛盾和严重的贫富差距,让霍乱时期的法国民众认识到,他们不仅需要在身体的层面必须承受疾病的折磨,而且在心理层面也不得不体味政治与社会的不平等带来的痛苦。霍乱危机、拾荒者骚乱和投毒谣言让许多人得出结论说,法国社会本身已经病入膏肓。譬如,《立宪报》指出1832年的法国遭受着两种疾病——即霍乱和贫困——的双重折磨,认为贫困是霍乱的根源,并表示战胜贫困远比战胜疾病更为重要。[70]1832年底,法国剧作家欧仁·洛克的戏剧《患病的巴黎》对霍乱时期法国的社会矛盾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71]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里也曾经指出,法国患上了严重的“社会病”和“政治病”[72]。总之,1832年以后,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疾病的隐喻,用以形容法国社会的病态。
但是,如何诊治法国的弊病?隶属“运动派”的政治家看来,当务之急就是要限制“抵抗派”确立的政治体系,降低选举与被选举的纳税标准,避免金钱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原则。[73]共和派的人数虽然有限,但却坚决要求废除君主制,在圣佩拉热监狱的暴动中已经喊出了“共和国万岁!”的口号。[74]运动派与共和派的诉求只停留于政治层面,但在霍乱期间,社会革命的呼声也开始出现。普通民众不仅对自己被剥夺政治权利感到愤怒,而且要求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1832年4月初流行的《告人民书》甚至主张暴力:“用什么方法消除如此多的弊病呢?……应当用火炬、长矛和斧头披荆斩棘,铲除暴政!没有中间道路可选。”[75]与此同时,圣西门主义、傅立叶主义等社会主义流派逐渐流行,与之密切相关的“无产者”(prolétaire)概念自从1832年开始也逐渐得到普及。[76]某种意义上,在霍乱危机期间,我们已经能够依稀地看到了未来法国社会的影子。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3期)
[1] 乐启良,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 1832年3月26日首次发现霍乱的确证病例,同年9月24是巴黎报纸报道有霍乱死亡者的最后一天。根据时任巴黎警察局长热斯盖(Gisquet)的统计,总共有18402人死于此次霍乱病祸。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aris:Imprimerie de Ve Donde-Dupré,1840,p.439.
[3] Thibault Weitzel,Le fléau invisible.La dernière de choléra en France,Paris:Vendémiaire,2011.
[4] J.Lucas-Dubreton,La grande peur de 1832,Paris:Gallimard,1832.
[5] Louis Chevalier,Le Choléra.La première épidémie du XIXe siècle,La Roche-sur-Yon:Imprimerie de L'Ouest,1958.
[6] François Delaporte,Le Savoir de la maladie.Essai sur le choléra de 1832 à Paris,Paris:PUF,1990;Catherine J.Kudlick,Cholera in post-revolutionnary Paris.A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7] Patrice Bourdelais et Jean-Yves Raulot,Une peur bleue.Histoire du choléra en France 1832-1854,Paris:Payot,1987,pp.46-51.
[8] 对于霍乱在来到欧洲的传播路线,法国医学院在1831年8月8日做出的一份报告中进行过着清楚的描述:“自从1817年末直至今天,诞生于恒河河谷的霍乱从它的孕育地孟加拉,向南传到毛里求斯、帝汶岛,接近新荷兰。向西出现在俄罗斯的Kussuchou,向东传到北京。向北抵达西伯利亚、阿斯特拉罕直至阿尔切尔。最后,它攻击莫斯科、圣彼得堡,然而扩散到但泽和奥尔姆兹,随后伴着大量俄罗斯人的涌入,它入侵到波兰的腹地。”“Choléra-morbus.Conclusion du rapport de M.Double sur le Choléra-morbus”,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Journal de medicine et des sciences accessoires,tome 2,No.1(1831),p.285.
[9] “Mémoire sur le choléra-morbus qui règne en Russie,adressé de Moscou à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par M le docteur Jachnichen”,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Journal de medicine et des sciences accessoires,tome 2,No.1(1831),p.87.
[10] “Choléra-morbus.Conclusion du rapport de M.Double sur le Choléra-morbus”,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Journal de medicine et des sciences accessoires,tome 2,No.1(1831),p.285.
[11] Brière de Boismont,“Relation historique et médicale du choléra-morbus de Pologne”,Gazette Médicale de Paris,Journal de medicine et des sciences accessoires,tome 2,No.1(1831),p.394.
[12] Stanis Perez,Histoire des médecins,Paris:Perin,2018,p.320.
[13] Lousi René Villermé,“De la mortalité dans les divers quartiers de la ville de Paris”,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No.3(1830),p.309.
[14] Henry Heine,De la France,Paris:Gallimard,1994,p.69.
[15] Jules Janin,L'été à Paris,Paris:L.Curmer,1844,p.13.
[16] 警察局长热斯盖(Gisquet)在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各街区卫生委员会的工作热诚及其做出的巨大努力。他指出,各街区卫生委员会总共发现了将近20000个肮脏的房屋,给他提交了估计10000份的整改报告。当然,这位警察局长也不忘自我表彰,宣称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内,他给巴黎居民写了大约20000份的信件。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24.
[17]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p.426-427.
[18] Instruction polulaire sur les principaux moyens à employer pour se garantir du choléra-morbus,et sur la conduit à tenir lorsque cette maladie se déclare,Paris,1832.
[19]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p.545-555.
[20] Instruction polulaire sur les principaux moyens à employer pour se garantir du choléra-morbus,et sur la conduit à tenir lorsque cette maladiese déclare,Paris,1832,pp.2-11.
[21] Dominique-Jean Larrey,Mémoire sur le choléra-morbus,Paris:J.-B.Baillière,1831,pp.27-32.
[22] Ange-Pierre Leca,Et le choléra s’abattit sur Paris 1832,Paris:Albin Michel,1982,p.77.
[23]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p.533-537.根据路易·勒内·维莱美的统计,1832年霍乱期间正常营业以及在4月1日至9月30日歇业的3171家出租屋、旅店、客店,总共入住32434人。Louis Ré Villermé,“Note sur les ravages du cholera morbus dans les maisons garnies de Paris depuis le 29 mars jusqu’à 1 août 1832”,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 legale,No.11(1834),p.388.
[24]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p.539-543.
[25]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43.
[26]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60.
[27]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ar la liquidation de MM.Savalète ET Cie,Paris:Imprimerie de Cosset e Gaultier-Lauguionie,1839,p.2.
[28]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2.
[29] Pierre-Gaspard Chaumette,Résumé du système de né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Paris:Chez Noel Lefevre,1829,p.8.
[30] Cahier des charges du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le 29 Décembre 1831.
[31]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4.
[32]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6.
[33]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5.
[34]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7.
[35]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61.
[36] 警察局长热斯盖认为,在拾荒者的骚乱中,旧马车的主人是主要的教唆人和组织者。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62.
[37] Le National,3 avril 1832.
[38] 1840年,巴黎拥有的拾荒者数量估计在4000左右,成年男拾荒者的日收入估计是25—40苏,女拾荒者是15—20苏,儿童拾荒者则是10苏。Honoré Antoine Frégier,Des classes dangereuses de la population dans les grandes villes,Paris:Librairie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Médecine,p.104,p.108,p.109.
[39] 根据警察局长热斯盖的估算,巴黎存在1800左右的拾荒者,他们每天靠拾荒赚取1.5法郎,每年的总收入将近100万。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60.
[40] 《宗教与国王之友报》如是报道了霍乱毫无征兆侵入了巴黎:“它没有出现在法国其他地区,人们在边境也没有发现它。它是突然闯入了首都,在放纵、革命与不信宗教的中心站稳了脚跟。一份报纸说,这是一个最独特、最无法解释的事实。”L'Ami de la religion et du roi,3 mars 1832,p.421.
[41] Le National,3 avril 1832.
[42] Enfan Lallumette,Protestations adressée par le chiffonniers de Paris à M.Gisquet,Paris:1832,pp.7-8.
[43] Le National,3 avril 1832.
[44] Le Constitutionnel,3 avril 1832.
[45] Le Courrier français,3 avril 1832.
[46] Henry Heine,De la France,Paris:Gallimard,1984,p.110.
[47] Journal des Débats,3 avril,1832.
[48]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69.《辩论报》表态支持巴黎警察局的镇压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全生命而非支持某种政治体系,在于抵制夺人性命的灾祸而非反对某种原则”。Journal des Débats,4 avril 1832.
[49] Le National,3 avril 1832.
[50] Nettoiement de la ville de Paris.Mémoire présenté au conseil de prefecture du department de Seine,p.7.
[51] “De l’assainissement de Paris”,Gazette de l’Adminstration de l’Industrie et des Beaux-Arts,tome troisième,1832,Paris:Bureau de la Gazette de l’Administration,pp.176-177.
[52] L'Ami de la religion et du roi,3 mars 1832,p.428.
[53] L'Ami de la religion et du roi,3 mars 1832,p.427,p.444.
[54] 巴黎各家报纸关于霍乱的报道都是始于1832年3月31日,它们报道的病患人数和死亡人数均转自官方报纸《导报》(Moniteur),没有任何的出入。由于笔者无法获取《导报》,只能根据掌握的其中一份报纸《法国信报》,制定相应的统计表格。需要强调,表格的数字是指从霍乱爆发之日到报道当日的前一天,总共出现的病患总数和死亡总数,而并非是当日新增的病患与死亡的人数。
[55] 路易·勃朗指出,在霍乱爆发的高峰期,保守的说法是每天死亡800人,但多数人认为在1300—1400之间。Louis Blanc,Histoire de dix ans 1830-184,tome 3,Paris:Pagnerre,1843,p.236.
[56] 《辩论报》报道说:“据传,有人在商家的酒桶或肉铺投毒时被逮捕了。”Le Journal des débats,5 avril 1832.
[57] Le Constitutionnel,5 avril 1832.
[58] Le Constitutionnel,4 avril,1832;Le Constitutionnel,5 avril,1832.
[59] Victor de Nouvion,Histoire du règne de Louis-Philippe,tome 2,Paris:Librairie Didier et Cie,1879,p.566.
[60] Le Constitutionnel,5 avril,1832.
[61] Henry Heine,De la France,pp.113-114.
[62] Le Constitutionnel,5 avril,1832.有关可疑物的检查报告,可参见A Chevalier,“Examen de divers produits souçonnés empoisonnés ou pouvant causer des empoisonnements”,in 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 et de Médecine Légale,tome huitième,Paris:E.Crochard,1832,pp.311-324.
[63] 主宫医院的医生们宣布,“对呕吐物和排泄物作出的最仔细检查并没有提供任何中毒的迹象”,“在尸检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质”,“无论是在胃,抑或在肠道里,没有任何由毒药造成的损伤”。Le Constitutionnel,6 avril,1832.
[64]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489.
[65] Le National,3 avril 1832.
[66] Le National,4 avril 1832.
[67] Académie royale de medicine,Rapport et instruction sur le choléra-morbus,Paris,Imprimerie Royale,1832,p.32.
[68] Henri Gisquet,Mémoires,tome I,pp.482-483.
[69] 澳大利亚知名法国史家彼得·迈克菲指出,“西部巴黎富裕街区的死亡率低于17‰,但第8、9和12区的死亡率几乎接近30‰。同样,尽管1832年霍乱造成了卡西米尔·佩利耶和拉马克将军的死亡,但它在富裕的第二区里每107人中才出现1人死亡,但在第9区每22人便死亡1人”。Peter Macphee,A social history of France,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 Press,2004,141.
[70] Le Constitutionnel,6 avril,1832.
[71] Eugène Roch,Paris malade:esquisses du jour,Paris:Moutardier,1832.
[72]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雨果文集》第3卷,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6页。
[73] 在七月王朝期间,自由派的政治家分为运动派(拉斐特和奥迪隆·巴罗)和抵制派(卡西米尔·佩利耶以及基佐),前者主张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要不断降低纳税标准,向越来越多的人敞开大门,而后者则坚持选举和被选举的纳税标准始终应是200法郎和500法郎。对于纳税选举,奥迪隆·巴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已经存在某种把一切和金钱相连的倾向;应当反对它,而不是助长它。……否则,金钱将成为所有人顶礼膜拜的上帝。”Odilon Barrot,Mémoires posthumes,tome 1,Paris:Charpentier et Cie,1875,pp.252-253.
[74] Le National,3 avril 1832.共和派用普选解决贫富差距的信念,可以在激进共和派赖德律-罗兰谈论第二共和国确立普选制时所说的一句话中得到体现:“自从该法颁布之日起,法国不再有无产阶级了。”转引自Pierre Rosanvallon,Notre histoire intellectuelle et politique,1968-2018,Paris:Seuil,2018,p.95.
[75] Le Constitutionnel,4 avril,1832.
[76] 根据笔者在法国图书馆Gallica网站上的初步检索,1831年以前只出现一份标题中含有“无产者”概念的宣传册,但在1832年却出现了十多份:Charles Béranger,Pétition d'un prolétaire à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Paris:Au Bureau de l’Organisation,1831;Henri Aubert,En avant! Ou réflexions d'un prolétaire sur la position politique de la France,Paris et Lyon:Chez Tous les Principaux Librairies,1832;Jean Reynaud,De la necessité d'une representation spéciale pour prolétaires,Paris:avril 1832;L.D.,Le prolétaire destinées à l’instruction politique du peuple,1832;Selme Davenay,Cri d'un prolétaire,Paris,Imrimerie de Auguste Mie,1832;Joseph Babeuf,Aux prolétaires.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es prolétaires,Paris,1832,etc.需要指出,无产阶级概念的流行是否和1832年霍乱是否有直接关联,尚有待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