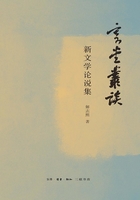
二
当格非写作《望春风》的时候,他的创作生涯早已过了浪漫抒情的阶段,所以他并不满足于将这部小说写成一部浪漫—感伤主义的乡愁抒情之作,而是以真正直面历史的勇气和生动自如的笔触,贡献给读者一部相当深广地反映出乡土中国当代命运的写实叙事之力作。
对格非及我这样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七八十年代离乡进城上大学的人来说,乡土中国仍是我们的生命之根,因此它的兴衰命运,在我们几乎可说是出乎生命本能的关切和挂牵。《望春风》显然寄托了格非发自衷心的乡土关怀,其所悉心描写的乡土生活,无疑都出自格非自己切身的乡土生活经验及其基于经验之想象。饶有意味的是,《望春风》的关怀、经验和想象,与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土叙事文学构成了有意味的呼应。比如,《望春风》第一章所介绍的两个相邻村落——“儒里赵”村和“窑头赵”村,前者多是读书士绅之家,后者多是出身窑工的穷苦人家。这不禁让人想起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里阎家山的“西头”与“东头”之分野。不待说,不论是北方村落阎家山的“西头”与“东头”,还是江南水乡的“儒里赵”和“窑头赵”,其间的分野都折射出了旧中国农村人的身份及阶级之差异。其实,即便是以读书士绅之家为多的“儒里赵”村,也有穷人如赵永贵的存在。赵永贵穷困潦倒、醉酒而死之后,留下了孤儿赵德正,而“儒里赵”村的士绅们唯一的德政,就是允许同宗的孤儿赵德正寄居在祠堂里,听任他靠吃百家饭糊口、勉强长大后当了一名下苦力的轿夫。毫无疑问,从赵树理到格非对旧中国农村阶级分化的书写,显然更符合历史的实情,他们对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分野之揭示,拆穿了当今的新修正主义史学所标榜的“儒教—乡绅礼治秩序”的新神话,和一些跟风而起的新儒风小说如《白鹿原》对乡土中国儒教礼俗的美化叙事及其对旧中国农村社会阶级分野之掩饰。而与《李有才板话》略有不同的是,《望春风》还增加了对旧中国乡村士绅如古琴家赵孟舒、“老菩萨”唐文宽、老刀笔赵锡光、理学家周蓉曾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样式之展示——他们要么孤傲自负而迂腐不通世务,要么投机钻营与时俯仰,要么装腔作势男盗女娼,看起来显然没有《白鹿原》里的朱先生那么博古通今、指挥若定的高大上,却也没有朱先生的方巾气而俗得更富人间味。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农村并且生长于农村礼教大家族的读者,我对乡土中国的儒教—礼俗文化传统也算有些切身的经验,坦诚地说,我更赞赏格非这种不跟风美化旧传统、旧礼俗的写实精神。
《望春风》随后的章节着重描写了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儒里赵”村之变迁。在土改运动中,穷棒子赵德正被选为农会主任,稍后又成为村支书,从此“抬轿子的管着坐轿子的”,“儒里赵”村进入了赵德正主政的时代,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望春风》所着重描写的核心人物。“儒里赵”村的土改相当和平、并不暴力,地主富农及其他上层士绅不仅仍然有活路,而且即便在新中国,宗亲的关系依然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并得到来自下层的村干部赵德正等人的善意保护。穷棒子出身的赵德正虽然掌握着权力,但他并没有利用权力作威作福、谋取私利。事实上,作为党员的赵德正既受到执政党的社会集体主义理想之感召,同时作为乡民的他也继承了渗透于乡土中国的仁义为公等儒家里仁传统之熏陶,毋宁说正是集此二者于一身,才使赵德正成为一心为民为公的农村好干部之典型。他尽可能公正地处理村里的事务,为了发展集体事业,不惜牺牲个人利益,拒绝给自己建私房、年近四十还没有结婚,而努力带领群众兴办学校、开拓荒地、兴修水利,使村里的教育状况和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格非显然是带着有同情的理解,来刻画赵德正这个新中国农村当家人的形象的。作为从穷棒子出身的乡村干部,赵德正可谓不忘初心、艰苦朴素、一心为公,他的个人生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一门心思想着为村民的集体福利和村里的集体事业尽力。为此,他谋划着办“三件大事”,有两件都在他的精心筹划和大力推动下顺利实现:一件是为村里建学校,这是普惠众乡民的创举,为此他把老首长资助他建私房的材料,无偿地拿来修建校舍,显现出一个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的本色。二是开拓磨笄山,壮大集体经济,这是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壮大集体经济的根本之举。为此,赵德正殚精竭虑且甘冒平祖坟之大不韪,力排众议、坚定不移,终获成功。值得注意的是,这第二件大事就发生在“文革”期间,作为大队支书和革委会主任的赵德正,显然也利用了“文革”时期破除迷信的文化革命精神,才做成了这件大事,而这个生动的事例也适足以说明,即使在政治激进的“文革”时期,其“抓革命”的政治仍然是为了“促生产”,新中国的农业以至于工业仍然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历史性进步。
赵德正当然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格非在描写他克己奉公的同时,也生动地叙写了他的世故人情乃至私情。赵德正与王曼卿的私情就是很有趣的事例。了解农村实情的人都知道,作为不尽合情合理的婚姻制度之补充,大多数的中国乡村都有一两个风骚开放的“大众情人”,王曼卿乃正是“儒里赵”村的“大众情人”。顺便说一句,多年前看过旅外作家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其女主角王葡萄是一个既如“地母”一样伟大博爱又像自由女神一样庄严神圣的农村寡妇,那其实是按照反思革命如何摧残人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捣出来的人物,所以虚假得像个牵线木偶。格非当然比严歌苓更了解农村和农妇,所以他写王曼卿既没有刻意贬低也没有有意拔高,而是恰如其分地写出了她的特殊性——作为一个出身卑贱的妓女,职业的磨炼使她颇懂风情,却又因为不能生育、不能自主命运,而只能被迫辗转于一些乡村士绅之手,受压抑的她不甘寂寞,因此成为一些乡村青少年的性启蒙老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王曼卿与赵德正的关系就是如此,对赵德正这样一个年近四十尚未婚配的男子来说,在婚前与别的女人有点私情、打点饥荒,那的确是其情难免的事;即使在与一个不甚解风情的女孩春琴结婚之后,赵德正仍然对王曼卿旧情难忘、藕断丝连。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道德污点,无损于赵德正作为一个公正有为的乡村干部形象,反而使他的性格显得更为血肉丰满、富有人情。的确,赵德正是一个深通人情世故的乡村政治家,很善于折中人情、妥善处理村民们的一些敏感问题。从他对唐文宽性侵小满一事的处理,可以看出他体恤人情、保护村民的苦心。谁也没想到喜欢孩子的“老菩萨”唐文宽竟然有断袖之癖,他性侵学生小满,这固然很可恶,但此事一旦传出去,愤怒的村民们会要了唐文宽的命,那就惩罚过分了,更重要的是年轻的小满也会因为这个丑闻而毁于一旦,那就更不值得了。所以赵德正与村干部们计议,决定压住此事的真相不发,而另找借口处理了唐文宽,也给小满的受伤害编出了一套很有说服力的说辞,使他免受第二次伤害。《望春风》借助诸如此类的情节和细节,写活了赵德正,一个并不拘泥政治教条而深通人情世故、很有头脑手腕而又不失仁义善良的乡村基层干部的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其他几个干部形象如梅芳等也都写得栩栩如生。
像赵德正这样的优秀村干部,在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里无疑是大量真实存在的,他们乃是新中国农村的真正主事人和顶梁柱。正是在他们的带领和推动之下,新中国的农村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读者也可从《望春风》里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直到“文革”时期的“儒里赵”村,村民的个性意识其实相当活跃,人性的解放比如男女平等、婚恋自由等都比旧时代有显著推进,更不用说教育的普及、卫生的改善了,这一切当然意味着现代文明在乡村的推进。
看得出来,《望春风》所描写的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新中国农村,与当今学界文坛的流行观点是很不一样的。即如在当今史学界流行的新修正主义史学叙述中,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就被贬斥为土改运动连根拔掉美好的乡绅制度,驯至摧毁一切伦常、善恶颠倒、民不聊生的乱世,而在当今盛行的新启蒙—新自由主义的文学想象里,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则被描绘成下层暴民专政、干部作威作福、既不平等也不自由、人性普遍压抑、文化被革命的黑暗中世纪。然则,真实情况如何呢?由于事情的复杂性,下面不得不多啰唆几句。
诚然,土改确是彻底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大革命,不可能完全和平地进行,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也确实发生了过激的错误,但很快就得到纠正,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土地改革进行得相当和平,远比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处理得妥当,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此后,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这个新的国家必须尽快实现现代化,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可是面对“一穷二白”和“地少人多”的现实,乡土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不能给中国农村带来新出路,更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带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更加严峻的挑战是,新中国的农业又责无旁贷地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唯一可以依赖的基础——它既要养活愈来愈多的全国人口,又要为工业乃至国防的现代化提供资源和资金。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农村实行土改、农民分得田地之后,新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却又不得不走上集体化的真正原因——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人口和工业建设、国防建设的巨大资金缺口,单纯、分散的小农经济是无济于事、无法支撑的,而只有实行农业集体化,以便取资于农业和农民,并辅之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激励和政策控制,才能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就此而言,新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并非所谓纯属乌托邦的社会实践,而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和农民被迫担当起整个国家的基础性角色,在执政党的推动下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广大农民在“革命”政治的约束和“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且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竭力为整个国家提供资源和资金,以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这条路走得很艰苦,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如“大跃进”和三年饥荒等,但功绩仍是巨大的——从十七年到“文革”,新中国农业和农民克勤克俭,为全国翻了一倍的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生存保障,也为工业建设提供了资金和资源的支持,从而使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夕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比较完备的现代经济基础。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个新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一切积极势能都发挥殆尽,尤其是集体主义的经济效能已近于失效、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则让人再难忍受,于是逼出了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由此迈入了所谓的新时期,这是一个走向务实的改良主义和趋于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所谓改革,当然是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问题之改革,但也必须认识到,改革同时也是以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成就为基础的,没有那些成绩,改革与开放从何做起?而检点此前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显然有两大问题:一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中国经济乃是执政党主导下的有计划的公有经济,执政党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不断以政治运动来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取资于民、壮大国家、迅速地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但革命政治的推动、激励和约束力必有限度,到“文革”后期已成强弩之末,此所以新时期的改革首先就要为中国经济松去政治之捆绑,逐渐恢复市场的调节作用。二是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固然有利于国家资本的迅速发展,却长期剥夺了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这同样不可能长久持续,而必有竭蹶之日,所以到了“文革”后期,人浮于事、消极怠工是普遍现象。因此新时期的改革之道就必然是逐渐恢复和增加个人的权与利,尤其是经济上的权与利,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活力。
所谓新时期的改革其实就是从这两方面下手的,而改革的浪潮则是首先从农村开启的。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恢复了农村社会的活力,改革的浪潮接着扩展到城市和工业等领域,迨至世纪之交,市场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我们必须承认,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发展非常火爆,国民各阶层都程度不同地提高了生活水平,但问题也于焉而生。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市场经济无所谓善恶,趋利是经济人的唯一动机,可是并非任何经济个体都有在市场经济里自由博弈的能力和资本。其中最被动无奈的是广大的农民。他们刚刚在家庭承包责任制里得以休养生息,却很快发现小家小户的他们根本无法在市场的海洋里参与博弈,土地里的那点收获,除了满足个人温饱,此外的事——如子女教育、就医养老等,他们就几乎无能为力了。残酷的现实是,他们所能出卖给市场的,一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力,二是他们仅有的一点土地。于是,大批农民进城或远走他乡成了农民工;而他们的土地则要么荒芜,要么——如果靠近城镇的话——就被征收为城市建设用地,最常见的就是成了房地产业的开发用地。土地被征收,当然也给农民一些补偿,钱啊,房子啊,但最大的获益者是相互勾结的官与商,至于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虽然有可能成为城镇居民,但在城市里他们不能不是最微末的存在,如同无根的游魂野鬼。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乡土中国就这样被市场经济迅速地劫收甚至摧毁了。究其实,土改、“文革”都没有摧毁乡土中国,倒是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并带动了整个新中国的发展,真正给乡土中国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却是今日中国触目惊心的现实。农村的工业化在给老板们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农村带来了遍地的污染,而所谓城镇化则往往迹近掠夺,农民的土地变成了高楼或废墟,他们从此失去了赖以生息的最后庇护地,或者外出打工聊以谋生,或者迷惘地寄居在用养命的土地换来的城市楼房里。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农村人心的涣散和人性的颓变——大多数人成了苟延残喘的“沉默的大多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的只是极少数人,如《望春风》里所写到的为富不仁的地产商赵礼平。在作品的最后,美丽的江南乡村“儒里赵”村被开发商赚够了钱之后惨遭遗弃,成了一片废墟。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继赵德正担任支书的高定邦,眼看村里无人愿意继续种地,于是决心修一条渠以挽救颓势,可是他却无能为力,自己也病倒住院了。此时财大气粗的赵礼平似乎不忘旧情,不仅给他付了医药费,而且命人调用机器几乎一夜之间修好了渠道,让大病初愈的高定邦感慨地认识到:“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当然,商人赵礼平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他随即和一个福建老板联手把“儒里赵”一带的土地“全部吃下来”,他花钱修建的渠道则成了污染的通道,逼得村民们不得不“自动”迁移——
那时的金锣湾早已被附近的化工厂污染。浓稠的黑水顺着高定邦下令开挖的水渠倒灌进来,很快就将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泽国。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
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们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留给卸任的村支书高定邦及其儿子的是沦落的命运——“父子二人挑着锅碗瓢盆,在朱方镇走东家,串西家,靠给人烧菜做饭,勉强度日。”命运同样落寞的还有不少干部和群众。
像《望春风》这样长度、广度和深度的乡土中国叙事,在当今中国文坛上还是很少见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感谢格非用力透纸背的笔触,记下了有情的与无情的历史——多半个世纪的乡土中国变迁史,而他寄托于其中的沧桑感怀和历史反思,更是用心良苦而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