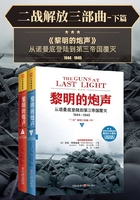
遥远的彼岸
随着诺曼底的海岸线越来越近,歌声也逐渐消歇。星星在夜空中闪烁着银色的微光,800架飞机组成长长的纵队,载着1.3万名美国伞兵奔赴战场。飞机降低高度向南方飞去,掠过墨黑的英吉利海峡,缓慢爬升,在根西岛与奥尔德尼岛之间急转向东。月光照耀着寂静的科唐坦半岛,这里素以养牛闻名,但是与德国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引擎的轰鸣声中,指导员喝令士兵准备跳伞。一阵咔嗒声过后,机舱内十六七名伞兵都纷纷把降落伞扣到了头顶的拉绳上。
1944年6月6日星期二,凌晨1点刚过,飞机舱门缓缓打开,一名上尉迎着气流站在门口向下望去,白色的波涛拍打着海岸。“向法国问好吧!”他大声喊道。红灯开始闪烁,提醒士兵们距抵达跳伞区域仅剩4分钟。其中3个椭圆形区域是率先抵达的第101空降师的跳伞区,另外3个是紧随其后的第82空降师的跳伞区。
法国消失了。灰色的云堤正悄无声息地逼近。由于云层很厚,飞行员几乎看不清飞机的翼尖。一架架飞机,乃至全部机群很快就被这道云堤吞没了。为避免撞机,C-47达科塔运输机时而攀升、时而俯冲,整个编队的队形很快就乱了。一片片黑魆魆的土地偶尔显现出来,但霎时就会隐没在夜空中。据一名目击者说,德军的防空炮弹就像“无数个点亮了的网球一样”刺入云层。
驾驶舱仿佛被敌军的探照灯光束和照明弹发出的灼热光线淹没,耀眼的强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尽管有命令禁止飞机为躲避炮火急转方向,一些初出茅庐的飞行员仍然不顾一切地左躲右闪。高射炮在夜空中发出阵阵闪光,曳光弹穿插其间,散发出“滚滚浓烟,烟厚得简直可以在上面行走”,一名伞兵在报告中写道。炮弹穿过铝制的机身,轰然炸裂,仿佛“有人向飞机一侧扔了一桶铁钉”。一架飞机的机身被撕开了一个2英尺宽的口子,机身冒出阵阵浓烟,3名美国士兵当场阵亡。机舱内的地板上污物横流,滑得难以行走,其他十几个人摔得东倒西歪,没有跳伞就返回了英国。
虽然东侧的云堤较为稀薄,但机组成员仍然不知所措,误把法国的一个村庄当成了另外一个。1个小时前,一批探路者已经在附近着陆,但其中有些人没有找到跳伞区。按照约定,他们本应使用7盏信号灯围出的一片T字形跳伞区,并通过电子发射机通知其他伞兵在跳伞区内降落。一些探路者着陆后,发现附近有大批敌军出没。尽管情况混乱,机舱内绿色的跳伞指示灯还是陆续开始闪烁。可是有些飞机的亮灯时间过早或过晚,导致很多伞兵哀号着落入海中。还有一些飞机上,成捆的货物卡在机舱门口,伞兵们不得不排队等候。等险情排除,飞机已经超出跳伞区2英里甚至更远的距离。
还有的飞机未能降低到500英尺的指定跳伞高度,或者未能将速度减缓到每小时110英里。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一些降落伞被撕裂,“尽管口袋底部经过了加固,但跳伞裤里的东西还是噼里啪啦地冲了出来”,一名伞兵回忆道。口粮、手榴弹、内衣和咕咕低鸣的信鸽在空中纷纷扬扬地散落。猛烈的炮火“就像一堵熊熊燃烧的火墙”。整个降落过程虽然只有半分钟,“但是像一千年那样漫长”,一名列兵后来告诉自己的家人。一顶降落伞不知怎么挂到了一架飞机的垂直稳定翼上,拼命挣扎的伞兵很快就被夜色吞没。在降落伞余烬未熄的碎片间,另一名伞兵奋力向东冲了过去。一些伞兵在着陆前未能成功打开降落伞,坠地时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从卡车后面掉落的西瓜”,一名伞兵回忆道。
“我一直抱紧自己的膝盖,尽可能地缩小身体体积,以免成为袭击目标”,第507伞兵团的一名伞兵写道,“然后拉动操纵带,以便尽快逃离身旁的大火。”一架C-47达科塔运输机的腹部被炮火击中后,火舌迅速喷进机舱,士兵们慌不择路,疯狂向舱门冲去。飞机的左翼突然擦地,导致引擎熄火,机身撞毁。虽然大多数伞兵得以幸存,机组成员却无一生还。在圣科姆迪蒙附近,一栋大楼被炮弹击中起火。火光照耀下,一名营长、一名副营长和一名连长尚未踏上法国土地,就在德国守军密集的火力下阵亡。此外,还有3名连长被俘。
第101空降师即将开展的“奥尔巴尼行动”,目标是夺取从犹他海滩到科唐坦半岛的4条增强堤道,每条堤道间相距约1英里。美国的战争策划者们得知,为了将登陆军阻隔在海岸线以外,德国工兵向海沙丘后的沼泽地灌注了2至4英尺深的海水,并且用卵石和树枝堵塞了8条溪流。然而盟军并不知道,敌军蓄积洪水是为了更大的野心。一些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代的运河、水坝以及科唐坦半岛东南部的水闸排干了杜沃河与梅德列河的河水,致使该流域变成了当地著名的奶牛牧场。
从1942年初开始,德国占领军关闭了部分防洪闸,打开了另外一些水闸,汹涌的潮汐形成了一个长10英里、深10英尺的碱水湖。由于当地芦苇和杂草丛生,盟军侦察机拍摄的100多万张航空照片没能显示出泛滥的洪水。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从半空跳下的伞兵更惊讶。在抵达法国沿岸前,他们已经在机舱内脱掉了救生衣,由于背负着沉重的装备,所以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最终都葬身于这片略带咸味的碱水湖。
凌晨4点,当数以千计迷失方向或散落四处的伞兵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前行时,52架滑翔机“就像一群乌鸦般”呼啸而至,一个德国人描述道。其中大都是50英尺长的韦科滑翔机,机身单薄得“可以用一支箭将其射穿”,就像一名上尉承认的那样。这批滑翔机均未安装机头盖帽,虽然盟军早在2月就已经订购,但至今仍未运抵。很多飞行员都从未在夜间飞行过,当滑翔机离开牵引机向地面滑行时,他们什么都看不清,只能凭感觉寻找陆地。与此同时,无数子弹穿透了机身单薄的外壳,那声音就像“打字机键敲打在松软的纸张上一样”,一名飞行员回忆道。一些士兵找到了位于布洛斯维尔的着陆区,而另外一些却在着陆时碰到了石墙、树干、睡梦中的家畜以及大片危险的木桩。这些木桩是为防止滑翔机着陆特地埋设的,人称“隆美尔的芦笋”。
在一次坠机事故中,第101空降师外科手术队的8名成员全部负伤。一架机鼻上印有巨大“1”字的韦科滑翔机跌落山坡,在潮湿的草地上滚过800英尺后撞向一棵坚硬的枫树,导致驾驶员和副驾驶员双腿骨折。在货舱内,第101空降师副师长唐·F.普拉特准将由于颈部折断而气绝身亡,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死里逃生的人们踢破滑翔机的外壳,“像蜜蜂从蜂巢中钻出来一样”,一名目击者在报告中写道。随后,他们开始搜集散落在诺曼底的小型推土机、反坦克炮和医疗设备。
星期二清晨,第101空降师的6 000多名伞兵中只有不到1 000人在袭击目标附近降落。约有1 500名伞兵飘到了着陆区8平方英里以外,其中大部分被俘或遇难。只有少数人靠法国农民从电话簿上撕下的地图安全抵达指定区域。一半以上补给物资由于掉入河边草原的水底而无法使用,大量无线电设备和迫击炮被毁,12门75毫米口径驮载榴弹炮中就有11门被淹。
一名中士向谷仓里望去,只见“人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稻草上,身上裹着血迹斑斑的降落伞,黢黑的脸上缠着满是血渍的绷带”。
即便如此,那些英勇无畏的士兵仍然一边引吭高歌,一边集合起来继续前行。一名军官敲响了一个农户的家门问路,并用字正腔圆的法语向农户宣布:“盟军已经抵达。”有人在二楼应声答道:“太好了。”第101空降师师长泰勒少将拔出手枪,另一只手拿着一按就发出声响的金属小玩具,一瘸一拐地在黑暗中摸索,搜寻迷失方向的伞兵。当一个法国农夫拿出一把老式步枪,请泰勒替他“干掉一个德国鬼子”时,泰勒婉言谢绝。随着晨光熹微,他可以隐约看到圣玛丽迪蒙一座11世纪的教堂。在高耸入云的石塔上,矗立着一尊张牙舞爪的滴水兽雕塑。当伞兵和德军在钟楼内以及忏悔室旁交火之际,泰勒向东侧的普皮维尔派出小股军队,赶跑了那里的守军,夺取了通向犹他海滩堤道最南端的通道。此地以北3英里外,第502伞兵团第3营也占领了北侧的两条堤道。
在诺曼底着陆5小时后,伞兵们已经在沙垄上排成一队,等待U编队从海面上现身。在他们的下方,沙丘的后面就是洪水泛滥的沼泽。
★★★
1940年6月,第一批德军部队在骑着马的军官带领下,唱着《我们要远征英格兰》,来到了圣梅尔埃格利斯镇。尽管德军没有继续挺进英格兰,但作为诺曼底的占领者,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不仅当地时间要以柏林时间为准,而且为确保“优等民族”能享受到足够的黄油和奶油,德军还向诺曼底居民发放定量供应卡。市政厅外悬挂着一面“卐”字旗,据传旁边的喷泉能治愈百病,因此经常有人前来朝圣。当地的教堂历史悠久,不仅装有哥特式的对窗,栏杆上还雕刻有四叶草花纹。德军入侵4年后,每逢赶集的日子,在教堂对面的栗子树和菩提树下,仍然有农夫出售羊毛和谷物。
一小队由奥地利高射炮兵组成的守军就驻扎在附近。他们驾驶的卡车以木材为燃料。司令官已经上了年纪,据说他曾经是维也纳一家报纸的音乐评论家,但现在,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醉方休。对于即将到来的盟军,德国人越来越不安。当年春天,德军就开始紧张地埋设“隆美尔的芦笋”(隆美尔发明的防空降障碍物,在特别适合着陆的地点打上木桩,并用铁丝相连,挂上地雷。——译者注),并对收听BBC电台的人们处以重罚,其慌乱程度从中可窥一斑。
对第82空降师来说,没有哪个袭击目标比圣梅尔埃格利斯镇更重要。第101空降师空降1小时后,该师6 000名伞兵将迅速登陆诺曼底。圣梅尔埃格利斯镇不仅是各条道路的交会点,连接北部瑟堡和南部卡朗唐的电缆干线也经过此地。如果不能拿下该镇,第82空降师“对梅德列河及其以西地区的进攻行动几乎毫无胜算”,一份军事研究报告称。因此,盟军在5月底突然改变了第82空降师的着陆地点,计划将这座沉寂的、仅有1 000名居民的中世纪要塞团团包围。
悲哀的是,波士顿空降行动比“奥尔巴尼行动”的情况更混乱。伞兵的着陆地点远远偏离了指定区域,有的向北偏离了15英里,有的向南偏离了25英里,还有人由于过于偏东或偏西,在坠入大西洋后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滑翔机紧随其后,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在着陆区方圆1英里的范围内降落。很多滑翔机遭到重创,反坦克炮和其他重型装备也损失惨重。
詹姆斯·加文准将曾经担心,这场战役将成为另一场小大角河战役。6月6日凌晨,在落入一座苹果园后,他手持M-1步枪,集结散落四处的士兵,向拉菲和谢迪蓬的要塞梅尔德雷桥逼近。月光下,士兵们脱得一丝不挂,跳入沼泽中寻找失落的装备。一列满载诺曼奶酪和空瓶的德国火车穿过密林,驶入谢迪蓬站。梅德列河沿岸的交火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激战,伞兵们纷纷开枪射击,除了敌军士兵,还有不少躲在牲口棚里的家畜也中弹死亡。一名中尉率领侦察队将三个受伤的德国人逼到了一条土路上,但他“认为自己无力羁押任何俘虏”,侦察队的报告上写道,“因此遣散了他们。”但战争的凶残已经初露端倪。
在该师3个空降步兵团中,只有第505团成功在位于圣梅尔埃格利斯镇西北的预定地点降落。一枚嘶嘶作响的照明弹引发了一场大火,惊醒了镇子里的居民与德国守军。随着教堂司事拉响塔楼的警钟,村民们纷纷拿起帆布水桶,从牲口市场的水泵取水,为教堂广场对面那座熊熊燃烧的住宅灭火。与此同时,一队C-47达科塔运输机肩并肩呼啸而至,突然出现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镇上空。大批伞兵从空中跳下,一边紧张地拉动降落伞吊带,一边竭力躲避身旁的火焰与德军的枪炮。
一些美国士兵在降落前就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名年轻的伞兵。他挂在树枝上“向下望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上的弹孔”,圣梅尔埃格利斯镇镇长写道。但仍有飞行员在炮火中穿行盘旋,找到了正确的降落地点,数以百计幸运的伞兵在着陆时毫发无损。人称“炮弹”的第3营营长爱德华·C.克劳斯中校集结了手下仅剩的1/4个营的兵力,在一名自愿担任向导的法国醉鬼的指引下,从西北方向潜入圣梅尔埃格利斯镇。他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搜寻德兵。为避免暴露行踪,他们接到命令不得开枪,只能使用军刀、刺刀和手榴弹。
德军已经在圣梅尔埃格利斯镇盘踞了4年之久。在守卫该镇的过程中,10名德国士兵死于非命,但大多数逃之夭夭,仅有部分士兵在睡梦中被活捉。在距离教堂广场400码的地方,克劳斯亲手切断了连接瑟堡的电缆。侦察兵在镇外用反坦克地雷和装有塑胶炸药的加蒙手榴弹设置了路障。6名阵亡的伞兵仍然悬挂在栗子树上,为了把他们放下来,葬礼队不得不割断了降落伞的绳索。
市政厅前,克劳斯从帆布背包里取出了一面美国国旗,在一根颤巍巍的旗杆上升了起来。1943年10月1日,当该营率先进入那不勒斯时,克劳斯就在当地升起了这面国旗。由于无线电设备已经在空降过程中全部丢失或损坏,凌晨5点,克劳斯派遣传令兵向师长马修·B.李奇微少将报告:“我已进入圣梅尔埃格利斯镇。”1小时后,另一名传令兵再次传出捷报:“我已拿下圣梅尔埃格利斯镇。”这是美国人解放的第一座法国城镇。
拂晓时分,816架飞机和100架滑翔机载着1.3万名美国士兵抵达欧洲大陆。仅有21架飞机被击落,这一数字远远低于空军中将利·马洛里的预计。然而,6个团中只有1个在预定地点降落,该团3个营的兵力已经损失过半,却是唯一一支建制较为完整的作战力量。空军司令没有提前出动气象侦察机,对诺曼底6月份常见的低空云层发出预警,可谓疏于职守。对于仅仅配备步枪和手榴弹的美国士兵来说,由于兵力分散,战斗力大大削弱。
但是,就像在西西里岛时那样,这种杂乱无章的布局“并非一无是处”。美国陆军的官方历史中写道:“分散的兵力让敌我双方全都晕头转向。”在科唐坦半岛的各个地方,不时传来电话和电报线被切断的刺耳咔啦声。美军命令被俘的德国人脚掌相抵,呈放射状平躺在地上,等着被送到战俘营。很多德国士兵在伏击中中弹身亡,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天色尚未放亮,一架美国轻型轰炸机首次飞赴欧洲上空,执行夜间照相侦察任务。在8 000英尺的高空,侦察机炸弹舱内那盏亮度为2亿标准烛光的电灯就像一个小型太阳,照亮了整个诺曼底地区。用掉了180张胶片后,飞机折回英国,分析人员逐帧查看,寻找德国坦克的踪迹。毫无疑问,德国必定会对科唐坦半岛发起反击。
★★★
距此50英里以东,英国第6空降师已经越过了法国的海岸线,急于一雪5年前的旧耻。英国士兵手持五花八门的“武器”——刻着脏话的砖头、绘有希特勒头像的足球以及从埃克塞特酒馆偷来的驼鹿头标本——跳出运输机的舱门,准备将德国人杀死在睡梦中。近5 000名士兵或跳伞或乘坐滑翔机紧随其后。
两个伞兵旅负责夺取奥恩河和位于卡昂东北方的运河,打通5英里以东流向大致相同的迪沃河,以确保“霸王行动”左翼的安全。在科唐坦半岛,曾经困扰美国士兵的种种问题如今同样困扰着英国人:一半以上的探路者在错误的地点降落,电子信号浮标和信号灯大都受损或遗失,还有的由于被误置在麦田里,被高高的麦子遮住,从空中根本看不到。在飞机左右躲闪的过程中,很多伞兵都失去了平衡,不得不推迟跳伞。其中一个机群里,91架飞机中仅有17架在正确的地点着陆。一枚高射炮弹穿透机身,冲击波将第3旅的一名少校掀了下去。由于双腿被强制开伞拉绳缠住,他足足在机身下悬挂了半个小时后才被拽回机舱,虽然衣衫不整,但好在安然无恙。返回英国后,他于6月6日晚些时候再次乘滑翔机抵达法国。
相比之下,那些坠入大西洋或水流湍急的迪沃河中的伞兵更加不幸。一名浑身湿透的旅长花了整整4个小时,才来到瑟堡的河堤上。他缝在作战服里的60个茶包也全部毁于一旦。“我们亲眼看见,降落伞的顶篷在光滑如镜的波纹中凹陷下去”,一名军官在报告中写道。此后50年里,迪沃河里不断有尸体被打捞出来。
种种磨难过后,盟军终于迎来了一次大捷。6架霍莎式滑翔机载着以前牛津市警察约翰·霍华德少校为首的181名士兵抵达法国。这种滑翔机以一位撒克逊王后的名字命名,由于在硬着陆时一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因此被戏称为“会飞的停尸房”。士兵们苦中作乐,一边在茶壶中兑入朗姆酒,一边唱起了《牛仔摇摆》和《蒂珀雷里之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蒂珀雷里郡士兵出征时唱的军歌。——译者注)。当飞行员高喊“解开缆绳”,并拉回与前方哈利法克斯式重型轰炸机相连的绳索时,士兵们的歌声戛然而止。整整3分钟,霍华德和手下鸦雀无声,他们挽着彼此的手臂,十指紧握,只有狂风在舱外呼啸而过,发出凄厉的声音。
以“和平女神”为首的三架霍莎式滑翔机一路向西飞行。一名飞行员发现了目的地,突然喊道:“天哪,桥就在那里!准备着陆!”滑翔机开始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地面上滑行,风的声音就像“一张巨大的床单被撕裂”,一名列兵描述道。起落架的轮子很快就完全磨损,三架霍莎式滑翔机弹回空中后,启动了制轮器着地。橘色的火光四处飞溅,一些士兵误以为那是德国的曳光弹。霍华德及其手下虽然惊魂未定,但是全都毫发无损。他们拖着斯特恩轻机枪和装满手榴弹的帆布桶,奋力扭动身躯,从滑翔机上大大小小的洞眼中挤了出来。
“和平女神”的机鼻遭到重创,距离机身不到50码的地方就是卡昂运河,河上就是矮墩墩的贝努维尔桥。一名哨兵见状立即转身,一边仓皇逃窜,一边惊恐地大声呼喊。一枚华利照明弹在空中引爆,照亮了黑漆漆的河面。50名敌军士兵——大都隶属于德国从东欧招募的“东线部队”——跌跌撞撞地向西侧的引桥冲去,枪声在桥梁和栏杆上乒乓作响。但一切都为时已晚,霍华德的手下已经用机枪和手榴弹杀开了一条血路。为了保持队形,3个排高喊着自己的代号——“埃布尔”“贝克”和“查利”。“只要看到有东西在动”,一名英国士兵后来承认,“我们就会开枪射击。”
在敌军的炮火下,一名排长中弹身亡。15分钟后,英军占领了贝努维尔桥。负责守桥的德国指挥官那辆装满内衣和香水的汽车也不慎跌入沟中。被俘后,为了保存颜面,这名指挥官要求盟军枪毙自己,但这显然是徒劳。随后,德军驾驶三辆摇摇晃晃的法国坦克向贝努维尔桥驶来,但其攻势很快就被反坦克炮摧毁。两辆坦克逃之夭夭,在一名失去了双腿的士兵从舱口爬出来后,第三辆坦克足足燃烧了一个小时。没过多久,霍华德少校得到消息,他手下另一股人马已经夺取了位于朗维尔附近的奥恩河桥。于是,他下令用加密无线电播发出了这则振奋人心的捷报,然后便开始挖掘战壕,以迎接敌人更加顽强的反击,同时等待援军到来。
变幻莫测的风向导致飞机在空中相撞,越来越多的滑翔机放下残缺不全的起落架,在奥恩河和迪沃河漫滩上紧急着陆,还有一些则骤然跌落。据说,一架霍莎式滑翔机穿过农舍,驮着一张双人床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床上的法国夫妇仍然裹在羽绒被里。在苍茫的夜色中,号角声四起,军官们开始集结四散奔逃的部队。一场激烈的交火过后,一名情绪失控的年轻伞兵喊道:“他们打死了我的战友!他们打死了我的战友!”随着士兵们不断阵亡,一座座桥梁被夷为平地。盟军俘虏了奥恩河上的敌兵,炸毁了迪沃河上的四座桥梁。
最危险的任务落在了伞兵团第9营的肩上。他们奉命摧毁梅尔维尔沿岸的炮台,因为其射程据说可以达到“霸王行动”最东端的剑滩。在护栏、地雷、带刺的铁丝网、灌木丛和战壕的环绕下,大口径火炮和200名炮手藏在重重铁门和6英尺厚的水泥墙后,他们的上方是厚达12英尺的泥土屋顶。750名伞兵参与了这次行动,但仅有150人在集结地点附近降落。按照计划,盟军需要60节爆破筒(即装满炸药的金属管),以突破带刺的铁丝网,但截至凌晨3点,人们只找到了16节。
盟军原定要在铁丝网上炸开四个缺口,但他们只炸开了两个。一批伞兵匍匐前进,徒手排除了地雷和诡雷的绊发线。为牵制敌军力量,突击队在大门处发动了攻击,消灭了数十名德国士兵,卸下了敌方大炮的炮栓。一名通信官把信件绑在信鸽身上,将这则消息传往英国。事实证明,这里只有两门75毫米口径大炮,而不是四门,其威力和数量远低于盟军的预计。虽然解除了梅尔维尔炮台的威胁,盟军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150人和我一起进入了该地区”,第9营营长汇报称,“但只有65人活着回来。”
在呈新月形的登陆地点两翼,空降部队伤亡惨重。在4 800名抵达法国的英军中,有近一半士兵因为降落的地点过远或伤势严重,而无法参加6月6日的战斗。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西侧美军不能参与战斗的士兵人数。尽管黎明尚未到来,但这些从天而降的勇士们却让这一天被永远载入了史册。虽然从一开始他们就被厄运和混乱所困扰,但仍然完成了大多数既定的任务。接下来,战争的胜负就要取决于那些乘风破浪、从海上登陆的勇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