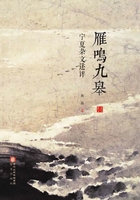
第二章 大漠孤烟直:张贤亮杂文随笔的启蒙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贤亮是一个响亮的存在。他20世纪80年代以小说名世,90年代后又创作了一部分在全国都产生影响的杂文随笔、创作谈、文艺杂谈,《小说中国》等甫一出版即在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张贤亮的一生是与国家与时代的命运紧密关联的一生,其小说成就斐然,杂文随笔则更直接关注人的心灵现实和对历史理念、国家发展、西部未来的哲理思辨,他用自身特有的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对命运的顽强抗争和对真理的持续思考,用灵魂、血泪铸就的智慧在中国思想启蒙道路上留下一名知识分子的探索和实践。张贤亮曾给陕西作家石岗题字:大漠孤烟甘寂寞,长河落日自辉煌。颇有几分自己的人生写照:因时代际会而沦落至西北边塞,又在新的时代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化旅游事业的突出成就而在西部繁荣崛起,孤烟直竖。
张贤亮(1936—2014),国家一级作家、收藏家、企业家。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在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从北京移居宁夏,在南梁农场插队,先做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管制、监禁长达22年。1979年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1980年调入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任编辑,重新开始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的重要作家之一。1993年在宁夏银川市郊创办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担任董事长。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无法苏醒》《早安朋友》《浪漫的黑袍》《绿化树》等,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一亿六》等,杂文随笔作品有《小说编余》(1996年)、《小说中国》(1997年)、《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2008年)、《心安即福地》(2013年)、《繁华的荒凉》(2016年)等。立体作品为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老银川一条街。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中的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中国文学也同样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文学史谓之的新时期文学就此拉开帷幕。身处宁夏并刚刚结束20多年监役与牢狱之苦的张贤亮使这一时期的宁夏文学没有缺席。1980年,改刊不久的《朔方》文学月刊发表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随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前身),紧接着作品由李准改编、谢晋执导拍摄成电影《牧马人》在全国公映。冯剑华在《西北大地上的文学绿荫》一文中说:“当历史一旦结束了它灾难的局面,翻开新的篇章之后,张贤亮便带着心灵的创伤和思想的成熟,令人惊异地出现在广大读者的视线里。”[1]这些作品甫一发表即获得好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接连不断。评论家阎纲以《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一文对他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他的作品因其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探索,一次次引起反响,波及世界文坛。曾三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
张贤亮长期生活在底层,西北地区的普通劳动人民给予他的温情和悲悯及其粗犷原始的生活状态化为他作文和为人的基本底色,底层人民的生活情状和作家的内心情感经过提炼升华,行之于文字。无论是80年代久负盛名的中短篇长篇小说还是90年代后的杂文随笔所涉及的题材和思考都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和社会风潮。作为一个有资本家出身背景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凝结的文字自觉超越苦难的历程,寻找并试图解答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借此唤起普通公民的思想认知和情感共鸣——作家的反思亦是思想启蒙路径的创作成果。在当下中国的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正在全国确立自己的地位,也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意义系统。就西部作家的创作来看,是张贤亮等人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就宁夏的文学创作而言,张贤亮毕竟不只是“一棵大树”,同时还是一个极具效应的鼓舞者和带动者,特别是对宁夏青年作家的成长及这个群体的形成,张贤亮功不可没。
第一节 满纸荒凉:从磨难到财富之间的距离
个体身处哪一个时代是偶然的,一个时代要发生什么却具有历史的必然,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承受特殊年代带来的特殊经历,这种经历或者不幸成为人生的磨难,或者有幸被作家转化为优秀的作品而成为精神财富。张贤亮则不仅把个体体验变为精神财富也以西部第一家影视基地的诞生将时代的创伤变成物质财富。坊间说他是中国作家里非常富有的,也是中国企业家里非常会写文章的,不一定绝对恰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从时代机遇、个体磨难到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之间,作家在水与火的淬炼中走过几重炼狱和天堂,除了作家内心冷暖自知,再就是他留下的文字了。笔者一直认为,文字是通向作家心灵最直接的通道,即使不是全面反映作家心灵史的全部,也至少相对最真实地再现了独特作家充满了谅解和宽恕的深层记忆。这种记忆,形式可能是小说,可能是诗歌,可能是纪实散文、也可能是杂文随笔,固然,一个如张贤亮这样的优秀作家,几乎在各种文学领域都有所长,只是他的小说盛名久负,遐迩皆知,以至于他的杂文随笔常常被小说的光芒遮掩而评论界鲜有涉及。
中国现代文学以曲折艰难的历程呼唤启蒙意识和人的觉醒,但是在一个世纪政治革命和社会解放的时代进程中,尤其是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末30年间历次社会运动形成新的政治规范的过程里,个人主体精神的独立逐步被完全遮蔽,“五四新文化”追求的个性自我和现代民主倡导的博爱自由被禁锢或驱逐。张贤亮作为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完整经历了此一历史时期的种种变故。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拾笔自由创作的张贤亮呼应伤痕文学的文艺思潮,创作了大量小说作品,随后也创作了多篇散文随笔,竭力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人性还原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之处,也会在受损害者本人那里看到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满纸荒唐言》《悼外公》《父子篇》《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等作品再现了特殊年代的苦难记忆和深沉的人生感悟。其中也有对一些中国历史的基本主题如启蒙者命运的思索,既警惕地提防对纯粹精神理念的沉迷,质疑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又流露出对精神信念旗帜一般的留恋。如同《绿化树》对章永麟的描述一样,曲折复杂的生活道路和坎坷命运,被作家书写成一篇篇内心启示录,彰显了人道主义作家高尚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心。
《满纸荒唐言》阐述了自己将痛苦的人生经验转化成文学创作素材的结果,只是这种“痛苦的结果”与漫长的痛苦的过程相比较,依然是“得不偿失”。作者将自己这一代作家与高尔基、契诃夫主观上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而有意识去经历痛苦捕捉众生相以备文学创作相比较,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中年作家,在踏上苦难的历程的同时,就把文学创作置诸脑后了。待痛苦的历程到了头,回顾过去,脑子里只剩下一股惋惜和惆怅而已。”于是他不堪回首地发出内心的呼唤:“不要再使作家经历那样的浩劫,不要再用那种方式来培养作家吧。”作家并不一味沉溺于苦痛,相反是在努力发现苦痛岁月中的温情,总要有所依傍才有勇气让心继续跳动:“孤独冰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这就是我因祸所得之福。”在多年以后的文字中,作家更多不是在叙述自身的磨难,而是在发掘磨难中人性美好的一部分,甚至变成了对那些苦难中温情的感恩:“我在困苦中得到平凡微贱的劳动者的关怀,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即使我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我就暗暗地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2]这是一种财富,虽然为之付出的代价太大。在这些自叙传一样的随笔中,作者在西北贫瘠的荒漠地区经受饥饿、疲惫和精神的困顿,细致地展示知识者受难情景和心里矛盾时,通常又展示了作家痛苦身心中难得的心灵救赎:生存和劳动都相当原始的底层劳动者,尤其是一些能干、泼辣而痴情的女性,其坚韧的生命力和灵魂的美,抚慰他濒于崩溃的精神,成为他超越苦难的力量。《我失去了我的报晓鸡》从一句“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的歌词跨越到上海“老建筑”的保存,“以暴力剥夺别人财富的革命者固然可敬,眼看着自己财富被别人剥夺而不加以毁坏的人也值得赞赏,因为有这样贵族气质的人,人类文明才得以传承下来”。[3]时过境迁之后,作家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悼“外公”》一文他感慨道:“这既是生命的无情,也是社会的无情。而对这两方面的销蚀和挤压,我们都是无力与之抗争的。”[4]在《心安即福地》中,作家意识到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其实是一体的,国家纷乱,他被下放,国家兴盛,他也崛起,“仿佛一片永远飘荡在河中间的落叶,从来都没有被榔头推到岸边停顿下。活下来的每一个当时‘打击的对象’,实际上都是事件的见证者,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次次地,历史的行程总违反个人希望过安宁生活的意愿,强行地在我身上刻画下一块块疤痕。”[5]作家的大半生与国家的苦难、国家的改革同呼吸,共命运,作家的生命已经很难与他度过了大半生的这块土地剥离,这块土地成了他的安心福地。

作家真诚地回忆往昔,纪念青春,剖析自我。在这样的创作中,写作完全是出于作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在随笔中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有过特殊经历的作家对自身经历的回顾,逐渐转化为现实成功者的怀旧,对昔日“辉煌”的构造,反思与批判色彩渐渐消失。在这样的潮流中,一些事件和场景通常被放置在叙述的关节处,构成电影场景般的静穆,对受难者及卑微生命的毁灭怀着深切的人文关怀。既在具体场景上也在意义象征上试图揭示其中的时代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意义。从作家个人角度来说,那十几年里有青春和生命最宝贵的部分,它影响作家一生,也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作家用文字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了那些经历,读者阅读作品,无论是否有共同的经历,都会对那段历史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考,这正是作家创作的使命所在。
第二节 人的解放:人才环境的改善与文人的另类思路
在国家开始改革开放走向新时代的历史发展中,经济体制和文化思潮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文艺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文艺启蒙的现代性追求就是文艺的自由创作和大众审美教育的革新。无论是“五四”时期鲁迅等强调文艺启蒙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还是20世纪80年代重新接受世界文艺思潮的洗礼而对社会批判和启蒙价值重新反思,中国作家都会从开放的时代汲取新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学近代几百年积淀的人文精神仍然滋养着中国作家的内在情怀,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也错综复杂影响着中国作家并不成熟的现代启蒙追求。“人性的发现,也就意味着对神的轻视。文艺复兴运动的功绩,在于将它在中世纪主宰人的生活的宗教观念逐步加以剔除,至少让其不具有以前那样的影响力。”[6]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引发了深层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则强调人的觉醒和人类发展的科学理性和人的自由,进一步推进了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启发人们反对封建专制思想和宗教的精神束缚,提倡思想自由、平等,注重个性精神。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与西方启蒙运动的价值理念一脉相承却又另辟蹊径,生面别开。启蒙意识引领下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赖以依存的精神家园之一,虽然这一家园在20世纪至今百年间遭受严重的迫害和桎梏,人的主体自由被专制、愚昧一再蒙蔽,唯有时刻保持警醒的知识分子依然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呐喊,这也正是张贤亮在新世纪初重提《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心理动因。呼唤人性解放的人文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的主体性和思想的独立性将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济政治转型中引发新的思想启蒙。

张贤亮的杂文随笔义无反顾地融入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对社会、历史、时代的质疑与思考深邃而宽厚,以锐利锋芒面对现代语境。《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创作于2008年,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作。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整个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张力,思想上的解放从人的解放开始。作家借此回忆了自己的半生经历,意欲不加虚构地描述一个荒谬的年代,真实反映那一段历史和几代人的真实感受。在详赡的叙述中,作家也在进行着精神伤痕的自我修复,借一个人的历史,反思国家的历史劫难,反思特殊时代的“身份识别制度”使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专制的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到的迫害,也最终构成“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
“根本问题是贫富之间能否流动,阶层之间能否流动。如果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草根’不能长成树木,穷人没有机会、没有可能成为富人,没有平等的自由竞争机制在富人阶层中将无德无能又无运的人分化衰落成穷人,那才是大问题。
任何社会都分有阶层,良好的社会制度是能保证阶层之间开放性的制度,是‘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的制度,是能‘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的制度。”[7]
作家坦言在中国作家中,自己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风起于青萍之末”,几十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则首先是人权和尊严意识的觉醒: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人们需要理想,但必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理想。
但是,怎样在新的社会形态上重新收拾已被摧残殆尽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8]
以冷静的笔触再现特殊时代的荒谬,不忘自我改造,重提人的解放,珍视每一个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恰是张贤亮此类政论随笔的启蒙意义的闪光处。他的杂文随笔直面改革的年代,紧扣社会的脉搏,以丰富的文字表达含量来阐述中国文人由传统到现代的身份转型,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文人,可以有多重身份,可以有“另类思路”。在《中国文人的另类思路》《美丽》等文集中,他的文章大体都分为“文人参政”“文人经商”“文人说文”“文人观点”等辑。作为六届政协委员,张贤亮诸多杂文都有参政议政秉笔谏言之功用,为THE GUARDIAN (英国《卫报》)《国际作家》专栏而作的《参与、逃避和超越》一文中,作家直言:“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种态度:参与、逃避和超越。”不论是参与、逃避还是超越,“都会有极为高尚的道德信念和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心理支柱”。[9]“文人参政”一辑中的大量文章如《参政议政应有一定的前瞻性》《建设文化大国》《加强地方人大、政协在地方政治生活的作用》《农村产权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拖欠民工工资应受法律惩罚》《发展职业教育,树立多途径成才观念》《关于筹建“文革”博物馆的提案》等,立场鲜明,观点明确,为国计民生献言献策,充分履行一位政协委员的职责。张贤亮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企业家,是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在经商领域,他依然有相关的深入思考:《“文人下海”》《宁夏有个镇北堡》《关于宁夏旅游业》《西部企业管理秘笈》《出卖“荒凉”》等文章,围绕镇北堡影视城的管理模式和成功经验,探索宁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前景和路径,这是中国作家鲜有的创作领域。
对历史的宽恕,对精神伤痕在灵魂层面的解脱,才能带来人的解放。而只有人的最大限度的解放,才能使一个作家创造最大的可能,参政议政,经营企业,从事文化旅游,出卖“荒凉”,尽可能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才是一个中国文人应该具有的风貌,在这个意义上,张贤亮当然已完全超越了一个小说家或杂文家的身份局限和视域局限,在个体的生命中,创造了普通写作者终难望其项背的熠熠生辉的价值。
第三节 指点江山:西部人物和社会现象的评点
张贤亮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的精神立场,关注作为社会个体的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和处境,思考中国文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经商、参政等参与社会事务的种种思考,毫无疑问,作家的自我道路与大半个世纪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事件、政策的关联是作品的基本结构。尤其自己长期居住在西部地区,作为生活并成名于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又以比较裕如的视角来描述具有特定风情、习俗、世态的西部市民生活图景、社会现象及西部企业现状。
张贤亮聚焦西部人才环境、西部企业管理、西部人民的民生百态。他生于东部,又常年生活于西部宁夏,自然对东西部差异、对发达地区和偏远落后地区各自的问题和优劣有着深刻的感受。从一个下放劳动的“右派分子”到知名作家、政协委员、企业高管,张贤亮具备了从底层一直到高层接触中国社会的机会,近距离观察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历程,为作家深入的思考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他对社会改革和国家经济比一般作家熟悉得多,又比一般企业家更多一些理性思考和文化批判,这些人生经验和社会批判也许不适宜用小说形式表达,杂文随笔就是他选择的最好方式了。他在1997年发表的自称为“文学性政论随笔”的20多万字的《小说中国》就是“小小地、略微地”说一下中国问题,说西部问题更是高屋建瓴游刃有余。张贤亮恰当地将企业管理的经验和文化产业的思考以杂文随笔的形式向公众充分表达的个人见解是符合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的现实的。他创办经营文化产业的经验和对文化产业化的探索类文章游离于小说盛名外而更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现实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延续,要洞察现实会发展到怎样的地步,怎样发展到那个地步,不与历史相联系就不是辩证唯物的历史观。”[10]
恰是本着这个目的,作家的文章围绕西部的核心问题层层展开。《宁夏有个镇北堡》和《出卖“荒凉”》中说到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自然是首要之功:

“再也没有一个作家像我这样,不但改写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还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地理面貌和人文景观,使周围数千人靠它吃饭。”[11]
20世纪90年代起他将银川西北郊的城堡废墟改造成国家AAAAA级景区和影视基地,其中享誉新时期至今的《红高粱》《老人与狗》《牧马人》《黄河绝恋》《双旗镇刀客》《大漠豪情》《新龙门客栈》《大话西游》等著名影视剧都在此拍摄,其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经济价值不可估量,“这比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还值得欣慰”。[12]他的文字记录了多元时代文人顺应市场经济潮流把西部的“荒凉”改造成一种世人瞩目的强烈的文化经济效应,宁夏成全了他的文化世界,他的文学才华又成就了他创造“荒凉中的神话”,在宁夏乃至中国文坛,这都是绝无仅有。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作者留下了《西部企业管理秘笈》《西部生意随想》等颇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同时又继续深入思考中国文化产业、宁夏本土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如《中国文化产业概谈》《对树立宁夏文化品牌的一点思考》等。
除了文化体制层面的考量,张贤亮在诸多文章中对西部人民群体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勤劳坚韧、逆来顺受、隐忍的惰性和热爱新社会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进行了细致剖析,继续延伸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往往会被升华为社会体制层面的探究。在《东西部的差距究竟在哪里》《给中国西部“把脉”》《西部,你准备好了吗》《西部“入世”》等文章中他呼吁人们在关注改善西部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要改善西部的人文环境。改善人文环境的根本在于改善人才环境,激活用人机制,尊重人才,改善投资者的经营环境,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来解决人才资源匮乏的矛盾,《西部吸引人才应有新思路新办法》《莫让孔雀东南飞》等都是这一层面的得力之作。

多重社会身份的张贤亮,以指点江山的情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笔下的文字深情渴望着自己所在的“安心福地”能更文明更繁荣。小到一个区域,大到一个国家,都是作家心系之处,都是作家想用自己的笔投射启蒙光亮的地方,只是张贤亮比其他作家更多了自信的气度,这来自于他曾经受的莫大苦难,来自于他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文化经济效应,更来自于他对国家对社会前瞻性的思考,这也是他为整个时代留下的“夜莺般的歌唱”。文明国家不是没有黑暗和龌龊,而是敢于揭露黑暗和龌龊;民主国家不是没有不公与缺陷,而是竭力去消除不公与缺陷。作家希冀的自由而繁荣的世界不只是停留在叙述身心伤痕、暴露丑恶不公,还在于推动社会制度完善、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中披肝沥胆,前仆后继。
2013年3月,由杂文选刊杂志社社长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作品集大成的《中国杂文(百部)》“卷六·当代合集之五”收录了张贤亮、贾平凹、张抗抗等杂文作家的杂文代表作,其中,张贤亮的《中国土著的廉政观》《家长会》《排泄与喧嚣》等杂文入选,这对作为作家的张贤亮也是另一重的身份定位和创作认可。文艺启蒙与人的觉醒是20世纪至今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我解脱和社会文明理性汹涌澎湃的激流,提倡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反对专制禁锢,肯定人本身的才能、情感和价值,在这一路径上,堪称宁夏新时期文化启蒙先驱之一的张贤亮及诸多杂文写作者共同为西部小省区的文化兴盛和生态改善而竭尽全力地前进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贤亮多次为吴宣文、牛撇捺、暮远、王庆同等人的杂文著作作序、题字并不吝笔墨地支持鼓励他们的创作。他曾在暮远的《夜行者独语》序言中表示自己一度热切关注宁夏作家的成长,也在努力发现宁夏作家的可塑之才。一枝独秀不是春天,大漠孤烟亦不免寂寞,作家在主观上期待着熔铸了自己苦难青春以及显赫后半生的宁夏能形成宽松的文化环境,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活跃,离东部发达城市、离世界文明的距离更小一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贤亮的存在是特殊的。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走过的弯路,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无疑是个体一生的毁灭,甚或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没落、沉沦,否定和反思才是对待灾难的主基调。当潜在的不幸变成现实的不幸之后,对于幸存者而言,可以认为是灾难磨炼了个体意志,丰富了人生阅历,但永远不会因此说灾难是美好的,尤其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又尤其弯路可能还在继续,灾难可能在新时代民族前行途中还要重演但集体的反思、警示又喑哑缺席时,一个经历过灾难的个体的倾诉和思考就极为重要。

[1]张贤亮:《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页。
[2]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174、176页。
[3] 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172页。
[4]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30页。
[5] 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79页。
[6]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7]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202页。
[8]1 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217页。
[9]张贤亮:《繁华的荒凉》,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第255页。
[10] 张贤亮:《张贤亮近作》,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第5页。
[11]张贤亮:《张贤亮近作》,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第9页。
[12] 张贤亮:《张贤亮近作》,文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0页。

一名新闻人,以自己的文字观察、瞭望、考量、记载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和人的历史。
——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