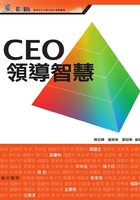
問答Q&A
艾默生的品牌重組策略
問:在《財富》雜誌的一項調查裏,艾默生被列為全球最受讚賞的公司之一,僅次於通用電氣和新力。艾默生究竟有甚麼魔法,令看來沉悶的電子製造公司深受愛戴?(劉燕玲)
答:如剛才所言,艾默生一直努力不懈,長時期維持競爭力。至於在過去五年,較特別的要算是重組我們的品牌策略。公司在過去25年併購了超過200家公司,它們多數是行業或市場裏的領先者,本身已有很強的品牌。你們或許不認識,但對於業界的朋友來說,谷輪(Copeland)、力博特(Liebert)都是很有名的品牌,甚至比艾默生更有名。
我們要為多達60個品牌做營銷工作。大家大概知道P&G旗下也有很多品牌,例如Head & Shoulders、Olay、Wella、Clairol……但在它們那一行業並沒多大關係,因為消費者自然會做決定。可是我們不同,我們的產品很可能都由同一個客戶購買,結果艾默生共有七至八個部門或品牌和同一個客戶接洽,客戶會不明所以,說:“艾默生,你給我一張賬單就可以了,為何要分成七張?我只想和一家公司接洽,而不是有七個不同的推銷員打電話給我。”
我們大概在2000年認真處理這問題。我們聘請了一位首席營銷官(chief marketing officer)統籌此事,並採用一套overbrand的品牌策略,即把各品牌都歸入艾默生這個母公司品牌裏,各子公司品牌依然存在,但以艾默生這個品牌來和客人接洽,溝通起來會比較容易明瞭。現在客戶都知道艾默生是誰,儘管對下仍然有一大串子公司。這做法很有效。所以我一開始時便說品牌是很有效用的,若能善用,會為你帶來很大的競爭優勢。採用新的品牌策略後,不僅有助和客戶溝通,也有助和員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溝通。客戶終於恍然大悟:“噢,你就是艾默生,你有這麼多好東西。”過去一段長時間,我們沒有和受眾(recipients)好好溝通,所以也沒有人認得我們。現在他們知道了。
除了加強品牌和重整品牌方面的工作,我們亦透過電子商業工具來加強和客戶的聯繫,如採用客戶關係管理(CRM,即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透過這些效果顯著的工具,即使我們有時不能跟客戶見面也可以保持聯繫。艾默生非常重視電子溝通這渠道。
另外,艾默生在過去五、六年備受注目,也得歸功於我們在新興市場的成功。我們不只進入中國,還同時前往俄羅斯、拉丁美洲和東歐。只可惜我對那些旅程所知不多,故只能和你們分享中國之旅。
艾默生如何推動創新文化
問:艾默生在科技創新方面贏取過很多獎項,這和艾默生的文化是否有關?這文化和其他香港公司的文化有甚麼差異?(陳伯強)
答:我對其他香港公司認識不深,只在20年多前曾為其中一家工作,我已是脫節了。但我可以談談艾默生的文化。
你可以讀讀我最初介紹的那本書,書中詳細論述我們的文化。有一點是知易行難的──我們的架構總是非常簡單。我們是環繞着工作來組織人手的,不會架牀疊屋。第二,我們很重視策劃。策劃二字看似容易,但其實可以很痛苦;我們的策劃會議往往由CEO或COO(chief operating officer,首席營運官)親自主持。如果你要參加策劃會議,你便要直接面對CEO或COO;若你的準備不充分,不消兩秒他們便能對你狠狠的迎頭痛擊,使你非常尷尬。
我記得我第一次要開這類會議前,失眠了兩星期。我很擔心,不想在CEO面前出醜。但過後我覺得非常受用,由於他們很注重策劃,促使我深入思考每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只要那個計劃獲通過,我便可以安心地執行,知道多數不會有問題出現,因為我已作全盤考慮。
艾默生向來以行動見稱。我們不尚空談,會注重實務。當然我們也有很強的監控系統及跟進行動。這些都是基本概念,但知易行難。那需要很多工夫。談到創新,艾默生有一套獎勵制度。營運部門如能構思一項新產品,便獲獎賞。何謂新產品?那必須是一個新的平台、新的設計。改良現有的產品並不算創新。新產品的週期只有五年,在市場推出了五年後,它便不再稱作新產品,那營運部門又要構思新的東西,否則他們的獎金和花紅便受影響。艾默生專注於新產品,會檢查及衡量新產品,及獎勵構思出新產品的部門。
當然我們也很重視全球的團隊合作。不知你曾否為跨國公司工作?其中一個難點是打破地域間的障礙。例如香港的團隊跟南斯拉夫的團隊可能難以溝通,他們又可能會想保護各自的地盤。
艾默生則強調全球的團隊合作。那能帶來更優良的業績。因為只要全球團隊互相合作,我們就可以日以繼夜向前邁進。香港的同事睡覺了,美國的同事便起來,工作又可以繼續,生生不息。
另一個成功因素是比競爭對手更快發明新科技。要怎樣做?就要靠眾人合作。我們在經濟環境不景氣時也會繼續投資科技,那是很重要的。
技術轉移要注意的事
問:我對你談到的技術轉移特別有興趣,因為我也是在科技公司工作,對象是中國市場。技術轉移能否加快分銷?藉着內地夥伴自然成長(organic growth),它是否可以幫助我們以低成本加快分銷產品或技術?但你說到未來可能會後悔。你如何取捨?(趙麗娟)
答:我想如今我要再做技術轉移的話,我會建議你務必花很多時間在細節上,例如合約上那些微小的字。回首1978或79年,由於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了解不足,簽了一紙合約,同意了出讓技術,但在合約完結後卻無法完全控制產品品質及功能表現。
我們在轉讓技術時的確也受惠,雖然得益並非來自直接銷售。我們透過夥伴把產品售予市場,從而為我們帶來收入。我們沒有直接把產品售給市場,而是由技術夥伴裝嵌,再售賣給最終的顧客。
關於技術轉移,我並不是說要完全敬而遠之。我只是提醒大家要確保在合約完結後也能保障自己。你如何確保產品質素和功能表現不會“走樣”?還有,你應否准許夥伴使用你的品牌?夥伴的產品應否看起來和你的一樣?這些都是你要留意的地方。
我記得當年的第一張技術合約,是由人手從打字機打出來的,也許因此大家當時都想把合約弄得越短越好,以免經常要修改。我還記得當年負責此事的人,給我看過他那部手提打字機。他帶了去西安,準備這份合約。那真是要很多工夫。但今天有電腦了,這不再是問題。
總的而言我分享的是我們的經驗,到你落實時,特別小心我剛才所提的問題就是了。如果你能防範這些問題,而你的夥伴又為你帶來收入和業績,那當然值得做。
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你除了可以作技術轉移外,還可以成立自己的公司,及收購其他公司。你要比較一下這三個選項,何者長遠來說對你是最有利的。如追求短期業績,那技術轉移可能仍是捷徑。
中國經濟增長和公司表現攸關
問:我很想知道艾默生如何在中國取得成功。有一點很有趣,你們在1978年進入中國,而你們在中國的旅程,跟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十分吻合,你們亦在上世紀末突飛猛進。那麼,你們的成功是否得歸功於中國的增長?(紀文鳳)
答:中國的經濟增長固然對我們在中國的成長很有幫助。若中國沒有經濟增長,縱使我們有最好的技術和策略,也無用武之地。中國的經濟狀況肯定是關鍵因素。
話雖如此,在這段期間進入中國的公司不計其數,其中有多少家成功?跟我的同輩談起,跟眾多投資中國的跨國企業代表談起,他們總抱怨:“我們仍沒錢賺,你是怎樣做得到的?”之類。
雖然經濟狀況良好,經濟增長亦持續迅速,但還是有贏家有輸家。當然我說過我們會先確保有銷售和收入,才會再作投資。
我知道有一家公司,夢想在中國會有數以億計的消費者購買它們的產品,於是一口氣成立了多家合資企業,並聘請了數十位美國高層人員舉家遷居。他們認為中國正是那應許之地(the promised land)。幾年後他們把一切都結束了,撤出中國,提起就令人傷感。那究竟艾默生和它們有何分別?
這家公司在投資前,並沒有確保銷情,它們以為一到中國便自然有銷量。可是中國並非如此簡單。人人都可以製造產品,但如何銷售?那很考工夫。你得對這個國家很熟悉。
“關係”一詞被濫用
問:就我經營的範疇,內地只准成立合資企業。那麼,如果我真的要進入內地市場,你會有甚麼建議?(邵國強)
答:我試試這樣回答吧。在我親身走這趟中國之旅時,我也讀了一些書,並向他人學習,而世界各地的商學院也聘請了中國專家講授內地營商之道。我覺得有個詞被濫用了,那是“關係”。有人說,如果你不搞好關係,在中國就死定了。
我吃過教訓了。我的經驗是在做任何事情前,你還是要有良好的商業計劃。關係能幫助你實行這個計劃,但如果你的計劃核心就只是關係,那就只好等上帝拯救了。而且關係會變。如果對方的接頭人物升職或降職甚至坐牢,你便失去所有聯繫,又要重新開始。
所以我還是建議你回到最基本的。看看你的商業計劃是否健全和周詳。有些事你若做不來,是否有夥伴可以幫助你,而那夥伴是否忠誠可靠,更重要的是他在和你合作時,是否有共同的目標。其間可能會有很多問題,如文化衝突,但擁有共同目標和願景是必需的,然後再適當地運用關係來幫助你解決問題,但關係絕對不應是商業計劃的基礎。
收購合併不能只看財務數據
問:我在中國也有好幾年工作經驗,也是從事電子製造業。你如何在中國實行那種重視策劃的文化?中國的管理人員不習慣多做計劃,也沒有經驗。但你要他們跟隨你的模式,一起爭取表現,維持理想業績。那是怎樣做到的?(姚美玲)
答:好問題。這真的不易。我提過我們早年在亞洲派駐了高層人員,他們為亞洲的經理帶來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那時我們在亞洲還沒有太多員工,現在則有三萬多人了。當年那些高層人員經年累月地和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策劃。很多人都藉此親身體會到艾默生管理文化的精粹。
第二,在中國我們都盡可能成立全資公司,即使是合資企業我們也盡可能爭取控股權。這樣我們便可以從一開始就引入我們的文化,薰陶公司裏的每一個人,教導他們艾默生的經營模式。
在內部我們有一個總裁營運報告(President Operating Report,簡稱POR)。每月,世界各地的經理都要提交報告,並整合成為一份中央資料表。如果你達標,管理層便會問你是否能更上一層樓;如果你不達標,管理層便會查問原因。如果是因為市場一蹶不振,管理層便會問你將採取甚麼辦法來扭轉情況。
這份報告每月一次,而每天跟員工的互動便會以這報告為依歸,再度鞏固艾默生的文化。
不過成立新公司並非最難的事,最具挑戰的反而是收購公司。它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管理理念,你要如何把它改變過來?這個課題可以討論三小時甚至三天。
但我想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剛才談過一宗七億五千萬美元的收購,那次收購計劃很成功,而我們只是派了三個人去管理這家新公司,三個人而已。
有機會讀讀Mr. Knight這本書,裏面談到如何綜合不同的文化。因為我們收購過很多公司,已習慣了把不同的文化迅速融入艾默生的文化。
可惜時間有限,不然我們還可以討論併購,討論如何融合不同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找收購對象時,必須先看看對方的公司文化是否為你所接受,不然不要簽約。很多人收購時只看數字,看財務數據,但對文化差異卻置若罔聞,這是大錯特錯。最近有一宗收購合併,兩家公司合併後市值下跌七成,為甚麼?
那不是因為商業計劃不周。它們已做好計劃,財務數據看來非常理想,可是它們的文化合不來。我個人對企業文化或企業DNA特別感興趣。成功的企業都有些甚麼特徵呢?這是很有趣的題目。我想如果我知道答案,那便可以幫助艾默生收購更多成功的公司。
(本文內容出自2006年3月6日香港中文大學EMBA論壇,陳志輝、盧榮俊統籌,劉燕玲、陳伯強主持,主講人以英語發言,由蔡慧蓓筆錄,謝冠東翻譯為中文。)
(1)編者註:范鴻齡及蘇澤光的演講收錄於中大EMBA叢書7《CEO實戰智慧》(商務印書館,2006),紀文鳳的演講收錄於中大EMBA叢書8《CEO營銷智慧》(商務印書館,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