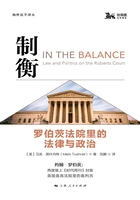
前言
在罗伯茨法院寻求平衡
ix
2005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资格听证会上,约翰·罗伯茨首先向各位参议员例行致谢并优雅地对其导师兼前任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过去一年中尽职尽责的奉献”表示了致意,随后他在开场白中加入了以下内容:“法官与大法官只应顺从于法律,别无其他。法官就像棒球裁判员。裁判员从不创设规则,只是规则适用者。”裁判员和法官必须“保证每个人按规则行事”,但“没人专程跑到赛场上去看裁判员表演”。他宣称自己虽然没有“既定议程”或“平台”但又“承诺”会以“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每个案件,继而又回到了其开头部分的比喻,“我不会忘记自己的工作就是判断是好球还是坏球而不是投球或击球”。
五年后,艾琳娜·卡根(Elena Kagan)在自己的提名听证会上谈到了罗伯茨这一有关裁判员的比喻。像时下绝大部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一样,2010年7月的时候卡根三缄其口,拒绝回答任何可能被呈交法庭的问题。(这一如今司空见惯的策略可能令人对这类万众瞩目的听证会的宗旨提出质疑。)不过,她比之前的罗伯茨还是略为开放。谈及罗伯茨的“裁判员”一说,她认为该比喻虽“贴切”但“亦有其局限之处”。如果其本意指法官不应偏向某一方,“比如,裁判员走过来说‘把所有得分都判给费城人队’,那这个裁判员就不怎么样”,这一比喻就有些意思。她又说,不过“这一比喻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暗示法律是某种机器人企业,带有某种自动性,一切都好办,我们只要站在一旁,计分显示坏球或好球,一切都清晰明了,这一过程无关裁定”。她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法官“必须进行裁决”。
x
有些学术界的批评人士认为她对于法官实施裁决的认定与她所持的决定“一直以来都是律条”的主张并不相符,她一再重复这一主张,该主张肯定已经写入了其发言之中。我认为她的这一观点微妙而且深刻:法律一直与司法判决的实施有关。“法律不是个人看法,不是道德观点,也不是政治观点。”然而,重要的是,法律也不是某种“机器人”或“自动化”企业。
卡根的就职确认听证会预示了卡根可能在最高法院带头反对罗伯茨大法官。卡根担任总检察长的那年,罗伯茨似乎就了解卡根可能会入职最高法院并成为其中的一股重大势力。在一桩相对平淡的案件中,卡根面对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大法官的一个问题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似乎斯卡利亚大法官是她的一个学生。首席大法官打断了她:“通常问题是由我来问的。”卡根为此进行了道歉。罗伯茨和卡根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卡根担任总检察长任期中最有趣的特色。正如法院观察家达赫利亚·利斯威克(Dahlia Lithwick)所说,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干巴巴的文字记录中并不明显,但如果你在读这些记录时用心倾听,你就会有所发现。在一次激烈的交锋后,罗伯茨声称卡根的立场“绝对令人震惊”。卡根回应说:“美国政府真是个复杂的地方。”对此罗伯茨大法官不屑一顾地回应说:“你说得没错。”
xi
在其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罗伯茨法院在党派分立方面非常均衡: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大法官有五人,而民主党总统提名的有四人。最高法院内部在思想对立方面也十分均衡,罗伯茨和卡根对于宪法各执一词,法律与政治搅在一起而各自权重又略有不同。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曾为法学教授)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注意到了这一对立,宣称他将对于罗伯茨的就职确认投反对票:
尽管因循判例和成文法或宪法建设规则能够处理呈交法庭的95%的案件,而在绝大部分时候斯卡利亚或金斯伯格(Ginsburg)式的大法官对这95%的案件的判决都会如出一辙,但对最高法院来说重要的是剩下的5%才是真正的疑难案件……对于这5%的疑难案件来说,宪法文本并不直接适用,因为这一法规的语言表达不够清楚。诉讼程序本身不会带来判决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其关键因素来自法官的内心……
奥巴马明白,在这5%的案件中,法律使它们的情况处于开放状态而“关键因素”来自法律之外。这一因素就是政治,不是我们在国会山看到的日常党派政治,而是有关原则,有关以最好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政府以使其能够保护我们的自由和安全、彼此竞争的不同愿景的政治。然而,说它们有关原则并不是说它们是纯粹理性主义的。对我们的政治活动——诸如总统如何领导其政党以及各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提名和诉讼——进行组织的那些更大的结构生成并支撑这些愿景以及大法官对它们的实施。
xii
《制衡》一书认为罗伯茨法院里面的平衡一直受到上述政治结构和政治愿景的左右而且将来仍会受到其影响。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卡根大法官都是这些结构和愿景提出者所造就的。最高法院的未来不仅将由奥巴马总统及其继任者的提名塑造而且也将由罗伯茨和卡根对于最高法院中智识领导权的争夺塑造,因为各方力推的有关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平衡的观点格格不入。《制衡》暗示我们,形式上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统领,是“罗伯茨法院”,而思想上则由卡根大法官所统领,是“卡根法院”。
当下罗伯茨法院中的近乎平衡体现于其判决之中:有些是“自由主义的”,赞成《平价医疗法案》(“奥巴马医改”),废弃了某些布什政府的反恐怖主义提案,有些是“保守主义的”,赞成联邦有关晚期堕胎(“成形胎儿堕胎”)的禁令、“海勒持枪权案”以及公民联合会竞选经费决策。此外,整体来看,罗伯茨法院的工作略显怪异。单从人员而论,人们可能会臆想罗伯茨法院肯定是一个保守主义法院。不过,它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法院,保守主义者对于《平价医疗法案》判决的怒火中烧即为明证。
它并非百分之百可靠,也就是说,它并非共和党的玩偶。不过,虽然个中情况十分复杂,罗伯茨法院的判决符合与21世纪初的共和党相关的主要宪法立场。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命罗伯茨法院的核心人选时基本是称心如意的。民主党一边的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也同样如此。
xiii
本书指出,罗伯茨法院试图使最高法院的工作成为当代政治的组成部分,这一论述可能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我前文勾勒的复杂图景。本书部分内容涉及任命政治学,我在第二章将对此加以探讨。本书另外一部分内容涉及宪法法律部分。在本书中,我始终认为人们应当严肃对待法律论据而不应简单地把法官们的判决归罪于“政治”。不过,人们也不应执拗于法律论据。法官策略性地将论据作为更大型活动的组成部分,因而人们需要专注于这些策略所服务的更大的战略。本书整体上讲述的是时下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自称要论述政治并不意味着大法官们看民主党或共和党搭建的平台或领导的脸色行事。大法官们的行为确实会对总统和国会之所能为产生影响,对此大法官们心知肚明。不过,通常来说大法官们比总统或政客拥有更长的时间来确定其政治形式:大法官们关心的是未来几十年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政客们关心的是下次选举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下一次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后,短期平衡可能会发生变化。
任命政治学意味着大法官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他们被任命的那一历史时刻他们对于宪法的整体看法与那些政党的整体观点相一致。政党是会变化的。某个大法官任职时间越长,其被任命时所附属的那个“政党”越有可能变得面目全非。最为戏剧性的是,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所属的共和党与小布什所在的共和党不同,因而肯尼迪的“共和主义”与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的并不相同。2013年带有极强的茶叶党(Tea Party)色彩的共和党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当选总统时的共和党不同,甚至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时的共和党也不同。约翰·罗伯茨的宪法哲学成型于里根任期之前和任期之内,人们没理由认为他是一个因为党内新领导上台而改换观点的党派黑客。(正如我在第一章将讲到的,要理解保守主义者所称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平价医疗法案》判决时的“背叛”,时间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xiv
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罗伯茨法院的所有判决都可以用党派术语加以解释。另外,还有奥巴马参议员所描述过的95%的案件,对这些案件的判决的最佳解释就是大法官们认为这是法规和判例的要求。例如,2012年最高法院对某个案件作出了判决,该案提请对生父亡故18个月后出生的子女(其生母系利用孩子父亲的冷冻精子而受孕)是否能够依据《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1935)而获得“遗属抚恤金”作出判决。法院判决一致通过,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出具的书面意见是“除非该州法律认定其为继承人”。如果您认为自由主义者始终希望将社会安全这张大网最大化,从本案中您可能嗅出某些政治的味道,不过您这么做就太傻了。该案提出了法律解释以及行政法中的一个直来直去的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政治意味。对其结果的最佳解释就是各位大法官认为“法律”支持金斯伯格法官的分析。这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所说的法官的工作就是判定好球和坏球时要表达的意思。他说得没错,只不过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关于那些没有或少有政治意味的案件。
对于那些确实带有政治意味的案件,情况又是怎样呢?我非常肯定大法官们不会费神去思考自己怎样做才能使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治特征更为靓丽(或更为阴郁)。然而,他们的行为支持主要党派就宪法的内涵所持的许多立场。正如“教会女士”在“周六夜现场”节目中常常说的,这并非仅仅出于行事方便。这来自那些令五位共和党被任命者和四位民主党被任命者入选,以及各政党和利益集团形成其自身政治结构和战略的政治结构和战略。
xv
然而,即便大法官们的确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自身(事实上并非如此),了解上述事实并不会有助于我们对最高法院行为的理解。假如,在最高法院听到有关奥巴马医改案的有关争议的那一天,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早上醒来后心想:“这件案子我该怎么判才能让共和党的候选人在11月大选时击败奥巴马总统呢?”他将无法给自己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最高法院对该案进行审查的那天,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其博客中写道:
那么,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支持或驳回或搁置该指令,会带来什么政治后果呢?如果法庭支持该指令,奥巴马政府将被证实清白,兜里塞上两块钱,他们就可以搭上地铁四处溜达了。支持这一指令意味着右派会得出如下结论,即唯一的清除“奥巴马医改”的方法就是通过选出一个共和党总统,重选共和党众议院以及赢得“老大党” 掌控的参议院中多数席位,确保议事顺利。(或者也许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能确保议事顺利的参议院,因为很多民主党参议员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赞成废除该指令。)换句话说,右派将更加踌躇满志地参选。同时,从总统本人而下的民主党都无意维护奥巴马医改。人们很难想象围绕着维护一项从未能激发公众甚至民主党基层想象力的医疗改革的民主党动员选票活动会怎样。
掌控的参议院中多数席位,确保议事顺利。(或者也许并不需要这样一个能确保议事顺利的参议院,因为很多民主党参议员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赞成废除该指令。)换句话说,右派将更加踌躇满志地参选。同时,从总统本人而下的民主党都无意维护奥巴马医改。人们很难想象围绕着维护一项从未能激发公众甚至民主党基层想象力的医疗改革的民主党动员选票活动会怎样。
另一方面,如果最高法院驳回“奥巴马医改”,共和党人将视之为被证实清白而自居于有利地位。民主党不会奋力去通过另外一个符合法院要求的版本(具有讽刺性的是,单一支付符合其要求,因为它会是一个像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一样覆盖全民的政府计划)。换句话说,对“老大党”而言政治上略有感触,但对民主党毫无影响。
xvi
总体来说,以政治来判案的大法官可能会认为他或她想要做的所有事情都有益于自己所在的一方。这与“布什诉戈尔案”不同,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清楚多数决定几乎等同于保证小布什将于2001年1月20日入主白宫。在奥巴马医改案中,人们要做的唯一明智的事情就是将政治算计放在一边,完全按照大法官对宪法的整体看法行事。
由于分属于某个党派,每个大法官都有对于宪法内涵的不同理解方式。但是,没有哪个政党会告诉他们要去理解什么。有时候该“党”与很多派别搅作一团,而这些派别则坚守有关宪法内涵的某些论述,这些论述在很多问题上互相重叠而又在某些问题上相背而行。罗伯茨法院的故事就是一例,它是一个亲商法院,在本书第五章我将对此加以详述和说明:提交该院的很多案件都涉及共和党内部的冲突,即其商业拥趸和本位主义者之间的冲突。
我将大法官称为“共和党人”或“保守主义者”、“民主党人”或“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拥有与这两个政党系统关联的不同宪法愿景,相对的,提名听证会上使用的术语则是“司法哲学”。但是,司法哲学指的是考虑问题的宏观方式而不是党派立场的检查表。约翰·罗伯茨对于《平价医疗法案》的支持判决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大法官会依据其司法哲学来考量最高法院必须予以裁定的特定案件,该大法官的结论是否会符合该党的清单就无法得到保障了。不过,正如那些保守的持异见者的投票所表明的,没有保障并不意味着二者相符的机会不大。
xvii
此外:大法官们不得不通过法律和宪法原则来实现其宪法愿景。他们所使用的法律材料充满韧性而且易于操作,但让这些材料符合纯粹的党派议程有时并不轻松。如果风险太大,大法官们会将法律强加于法官行为的约束放在一边,在“布什诉戈尔案”中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构建了宪法原则的结构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有时法律非常重要。除非人们理解宪法原则,否则人们无法预测政治会在什么时候或如何支配法律,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最高法院是个仅有九人的小团体,有时候法律对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十分重要。我估计对80%的政治性较强的案件进行投票表决时,90%的大法官投票的方式都可以在政党检查表上找到。在其他案件中,大法官的立场来自自己对法律要求的评估。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哪个大法官在哪些案件中会跨越雷池。九张投票收齐后,原以为投票结果会是“共和党对民主党”的人可能会大吃一惊。一位数学比我好的同事算出来的是:根据我列出来的数字,我们可以预计,平均而论,那些政治性较强的案件中大约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反”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罗伯茨法院的判决会站在自由主义一边。
不论本书的出版周期有多长,最高法院的工作一刻也不会停止。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最高法院正在审议与《平权法案》有关的重大案件,《选举权法案》以及同性婚姻。我所描述的结构对于人们如何看待单个案件有所暗示,但不会带来可靠的预测。罗伯茨法院里面的平衡非常接近,谁都不应该把赌注压在具体的结果上。此外,正如林·拉德纳(Ring Lardner)所说的:“身手敏捷不一定就能赢得比赛,力量强大不一定就能赢得战争。”因此,对于最高法院来说也是如此。
xviii
(1) 即共和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