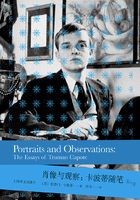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5章 海地
(1948)
看上去,希波莱特或许是个长相难看的人:瘦得像只猴子,面容憔悴,皮肤极黑。他以一种稳定、精确到极致的方式(通过女教师的银质眼镜)去观察,去聆听,他的眼睛投射出一种简单而微妙的领悟。和他在一块儿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你和他之间在不同寻常的处境下,并不会感到孤立。
今天早晨闻讯,他女儿离开了人世,昨天夜里走的,只有八个月大;他还有别的孩子,他再婚多次,有五六次吧;即便如此,想必他一定很难过,毕竟他已不算年轻。我不知道会不会安排有守灵仪式,没人告诉过我。在海地,守灵仪式都是极度奢华的,这些守灵仪式会严格按照特定的程序来进行:那些前来悼念的人,大部分都素不相识,手在空中挥舞,头在地上磕得砰砰作响,异口同声地发出像狗一样低沉的叹息声。有时这声音会在晚上听见,有时这情景会在乡间小路上撞见,它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怪诞,以至于令人心中颤抖,后来我才明白其实这些在本质上都只是哑剧表演。
希波莱特是海地最受欢迎的原始派画家,本可以买得起一幢有自来水的房子,睡在真材实料的床上,也能够用得起电;而实际上,他的住处点着灯,伴着烛光,左邻右舍——无论是老气横秋、头似椰果的老妇人,外表帅气的年轻水手,还是驼背的鞋匠——都能够窥见他的私生活,正如他也同样可以了解他们。前段时间,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自告奋勇地给希波莱特租了一幢新房,地面和墙壁都是水泥砌成的,十分牢靠,墙的后面还可以藏身,当然,他在那儿住得并不开心,因为他并没有什么隐私和舒适的需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发现希波莱特的可敬之处,因为他的艺术作品中没有什么是矫揉造作的,他的取材就是来源于自身,这便是他的国度的精神史,它的歌唱与崇拜仪式。
在他作画的房间,摆放着一个巨型海螺,显得格外抢眼。海螺的形状像个喇叭;粉红色,曲线很精致,宛如海洋里的花朵,一朵水下的玫瑰,若是你吹起它,会发出嘶哑的嗥叫声,一种海风般孤寂的声音:对于水手来说,这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魔力号角,而希波莱特正打算驾驶他自己的那艘红色大船环游世界,所以反复练习如何吹响。他大部分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建造这艘船当中;他的这种投入,和你经常看到有些人规划自己的葬礼、建造自己的坟墓相比,就本质而言其实是一样的。一旦他出海远航,消失于陆地的视野之外,我在想人们会不会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早晨,我时常在阳台上读书或是写作,从这里,我能够看到群山一点一点向港湾滑落,越变越蓝。山下是整个太子港[14],这座城镇经过几个世纪阳光的曝晒,色彩已经变得黯淡,像是旧时的彩绘褪去了颜色:灰蓝色的大教堂,风信子般紫蓝色的喷泉,绿褐色的围栏。左边坐落着一片偌大的巴洛克风格石园,仿佛一座城中之城;就是在这里,在单调的金属光泽与鸟笼般的纪念碑间,他们会把希波莱特的女儿带来:他们要把她送上山去,他们当中有十来个人穿着丧服,头戴草帽,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1.告诉我,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狗?它们都是哪些人养的,又为什么要去养它们呢?它们外表污秽,目露凶光,沿着街道缓缓行进,成群结队,像是一群受到戕害的基督徒,白天倒还无伤大雅,可到了夜里,它们的存在和声音居然能够如此夸张!先是一只狗开始叫,而后另一只跟着叫,最后是全部的狗一起叫,一连数小时,你能够听见它们狂怒而愤懑的对天哀号。S说这就像是颠倒过来的闹钟,因为只要这些狗开始发作,那就说明时间一定还早,也就该去睡觉了。你不妨一试;这个城镇在十点前都会放下窗帘,除非是喧嚣的周末,那时的鼓声和醉汉的鼾声会把狗的叫声淹没。不过我倒是喜欢早晨一大群鸡叫声;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混响效果。另一方面,还有什么声音比小汽车的喇叭声更让人心生厌恶呢?这里有车的海地人看上去热衷于鸣笛;你会开始怀疑这种行为是否带有政治意义或者性别意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2.若是有可能,我很想在这里拍部电影;除了偶有音乐穿插其中,应该会是部无声电影吧,唯有摄像机的镜头能够将这里的建筑和景物如此这般完美地捕捉下来。天上风筝飞舞,风筝上是蜡笔描绘的眼睛,这眼睛无拘无束,在空中浮动,它忽然挂在了栅栏上,而我们、这眼睛、这摄像机,看见了一座房子(像是M·里高家的)。这幢建筑看起来高大却并不坚固,某种程度上还有些滑稽,并无特别的时代印记,但却更像是一种无限混合的血统传承:有法国的影响,也有英格兰维多利亚时期的庄重风格;还带有一些东方的元素,质感很像是皱纸灯笼。这是一幢有雕花的房子,房子的角楼、塔楼以及门廊都刻有天使头像、雪花的形状和恋人的心形:随着摄像机追寻这里的每个地方,我们听到有急促的竹棍敲击声传来,带有音乐的节奏感。只见有扇窗子,十分突兀;蛋白糖饼颜色的窗帘,接着是一双浮肿的眼睛,然后是一张脸,一个女人,像一支年代久远的干花,咽喉处一块黑玉,头发中一把黑玉梳子;我们从她的身边走过,到了屋里,两条绿色的蜥蜴在衣橱柜的镜子上爬行,镜中投射出她的身影。如同钢琴上不和谐的音符,摄像机猛然将镜头一转,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的眼睛从未注意到的东西:一片玫瑰花的叶子落了下来,一幅倾斜的画已弯曲。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
3.相对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游客来海地,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普通的美国夫妇,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里围坐一团,怒气冲冲。这很不幸,因为在所有的西印度群岛中,海地是最有意思的一处;而且,你只需一想这些游客到此的原因,他们的这种反应也就不无道理了:距离最近的海滩都要三四个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夜生活平淡无奇,没有一家餐馆的菜单写得清楚明了。酒店的旁边,只有少数几家公共场所能够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喝到朗姆汽水;要说令人感到愉悦的,莫过于贝纳通沿途树丛里的那些妓院。所有这些妓院都有店名,都给自己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譬如说“天堂”。而这些妓院,分毫不失体面,保持着极好的客房礼仪:这些女子,大都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坐在走廊入口的摇椅上摇来摇去,用印着耶稣画像的硬纸板扇着扇子,闲言碎语,谈笑风生;这就像美国任何一处的夏夜场景。啤酒,而非威士忌或者香槟,被看作是合乎礼仪的饮品,如果你要想给人留下好印象,点它就行。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可以喝下三十瓶;她比其他女孩年纪都要大,涂着淡紫色的唇膏,长着跳伦巴的那种臀部,巧舌如簧,这些都让她成了不折不扣的万人迷,而她自己则说她从不觉得自己算得上成功,除非她能够有条件把自己的每一颗牙齿都换成纯金的。
4.伊斯蒂梅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不得赤脚在大街散步:这有点难,这法令让人既不省钱,又不舒服,尤其是对于那些徒步运送货物的农民而言。但是当地政府如今急于将本国变得更像是旅游胜地,他们觉得不穿鞋的海地人会影响其潜在的贸易,故而人民贫困的一面便不应公开展现了。总体而言,海地人的确是很贫困,但这种贫困不像另一种需要死撑门面的贫穷,在它周围找不到那种恶毒卑鄙的氛围。每当有某句陈词滥调应验时,我的感觉总是糟透了;但我想这句话的确是没错:我们当中最慷慨的人,都是那些最不具备慷慨资本的人。几乎任何一个前来拜访的海地人都会送你一件礼物,为访问画上一个句号,礼物虽小,却通常很奇特:一罐沙丁鱼啊,一卷丝线啊;但是这些礼物给出去都显得体面而亲切,啊!沙丁鱼把珍珠吞进了肚子里,而丝线是最纯的银色。
5.这是关于R的故事。几天前,他到这个国家画素描;突然之间,他来到一座小山的脚下,看见了一个女孩,个子高挑,眼睛斜视,衣衫褴褛。她被绑在一棵大树的树干上,绑住她的是电线和绳索。起初,她冲着他大笑,所以他还以为只是个恶作剧罢了,然而当他尽力去替她松绑的时候,几个小孩儿一下子出现了,并且用树枝戳他;他问这些小孩儿为什么要把她绑在树上,他们一个劲儿地咯咯直笑,大喊大叫,可就是不作答。这时一位老人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他带着一个装满水的葫芦。R又问了一遍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时候,那位老人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说,“她是个坏人,先生,已经坏到无可救药,”而后摇了摇头。R开始往山上走;然后,转过头,看见这个人让她喝着葫芦里的水,当她喝到最后一口时,她冲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那位老人只是擦了一下脸,心平气和地走开了。
6.我喜欢埃斯特尔,我承认我对S关心得少了,因为他不喜欢埃斯特尔:最令人厌烦的不宽容莫过于谴责那些在你自己身上也有影子的个性了:在S看来,埃斯特尔精力旺盛,行为粗俗,还招摇撞骗;当然,这些秉性,除了刚提到的第一条,在S身上也并不是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无意识的粗鄙比有意识的正直要更能展现人性美好的一面。不过S当然和这里的美国侨民很合得来,他们的观点,除了偶有的例外,经常是消极而严肃的。埃斯特尔不受任何人群的欣赏。“谁他妈又在乎呢?”她说。“听着,书呆子,我根本没有错,事实就是我长得太好看了,像我这样长得好看的女的,是不会让那些小喽罗们四处拍马屁的,就这样,没门儿,懂了吗?”
埃斯特尔是我所见过的个子最高的女孩之一,随便那么一站,就有六英尺高;她的脸颊结实而骨感,属于瑞典人的风格,头发是玫红色的,眼睛绿得像猫眼一样:她身上总有一种光环,仿佛她是在飓风中被吹过来的一样。事实上,她是多个自我的复合体。其中一个“她”是一本不怎么精彩的小说里的女主角:今天还在——明天就不见了,你好,你这个怪人,让整个世界头疼。另一个“她”是一个傻乎乎的大姑娘,被爱情冲昏头脑:她总是深信,最没希望的人有着最可敬的想法。第三个埃斯特尔与其说可疑,不如说神秘:埃斯特尔是谁?她在这儿干什么?她打算在这儿待多久?是什么让她早上起床?有些时候,这个E小姐复合体的第三个元素会提到她的“工作”。但是她工作的本质却从未贴上标签。大多数时候,她都是坐在战神广场的酒馆里,一次花上十美分,喝着朗姆混合酒。酒吧的招待总是酣睡,但凡她需要什么的时候,她总是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拍他的脑袋,仿佛是个熟了的大西瓜。她走到哪里,总会有只小狗跟到哪里,耷拉着耳朵,习性乖张,通常还有一些人类朋友也会陪伴着她。她最喜欢的一个是面色苍白、一本正经的家伙,像是个卖《圣经》的;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云游四方的卖艺人,拎着手提箱,装着满满一箱子木偶和没用的家当,穿梭于岛屿与岛屿之间。每逢晴朗的傍晚,埃斯特尔就在酒馆外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安营扎寨;许多当地的少女把她们感情上遇到的问题拿到桌边倾诉:对于他人的爱情,她感到凝重而悲切。她自己曾经结过婚,什么时候,跟谁结的,我都无从知晓,她也同样迷茫,然而,即便她只有二十五岁,想必也一定是陈年往事了。昨天晚上我经过这家酒馆,和往常一样,她依然坐在人行道上的桌旁。但有些不同。她化了妆,而她平时几乎是从不化妆的,穿着一件整洁而传统的衣服;两朵粉色的康乃馨在她的发间如火一般地燃烧,这样的饰物我想并不适合她。而且,我此前从未见过她喝醉的样子。“书呆子,你好啊,是你吗?是的是的是的,”她拍着我的胸脯说道,“听着,小子,我要证明给你看,我要给你看看这就是事实,一旦你爱上一个人,那个人就能让你吃下任何该死的东西,这就是事实。看好了”——她从头发里猛然拔出一支康乃馨——“他对我痴情着呢,”话音未落,她把那朵花猛地塞进趴在她脚边的小狗嘴里,“我让他吃,他就吃,他要是不吃,就给我去死。”
但是这只狗只是喘了喘气而已。
在这里,过去的几周都花在狂欢节的彩排中了,而昨天开始的狂欢节一直要持续三天。彩排只不过是狂欢节本身的一种微型预演;礼拜六的午后,鼓声渐渐响了起来,开始是分散的,山头有一处,离城较近的地方有一处,这鼓声来回涌动,似乎在暗示什么,不绝于耳,到最后构成了一种四处弥漫的震颤,这震颤,令安静的地面发着微光,像一股热浪泛起的涟漪。而我就在此地,独自一人,在这砒霜色的屋子里,一切行动似乎都是因这些声响而起:咚哒咚。就在那里,看吧:罐里的水泛起亮光,水晶般的泡泡在移动,沿着桌子滚落下来,砸碎在地面上,风吹拂着窗帘,翻动着《圣经》的书页。那声音:咚哒咚。黄昏之前,这个小岛的鼓声已经逐渐声势浩大。一些小型乐队在街头痛饮作乐;这些人都是以家庭为班底,或者是什么秘密协会的,唱着不一样的曲目,听上去却都差不多;每个乐队的领唱头发里面都插着羽毛,身上穿着带有小亮片的衣服,活像是披着一床古怪的被子,每个人都戴着一副廉价的墨镜;其他人唱着歌,跺着脚,他则在原地打着转扭着臀,头向两边转来转去,像是一只邪恶的鹦鹉:每个人都在大笑,还有一些夫妇也加入其中,边跳边向后甩着脑袋,半张着嘴,咚哒咚,腰部伴着鼓点扭动,眼睛睁得好似满月,咚哒咚。
昨天夜里R带我去了这次狂欢节的中心。我们打算去看看一个年轻邦甘,也就是伏都教[15]神父的仪式,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小男孩,名字我从未听过。仪式安排在离城市较远的地方,于是我们只好乘坐公共汽车,车很小,只勉强装得下十名乘客;但车上的人足有近两倍之多,有些穿着戏服,有一个戴着铃铛帽子的侏儒,还有一个老人戴着像乌鸦翅膀一样的面具;R就坐在这个老人旁边,那人一下子问道,“你知道天吗?对,我想你是知道的,天就是我造的。”
对于这个问题,R回答说,“我想月亮也是您老人家造的吧?”
那人点了点头。“还有星星呢,他们都是我的孙子。”
一个吵闹的女人拍着巴掌,声称这个老头子简直是个疯子。“可我说亲爱的女士,”他回答说,“我要是个疯子的话,又怎么能够造出这些宝贝呢?”
行程十分缓慢;车停了,车内的人蜂拥而出,藏在面具背后的面孔在黑暗中摇晃,烛形火把发出古老的亮光浇在他们身上,如同怪异的黄色雨水。
我们到了城外邦甘的住处,那是一块安静的地方,只有夜间的昆虫发出沙沙的声响,仪式早已开始,不过邦甘本人还没有露面。寺庙的周围,有一间狭长的棚子,茅草屋顶,祭坛室位于两端(两间祭坛室都是大门紧闭,因为至少有一间是等待邦甘出门的),大概有上百个海地人,安静而肃穆。在屋子中间的空地上,有七八个打着赤脚的小女孩,全都身着一袭白衣,头上也扎着白色的印花布,像盘蛇一样扭动,拍着自己的两侧,唱着歌谣,还有两个打鼓的人在附和。一盏煤油灯下,舞者和击鼓人那烟雾般的、水平的影子在墙上摇曳,他们全都聚精会神,身形如蛙。忽然,鼓声停了下来,女孩们组成一条通道,延伸到祭坛室的门口。这个时刻是那般安静,你都能够分辨出有哪些昆虫在奏着小夜曲。R想要一根香烟,可我不想给他:谁在教堂抽烟呢?而且伏都教毕竟是个实实在在的组织庞大的宗教,尽管海地的中产阶级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后者全都是些天主教徒,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相互妥协——天主教渗透到了伏都教当中:譬如说一幅圣母马利亚的图片,还有圣婴耶稣的形象——有时代表他的是一个手工娃娃——都随处可见,都几乎可以用作任何一个邦甘神龛的装饰。而伏都教最主要的功能,在我看来,与其他那些宗教并无二致:虔敬某位尊神,缓解邪恶的压力,人是孱弱的,但有神在保护着你,有一种外在的魔力,那是神灵拥有的魔力,他们可以让男人的妻子怀孕,也可以让阳光灼烧你的庄稼,将肉体的呼吸带走,而同时赐予他灵魂。然而,在伏都教当中,生者与死者的国度并没有界限;死者可以复生,游走于生者之间。
这时鼓声再度响起,女孩们的歌声就穿插在一声声缓慢的巨响中间,而后祭坛室的门终于开了:三个小男孩走了出来,每人拿着一个盘子,上面盛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香灰、玉米粉和黑火药——还有蜡烛,像是生日蛋糕上点着的那种,在这些东西的中间燃烧;这些男孩把盘子放在一个磨圆的石头上,朝门跪下。鼓声渐弱,慢慢变成了急促而有节奏的敲打声,这声音是摇动着装在葫芦里的蛇椎骨发出来的,然后,邦甘从女孩们排成的过道中敏捷地滑行出来,像鸟儿一般轻盈,像一个灵魂不经意间固化了一样,屋子的周围,他的腿上和脚踝上戴着的银质镯子发出丁零的响声,好像丝毫都没有接触到地面,他宽松的丝质红袍像鸟翼一样沙沙作响。他头上裹着红色的天鹅绒,耳朵上戴着的珍珠熠熠生辉。他随处停停,像一只蜂鸟,然后紧紧握住一名朝圣者的双手:他抓住了我的手,我则洞察着他的脸,雌雄莫辨,美貌绝伦,实在是不可思议,那深蓝色的皮肤又混合着高加索人的特征;他应该没到二十岁,却有一种无以名状的老态,睡眼惺忪,灵魂出窍。
最后,他抓了一大把玉米粉和香灰,在地上画出一张巫网;在伏都教里面,有上百张巫网,错综复杂,属于某种超现实主义的图案,每处细节都有其寓意,要全部完成需要的不仅是钢琴师所具备的那种记谱能力,就好比是弹奏一整部巴赫的作品,而且还需要超常敏捷的艺术技巧。随着鼓声爆炸般地变得越来越快,他俯下身来,沉湎于他的法术之中,就像一只红蜘蛛,不是在吐丝,而是把香灰撒在地上,织成一张凶险的网,有皇冠,有十字架,有毒蛇,像是生殖器的形状,还有眼睛和鱼尾。而后,巫网完成了,他又重新回到了祭坛室,等他再度出现的时候,他身着绿衣,手中拿着一个巨大的铁球;他站在那儿,球被点上了火,圣洁的蓝色环绕着火球,仿佛是地球的大气层;他接着把球托在手上,跪倒在地,匍匐前行,吟诵声与呼喊声为其喝彩,火焰渐渐熄灭,他方才起身,向上摊开掌心,那手掌竟然没有被灼伤,一阵战栗掠过他的身体,好像一阵莫名的风拂过,他的眼睛滚入头颅,神灵(上帝和恶魔)像一粒种子在他的肉体中发芽,开花:没有性别,也无从辨认,他将男人与女人揽在怀里。无论是谁,他们都在巫网的蛇和眼睛的图案上转动,灵异的是图案却几乎没有被扰乱,而当他换到另一个人那里时,先前的那个人就如猛然投入无限之中一般,撕扯胸膛,高声尖叫。而这个年轻的邦甘,汗珠闪着光亮,珍珠耳饰散落在地,奔跑着猛撞向最远端那扇紧闭的大门:他口中念念有词,双手击门,直到在门上留下血印。他就好似一只飞蛾,而那扇门就是最明亮的电灯泡,因为一旦超越了这层阻碍,顷刻间就会有魔力出现:真理是秘密,是纯粹的宁静。要是大门真的打开,他会找到想要的东西吗,这个永不可及的东西?当然大门是永远不会打开的。重要的是,他相信他会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