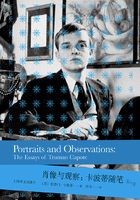
第11章 品味:以及日本人
(1955)
在我的家庭范围以外,第一个打动过我的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绅士,名叫弗雷德里克·麻里子先生。麻里子先生在新奥尔良经营一家花店。我大概是六岁那年遇见的他,你可以说,我就是闲逛进了他的店里,我们保持了十年的友谊,或者说直到他在乘汽船去圣路易斯的途中猝然离世为止,其间,他亲手为我做过二十几件玩具——提在线上摇曳的飞鱼;花园的模型,花园里面满是袖珍鲜花和长着羽毛的中世纪动物;一个跳舞的人偶,上满发条,可以翩翩起舞三分钟。这些玩具太过精致,并不适合玩,可它们带给我的是最初的审美体验——它们构建了一个世界,设定了品味的标准。说起麻里子先生,简直就是个谜,倒不是在于这个人(他很平凡,孤身一人,听觉也有障碍,这也使得他愈发孤僻),而是因为你看他在摆弄那些家当的时候,根本无法判断是什么让他在棕色树叶和绿色藤蔓之间作出选择,从而达到一种微妙而精确的境界。多年过后,当我读到紫夫人的小说,或是《清少纳言枕草子》,欣赏到歌舞伎和三部令人叹为观止的电影(《罗生门》,《雨月》还有《地狱之门》)时,对于麻里子先生的记忆就会浮上心头,但是他那些闪亮的玩具和袖珍花束的神秘感在某种程度上却消退了,因为我意识到了他的天赋是整个民族感悟的一种延伸:日本人就像视觉乐师,他们似乎在形状和色彩领域有着极高的造诣。
完美:当歌舞伎演出的大幕徐徐升起时,在色彩斑斓的图案中,在舞者们身着长袍如瓷像般跪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庄重姿态中,一种预感——对于这场表演,以及对它最终将要达到的心灵的震颤——就已经存在了。然后,出自《罗生门》的某一幕无声桥段再度上演:年轻的新娘,坐着轿子,轿子外面套着布帘,还有她的丈夫,慢慢悠悠地穿过树林,摄像机通过树叶、阳光,还有窥视的强盗迷离而淫荡的眼神,营造出一种极度的险象。当然,《罗生门》是部黑白电影;直到拍摄《地狱之门》,完整的色调才得以呈现,那些色彩就像是新发明的一样:它们是苦艾酒,还有像雪利酒一样透亮的褐色。这完全是一个格调的仪式:一个奇观,貌似以脱离于情感内容的方式,仅仅围绕绝对的格调旋转。
这种高雅格调从来就不是西方剧院的强项;总而言之,我们从未发展出任何东西,其成分能够如此纯净,如此缜密。我们可以粗略地拿一部王政复辟时代的喜剧来做类比:至少那样一部作品对于人工雕琢的东西同样欣赏;另外,黑帮惊悚片和美国西部片的确也产生了一种经典格式化的准则与行为模式。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碎片的简单迸发;而日本的格调感是长期严肃的唯美美学思潮积累的产物。尽管正如阿瑟·韦利[39]所言,这种思想的主要根基是恐惧——对于直言与断然的恐惧——因此简单的一叶小草刻画的是整个夏天,眼睛微微向下,便是预示着最深邃的激情。
在九世纪的日本,甚至是更早以前,大多数信件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成的:一个有涵养的日本人通晓上百首诗和经书,他们可以从中引用几行适合用来表情和状物的诗句——如果行不通,那他就会自己创作,因为诗歌就是一天当中的娱乐消遣。从我们近期看到的日式娱乐作品——他们的舞蹈与电影——来看,这种风俗依然盛行;毫无疑问,我们接收到的是交流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