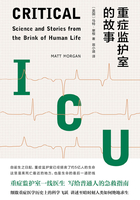
第三章 皮肤与骨骼
当生命的脚手架受损
以医学为职业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医生能够在世界各地将自己的技艺运用于任何需要的地方。我有幸与家人去往澳大利亚西部的美丽城市珀斯,在一所全世界最繁忙的创伤医院里工作了整整一年。那段奇遇始于一次长达24小时的飞机航行,途中我百般取悦我那18个月大的女儿,她精力充沛,扭个不停。由此获得的奖励,是在一座阳光充沛的城市里生活,它坐落在天鹅河畔,河水幽蓝。那真是美好的一年。
在那架飞机的轮子触碰到澳大利亚滚烫的柏油碎石路面12个月后,我们回家了。我时常问自己为什么回来,我在珀斯收入更高,工作时间更短,从事感兴趣的医学专业,那里景色优美,风和日丽。答案显而易见,我们回家的原因,跟罗布的爸爸于皇家珀斯医院外沉默地在车里坐了一个小时的原因一样。我是在珀斯工作期间遇到罗布的爸爸的。我们回家是为了离家人更近,罗布的爸爸也急切地想做到这一点。但他尚未做到,也做不到。时候未到。
一个小时前,宁静的天鹅河以南,清寂郊区的某栋木屋中传出爆炸声,那声音一定震耳欲聋。随着声波回荡,木屋的屋顶被掀翻,仿若一块陈年水泡的表皮。这场爆炸带来的损失高达20万英镑。人们看到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跑过散布着碎片的、烧焦了的草坪,在他身后是他4岁大的姐姐。屋内的5个成年人均受伤,伤得最重的是罗布。在澳大利亚紧急救援服务的营救鸣笛声中,罗布躺在地上,毫无知觉,呼吸急促,面部、胳膊和背部严重烧伤。罗布试图在他的简易实验室里制造一种江湖人称冰毒的毒品,而此时,冰也正是他的伤口所需要的东西。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冰毒实验室爆炸事件之一。
值得庆幸的是,在平民医疗机构中,我们极少会看到爆炸后发生的伤害。我曾在皇家空军与美国军人一道接受训练,在那儿学到的东西让我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爆炸性损伤大体可以分为三阶段。初始伤害是由高能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造成的。这股力量在整个空间内传送,能够影响内含空气和液体的人体部位。其可能导致的伤害包括肠、肺、眼球和鼓膜破裂,单单是这种无形但致命的力量就很容易致人死亡。二次伤害是由冲击波携带的飞行物品造成的。由于动量=质量×速度,即便最平常的物品也可能转变为致命武器。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部手机甚至某人的断肢,当这些东西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撞击你的头部时,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最后,当你的身体被冲击波甩到附近的静止物体上时,便会造成第三次伤害。
在我的重症监护室里,一年中就诊的病人数量有规律地起起落落,我早已习惯了这一点。当秋树开始生出白霜,我会遇到流感病人;6个月后,我又着手救助炎热暑月里游泳溺水的病人。这些故事循环往复,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家庭来说,这些经历都是个人化的、不可预测的悲剧,是“黑天鹅事件”。这个术语描述的是一些异常事件,比如“9·11”恐怖袭击,甚或“英国脱欧”带来的全球影响。“黑天鹅事件”在词源学上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人们认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1697年威廉·德·弗拉明的远征队在澳大利亚西部天鹅河流域发现了黑天鹅,而天鹅河畔正是如今罗布居住的地方。威廉在探索该区域时描述称,发现了一种大型水禽,全身长满黑色的羽毛,有着鲜红色的喙。它后来被称为黑天鹅。2007年,黎巴嫩裔美国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著作《黑天鹅》中借用了这个称呼,来描述那些带来广泛而极具变革性影响的意外事件。塔勒布坚称,人类并不善于预测未来,出人意料的事件由此发生,并急剧改变我们的生活。从总体上来看,任何一个特定的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概率都非常低,但是就像预测是否要接受重症监护治疗一样,其在某一时刻内发生的概率是很高的。
2002年10月12日就发生了这样一次事件。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库塔海滩,一次恐怖主义炸弹袭击造成202人遇难,209人受伤。悲剧发生几小时后,严重烧伤的幸存者就被运抵皇家珀斯医院,这是离遭袭地点最近的医疗机构。医院总共收治了28名病人,其中许多人都受惠于由顶尖外科医生菲奥娜·伍德研发的突破性皮肤喷涂技术。[48]这一黑天鹅事件令皇家珀斯医院成为顶级烧伤救治中心,在这里,罗布有极大的概率能存活下来。
罗布被送到急诊部时,一股沙滩烧烤般的肉焦味在我喉咙里弥久不散。看到这么严重的面部烧伤,我们首先担心的是灼伤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会出现的肿胀。我们可以通过许多迹象来识别病人的呼吸道是否被过热的气体损伤。病人的声音发生了改变,咳出炭黑色的痰,或是鼻毛烧焦,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信号。除非病人的呼吸道尽早接受防护,不然急性严重肿胀会在灼伤发生几分钟后就让他无法呼吸。若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唯一能打开病人呼吸道、让他不至于窒息而死的方式就只有从颈部前方切开。每个重症监护室医生最可怕的噩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急救手术,床边只有一把解剖刀和一根塑料管作为工具。本需要一个小时做完的精细手术,如今要在120秒内完成,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任何准备,只有最基础的装备,以及非生即死的结局。
还好罗布并不需要做这个手术,这不禁让我松了口气。我们及时往罗布的口腔注射了麻醉药物,他的呼吸道安全了。我通过喉镜上的弧形金属刀片观察他的声带,这块刀片的作用在于推开嘴部的软组织,同时用其顶端的灯照亮通向声带的路径。我们观察发现,罗布的呼吸道内壁覆满了红红的肿胀组织以及黑色的碳化斑点。尽管我们已经给罗布戴上了呼吸机,但他血液中的氧气含量仍然处于低水平,这十分危险。
当病人被从密闭的火灾现场救出后,包括一氧化碳在内的有毒烟雾可导致其血液处于低氧水平。但我们怀疑,猛烈的爆炸冲击波已经对罗布的肺部造成直接伤害。我们赶紧给他拍了X光胸片,结果证实了我们的担忧。他的肺部在片子中呈现亮白色,这是爆炸性损伤的缘故,其肺泡里充满积液。更令人担忧的是,罗布的胸壁内部和肺部表面之间形成了厚厚的空气圈。这一症状是气胸的表现,当木屋的屋顶被掀翻的时候,爆炸导致气体快速膨胀,而罗布的肺内也发生了同样的气体膨胀。极快的增压使肺泡壁破裂,导致空气泄入胸膜腔。爆破孔周围的组织会形成一个临时的单向阀门。我们每让罗布呼吸一次,就有更多的空气流入这个空间。除非解决这一问题,否则胸膜腔的气压会越来越高,最终导致罗布的心脏停止跳动。
我拿起一把手术刀,在罗伯腋窝底部的皮肤上深切一刀,直到看到一节肋软骨的表面。我将手指伸入他肋骨之间的狭小空间,左右推挤,分离肌肉纤维。这块地方我很熟悉。当我的手指从他胸腔内的最后一层中抽回时,一股带血腥气的空气喷薄而出,我知道自己找对了位置。我将手指绕着肋骨的内表面扫过一圈,感觉到罗布柔软的肺随着每次呼吸而扩张、收缩,他的心跳抚动着我的指尖。
一旦威胁罗布生命的首要创伤稳定下来,我们就可以评估其烧伤的程度。经过细致的检查,我们推测其身体的20%被烧伤,大多数为部分烧伤,也有一些是全层烧伤,即皮肤的三个皮层均被烧伤。显然,罗布需要接受外科手术和植皮手术。
皮肤是我们最大也最重要的免疫结构。如果把人体的皮肤摊平,它有两张大餐桌那么大。皮肤上布满各种形式的生命,有超过1 000种不同类型的细菌和真菌栖息于皮肤表面,这些微生物的组合和你的指纹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如果用消毒剂擦拭这块栖息地,仅12个小时后,你独一无二的“微生物指纹”又会重新产生,仿佛乘时光机器回到了过去一般。[49]
你的皮肤是外部入侵者遭遇的第一道屏障,也是他们需要克服的最艰难的障碍。严重烧伤发生后,由多重耐药生物体引发的严重感染几乎注定会发生。皮肤不仅能阻止入侵者进入人体,也为人体提供基本的构架,使你体内的各个部分各安其位。在严重烧伤发生的几分钟之内,人体内的体液便会发生巨大改变。当自然界最精妙的“防水风衣”不再运作,人体每小时会流失200毫升的体液。不单单是体液,烧伤病人还会流失大量热量。专业的烧伤治疗设备内会维持稍高的环境温度以补偿这些流失的热量,毫无准备者踏入这里,无异于走下刚刚降落在澳大利亚红土中心的飞机。
尽管我们在经精确计算后补充了遗失的体液,但由于这一严重创伤的影响,细胞连接处仍然会出现大量渗漏。这导致整个身体出现浮肿,甚至器官内部也肿了起来。再加上病人的新陈代谢(人体中的化学反应)迅速增强,严重烧伤的病人出现器官衰竭也就不足为奇了。大量肌肉与组织分解,导致人体产生高量肌红蛋白,更是令情况雪上加霜。这些大分子被运输到肾脏后,会滞留在肾脏系统的小孔,导致肾衰竭。
罗布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爸爸有一场自己的战役要打。这位父亲在得知儿子重伤的消息后,他做了所有家长会做的事情,急匆匆开车赶到医院。在那个有记录以来最炎热夏天的湿热夜晚,他把车停在了距重症监护室几米远的地方。随着车钥匙的转动,车熄了火,他犹豫了。他脑海里浮现出一千种可能出现的情景。在经过20分钟的无所适从后,残酷的现实逐渐明晰。他又拧动车钥匙,汽车引擎散发的热量融入了夏夜。罗布的爸爸开车回家了,在接下来5天里都没有来看自己的儿子。多年后他在接受一家全国性报纸的采访时,说出了那晚的两难处境:“你要么就走进去,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要么就待在外面,做好警察局长。不可能两者兼得。”
在遇到罗布多年之后,我与这对父子重新取得联系。尽管罗布在爆炸受伤后需要做大面积的植皮手术,但好在他的肺部情况很快得以改善,不到一周,他就搬出了重症监护室。数日后,他的父亲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次拥抱了儿子。两人拥抱时都清楚,往后的道路漫长且险阻。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很快,澳大利亚各地报纸的头版都充斥着面露悲哀却保持坚强的警察局长看望他那个罪犯儿子的凄凉形象。
想想你曾犯过的最严重的错误吧。也许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事情,有可能是犯法的,不道德的,或仅仅是不公平的。你也许是昨天犯下了错,也可能是50年前。无论这错误有多么不堪,它也不能代表你的整个人生。你不是由你最严重的错误来定义的。我们大多数人运气不错,通常能侥幸逃脱生命中犯下的错误。你上周一边开车一边发手机短信,这并没有导致一场灾难。但对某地的某人来说,灾难确实发生了。对于那个人,人们将永远戴着他犯过错的有色眼镜来看他。但除了这一偶然际遇,那个犯错者和我们余下的人没什么不同。
我曾给不少犯过错的人进行治疗。我为恋童癖者、毒贩、杀人犯、强奸犯和家暴者治过病,也照顾过酒鬼和烟鬼,他们曾毫不节制地戕害自己的身体。我这样做对吗?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时间和资金用在这些给别人带来悲苦的人身上吗?是的。是的,我们应该如此。
要说清楚这一点,我首先想让大家明白,人们从别处获得的与重症监护室有关的“事实”通常是错误的。在澳大利亚工作时,我记得接诊过一位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的原住民女士。她酗酒成性。我被告知,她之所以入院,是因为醉酒驾驶出了车祸。这场车祸夺去了她三个孙儿的生命,他们当时就坐在后座上。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愤怒,给她做心脏移植手术一定耗费了不少资源,她却因为自私的行径使无辜的生命平白消逝。最终,她死于严重受伤,我当时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她竟然不用接受审判就这样死了。
几周后,我在完成与她死亡相关的文件时,得知她入院时血液酒精浓度测试的结果实际上是0。后来我与她的家人交流,得知她无力负担预防移植心脏排斥反应所需的药物,同时还要独自照顾三个孙儿。实际上,她是在开车时死于心脏病,仅仅因为她买不起抗排斥药。她并没有醉酒驾驶。我们无法为这位女士提供有效的解药或果决的救治,但我们可以给出事实和真相。她的家人十分感激,感谢我们“了解了她的经历”。
即便关于一个病人过往的事实是真的,医疗也并非须通过价值来准许获得的商品。用不予治疗作为惩罚手段,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谬误,它让我们失去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医疗不是对人们的选择颐指气使的武器,无论这些选择看起来多么愚蠢。医疗资源的配置应该考虑的是那些影响成功率的要素,而不是对病人人生选择的价值评判。如果社会选择不给老烟枪或酒鬼提供治疗,那它是不是哪天也会选择不治疗肥胖者、内向者、摩托车骑手、冒险运动爱好者或不按正确方式系鞋带的人呢?责任本是条双车道,社会有责任给所有人提供救治,包括那些曾做过糟糕决定的人。
我越是与那些做过糟糕“选择”的人沟通,就越怀疑自由意志所能起到的作用。一生中,我因自己的成就得到掌声和鼓励,但这些成就真的能追溯到仅由我自己做出的选择吗?生于一个不缺买书钱、爱意满满的家庭,生于一个能免费接受教育的国家,生于一个婴儿夭折率低到足以确保我能存活下来的世纪,这些通通不是我的选择。我大脑中的神经传导物质处于平衡状态,使我在能够理解科学的同时不沉溺于毒品或暴力,这也不是我的选择。即便我有能力做出“正确选择”,这些选择也不过是我被给予的一整片机会沙漠中的一粒沙罢了。山姆·哈里斯关于“自由意志幻象”的论断为我这种观点提供了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50]磁共振显像研究对大脑中涉及认知的区域进行扫描,现有的证据表明,早在我们察觉“自己”做出决定许久之前,潜意识过程已经做出了决定。[51]这一研究更加说明我们不应该依据“值不值得”来决定是否治疗一个人,也让我思考究竟是什么引导我选择以医学为职业。
我青少年时许下“长大要当医生”这个天真愿望的过程已经够曲折了,我真的成为一位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的道路也同样曲折。成为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并非深思熟虑的人生抉择,若不是因为我的职业导师,我如今的道路或许会有很大不同。导师查阅了我的档案,说道:“你上面写着希望成为《X档案》里的福克斯·穆德。这是在开玩笑吗?”并不是。大卫·杜楚尼[52]的那个角色杂糅了科学、逻辑和激情,以及神秘的元素,让观众一看再看。当时的我尚无法察觉,但今时今日在重症监护室里照顾你的母亲、孩子或祖母的过程,无形中让我青少年时的旧梦全都实现了。我在医学研究中遇到的未解之谜让我在医院里夜以继日、年复一年地钻研下去。危重疾病之谜可能意义重大,比如罹患同样疾病的病人,为何有的匆匆病亡,有的劫后余生。各种各样的因素决定了你能否幸存下来,其中就包括你的收入中位数,这一点增加了人们的忧虑,因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甚至对躺在重症监护室病床上的病人的健康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在日常工作中,我所遭遇的各种谜团与前述挑战相比要显得小些,但这些谜团依旧促我提升心智,世上最难的数独游戏也不及其万一。
少年时代收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记得自己双手颤抖,既是出于激动,也是出于对未来的期盼。那个时刻,与已经历过的考试相比,我对前路上究竟会有多少考试尚浑然不知。20年后,图书馆藏书的气味仍让我忆起本科和研究生时期的一系列考试、无数论文报告、学位论文和令人恐惧的临床测试,经历了这一切后,我才敢称自己为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
有个画面跟拍立得照片一样清晰,我一直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真正的医生面前为一个真正的病人做检查。我把听诊器挂在耳朵上的方式明显不对,果然它掉到了地上,我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笨拙。随着重症监护领域的技术进步,如今我甚至都用不到听诊器了。但在给我家的新晋成员,一只叫切斯特的狐红色可卡颇公犬做检查时,兽医将听诊器轮流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听小狗的心跳。在孩子们真真切切地听到切斯特心脏瓣膜突然关闭产生的“扑通”声后,我再次以错误的方式戴上了听诊器,不禁把家人逗笑了,这让我突然想起19岁那年自己还是医学院学生的那个灰色早晨,我被自己的狼狈弄得直冒冷汗。
20多年来,费时费力的考试和无休无止的实践测评一直是我生活中的常规固定项目。它们以可预测的模式来来去去,如同四季一般,有些轻松愉悦,另一些冰冷艰难。尽管在医学训练的尽头来一次老式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毕业测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已成往事,但在从学生转变为医生的道路上,考试仍然举足轻重。那些纯粹考察识记内容的考试仍然重要,但要培养出一个好的甚至可靠的医生,仅靠这种考试是不够的。随着医学蹒跚走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们倾向于认为,更多的数据、更好的答案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正如黑影是由最亮的光带来的,人工智能也给医学带来了新的难题。有时,在将简单答案汇总为复杂整体之前,我们首先要问对问题。这对重症监护考试至关重要,因为医生可能同时被病床边数百种数据点轰炸—从血液检测到手写笔记,从X光片到心电图。孤立评估各项数据,对治疗危重患者来说显然不够;我们需要将这些数据点整合为完整的图景。
病人真正需要的医生,是能够以问正确的问题为开端,将医疗的复杂性完整呈现出来的人。这些年,随着像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这样的机器被研发出来,人类的这种整合能力甚至也能被复制了。[53]要知道,我的医学训练耗费了公众超过50万英镑的资金,那么,社会是该依靠一个无心的机器人来完成医疗操作,还是该依靠一个有心的人类医生呢?作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的职责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做出诊断或制订治疗计划。如果我的工作仅限于这些,那确实可以找个机器人来取代我了。我作为一个人类医生的优势在于,我有能力指挥一个复杂、混乱的人类医疗团队,将所有人的关注点放到独一的人类病人身上。知晓所有答案,不过是问题解决过程的一部分。医院过道上都会挂着绘有杰出的、中产样貌的单个白人男性医生的海报,但这种海报早就应该成为历史。我们的海报上应该表现不同族裔的医生组成团队协同工作,性别也应更平衡。这种协同工作的能力,以及与病人、家属和同事沟通交流的人性,(至少目前)让我比沃森更有价值。
在医学训练中纠缠我的无止境的考试,往往关注那些拥有单一确定答案的问题。然而重症监护通常与不确定性打交道,因此考试更应该评估人类医生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情况下提出和回答问题的能力,即便这种考试比较难以设计。有能力做侵入性治疗与是否应该这样做之间存在差异,对此我们需要学会抱着开放的态度来接受。我能做的事并不总是我该做的事。医学关乎对病人经历的理解。我目前见过的机器人都不太擅长讲故事,但与我共事的人类医生精于此道。
珀斯那个炎炎夏日过去几年后,我窗外的景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8年3月的第一天,本该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日伊始,但实际上却是一个漫长寒冬的缓慢尾声。就是在那天,我差点离职。
作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所经历的压力与重负通常是彼此对立而又平行的轨迹。我不会因为一个重大的失误或事故就在精神上被击垮。尽管我记得许多病人的经历,但从没有谁的经历会比其他人的更能困扰或激励我。而我那天想要离职的原因,与英国国家自行车队对他们取得成功的归因—边际效益的聚合—恰恰相反。我差点离职,是因为边际损失的聚合。工作中的诸种小事让我近乎崩溃。
2018年3月初,令人恐惧的锋面“东方野兽”袭击整个英国,造成了反季节的天气乱象。3月的第一个周末,催促紫色郁金香从我的花园土壤中发芽的春季并没有到来,取而代之的是16人因极端天气而死,35年来最大的一次降雪就这样倾倒在准备不足的英国土地上。[54]这种恶劣天气与重症监护工作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正好重合,许多重症监护室的病人收治数都超过其设计收治量的150%。[55]我们这儿只有26个床位,但收治了46个病人。这个周末十分重要,但排班也很艰难—特别是在下了4天大雪后,很多人都被困在家里,只有很少的同事能到岗,更别说忙了一整天的同事能从医院回家了。大家几乎不食不眠,还要面对一大群病人。当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被告知某个国家的外交官刚抵达我们医院,要把我们这儿一个皮肤已严重感染的病人转到私立医院,边际损失的聚合终于从我内心爆发。我清楚,光是转院过程就足以要了这个病人的命,路上的颠簸可能造成危险的血压变化,而平躺则会减少氧气吸入量,但压力之下,我们只能让病人踏上不归路。当时我太累了,根本无力争辩。我本来那天都不用来上班,只是因为大雪才来帮忙的。我透过医院的窗户看着外面正在堆雪人的小孩,想着我家孩子此刻在干什么。何不直接回家,再也不回头呢?我付出了一切,却总显不够。
生活教导我,那些受伤的人往往也最容易伤害别人。但医生兼作家的维克多·弗兰克尔[56]向我们指明了一条逃出这个怪圈的秘密路线。从犹太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之后,他写道:“当我们无法改变局面时,我们面临的挑战便是改变自己。”[57]他接着说:“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有权选择如何反应。而我们的反应靠的是自身的成长与自由。”用冷静的思考而非发热的头脑来寻找做出反应的精神空间,这可能是件难事,但若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会伤害到自己和他人。
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有什么东西在阻止我,不让我在那天走出医院大门。也许是自由意志,也许是机缘巧合,又或许是注定的、机械论的命运。我们跟安排了转院到私立医院的病人家属沟通,他们对家人关爱备至,明事理,很理性,而且和我一样只想为他们所爱之人尽最大的努力。他们做出转院决定,不是因为不信任我们,而是出于对病人的爱,是父母对离乡万里、生命垂危的孩子的爱。他们感到无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其可能寻求支持。而当这对父母看清现实后,他们的反应是理智的而非一时冲动,他们同意让孩子留在我们医院,不转去伦敦。
这次谈话结束后,我继续工作了12个小时,没有离开医院。边际损失的聚合令我质疑自己的工作、角色和人生。但当我记起重要的问题时,这些小事又显得无足挂齿了。大事更加重要,直到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仍是如此。
我们该怎样改进重症监护医疗系统呢?唯有如此,我和像我这样的人便不至于想着离开。在医院管理会议介绍最新的改进举措时,我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速溶咖啡。年轻的毕业生们从艰难的商业世界中一拥而入,他们本意是好的,却谈论着商业管理方法能如何解决处于危机中的医院的困境。[58]他们提出了那些在秩序井然的硅谷工作环境中发展而来的策略,想将其运用到错综复杂的医院急诊部。他们谈论着诸如源自日本战后汽车工业金属手臂的“精益管理”等概念,试着把它套用到流血的手术室里。
我们有选择性地从具有强安全意识的行业中借鉴技术,这的确可以为医学带来帮助。我每日的例行巡房就受益于航空业所创立的机组资源管理理论和核查单。在试图提高手术核查单的效率,从而能够以相同的工作量实施更多的膝关节置换手术时,其他行业的策略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这些行业标准没告诉我们的是,该如何在出人意料的冷酷寒潮期,在凌晨2点,给病人提供重症监护。这些行业标准通常无法独自应对医学的复杂性或变数,以及其中的人性因素。比如,为了达到手术目标,你妈妈要做的那场需要术后重症监护病床的重大手术恰好被安排在了节礼日[59]晚上10点,她可能会因此意乱心烦。
这些安排会使患者和工作人员感到不够人性化。在医疗中处于另一端的任何一个病人都会记得那些最触及痛处的时刻:自动售货机是空的,在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几个小时,名字被读错。对于通过医学触动我们的人性体验,你无法用彩色的电子表格把这些经历解释清楚。
我现在期待的是这样的创新:聚焦于提供更好的体验,而不仅仅是更好的结果。体验、安全和效率可以而且应该共存。当我们把三者组合在一起时,它们相互补充,而非彼此冲突。经营一家医院所需要的策略就应该是这样—专为经营医院构想一套理念,而不是简单地从其他行业借来所谓的规则。医学需要自己培育、设计和发现这些东西。
2016年对格温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将是重要的一年。她很喜欢在当地学校任艺术课老师这份工作。这份工作让她将自己极富感染性的创造力传递给下一代,也让她有时间照看三个孩子,直到他们长大。35岁时,格温和她的丈夫准备开启另一段冒险。某天晚上,两人喝完了一整瓶酒后,聊起威尔士海岸风光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咖啡的热爱,人生计划就这样直接在桌布上被绘制出来。我遇见格温仅仅一周之前,他们一家打算在美丽的威尔士乡间沿海小路上开一家咖啡店。但因为那次意外,一切都改变了。
最早抵达现场的医护人员看到了令人不安的场景。三辆汽车的金属部件纠缠在一起,初看几乎无法区分,就像人为将三道色彩混合在一起。格温的大女儿跌跌撞撞地离开这团钢球,握住祖母的手,惊魂未定,不住颤抖。“妈咪在哪里?”她看向祖母身后,问道。
事发前,格温坐在婆婆的车上,婆婆正平稳地将车开向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人们至今也没弄清后来具体发生了什么,在这场严重的道路交通碰撞事故后,格温被困在了车里。其他人很快便逃了出来,仅受轻伤,但救援人员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将格温安全救出。人们将救出的格温放在她的车旁,给她盖上急救毯,她已命悬一线。格温陷入昏迷,主动脉(这是人体最大的血管)破裂,血流不止,而且由于多处肋骨骨折,她无法呼吸。
格温先被就近送到一家乡村小医院,随后一架急救直升机降落在这家医院旁边泥泞的地上,直升机医生欧文·麦金泰尔和重症特护医生克里斯·肖负责将格温安全转移到当地的创伤中心。这支直升机队伍行动迅速、动作轻柔,仿佛是一支处理进站加油的一级方程式赛车队,但他们面对的情况比香槟喷出酒瓶要更紧急。他们凭借自己的专业训练、常规的模拟实战和标准的操作流程,救了格温一命。麦金泰尔医生仅靠自己的手指和一把手术刀就排出了格温肺部周围的积血。团队其他人此时准备好了相应的设备,为她接上了生命维持器。与此同时,他们将一个大针头深扎进格温的肩骨深处,向她体内输送血液和凝血物质,由于她身体冰冷且伤得很重,其他部位的血管十分脆弱,难以下针。输血和凝血物质经过格温的骨髓血管,让她不至于失血过多而死。就算格温现在仍躺在路边也不妨碍这支团队进行救援,无论哪里有需求,这支直升机团队都会飞往事发地、停在停机坪上提供先进的救援,哪怕是遇到威尔士可怕的天气,防水布一遮,他们就可以开始工作。
作为裸猿,我们评估风险的能力非常差劲。我们容易对千里之外的奇闻产生过度反应,比如数百万英里之外一名冲浪者被鲨鱼袭击的故事,继而担心自己在假日游泳时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更应该担心开车从家去往机场的途中可能发生的危险。
全球每天有超过3 000人死于道路交通碰撞事故,也就是说,每年约130万人。[60]至于交通事故幸存者,其中有5 000万人肢体残疾。道路创伤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麻烦,在15~30岁的人群中,它是主要死因。西方国家在道路安全方面正稳步改善,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很难说,虽然这些国家的汽车保有量仅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但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全球的90%以上。[61]
格温能活着抵达医院,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追溯至英国的滑翔机行业。18世纪时,英国工程师乔治·凯莱设计出第一款安全带,将驾驶员固定在滑翔机内。尽管早在1885年,纽约的出租车就已经开始使用首个获得专利保护的安全带来保障乘客安全,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沃尔沃公司才引入今天仍在使用的三点式安全带。这改变了我们今天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的交通事故伤害范围,严重的头部伤害变成主要是胸部、腹部和骨骼创伤。系上安全带这个简单的行为会使你死于车祸的概率降低一半以上。安全带真的有效,请一定要系上它,每次都系。
格温所接受的输血,在历史深处也能找到其源头。许多医学进步源于战争的恐怖。输血服务的变革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医学成果之一。[62]在1913年之前,人类仅能实现个人对个人的常规输血。而“一战”中有数百万士兵死于严重失血,这加速了使用化学助剂实现血液贮存的相关研究。人们留意到,源自水果的柠檬酸盐能有效阻止血液凝结,日后才发现这是由于它会与凝血所需的钙相结合。贮存液态血液的能力让人类建立起第一个血库,并有能力针对大规模失血的情况制订前瞻性应对方案。
当格温躺在空客EC—145直升机上时,急救团队留意到她不曾移动过自己的腿。事故发生三小时后,格温已经远离车流滚滚的街道,她的丈夫坐在重症监护室里,相对平静地问了我一个艰难的问题。格温在手术室里接受手术,医生们在修复她破裂的肠部,稳定她严重损伤的脊椎。她之所以不曾移动过腿,是因为脊椎多处骨折导致她的脊髓受损。脊椎骨折是医生治疗严重创伤患者时会遇到的主要问题。脊髓从你的大脑底部一直延伸到臀部上方,顺着背部中间向下延伸大约半米。这一光滑的绳状构造内包含几千亿个神经细胞,全部储存于一个差不多只有你小手指那么宽的空间里。脊髓对生命至关重要,因此才会有坚硬的骨头完全包裹住它,保护其免受破坏。从许多方面来看,脊椎骨都可视作生命的脚手架。但当脊椎本身破裂时,骨头碎片就从保护性的构造变为一种致命武器。
格温脊髓的创伤正好发生在负责发出号令控制腿部的部分。我将格温目前的情况告诉了她的丈夫,有那么一刻,他陷入了死寂般的沉默。他的目光从地板转向我的眼睛,旋即问了一个我这一生所遇过的最艰难的问题之一:“我该怎么和孩子们说?”我不知如何回答。
解疑释惑向来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基本内容。“他能活下来吗?”“我要留下来守着他过夜吗?”以及“她还能和以前一样健康吗?”在全球任何一个重症监护室里,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深爱着病人的家属发出这些恳切的询问。无论是在哪儿,无论用何种语言,回答这些问题都很难,答案却基本一致。我猜得出答案,若引用数据,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病人的死亡率高达95%。然而,这对创造奇迹的病人来说算不得什么,他是每20个病人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但我并未宣之于口,作为重症监护室医生,我们应该以诚实的态度回答这些难以作答的问题:“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是医学界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要诀。它们拥有强大的力量,让你怀抱希望,同时也做好悲戚的准备。但医生也很难开口说这四个字。人们想要计划,想要确定性,想要源于多年教育和经验得出的答案。而医生们想给予的也是这些。承认不确定性无法被消除,这需要勇气。“我不知道”是我能给的最真诚,也是悖论般明智的回答。
在遇到格温和她的家人两年后,我终于有了回答她丈夫那个问题的答案。我和家人去威尔士的旧都城旅游,那里现在是一个叫作马汉莱斯的集镇。马汉莱斯是我逃离忙碌的医院轮班以及与家庭新成员小狗共处的绝好去处,而且它离格温家开车仅有一小段距离。更重要的是,我能去格温家里拜访他们一家。
如果我能直接穿越时间回到过去,我可以更轻松地回答格温丈夫的问题。我会直截了当地说,孩子们应该知道一切—多亏格温当时系了安全带,空中急救队及时展开救援,献血者和其他医疗护工提供帮助,格温不仅从危重病情中幸存下来,而且恢复得很好。康复的过程自然是漫长又艰难的,而她的家人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格温的丈夫应该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是个异常勇敢、坚强的女人,她不会被生活的挫折绊倒,不会减少对生活的热爱。他应该告诉孩子们,是啊,生活永远被改变了,但有些门合上的时候,另外一些门会被打开。
2018年去格温家与她及其家人见面,亲眼看到这一切变化,让我感到既愉快又荣幸。格温梦想中的咖啡馆没有开成,这场意外完全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尽管身体的大部分功能均已恢复,但格温仍需坐在轮椅上。格温在余下的人生里很可能一直需要倚靠轮椅行动,但总体而言,她忙碌而又幸福的家庭生活将继续下去。她告诉我,她曾有心灰意冷的日子,觉得自己只是个“长在棍子上的脑袋”,沉湎于对简单之事的怀念中,比如与孩子们一同跳舞。与残疾障碍作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告诉我,残障人士和特殊人士已被公众接受,但在残疾的同时维持简单的“正常人”形象则困难得多,她的话让我深省。残奥会运动员可能是社会名流,但大多数残障人士并不特殊,他们只是希望能在接受新常态后努力生活下去。
格温的想法正好与亨利·弗雷泽[63]在他了不起的著作《小小的大事》中体现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本书里,弗雷泽描述自己年轻时遭受了严重的脊椎创伤后的生活。格温非常清楚别人为自己的生活付出了许多,因为大家的付出,她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但如今她该继续自主地生活了。我们见面六周后,格温在自己所住的村庄里开了间新的工艺品商店,店里陈设着她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创作,是它们帮她度过了痛苦的历程。起初,她创作的作品充满了黑暗的元素,随着夏天到来,她对外销售的图画如今已重现些许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