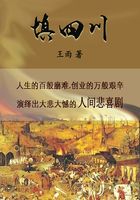
第2章
宁徙顾不得那么多了,撩起衣裙,脱下裤子,叉开双腿。她那人见人爱的肌肤在夏日的月辉下泛亮。有过生光儒经验的她惊骇、激动、悲伤,早产的胎儿临盆了。咳,竟会是在这种场合。此是在孤庙内端坐那泥塑菩萨背后的一道窄缝里,外面庙堂里躺满了同行的来自闽西老家的男女移民。
时值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的一个深夜。
腹痛剧烈的她憋足力气往下使劲,把呐喊声摁在肚腹里。
她是与夫君常维翰一起移民进川的。长她两岁的常维翰家那土楼与她家那土楼相邻,他俩自小便在一起玩耍。她爬树比他快,敢跟男孩子打架。前年,她十七岁,男人们看她的眼色有变化,说她是个带有宫廷气的美人儿。自幼和她一起玩耍的长她三岁的宣贵昌对她爱慕不已,看见她那雪白的脖颈就想到她那雪白的身子,发誓非她不娶。常维翰看她的眼色也变了,那天,他拉她到望月岭的树林里,说是要看看她。她说,你成天不是都在看么,由随你看。他就把她的衣裙脱了。自那,她怀上了常光儒。木已成舟,两家的老人只好把他俩的婚事办了。母亲柳春为此落泪,说她那秉性像她爸爸。她一直有个强烈心愿,要去四川寻找父亲,去看看那萧条的神秘的充满诱惑力的早先的天府之国,在那里陪伴父亲置业。
她与常维翰结婚后,宣贵昌伤心不已,茶饭不思,将怒怨全都发泄到常维翰的身上,发誓要夺回她来。
闽西老家人口剧增,土地瘠薄,堪种禾稻仅十之四五,其余仅属沙碛,只宜种植杂粮、地瓜。即便是晴雨应时,十分收成亦不敷半年食用。去年,祸不单行,望月岭遭逢天灾,又遇大疫,夺去了常维翰父母的性命。常维翰的父亲乃武举人,武功高强,自幼跟父亲习武的常维翰只好携家进县城开办了一家武馆,他和宁徙在望月岭老家的房子都依然留着,那是他们的根。不想,常维翰开办的武馆被官府查抄。是因为没有得到她而愤懑的宣贵昌花重金买通了官府,判常维翰明里习武暗里聚众反清复明,说他祖辈是明朝的官员,贼心不死。查抄武馆不说,人还险些被逮捕入狱。幸亏挚友傅盛才拔刀相助,出钱疏通,才暂且摆平此事。不想,又发生了宗族争斗,望月岭常氏的族人来求救,说是人多地少,宣贵昌给他那族长父亲出了恶主意,找来一帮歹徒,要强占常氏族人的一块公地为己有。常氏族人面对那帮手持棍棒的歹徒敢怒而不敢言。她和常维翰都恼怒。常维翰被宣贵昌诬陷刚脱离险境,她不让他回望月岭,自己跟了来人赶去。她代常维翰交给常氏族长二十两银子,建议他再凑些银子做赏金。常氏族长感动,也拿出了二十两银子,又找常氏的富户凑了六十两银子,用这一百两银子做赏金,招呼常氏族人站出来。这一招奏效,许多常氏族人都站了出来,与她一起操棍拿锄同那帮歹徒斗,才保住了常氏的那块公地。真是人心不古,她万不想,儿时的好友宣贵昌竟会如此的恶毒。该是去四川的时候了,她决心下定,对母亲和夫君说:“树挪死,人挪活。妈,维翰,我们去四川荣昌县,去寻找爸爸,打探他的真实下落。即便是找不到他我们也去,去承他的志向,置业发家。之后,再找宣贵昌报仇。”母亲赞同,担心盘费的事儿。傅盛才说,得有二百来两银子才行,他可以资助一些。说,四川地广人稀,四处竹树野草、荆棘蓬蒿,见荒土插茅秆为界即可据为己有,当地官府一概认可。朝廷那“填川诏”就鼓励外省移民填川。去川的路远,却有发财的机会。按照元代的划分,闽西也属于湖广行省管,算是四川的近邻。傅盛才是湖北麻城人,他很早就冒死进川去做生意,熟悉那里的情况。常维翰犹豫:“自古道,蜀道难于上青天。”傅盛才说:“么子啊,人还会被路给难倒了。”她决断:“走,我们上四川!”
她和母亲变卖了首饰、嫁妆,加上家里的余钱和傅盛才的资助,凑得二百六十三两银子做盘费。他们一家人深情地告别了故土,与众多进川的移民结伴,踏上了远徙四川的征程。
一路上,进川的移民越来越多,有因“填川诏”诱惑去四川的;有因天灾或是瘟疫逃难去四川的;有因家仇或是避祸去四川的;有因寻祖投亲去四川的;也有当年外逃来闽返回四川的。这些成千上万携家带口的移民,背包挑担赶牲口拉车潮涌西行。过江西省那道关隘时,她和家人挤在人群里,出气都困难。她担心母亲和一岁的儿子常光儒,拼死紧护。妈的,挤死人了!常维翰推搡身边人群怒喊。人们都想早些拥过关隘,谁也不会答理谁。他们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挤过了这道关隘。宁徙后来得知,仅闽西进川的移民就有二十多万人。
早产的孩子在她肚腹里折腾,折腾出两行泪水。
他们一家人数千里跋涉,吃干粮、舔盐蛋、住岩洞、越崇山峻岭、走蚕丛鸟道,万般艰辛,她没掉过一滴眼泪。路过湖南常德府境山道时,她落泪了。体弱的母亲柳春晕倒去世。这突然的打击令她肝胆俱裂,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和夫君只好就地择处掩埋了母亲,断肠离别。这会儿,她又酸心断肠落泪,她和夫君在武陵山道上被老虎驱散。常维翰为保她母子与虎搏斗,引虎进了老林,不知生死。
疼痛稍有缓解,她看了看身边熟睡的儿子,摸了摸怀揣的银子、银票、“行程图”和“族谱”,心里稍稍稳实。
夫君引虎进老林后,她抱了常光儒拎了行囊跟着惊惶的移民队伍奔逃。下山后,随结伴而行的人们拥上一艘装有货物的扁舟,移民挤得满满。袒胸露背的船老大颈子上挂着十多串铜钱,恶脸挨个儿收钱,踩着了挤坐在她身边的常光儒,儿子厉声哭喊。她朝船老大瞪眼呵骂:“踩着孩子了,你狗日的没长眼啦!”付了铜钱。木船顺了险恶的乌江下行。傅盛才说,乌江乃天险,只通木船,告诫他们要乘坐头高尾歪肚大的“歪屁股船”,那船行驶缓慢却安全,那些贩运盐巴、煤炭、杂货的“盐船帮”、“乌金帮”、“杂货帮”多用此船载货。叮嘱他们别乘坐船身细长的“蛇船”,那船行驶轻快却风险甚大。打问得知,此船正是“蛇船”。心里发怵。乌江流水并不欢迎这群不速之客,恶浪撕咬船板撕咬船上人。“沿流如着翅,不敢问归桡。”想到唐代这诗,她真切体会了诗人过乌江的惊险,母亲节衣缩食供她念过私塾。儿子渴了,她就从行囊里取出从家乡带来的青花瓷碗舀河水给儿子喝。
晚暮时分,风大起来,浪漩满江,扁舟似落叶翻腾。
船老大赶紧撑船靠岸,沙哑嗓子喊:“风浪太大,今晚黑不走了,上岸,全都上岸!”
她只好跟随众人下船,沿蜿蜒的荆棘山道登攀。高坡上空无一人,只有这座孤独的破庙。风更猛,暴雨倾盆,人们争相朝破庙里跑。搂抱儿子的她被人群推拥到这泥塑菩萨塑像跟前,看见菩萨身后有道窄缝,赶紧钻进去坐下,担心放有祖骸、画像、种子和米糠的担子还扔在武陵山道上。
是场过路的偏东雨,雨后,月亮出来,银色的月辉从门窗、瓦隙间扑落下来。挂在常光儒脖颈上的长命锁在月辉下闪亮。她记得那长命锁上刻的“认祖诗”:“骏马登程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年深外地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这出发时以避万一失散的“认祖诗”可千万得保存好。儿子已经熟睡,她却难以安眠。一家人自闽西老家出发后,经江西、湖南,来到四川彭水县境。他们要从水路入川的,傅盛才说,逆水入川生还者百无二三。就走陆路。陆路亦是险恶。米糠在那担子里,如何充饥?她掏出怀中的米饼咬了一小口,舔了舔出发时带的盐蛋,想起傅盛才唱的移民歌谣:“吾祖挈家西徙去,途经赣州又乌江。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被薄衣单舔盐蛋,半袋干粮半袋糠。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真正理解西徙前辈这歌谣的苦涩含义,也为其入川前景诱惑。
母亲对她描述过她父亲宁德功的威仪,讲述过他的为人,不相信返川失踪的他会变心。母亲说:“你爸爸呢,就是脾气暴躁些,为人却忠厚、爽直。他给我发过誓的,上不负圣恩,下不负川民。他说,他之所以急着回川,是要为复苏四川出力,待他安顿好后,就接我们去跟他一起安家置业。他还说,万一他遇不测,我们也要进川置业。他说,我们母女是他这个地方官的妻女,得要做移民填川的楷模。”她更急切要赴川寻找到父亲,父亲的音容早已在她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她觉得父亲一定还会在人世,他的失踪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想着,昏昏然入睡。是腹痛使她惊醒过来。
腹痛剧烈而频繁。
宁徙大口哈气,月辉映照她那张缀满汗粒的脸。她痛苦地低声哼吟,咬牙使尽全力,那急于脱离母体的婴孩伴随胎血“哇哇”坠地。撕心裂肺的疼痛令她呼吸急促、头晕目眩。脐带还连着婴孩,血水流淌,她觉得自己就要死去。倔强的她俯身用牙咬断脐带,咬了满口血水,发现竟是一对龙凤。啼声发自女婴,男婴没有声息,她心里发悸,难道是个死婴?挥手照男婴屁股狠抽几掌,“哇……嗯哇……”男婴用哭声宣告了他的降临人世。她凄然笑,“刷刷”撕开衣裙,包裹好两个婴孩,按出生先后,取名为常光莲、常光圣。孩啼声惊醒了庙内沉睡的人们,男人女人的头伸进来,男人被女人赶开。女人们进来相助,有个女人送来米羹,倒进她身边那青花瓷碗里,啧啧连声。她身边的长子常光儒还在熟睡之中。
微曦初透,船老大叫醒众人,喝道:“船漏了,我带各位客家到下一个渡口去找船。”屋漏偏遭偏东雨,移民们怨声载道,又无可奈何,只好跟了恶脸的船老大沿荆棘丛生的江边道走。
这支凌乱的疲惫不堪的队伍里,最苦最累的是宁徙。她背着常光莲、常光圣,抱着常光儒,挽了行囊走。几个好心的家乡女人伴随在她身边,那个送她米羹的女人哀叹造孽,接过她手中的行囊,她好生感激。
痛苦至极的她反倒啥也不怕了,紧跟队伍走进密林。
林间传来响动,“刷!”一声响,树上飞下个蒙面汉子,夺了她怀里的大儿子常光儒腾身上树,消逝在密林里。雪上加霜,大难临头,她疯狂喊叫:“儿子,我的光儒……”恶脸的船老大从队首走来,喝道:“莫号丧,老子跟你说,这是飞人,娃儿是找不到了。”
常维翰跟了匪首孙亮走。身佩腰刀的他穿“一裹圆”不开衩长袍,长袍下摆挽在腰间,裤腿塞在软靴里,全身汗透,布满血迹泥污。土匪喽啰皮娃子挑着他那装有祖宗遗骸、画像、种子和米糠的担子跟在后面。
他三人翻过一座险山,来到土匪山寨前。
盛夏的落日如火,霞光映照群山、古树、飞瀑、山花,倒是个如诗似画之地。说是山寨,也就几栋木屋,四周围有厚实的木栅栏,当间有道厚重的木门,站着看门的喽啰和二头目郭兴。见他三人走来,郭兴道:“大哥,兄弟们正等着呢!”孙亮点头一笑,拉了常维翰进寨。
常维翰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杀死老虎,宁徙那话对,人的能耐大。引虎进老林时,他一心想的是保住年轻的妻子和幼儿。精疲力竭的他在老虎向他扑来的一刹那,奋力挥刀,刀尖刺进虎腹。杀死老虎后,他怒喝虎血,赶回原处,早不见了妻儿和移民队伍。“宁徙,儒儿……”他悲怆呼号。山道上空无一人,只那担子还在,赶紧挑担朝山下走,他母子定是跟随移民队伍下山了。走不多远,遇见了土匪。领首者是豹眼黑眉、赤胸亮膀的孙亮:“识相的,留下买路钱来!”他叫苦不迭,扔下担子,抽出腰刀相迎。只几回合,上前来的两个土匪便倒在血泊之中。孙亮勃然大怒,瞠目持枪上前,二人你来我往厮杀,不分上下。
“算你厉害!”孙亮收枪道,“老子姓孙名亮,敢问好汉大名?”他收刀答:“鄙人姓常名维翰,自福建闽西老家冒死来川置业,还望好汉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日后如能发家,定来致谢!”说了妻儿离散、途中杀虎之事。
孙亮将信将疑,招呼弟兄们跟他走进老林,果真见一死虎,由衷赞叹:“英雄!”定要留他入伙。他誓死不从。孙亮就喝叫喽啰抬死虎回山寨,叫皮娃子挑担,亲自护送他下山。三人来到江边渡口,乌江流江水哗哗,岸边无船无人。他鼻头发酸,在这里等船顺流而下去寻找他们?可万一宁徙母子还在山上寻找自己呢?他难以决断。孙亮劝道:“不如先在我处栖身,边找寻你妻儿边从长计议。”一筹莫展的他觉得也只好如此,心想,寻到妻儿就赶紧离开,绝不与匪为伴。
这山寨外面简陋,进到当间那大木屋时,倒使常维翰吃惊。全是黄亮的木板铺地,正首挂有“聚义厅”匾额,匾额下有太师椅和黑漆木桌,两厢摆有小桌、小凳。地板和太师椅上铺有兽皮。四围火烛明亮。孙亮让弟兄们剥虎皮、炖虎肉,摆筵席款待常维翰。吃到尽兴时,执意要与他结为把兄弟,他不从,孙亮立时变脸,郭兴抽刀架到他脖颈上,嚷叫要用他人头为被他砍死的两个弟兄报仇。他面色铁青,心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渴盼寻到妻儿的他只好违心应承。孙亮转怒为喜,他长他八岁,为兄。二人在寨堂里歃血为盟,焚香跪拜。土匪们叫好。年方十八明眸皓齿的玉霞来向他敬酒:“维翰兄弟,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她乃孙亮的压寨夫人。他喝尽杯中酒:“谢谢嫂夫人。”玉霞虽说比常维翰小三岁,可论辈分却是嫂子。孙亮呵呵大笑:“对头,一家人,喝酒,喝酒!”
常维翰好是悲哀,不想自己竟混迹于匪巢。又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暂且栖身吧,寻找妻儿要紧。孙亮虽是土匪,也还通情达理,应承他随时可以离开。
与孙亮相处熟了,常维翰得知,孙亮是张献忠部属的后代,早先也是进川的移民,是从湖北结伴进川的,一群人走到这里时,干粮吃尽盘费用完求助无门,只好砸了鼎锅,聚众为匪。常维翰就好言相劝,劝他向官府自首,弃恶从善。孙亮闻言怒脸:“官府官府,吃人如虎,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老子当土匪是只抢富不抢穷的。”一口川腔,说了他就是因为官府的欺诈、追捕才逃进四川的。孙亮这么一说,倒引起常维翰共鸣。可不,自家那武馆的房院乃祖宗旧业,却被宣贵昌买通官府掠夺了。他对孙亮说了自己的这些苦衷。孙亮愤然道:“我说嘛,官患猛于虎患。哼,老子啸聚山林,就是要誓与官家为敌。”
二人说到了张献忠,孙亮的话就多了。
“官家说,是张献忠屠蜀,说他发兵搜索各州县山野,不论男女老幼,逢人便杀。这是诬陷。”孙亮怒道。
常维翰道:“我也这么听说。说那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近百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官朝会,引出斩之,曰‘天杀’。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
孙亮摇头:“哎呀,贤弟,你这是道听途说。顺治三年,张献忠就在盐亭县那凤凰山中箭身亡了,还这么诬蔑他,实在不公。我爷爷就跟随他征战四方,事情不是这样的。张献忠入蜀后,是听说有三次杀人较多。第一次是攻占重庆府,说献忠屠重庆丁壮万余,可那‘丁壮’乃是所俘的明军,并非是把全城民众都杀光了;第二次是攻占成都,杀的是明朝的宗室、官绅,并没有乱杀草民;第三次杀的是士子。是因为当时那些士子勾结清军围剿义军。其实呢,真正屠蜀的,一是明朝官军的乱杀,包括那些跟明军合流的‘摇黄’。二是清军长时间攻打四川的杀戮。三是清廷和吴三桂争夺川地的烧杀。唉,实是可悲,清初那三十多年的战乱,川人几乎都被杀光了。”
人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都是移民的二人饮酒长谈,竟心心相印。孙亮派了弟兄们山上山下以至于下乌江去涪州进重庆为常维翰寻找妻儿,均无果。常维翰悲伤也感动。
这一日,孙亮约常维翰去射猎,俩人的箭法都不错,射着了十几只野兔。骑马返回时,树上飞下一蒙面汉子,夺了常维翰搭在肩上的野兔,飞身上树。常维翰恼怒,纵身上树。那人好生灵巧,在树杈间如同飞鸟,蓦地,飞身下树钻进了丛林。常维翰突然闪念,莫非宁徙母子会是被此人抢去了?心中愤然,纵身下树追赶,追着,撞倒一个白发女,连忙俯身扶起道歉。那白发女并不答理,抽身飞跑而去。常维翰纳闷,看面相此女不过二十来岁,怎么满头白发?
孙亮跟来,说:“贤弟,莫追了,那飞人你是追不上的。”
常维翰说了遇见白发女的事。
孙亮叹曰:“都是因战乱所致,这逃进深山的女人长年吃不到盐巴,头发也就白了。”
常维翰摇头叹息:“大哥,为弟我暂且不走了,一定要找到这个飞人,也许你弟媳和侄儿就是被他掳去了。”
孙亮觉得有理,也为贤弟愿意留下而高兴。
玉霞骑枣红马而来,对常维翰怨艾道:“维翰兄弟,打猎也不喊我嗦。”
常维翰礼貌拱手:“啊,嫂夫人来了。”
孙亮笑道:“玉霞,下次打猎一定喊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