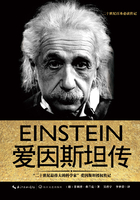
第一章 爱因斯坦的青少年时代和教育背景
家庭背景
在爱因斯坦的记忆里,德国西南部的士瓦本(Swabia)是他先辈们生活的地方。他们中有生活在小城镇的,有居住在小村庄的,还有经商的,开店铺的,甚至做手艺的。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因卓越的智力而引人注目。对于外界偶尔的质询声,爱因斯坦的回答是:“生活环境制约了我的先辈们的出类拔萃,那样的生存环境无法让他们脱颖而出。”
爱因斯坦个性的形成与德国西南部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莫大的关联,了解这段历史背景至关重要。在邻国阿尔萨斯人的影响下,士瓦本人悄然融入了法国文化。在生活中,他们善于思考,勤于实践,既热衷于各类艺术和娱乐活动,又醉心于哲学和宗教思索。士瓦本人讨厌所有一成不变的形式。在个性上,士瓦本人与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各具特色。普鲁士人理性严谨,重践诺,好秩序,善统治;巴伐利亚人朴实无华,好欢腾,偶尔也粗野甚至庸俗。士瓦本人、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性格差异也体现在他们的方言中。士瓦本语音律优美,绵言细语、娓娓叙来,宛若潺湲叮咚的溪水。而普鲁士军官和政府官员则声若军号,铿锵有力。士瓦本人的言辞不像柏林市民那样愤世嫉俗,怨天尤人,也不像德国牧师和教授那样能言善辩,精推细敲。
爱因斯坦游历各国之后,其士瓦本口音已经很不明显,几乎听不出。但他那种平和友善、娓娓叙来的话语风格还是能流露出士瓦本语的语调痕迹,尤其在听着他那夹杂某些瑞士腔的话语时,这种感觉更明显。其实这就是德国西南方言的语调,只是略显生硬罢了。不过,爱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艾尔莎,却操着一口纯正地道的士瓦本口音,轻言软语,和风细雨般。她叫爱因斯坦为“Albertle”,称“土地”为“Ländle”,唤“城市”为“Städtle”,所说的每个词,后面都带一个小后缀“le”,听起来更加柔声细语,声情并茂。
爱因斯坦的犹太人后裔身份的确影响了他。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影响竟然那般巨大。在爱因斯坦父母幼年时,士瓦本的犹太人与镇上其他居民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太大差异。当时,镇上的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并不墨守成规,因为犹太习俗的繁文缛节阻碍了他们与镇上其他居民的友好往来。消除这些障碍后,镇上的犹太人渐渐融入了周围的环境,他们与当地居民不再格格不入。生活在士瓦本的犹太人与生活在柏林的犹太人不一样,柏林的犹太人富裕阔绰、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是柏林文化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士瓦本的犹太人,与镇上其他居民一样,过着平静的生活,和谐地与周遭环境相处,远离大城市的喧嚣与纷扰。
当时,进步的犹太人不再把与《圣经》和犹太教义相关的书籍视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那时,《圣经》只被看成是纯文学和具有启发性的读物。在犹太人家里,德国古典作家和先知被视为指导道德和行为的导师。席勒[1](1759—1805)、莱辛[2](1729—1781)和海涅[3](1797—1856)等这些人与牧师所罗门和《约伯记》一样备受推崇。尤其是席勒,他的作品恪守道德准则、彰显《圣经》悲悯,赞美人间博爱,广受犹太人喜爱,成为他们教育小孩的重要范本。当然,席勒的士瓦本身份也让犹太人觉得更亲近。在爱因斯坦家里,也不例外,席勒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都是他家教育子女的重要素材和理念。
在爱因斯坦父母和祖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德籍犹太作家贝托尔德·奥尔巴赫(1812—1882)是士瓦本犹太人生命和智慧的代表。尤其在1840—1870年间,他更加活跃。他是第一位用作品呈现黑森林山区农民日常生活的作家。黑森林是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西边的一片山地。用现代眼光看,其作品《黑森林故事集》(Tales of the Black Forest)太过理想化、矫揉又造作。不过,该作品在当时被看作是制衡后来“柏林下流文学”的砝码,代表着犹太人在日耳曼文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
想了解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还必须说说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1870—1871)。1871年之后,普鲁士成为德意志地区实力最雄厚的王国,这从根本上影响了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实际上,统一日耳曼主要部落和复兴强大德意志帝国的希冀不是知识分子阶层发起的,但却是作家和学者们的夙愿。正如士瓦本浪漫派诗人乌兰特(1787—1862)所说,知识分子希望“德意志帝国能涂上一抹民主的色彩”。然而,这样的愿景未能成真。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1815—1898,人称“铁血宰相”)统治期间,不但未见“民主色彩”,反而以“铁血”统治手段威震四方,其系列举措招致所有进步知识分子团体的一致反对。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缺失了一种优良古老的民族文化背景,也就是缺失了曾经孕育了席勒、歌德、莫扎特和贝多芬等名人的士瓦本文化、莱茵文化和奥地利文化这样的背景。因为新的统治阶层都来自东部部落。而东部部落人员结构鱼龙混杂。他们有的是暴虐成性的压迫者,曾用武力收服原住斯拉夫人、残暴实施德国化、烧杀掠夺、霸占领土,为非作歹。有些则是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这些人基本都是原住民的后裔。
这种状况让德国知识分子处于尴尬无措的境地,尤其是年长的、较为传统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得不承认,新统治者的统治策略比他们倡导的那一套更管用。面对卓有成效的统治局面,知识分子一方面也鼓吹暴力,一方面又厌恶这种秩序,因为这种无视生命的统治手段有悖于他们所倡导的艺术和科学理念。他们不喜欢新统治者的那一套管理理念,但又不得不敬仰他们,甚至模仿他们。面对普鲁士军官,日耳曼学者产生了一种自卑感。他们学会了把自己束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将远离大众、跻身当权阶级等目标视为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学会了唯统治阶级马首是瞻的处事原则。
犹太人与知识分子有着相同的矛盾心境。一方面他们同样崇拜新帝国,仰慕治国有道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们在家依旧向子女传授犹太教经典和德国古典精粹。在公共社交场合,犹太人会尽量让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规范。
只有不为外在成功而沽名钓誉、不畏强权坚守自由和文化的人才有可能想保持不为他人左右的态度,对抗主流的风潮。青年时期的爱因斯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尽管后来他常与德国的主流趋势背道而驰,但对家乡士瓦本和父老乡亲总是充满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