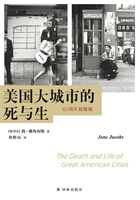
谁毁了城市?六十年后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
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
2020年3月4日,收到译林出版社的邀请,希望我能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60周年中文版作导言,因为编辑觉得我十五年前所写的“城市的生死明鉴:再读《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书评“非常合适”。而此时,我正在观看网上流传的一个武汉封城后的视频:随着无人机的镜头,壮丽的文化艺术中心绚丽夺目,博览中心流光溢彩,中央商务区的高楼大厦辉煌壮丽,其四周的广场上却空无一人,唯有八车道的中心大道上,一辆白色救护车在孤独行驶……尽管这场瘟疫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待解的问号,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反证了:离开了人,城市便毫无意义,城市的生命和活力来源于活生生的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决策者却似乎并不理解。
十五年前,我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读后感曾经先后在《新周刊》、《读书》和《北京城市规划》等刊物上,以“雅各布斯的城市生死明鉴”、“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和“城市的生死明鉴”等标题被刊登和转载,尽管文字长短不一,但核心内容一致。之所以我十五年前的读后感在今天仍然被觉得“非常适合”,只因为这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在这方面仍然亟待改进。尽管我们的城市已经变得更加“高雅”和“高端”,却并没有变得更富有活力。君不见北京的798艺术区,十年前曾经是何其热闹,充满生机,而今却屡有画廊倒闭;君不见在高雅化和高端化的名义下,古老胡同的店面被封,小摊被强行清理和驱逐,街道门可罗雀;君不见在治理环境和美化环境的名义下,洱海边的民宿被大面积拆除,曾经生机勃勃的景致,一夜之间只留下一片空寂。请不要用城市的美化、卫生、治安、环保等堂而皇之的名义来质疑我的上述观点,因为城市街道摊贩、个体艺术家、水边民宿等都只能使城市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文化、更加美丽、更加清洁,而不是相反。之所以它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被割除的对象,只因为它们最富有活力,不是官方规划的,因此要求城市管理者对枯燥、简单而僵硬的城市管理模式做适应性的改变。而这对一个强势的城市政府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十五年过去了,又有近20%的国民进入城市而成为城市居民,使城市户籍人口达到中国总人口的近60%,从名义上讲,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俨然已成为国家执政者的最高目标,而“美丽城市”建设也刚刚被城市建设主管部门作为行动目标,唯其如此,今天,译林出版社再次出版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城市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城市的生命来自何处?城市规划的目的是什么?是谁毁了我们的城市?怎样来挽救我们的城市活力?
简·雅各布斯以其鲜明的、建设性的批判立场,于1961年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宣言般地提出了城市的本质在于其多样性,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城市规划理论和乌托邦的城市模式,机械的和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扼杀了城市活力;要挽救大城市的活力,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必须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过程和联系,谨慎而精心地,而非粗鲁而简单地进行城市的改造和建设。
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的思想和对策是具体而日常的,却恰恰与正统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如:
街边步道要连续,有各类杂货店铺,才能成为安全健康的城市公共交流场所;
街区要短小,社区单元应沿街道来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
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孤立偏僻的公园和广场反而是危险的场所,周边应与其他功能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
城市需要不同年代的旧建筑,不是因为它们是文物,而是因为它们的租金便宜,从而可以孵化多种创新性的小企业,有利于促进城市的活力;
城市地区至少应存在两种以上的主要功能相混合,以保证在不同的时段都能够有足够的人流来满足对一些共同设施的使用;
巨大的单功能的机构和土地使用将产生死寂的边缘,当行政中心、音乐厅等大型设施与城市的居住区和其他功能相分离而独立成区时,必将会出现死寂的边缘带;
贫民区并不一定是正统规划人士所认为的“城市的毒瘤”,相反,可能是城市最具活力和安全的区域,不应采取大规模投资改造和搬迁的方式来加以消灭,而应通过鼓励和培植自我更新的能力来逐渐脱贫;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不是靠修更多的道路来解决,那只能使城市最具活力的区域不断受到侵蚀,而是应该通过减少汽车的使用机会的方式来解决,包括提高使用汽车的难度,以及提供多种出行选择来慢慢减少人们对进城汽车的依赖;
城市应该分解成高效的、尺度适宜的社区单位,通过这种社区单位使市民能在城市规划和改造中表达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大型旧城改造工程,特别是救济式住房项目,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物质和社会结构相割裂,改造后的工程必须能重新融入原有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肌理;
城市的视觉设计必须反映城市功能,城市的秩序是城市功能秩序的体现;等等。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面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明镜,值得每一个开发商、规划师,各级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者,尤其是市长们时时参考,观照一下自己的行为。
雅各布斯强调城市规划必须以理解城市为基础,而正是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出发,雅各布斯发现城市生命和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城市功用的综合性和混合性,而不是其单一性。因此,城市规划的第一要旨在于,如何实现多种功用的混合,为各种功用提供足够的空间。城市功用的丰富多样性,才使城市有了活力,城市文明才得以延续和繁荣。
而当时的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正统规划理论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实践,恰恰无情地扼杀了城市的活力。《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矛头所指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导西方城市建设的物质空间规划和设计方法论,主要包括霍华德的“花园城市”理论、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市”理论,以及始于19世纪90年代而流行于北美的城市美化运动(更确切地说是城市化妆运动),合起来,它们被雅各布斯讥讽为“光明花园城市美化”(Radiant Garden City Beautiful)的“伪科学”。它们不是从理解城市功能和解决城市问题出发,来规划设计一个以城市居民生活为核心的、富有活力的城市,而是以逃避城市和营造“反城市”的“花园”为目标,用一个假想的乌托邦模式,来实现一个纪念性、整齐划一、非人性、标准化、分工明确、功能单一的所谓理想城市;凡是与这一乌托邦模式相违背的城市功能和现象,都被作为整治和清理的对象。
确切地说,雅各布斯所激烈抨击的是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十多年里那种无视城市社会问题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和重建方式。在雅各布斯之前,这种批评和反思已经在许多社会学者和城市规划学者中悄然兴起,但雅各布斯的抨击是最无情而有力的。尽管有争议,且并非出自专业规划理论家之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仍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代表了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城市被理解为建筑的延伸,或是建筑的放大;城市规划被理解为物质空间的设计,尤其是美学意义上的城市整体设计;人们误认为一个优美的城市图案和空间设计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城市规划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规划师(常常是建筑师)依据一个乌托邦模式,设计他认为理想的城市;规划成果最终体现为作为终极成果的、类似建筑物施工图的蓝图。《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之后(更确切地说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城市逐渐被清晰地理解为一个系统,有着复杂的结构和丰富多样的功能,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而城市规划是一个建立在对城市的理解基础上的、系统的调控过程;它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更多的是一个政治过程,绝不是一个纯技术的过程;规划不是以技术蓝图为终结,而是一个多解的过程和一个不断根据系统的反馈进行调整的、动态的城市管治过程。
城市是个活的有机体,城市规划本身也是一个富有生命的活的过程。而价值观和社会道义,更确切地说是尊重和关怀普通人的价值观和道义,是这个生命过程中跳动的心脏和灵魂。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和西方的城市规划及建设的思想早已沿着雅各布斯所呼唤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向大大前进了,雅各布斯当年提出的许多思想和原理早已成为西方城市规划教科书的内容,并被广泛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导则而付诸实施。
斗转星移,快速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的幽灵从西半球来到了东半球的中国。今天不妨也将雅各布斯的那面城市生与死的明镜高悬在大江南北各大城市的上空,照照我们的大城市。我们会发现,非常可悲的是,我们并没有从美国和西方城市的生死试验中获得经验和教训,利用城市化这个三千年难得一遇的良机来建设美好家园,而是在变本加厉地扼杀我们城市的活力,毁灭城市的特色。
如果说学习西方先进思想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把雅各布斯女士的那面城市生死之镜,比作《红楼梦》中贾瑞从神秘道士那里得到的、警幻仙姑所制的那面“风月宝鉴”,它正可照见风花月夜,最终却使人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命归黄泉;反则可照见骷髅朽骨,却可以救人于膏肓,有起死回生之效。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们,抑或市长们,已经或正在用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代价,乐此不疲地为了片刻的短暂欢愉,挥霍着城市机体的生命:
看哪,各大城市的科技园区、大学园区、中央商务区、文化中心、大剧院如雨后春笋出现,创造了多少“干净整洁”的死寂边缘和毫无生机的单一功能区,而原有的故居民宅早已被推土机“三通一平”彻底抹去;
看哪,一个个活生生的“城中村”是如何被无情地“铲除”消灭,并作为城市建设的政绩被广为赞颂;
看哪,街边挣扎着生长出的小摊小贩们,或者是形形色色的特色零售街、艺术家村,是如何被警车和推土机当作有碍市容的垃圾,遭到周期性铲除,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无不在美化和净化的名义下不分青红皂白地不断受到遏制;
看哪,我们的一个个居住小区是如何被围困在各自的铁栏围墙内,与城市和街道分得清清楚楚,充满活力的街道生活正在被抛弃,隔阂与冷漠正在城市中滋生;
看哪,宽广的城市车行干道无情切割着城市的社会、经济和空间结构,恨不得让汽车开进城市的每个角落,步行和自行车空间一再被挤压,使城市的人性空间和活力不断受到侵蚀;
看哪,十几甚至几十公顷的巨大硬地广场、远离居民和其他城市功用的大型体育设施、奥林匹克中心和会议中心正在各地轰轰烈烈地剪彩,谁曾思考,它们除了纪念性的展示作用,对城市的活力又会有多大的贡献?
看哪,我们每个城市的财力和物力是如何被集中挥霍于城市总体规划所描绘的“××轴”和“××中心”等形式的蓝图,当年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中的故技、当年希特勒所热衷的城市轴线,是如何通过当年帝国建筑师的徒子徒孙们和狂热的信徒们在中国各地城市中上演。
借用雅各布斯“仙姑”的“风月宝鉴”,希望我们的民众、规划师和市长们能看到一个个正在走向病态的中国城市,果能如此,则城市生命由此走出歧途。
所以,让我们再次聆听雅各布斯的告诫: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城市活力,城市规划必须围绕促进和保持活力来作文章: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最大限度地催生和促进大城市的不同地区中的人及其使用功能的多样性;而要实现城区功用的多样性,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必须有两种以上主要使用功能,小街区,不同年代的旧建筑的同时存在,足够的人口密度。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促进连续的街道邻里网络的形成,它是城市孩子们可以安全健康地成长、大人们可以交流的公共空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空间结构。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打破对城市物质和社会结构有破坏作用的真空边缘带,它们往往由功能单一的设施和机构所造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市民对大城市和城市分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为原居民的就地脱贫和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实现城市贫民区的脱贫,而不是靠阉割手术式的集中安置和大规模拆迁来解决,那样只能使贫民区从城市的一个地方扩散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治标不治本。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珍惜和呵护已经形成的,基于功用多样性的城市区域,避免某种强势功能排斥其他有共生关系的弱势功能,导致其向功能的单一化趋势演化。
为了城市活力,规划必须彰显反映城市功用的城市视觉秩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与功能不符或者有碍功能的城市化妆。
感慨爱因斯坦的名言所揭示的:“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永恒的,其一是宇宙,其二便是人类的愚蠢,而对于前者我还不敢确定。”但我更愿看到中国古老寓言所期望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愿中国的城市不会落得《红楼梦》中贾瑞的结局,在狂欢与庆典中走向灾难。
2020年3月14日星期六,避疫于云南普洱太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