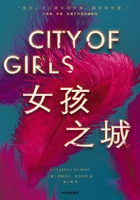
第02节
总之,我平安抵达了纽约——一个刚出壳的姑娘,头发上真的挂着鸡蛋黄。
佩格姑姑本该来中央火车站接我的。那天早上,在我从尤蒂卡上了火车之后,父母才告诉我这件事,但没人提到任何具体的安排。没人告诉我具体应该在哪里等她。而且,没人告诉我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拨哪个电话号码,也没人告诉我万一落单了可以去哪个地方。我只要“跟佩格姑姑在中央火车站见面”就行了,没别的。
嗯,中央火车站是够气派的,跟宣传的一模一样,但它也是个让你找不到人的好地方,所以我在到站之后找不到佩格姑姑没什么可惊讶的。我带着自己那堆行李在月台上站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看着火车站里人头攒动,但没有一个人像佩格。
不是我不知道佩格长什么样。在那之前我已经见过姑姑几次了,虽然她和我父亲走得并不近。(这么说可能都算是客气的了。我父亲有多不待见自己的妈,就有多不待见自己的姐。每当我们在饭桌上提起佩格时,父亲都会哼着鼻子说:“活得倒是挺潇洒啊——四处闲逛,活在假想的世界里,还大把大把地花钱!”而我则会想:这听上去确实挺潇洒啊……)
在我还小的时候,佩格回来跟家人一起过了几次圣诞节——但次数不多,因为她总是跟着剧团四处巡演。十一岁时我陪父亲来纽约出差,在这里玩了一天,这是关于佩格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佩格带我去中央公园滑冰,还带我去见了圣诞老人。(虽然我们都觉得以我当时的年纪,圣诞老人实在太幼稚了,但我说什么都不会错过他的,我还因为要跟他见面而暗暗激动来着。)我们俩还一起吃了顿自助午餐,那是我生命中相当快乐的一天。我和父亲没有在城里过夜,因为父亲讨厌纽约,也不信任它,但我可以跟你保证,那天非常辉煌灿烂。我觉得姑姑棒极了。她拿我当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小孩看待,这对于一个不想被当作小孩看待的十一岁小孩来说,意味着一切。
佩格姑姑最近一次回到我的家乡克林顿是为了参加莫里斯奶奶,也就是她母亲的葬礼。举行仪式时她坐在我旁边,用她又大又能干的手挽着我的手。这个姿态让我感到既宽慰又惊讶(我的家人不太喜欢手挽手,这可能会让你觉得震惊)。葬礼结束后,佩格用伐木工一样大的力气拥抱了我,我融化在她的臂弯里,眼泪像瀑布一样喷泻而出。她身上有薰衣草香皂、香烟和杜松子酒的味道。而我则像一只悲惨的小考拉一样挂在她的身上。但葬礼结束后,我并没能跟她相处太长时间。她得赶紧离开镇子,城里有一部剧等着她去制作。我觉得在她怀里崩溃挺丢人的,虽然那时候她让我觉得很踏实。
毕竟,我几乎不认识她。
实际上,当十九岁的我踏入纽约的时候,我对佩格姑姑的了解加起来只有下面这么多:
我知道佩格在曼哈顿中城区的某个地方开了一家剧院,叫莉莉剧院。
我知道她最开始没想干舞台剧这行,但却阴差阳错做了现在的工作。
我知道佩格受过培训,当过红十字会的护士,这事挺有意思的,一战期间她还被派到法国驻扎过。
我知道在那期间,佩格突然发现与照料受伤士兵的伤口相比,自己在为他们组织娱乐活动方面更有天赋。她发现自己在为战地医院和兵营组织既便宜又短小、虽艳俗却幽默的戏剧方面很有一套。战争是门可怕的生意,但它却能教给每个人一点东西;这场战争教会了我姑姑如何作戏。
我知道战争结束后,佩格在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的一家剧院里工作。她在西区制作时事讽刺剧时遇到了她未来的老公,比利·布尔——一个同样决定战后留在伦敦,在戏剧界闯出一片天地的潇洒帅气的美国军官。跟佩格一样,比利也是从“底层”出来的。莫里斯奶奶曾经形容布尔一家“富得让人恶心”。(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都纳闷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奶奶很尊重财富,财富多到什么地步会“让人恶心”呢?有一天我终于向她问了这个问题,她答道:“他们是纽波特人,亲爱的。”好像这就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了似的。)尽管比利·布尔是个纽波特人,他跟佩格还是很像,因为他一直将自己出身其中的那个精英阶层拒之门外。跟光鲜亮丽但却让人压抑的时髦生活相比,他还是更喜欢坚韧不拔、充满诱惑的戏剧世界。而且,他还是个花花公子。他喜欢“作乐”,莫里斯奶奶说,她这是在委婉地表达“喝酒,花钱,追女人”的意思。
比利和佩格·布尔结婚后就回到了美国,他们一起创办了一家巡演剧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会儿,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跟一小群核心戏骨在路上奔波,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巡回演出。比利负责撰写和主演时事讽刺剧,佩格负责执导并把它们制作出来。这对夫妻从来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野心。他们只不过是在享受生活,回避成年人更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已。但尽管他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成功,成功还是意外地追上了他们,将他们捕获。
一九三零年——那时大萧条愈演愈烈,整个国家都瑟瑟发抖、倍感恐惧——我姑姑和她爱人不小心创作了一部热门剧。比利写了一部叫《欢喜韵事》的舞台剧,这部剧太欢乐、太好玩了,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欢喜韵事》是一部滑稽音乐剧,讲的是一个来自英国贵族阶层的女继承人爱上了一个来自美国的花花公子的故事(这角色自然是比利·布尔演的)。那就是一个小打小闹的俗套剧,跟他们丢到舞台上的所有其他剧没什么两样,但它却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在全美范围内,好长时间没找过乐子的矿工和农民把他们兜里的最后一点零钱都掏了出来,就为了看一眼《欢喜韵事》,让这部简单的无脑剧成功地赚到了钱。事实上,这部剧积累的人气之高,在当地报纸上收获的好评之多,使得比利和佩格在一九三一年时把它带到了纽约,让它在一家著名的百老汇剧院里上演了一整年。
一九三二年,米高梅将《欢喜韵事》改编成了电影——是比利写的,但不是由他主演。(威廉·鲍威尔替他演了。那个时候比利已经想明白了,作家的生活比演员的生活要容易一些。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工作,他们不用看观众的脸色,也没有导演对他们发号施令。)《欢喜韵事》的成功催生了一系列摇钱树电影续集(《欢喜离婚》《欢喜婴儿》《欢喜游猎》),好莱坞在几年时间内一直批量生产这类电影,就像用灌肠机做香肠一样。“欢喜”宇宙让比利和佩格赚得盆满钵满,但它也标志了他们婚姻的终结。爱上好莱坞之后,比利再也不回头了。至于佩格,她决定关掉巡演剧院,用自己那一半的“欢喜”版税在纽约买下一家又大又老、破旧不堪、但却完全属于她的剧院:莉莉剧院。
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九三五年前后。
比利和佩格没有正式离婚。虽然他们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合,但在一九三五年之后,你没法说他们还是“夫妻”。他们不住在一起,也不在一起工作,而且在佩格的坚持下,他们的财产也不共有了——这意味着那些闪闪发光的纽波特银两现在都跟我姑姑没关系了。(莫里斯奶奶不明白为什么佩格会心甘情愿地离开比利的钱,她只能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而且毫不掩饰失望之情:“恐怕佩格向来不在乎钱吧。”)我奶奶猜测,佩格和比利之所以没有办离婚手续,是因为他们太“不拘泥于传统”了,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纠缠。或者没准他们还爱着对方。只不过他们的爱情是只有当夫妻二人被一整片大陆隔开的时候才保鲜得最好的那种。(“别笑,”我奶奶说,“很多夫妻这样才能处得更好。”)
我只知道比利姑父缺席了我的整个少女时代——最开始他在巡演,后来他去加利福尼亚定居了。实际上,因为他缺席得太厉害,所以我压根就没见过他。对我来说,比利·布尔就是一个谜,一个由故事和照片组成的谜。可那都是多迷人的故事和照片啊!我和莫里斯奶奶经常在好莱坞八卦杂志上看到比利的照片,或者在沃尔特·温切尔和洛厄拉·帕森斯 各自的八卦专栏里读到关于他的文章。比如说,当我们得知他参加了珍妮特·麦克唐纳和金·雷蒙德的婚礼时,我们简直喜出望外!《综艺》杂志上刊登了一张他在婚礼签到台的照片,当时他就站在穿着嫩粉色婚纱、闪闪发光的珍妮特·麦克唐纳身后。在照片里,比利正在跟金杰·罗杰斯和她那时候的老公刘·艾尔斯交谈。奶奶指着比利对我说:“他在这儿呢,还是老样子,在全国各地拈花惹草。瞧瞧金杰冲他笑的那副模样!如果我是刘·艾尔斯的话,我得盯紧自己的老婆了。”
各自的八卦专栏里读到关于他的文章。比如说,当我们得知他参加了珍妮特·麦克唐纳和金·雷蒙德的婚礼时,我们简直喜出望外!《综艺》杂志上刊登了一张他在婚礼签到台的照片,当时他就站在穿着嫩粉色婚纱、闪闪发光的珍妮特·麦克唐纳身后。在照片里,比利正在跟金杰·罗杰斯和她那时候的老公刘·艾尔斯交谈。奶奶指着比利对我说:“他在这儿呢,还是老样子,在全国各地拈花惹草。瞧瞧金杰冲他笑的那副模样!如果我是刘·艾尔斯的话,我得盯紧自己的老婆了。”
我借着奶奶那个镶着珠宝的放大镜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照片。我看到一个身穿燕尾服、长相帅气的金发男人把手搭在了金杰·罗杰斯的小臂上,而她也的确面露喜色,两眼冲他放着光。他比站在自己两边的那些明星更有明星的样子。
我很惊讶,这样一个人竟然娶了我的姑姑佩格。
佩格很棒,这毫无疑问,但她相貌平平。
他究竟看上了她什么?
我怎么也找不到佩格。
已经过了太长时间,我彻底放弃了在火车站台上跟她碰面的念头。一个戴红帽子的行李搬运工帮我寄存了行李,然后我便在中央火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闲逛了起来,想在不断汇合的人潮中找到我姑姑。你可能会以为当我发现自己在纽约只身一人,没有计划也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时候会很慌,但不知怎的我并没有。我相信一切最终都会没事的。(也许这是有优越感的人的特点:某些出身高贵的年轻姑娘就是无法想象,也许短时间之内不会有人来拯救她们。)
最后我放弃了闲逛,坐在了候车大厅附近一张很显眼的长椅上,等待着我的救赎。
呦,最后我还真被人给找到了。
拯救我的是个矮个子的银发女人,她穿着一身朴素的灰色西服,像圣伯纳犬靠近被困的滑雪者一样朝我走来——全神贯注,庄重严肃,一心只想救命。
实际上,“朴素”并不能强有力地描述这个女人身上的这套西服。那是一个双襟的、四四方方的东西——这种衣服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的,好让全世界都误以为女人没有胸、腰和屁股。我看这衣服像是从英国进口的,难看死了。这女人还穿了一双肥肥大大的黑色低跟牛津鞋,戴了一顶老式的绿色强缩绒羊毛帽,就是开孤儿院的女人喜欢戴的那种。我在寄宿学校里见识过这种人: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拿阿华田当晚饭,然后再用盐水漱漱喉咙好让自己精神抖擞的老处女。
她从头到脚都很平庸,更重要的是,她是故意让自己这么平庸的。
这个砖头一样的中年妇女向我走来,很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她皱着眉头,手里拿着一张镶在华丽银相框里的照片,尺寸大到让人尴尬。她看了看手里的照片,又看了看我。
“你是薇薇安·莫里斯吗?”她问道。她清脆的口音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件双襟西装不是全纽约唯一一件其貌不扬的英国进口货。
我回答说我是。
“你长个了。”她说。
我很困惑:我认识这个女人吗?我小时候见过她吗?
看到我这么困惑,这个陌生人给我看了下她手里的照片。这下我更迷糊了,因为那东西竟然是我家的全家福,大概是在四年前拍的。这照片是我们在一家很像样的照相馆照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觉得我们有必要“正式地留个影,哪怕就这一次”。照片上有我的父母,他们正强忍着被一个商人拍照的侮辱。照片上有我那个看上去心事重重的哥哥沃尔特,他把手搭在母亲的肩膀上。照片上还有年轻版的我,瘦瘦高高的,穿着一条对那个年龄的女孩来说幼稚得过头的水手裙。
“我是奥利芙·汤普森,”这女人宣布了自己的名字,她的语气说明她已经习惯了宣布各种东西,“我是你姑姑的秘书。她来不了了,今天剧院出了点紧急状况,着了场小火。她让我来接你。抱歉让你久等了。我几个小时前就来了,但因为我只能靠这张照片认你,所以花了点时间确认你的位置。你应该能理解的。”
那时候我很想笑,现在仅仅是回忆起这个场景我也很想笑。一想到这个决绝的中年妇女拿着一张镶了银相框的大照片在中央火车站里走来走去——这相框看上去像是从哪户有钱人家的墙上匆匆忙忙扯下来的一样(事实也的确如此)——盯着每张面孔看,想把眼前的人跟四年前这张照片上的小姑娘对上号,我就很不厚道地想笑。我怎么就没看见她呢?
不过奥利芙·汤普森似乎并不觉得这好笑。
我很快就会发现她这个人就这样。
“你的包,”她说,“拿过来。然后我们打车去莉莉剧院。晚场表演已经开始了。快点吧。别跟我耍滑头。”
我顺从地跟在她身后——像一只鸭宝宝跟在鸭妈妈身后。
我没跟她耍滑头。
我心想,“着了场小火?”——但我没有勇气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