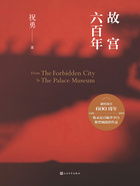
四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蛰伏已久的朱棣终于走出燕王府,誓师起兵,南下讨伐朱允炆,向自己的皇位挺进。

《明成祖朱棣像》轴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这场决定王朝未来命运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
三年后,朱棣率领军队冲入南京紫禁城的时候,朱允炆去向不明。《明史》说:“燕兵入,帝自焚”;又说:“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不知所终”,似乎在暗示朱允炆并没有死去。朱允炆是死是活,从此成为明朝最神秘的事件,一直争论到今天。
随着朱棣在龙椅上缓缓坐定,永乐时代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下诏改北平为北京;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又下诏以明年(即永乐五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
圣旨宣读完毕,我猜想宫殿上下一定会陷入一片寂静,好似有一块冰被放置在空气中,空气似乎变成一个巨大的固体。那时已是初秋,史书上写,是闰七月,南京城最热的时分,但当时在场的人,却仿佛坠入了寒武纪,分明看到空气中的冰块凝结着新的空气,一点一点地膨胀,变成一个庞然大物,重重地向每个人逼近。我猜想现场的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血流骤然停止,大脑严重缺氧,四肢变得麻木。时代的巨大变化,犹如一辆急剧翻转的过山车,让人猝不及防。
在北京营建新皇宫的原因,《明太宗实录》里不着一字,以至于清朝康熙皇帝曾经不无挖苦地说:“朕遍览明代《实录》,未录实事,即如永乐修京城之处,未记一字。”
在永乐皇帝以前,北京从来不曾做过汉族中央王朝的定都。
在永乐四年,明成祖永乐皇帝发布这道谕旨的时候,北京还是一座偏远荒蛮的小城。那时的北京,虽然空气清澈,没有雾霾,但永定河经常泛滥,土地荒寒,更加上战火不断,往往几百里不见人烟,以至于永乐皇帝登基之后,还要组织大规模移民。在中国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帝都,始终不离黄河左右,在长安—洛阳的轴线上迁徙。隋代开凿大运河,打通了帝国南北经络,长江以南地区成为丝绸、茶叶、瓷器、冶铁、铸铜等重要产业基地,宋室南迁,更使长江以南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成为“大中国经济圈的主要生产基地”,明朝立都南京,亦基于此。
北京的古名叫幽州。在夏代,有一个伟人画了一个圈,把北京(幽州)圈划在“中国”的区域之内,那个伟人就是夏禹。夏禹治水之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幽州就是其中之一。当然,有之前的一代代中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于斯、合于斯,夏禹画出那个圈,才不费吹灰之力。
两汉、魏、晋、唐代都曾设置过幽州。但历朝历代,北京都是中原王朝的边陲之城,一直处于中原游牧民族与北方草原部落势力的交叉点上。这座历史上著名的“边关”,仿佛一直停留在寒武纪,楼船夜雪,铁马秋风,千年的风雪,已将这座城池浸透,在砖石间凝结成一层又一层无法消融的冰花。唐代,一个名叫陈子昂的无名军曹,面对这座古城,吟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他诗里的那个幽州是那么的苍茫、幽远、悲怆,即使在繁花似锦、歌舞升平的盛唐,也读不出一点安乐的味道。五代十国时,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当作礼物,毕恭毕敬地送给辽国,让北方草原王朝的势力范围突破长城防线,拓展到长城以南,长城也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防守意义。收回燕云十六州,从此成为宋朝皇帝最强大的梦想。石敬瑭这个大礼包,就包括了北京(幽州)在内,北京自此由大宋王朝的北方城市,变成了辽帝国的南方城市。
有意思的是,北方游牧民族,却不止一次地把北京定为首都。北京仍然是战略前沿城市,只不过这一次转换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视角上。我们的视线,不再是中原北望,而是掉头向南,自林海雪原出发,伸展向中原的千里沃野。北京,是他们驻足南望时最近的“瞭望点”,是他们临近中原的“桥头堡”“前哨站”——在今天北京房山良乡,还有一座辽代砖塔(始建于隋代,辽代重建),朱棣发起“靖难之役”,就曾自它身边纵马驰过,然后,融入暮色苍茫的荒野,杀向灯火繁华的江南。它虽为佛塔,但辽代以后,一直用于作战。北宋据有北京(大名府)时,北宋军人用它观察辽国军人,而辽国据有北京(辽南京)时,辽国军人又以它观望南方军情。所幸的是,这座五层空心砖塔,历经千年战争风烟而依然伫立,如今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楼阁式空心砖塔。
自辽太宗会同元年(公元938年)起,幽州就成为辽国的五个首都(五京)之一,称“南京”。金朝时,中都设在北京。元代以金的离宫(今北海公园)为中心重建新城,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称大都,俗称元大都,亦称“汗八里”。它的浩大与繁华,让第一次走进它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张大了嘴巴,然后用他的威尼斯口音转告全世界,人世间居然有如此奇幻绮丽之城。体形硕大的元帝国,终于把北京养育成了一个国际大都会。
在这座城里,朱棣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早已与这座城血肉相融。朱棣不喜欢南京,这座由父亲朱元璋几经犹豫之后选定的都城,虽依傍帝国的经济中心、富庶之地,但它太小、太秀、太阴柔,容不下朱棣的野心。烟雨江南、吴侬软语,那么容易瓦解一个帝王的意志,使他成为一个偏安一隅的井底之蛙。那时,朱棣的视野,已超越了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整个大陆。那时的亚洲大陆东段,蒙古帝国的残余势力盘踞在北方,它的版图东起松辽平原,西逾阿尔泰山,南出燕山、阴山一线,势力不可谓不强大。永乐初年,这个蒙古帝国又分为东西两部,东部为“鞑靼”,西部为“瓦剌”。建立未久的大明王朝,被迅速裹入这样一个“三国鼎立”(即明朝、鞑靼蒙古、瓦剌蒙古)的大陆格局中。在朱棣的心底,更想做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在资本主义海洋霸权建立以前,这一地区,一直是东西方世界的重要交通线。而北京这座城,虽远不如南京繁华,却是北方天际线下一座“众多民族杂居”“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性大都市”![[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第2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E7F582/172421391051087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50741980-bAxHK0N9S7n773qVcUjLwwxxvB1KkAZT-0-34a3cb0167e023c84c58262aa8613959) 。况且,他也不愿在前两位皇帝的阴影之下亦步亦趋,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一个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盛世,那才堪称真正的“天下”。
。况且,他也不愿在前两位皇帝的阴影之下亦步亦趋,他要塑造一个全新的帝国——一个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盛世,那才堪称真正的“天下”。
我十分认同韩毓海先生的观点:世界史并非是随着西洋“发现世界”的航海才被揭开的,欧洲的海洋殖民和帝国主义活动,也并非世界史唯一的、根本的动力,——而在“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中又常常被忽略的,乃是横贯欧亚的大陆强权之间的交往、交融、冲突和竞争,这些交融与竞争既构成了元、明、清三个中国王朝更替的大背景,也是世界史展开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其中:奥斯曼帝国、帖木儿汗国、金帐汗国、沙法维王朝与中国历代王朝之间长期的交往与博弈,亦是世界史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头等大事,这也使得欧洲、西亚、中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深刻地嵌入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理念之中,使得中国的北方地区,成了一个被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称之为“内亚洲”或者“内亚-欧”区域中发生的,清朝兴起的根本原因,也只能从蒙古、东北亚和明朝之间的多方博弈中才能看出。
正如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所说:“成祖永乐颇有才能,只是除了夺取帝位及迁都北京的大动作之外,其他并无更张。” 但仅仅迁都北京一项,就足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定都选择,使边缘成为中心,成为帝国的枢纽,才有三个世纪后(清代)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使中华帝国同时拥有了整合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的两大平行体系,交互影响和运作,又进而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使中华帝国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但仅仅迁都北京一项,就足以奠定他的历史地位,因为他的定都选择,使边缘成为中心,成为帝国的枢纽,才有三个世纪后(清代)东亚草原、高原地带第一次的大统一,使中华帝国同时拥有了整合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的两大平行体系,交互影响和运作,又进而成为一个跨民族、跨文化的共同体,使中华帝国成为东亚超级大国,它的实力甚至“超过了成吉思汗全凭武力建立的大帝国”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Secret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中说,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六百年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Secrets of China's Forbidden City)中说,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六百年后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