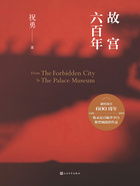
五
2020年,紫禁城迎来建成六百周年,我自然不会沉默。我要写紫禁城,写紫禁城里的十个甲子。只是紫禁城、六百年,无论空间,还是时间,都过于庞大,这个题目把我吓住,我在心里盘桓了许多年,迟迟没有落笔。
2014年,冬日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写下了第一行字。像一个旅人,整理好了行装和心情,开始了远行。由于其中交叉着其他书的写作,使本书的写作变得断断续续、迟迟疑疑,到2016年,因为我策划大型纪录片《紫禁城》的关系,才开始变成一项持续而稳定的工作。但它仍然是一部个人化的著作,与纪录片无关。唯有个人化,我才能将个人的认知与情感发挥到极致。
写作本书,前后用了将近五年,但集中写作的时间,我用了三年多,我惊奇地发现,这个时间几乎与当年集中建造紫禁城的时间一致。也就是说,我的写作速度,是与营建紫禁城的速度一致的,这让我对这座城的建造,有了一种更真切的体验。我还发现,写紫禁城与建紫禁城在有些地方极为相似,它需要耐心,需要经验,更需要时间。紫禁城是一块砖一块砖、一根木一根木搭建起来的,日久天长,它的轮廓才在地平线上显现出来,写作也是一样,日子久了,作品才眉目清晰、结构健全。不同的是,建故宫的材料是木,是石,写故宫的材料是文字,最多还要算上一些标点符号。我试图用文字筑起一座城,一如北岛在散文集《城门开》的自序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
六百年的故宫,那么沉重。我不想沉重,我想轻灵,想自由,像从故宫的天际线上划过的飞鸟。为此,我找到我自己的方法。营建这座城是有方法的,否则,像这样一座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的超级工程,在那个没有起重机的年代,是不可能在十五年之内(主要工程在三年半内)完成的。表达故宫,必然也要找到方法,才有可能找到一个支点,撬动这个庞大的主题。雨果写《巴黎圣母院》,罗兰·巴特写《埃菲尔铁塔》,三岛由纪夫写《金阁寺》,都成为了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当然,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我不可望其项背,但他们的作品,至少证明了写作的可能性,即:通过文字来驾驭一座伟大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文字不仅描述了一座建筑,甚至构成了一座建筑。
写城如同建城,首先要考虑结构问题。故宫(紫禁城)六百年,容纳进了无数的人与事,史料浩繁,线索纷乱,在我眼里是一片混沌,要讲清它的六百年历史,实在不知从哪里下手。历史是一盘散沙,而所有可供阅读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人为组织的历史。没有这种人为组织,也就没有历史。比如《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就是一种组织历史的方式。自从司马迁创造了这种组织方式,它贯穿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书写,《二十四史》中后来的那些史书(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合称《二十五史》)都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标准的历史写作方式也被称为“正史”。
历史不是已逝时间的总和,历史是我们认识过去的逻辑。因此,历史如同建筑,有感性的、具有审美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具有逻辑性的一面。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不准备把它写成一部编年史,那样太容易成为一本流水账。我要寻找一种更亲切、更妥帖的叙事结构。经过一次次的尝试,我还是决定采用以空间带时间的结构。
首先,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看那浩瀚的宫殿,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本书的讲述,也像所有走进故宫(紫禁城)的人一样,开始于午门,然后,越过一道道门,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全书共十九章,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在其余的十七章里,我把故宫(紫禁城)分割成许多个空间,然后,带着读者,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
其次,也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在周代,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进而划分出四季: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最短的为夏至日,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除此,中国人还通过观察星象(北斗星)来确认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中间日期,也就是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其他节气的日子,也就可以推算出来。
根据表杆和北斗星斗柄的指示,把一年分成四个季节、十二个月,又同样使用立表测影,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太和殿前的日晷,晷面上刻划着“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在平面上分出四隅(东南西北)、八天干、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根据晷针在十二地支的投影确认十二个时辰(二十四小时)。
时间产生于空间,空间就是时间。
故宫(紫禁城)是空间之城,同时也是时间之城。故宫的中轴线(从午门中心点到神武门中心点)是子午线,南为午,北为子,与夏至、冬至分别对应;而北京城的日坛与月坛的连线则刚好是卯酉线,与春分、秋分相对应——明清两朝,春分行日坛之祭,迎日于东;秋分行月坛之祭,迎月于西。
我的同事王军先生在2016年进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专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故宫(以及整个北京城)子午线与卯酉线的交叉点,刚好是太和殿前广场。这表明三大殿所代表的帝王权力,不仅是空间的主宰,也是时间的起始。
自河姆渡文化以至明清,这套时空一体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数千年不曾改变,故宫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分别悬挂在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三块匾,内容都取自《尚书》,分别是:“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皆象征着三大殿乃立表之位。
故宫的平面图里,其实也包含着一个“二十四山地平方位图”,可以分出四隅、八天干、十二地支。从某种意义上说,故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日晷。它的空间系统里,暗含着一套完整的时间系统。故宫的历史、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它特有的空间和时间秩序展开。
所以,讲建筑,讲空间,最终还是要讲历史,讲时间。写“硬件”(建筑),也是为了写“软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没有了空间,所有的时间(历史)都没有了附着物,都会坍塌下来;而没有了时间(历史),所有的空间都会变成空洞。
在故宫(紫禁城),绝大部分建筑空间都容纳了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风云,弱水三千,我只能取一瓢饮,面对每一个建筑空间,我也只能选取了一个时间的片段(当然是我认为重要的片段),让这些时间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间上,衔接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拼图。这样,当大家跟随着我的文字,走完了故宫的主要区域,从神武门出来,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完成了对故宫六百年历史的回望与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