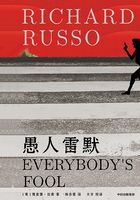
弹簧圈
“我相信,”长袍牧师颤抖着说,语调模仿着马丁·路德·金,“巴顿·弗拉特法官称这里为我们的正义之城,是想让我们理解这称之为家的地方不只美丽,而且还体现了另一含义‘公正’,我们的社区是公正的楷模,它代表……”
说到这儿,他仰视天空,像是在找一个生涩的词或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显然,在三万里高空飞机留下的尾迹云中,他找到了。
“正气凛然。”他下了结论。
雷默也向上看去,觉得头晕目眩,还犯恶心,他的膝盖在热浪中突然变软了。如果真在那飞机上该多好。在想象中,他看到自己在某个不知名的目的地着陆,神奇地穿着其他行业的制服——他擅长的行业。那是一种连贝卡、弗拉特法官,甚至贝丽尔小姐做梦都想不到的新生活。当然,他自己也没想到过。
“那么,我们会问,”长袍牧师继续说着,他的目光仍然盯着天空,“怎么才能把这个伟人的梦想变成现实?怎么才能保证我们的正义之城是他最深远的信念之一?”
他到底着了什么魔会去做警察?是因为司法机关强调规则吗?还是个孩子时,他就觉得规则令人欣慰。规则暗示着生活的根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确保了他一定能轮到击球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已经目睹,在他的同龄人中,有太多孩子要不是被大人强制要求,他们是不会公平竞争的。他最欣赏的规则是简单明确的。做这个。不准做那个。人们喜欢明确,不是吗?那么做警察,就是有关秩序,有关执行人们的意愿,有关公益。没错。事实上,这份工作教给了他一个道理,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会觉得规则令人欣慰,反而因规则而恼怒。即使是最通情达理、最不言自明的规则,他们也坚持要论证其合理性。在他们不可能网开一面的案子里,他们要求特殊处理。他们永远都在试图说服他,他们违背的规则要么是太愚蠢,要么是太专制。当然雷默不得不承认,其中有些确实是。更糟糕的是,各式各样的市民全都怀疑这些制定的法律对他们不利。穷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富人发牌时作了弊,而富人们则认为重新洗牌会毁了他们也毁了文明。贝卡情绪好时,会争辩说婚姻制度的设置是为了奴役整个性别。有时,她的辞藻特别针对个人,你会觉得雷默自己就是第一届婚姻规划委员会的一员。在警察学院,法律制度至少大体上还讲得通,但现在,雷默也不能肯定了。所以,他想,离开吧。只要登上飞机,离开。因为在贝卡死后,他变了。他对职业的信念被消磨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值得他留在这儿的?
在法官敞开的坟墓的另一边,站着一个大约十二岁的小姑娘——是尊敬的法官大人的侄女或孙辈?——她正专注地皱着眉头,盯着雷默的腹部。当然,她不可能知道他口袋里有车库钥匙,但她似乎对他的手在那儿做什么得出了错误的推论。他把手拿开时,他们的视线相交,她本来纯真的脸上泛起一个调皮又了然的微笑。雷默感觉自己脸红了,他两手放在胯前紧握,视线越过她投向远方。他的眼睛又一次被尾迹云吸引了。如果他去到一个崭新的地方,他会认得谁?谁又认得他?他又靠什么谋生?
一百码外的地方,在那条把山丘区与山谷区分开的土路边,停着一辆明黄色的挖土机,毫无疑问,就是它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挖出了法官的墓坑。雷默认出了罗布·斯奎尔斯,他是沙利的伙计,正坐在挖土机旁边的一片阴影下。他的姿势看起来像是在哭泣。他是在哭吗?难道他也想起了埋在附近的他爱的人?难道他也在渴望新生活、新工作?也许他会愿意和自己互换工作,雷默心想,挖墓和执法相比,更加平和、有益。死者不必再受到世界不公的困扰,也不会再抵制规则。把成千上万的死人都整整齐齐摆成排,他们也不会抱怨。你试试这样对待一个活人,看看会有啥结果。人们自称喜欢直线,毕竟,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但雷默越来越相信人类更喜欢走岔路。他天马行空地认为,也许贝卡就是这么想的——她有天生的不想走直线的本能。也许她并不是不爱他了,而是她对婚姻的刻板规则失望了:爱、荣誉、顺从。必须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也许对于她来说,作为警察的他逐渐代表了她不能再遵从的直线。想要走走岔路的冲动真的这么可怕吗?当你走了弯路,难道不还是有可能回到你的起点吗?如果有时间,难道贝卡不还是有可能回到他身边吗?也许他们之间耗尽的是时间,而不是爱。这么想令人好受多了。
最后发现她的人是他。那天他到家早了,他几乎从没早回来过,至少最近没有,从他们之间变了味后,就再没早回过了。一开始,慢慢有些兆头,然后就突然爆发了。那天早上他出发去工作前,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吵什么他甚至都不记得了。啥也不为又啥事都吵。最近,即使他最温和的言论都会引发一场由讽刺、泪水、生气和鄙视所形成的洪流。似乎一夜之间,能引发他妻子负面情绪的东西在以指数级暴增。然而,雷默可以感觉到,她那冗长乏味的抱怨中有一丝不同寻常。毫无疑问,她不爱他了,但仍有些不太对劲。她好像是在表演她所知道的所有有关婚姻危机的电视剧中的场景。他一直在找她周一发飙和周四发飙中的相同点。但并没有。她好像在用一大堆不相干的抱怨来吓跑他。这可以是很小很具体的事情——他忘了放下马桶盖,也可能是更含糊更泛泛的事——他不尊重她的感情,无论大小,都睚眦必报。
所以,当他把车开进他们的车道,看到走廊上那三个行李箱时,他马上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应该意味着什么:她要离开他了。相比其他情绪,这场景更让他觉得富有戏剧性甚至喜感。前门半开着——她是忘了东西,又进去拿吗?他记得自己穿过了草坪,想着他俩可能会在那儿碰巧碰上。她可能会犹豫一会儿,接着会下定决心。那他该怎么办?让她走吗?还是用武力强留下她,至少等到他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在困扰她?
她就在开着的门里面。她肯定走得很匆忙,这很是明显。楼梯最上面的地毯——现在团成一堆,垂在了半梯上——也许是罪魁祸首。雷默自己就不止一次在上面滑倒过。贝卡曾吩咐他去找块垫子铺在下面,但他一直将之抛在脑后。这,就在这儿,就是后果。她的前额栽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头发前垂遮住了脸,往上两个台阶是膝盖,胳膊在身后,屁股撅在半空中。她看起来就像是从楼梯顶部游着蛙泳去底部,在到达终点前死去的。
他在那儿全身僵硬地待了多久?他甚至都没有查看一下她是否真的死了,只是站在那儿盯着她,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哪怕是现在,已经过了十三个月了,他都不愿回想当时在现场他惊人的无能为力。他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是这整件事所具有的舞台效果——贝卡的身体居然不可思议地平衡成那样,也没有明显的血迹。对雷默而言,这就像是博物馆里的西洋镜,古古怪怪,令他难以琢磨。她毕竟是个演员,这让他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只是个表演。她不可能永远保持那可笑的姿势。如果他耐心些,她最终会站起来说,这就是你想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吗?快修好那该死的地毯!
但不是。那不是表演。贝卡死了。在等救护车的时候,他发现了她留在餐桌上折好的留言。对不起,上面写着,我也不想发生这事。请为我们高兴。上面的署名是贝卡一直用的大写的B。
她也不想发生这事?他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她说的“这事”不是指掉下楼梯或者死亡,因为她当然不可能预知这些。不,“这事”是指爱上别人。她不再爱他是他迟早都能妥协接受的事。事实上,他不是从最开始就明白,能娶到贝卡,是他的运气太好了,他们的婚姻是不可能持久的吗?但与另外一个人坠入爱河?替我们高兴?他连“我们”是谁他都不知道,这事就这么发生了?
在过去十三个月里,那个可怕的下午的情形——贝卡的死,急诊医生和那些在楼梯上围着她转的调查人员,被抬上轮床又被搬到前门的尸体,围观的邻居——都仁慈地开始褪散了,如曝光在太阳下的照片一样。汤姆·布里杰的话却还如重锤在耳。在他四十年的从业生涯中,汤姆学会了法医一贯尖酸刻薄的幽默。到了现场,他看了贝卡一眼——她的前额像是钉在了最下面的台阶上,她的屁股翘在空中——就开口说:“这女人到底在干啥?像弹簧圈一样翻跟头下楼吗?”他并没想到这样说是残忍的,没有意识到死者的丈夫就在隔壁,能听到。最可怕的是,他这话没错。因为贝卡看起来的确如此——像个弹簧圈一样弹下楼梯。这又让雷默想起了贝丽尔小姐,他八年级时,她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一个准确的词、一个精心选择的短语、一个确切的类比,抵得上一千幅图画。当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认为她说反了,但确实如此……当他记起那天下午可怕的场景,“像个弹簧圈”这个词组仍在他的脑子里循环播放,仍会让他的胃翻滚。这个词组甚至有味道:胃液在舌根翻滚。它们的含义还在逐渐演化,从恐惧到生气,再到绝望,最后到……什么?最近,当“像个弹簧圈”这个词组闪过他的脑海时,他发现自己不自觉地咧嘴笑了。为什么笑?他当然不认为这事有什么好笑的。即使贝卡是计划和别的男人私奔,她死了,他也并不高兴。至少他不认为自己高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并不意味着正义或者其他什么。那这不道德地想要笑的冲动从何而来?是从他内心某个黑暗的角落吗?他思考贝丽尔小姐经常问的那个问题,这个道格拉斯·雷默是谁?
“我亲爱的朋友们……”长袍牧师吟诵着,如果雷默没猜错的话,眼耳所及之处他根本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我认为在这世上,公平和正义不只是一个人的责任,不管他有多么伟大,多么睿智。不,那责任属于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个体……”
除了我,警察局局长道格拉斯·雷默心想。他眨眨眼睛,把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的东西眨进了眼里。他对任何责任都十分厌倦。不,他要做的事是放弃。投降。承认被打败。去做个挖墓人。
他突然意识到,当他沉浸在贝卡那悲剧的结局里时,他的手又下意识地移到了裤兜里,他又在按着那个车库遥控器的金属面了。这玩意儿能遥控多远?他心想。会不会有一扇门,或是几扇门——如果夏莉丝说得对的话,正在同时上升?是巴斯的某个地方?还是斯凯勒温泉镇?还是在奥尔巴尼?雷默发现自己因为这明显荒唐的想法笑了,想象着他老婆的情人,那个该死的家伙,看着他的车库门上去,然后下来,接着又上去,明白那个始作俑者就在附近,全副武装。
这就是他要寻求的妥协吗?放弃那个并不适合他的工作。但在那之前首先要找到这车库门的钥匙是谁的,让那狗娘养的家伙知道他被逮住了?只要雷默能够解决这一个谜团,他就能放下其他所有事情——责任、正义、义务、穿着灵活的鹿皮鞋的该死的易洛魁人,以及那些被长袍牧师兴高采烈挂到精神旗杆上的屁话。好吧,可能重塑自我是不太可能了,但你可以放下过去继续前进,不是吗?人们每天都是这么做的。他并不恨贝卡不忠。娶了她只是——就像他从事了执法工作一样——一个错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所有人,似乎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在排演晚宴上被介绍给准新娘时,杰罗姆(在雷默坦言除了他再也没有别的亲密朋友后,他才勉强同意做伴郎)脱口说出了这真相。“见鬼,道格,”他说,“你这是攀上高枝了啊,伙计。”当时,雷默很高兴听到别的男人的热忱赞誉,很骄傲能娶到贝卡这般美貌的女子。他的判断——自己是个幸运的家伙——能被他人明证当然让他感觉很好。但伴随着他朋友的热情盛誉,他的内心也开始揣测——这么好的运气注定会用光的。
“有个词,”牧师吟道,“用来描述我们当中那些没有每天肩负起让世界更美好更公正的重担的人。”
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现在在用胳膊肘轻推她的母亲。看,妈妈。看那个人手放在口袋里。他在干吗,妈妈?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个词是……‘逃兵’。”
他已经不再出汗了,雷默意识到,他湿透了的、沉甸甸的衬衫现在冰冷湿黏。他的膝盖像陷在了果冻里。
“那些人不光逃避了责任和人类的义务,还有上帝本身。是的,朋友们,逃兵逃离了上帝。”
对对,雷默心想,步兵步行了三里,炮兵炮打了田地。
女孩的妈妈正满含厌恶地审视着他,但这一次,他真正感到了自己的无辜,于是给了那女人一个圣洁的微笑。他一遍遍地按压着那金属按键,沉迷于那令人愉悦的想法——某个地方正有扇门因为真正的罪行而升起落下。
“那么上帝会怎样呢?”长袍牧师问道。
好问题,雷默心想。
“上帝爱逃兵吗?”
是的。他爱我们每个人。
“不!”长袍断然,反驳,“上帝并不。”
好吧,那上帝去死吧,雷默心想,他因为热浪和渎神而感到头晕目眩。上帝活该去死。
“因为逃兵就是懦夫。”
不,上帝才是。
“逃兵认为生活中的困难都是别人的,遮蔽太阳和理性之光的乌云都来自别人。”
但为什么云会成为任何人的问题?
“不,朋友们,巴顿·弗拉特不是逃兵。逃避不是他的遗产。在他朝着最后的福报进发时……”
泥土?腐烂?蠕虫?
“……我们最后一次向他致敬,在他面前重申……”
是在他身后吧,这不是明显的吗?
“……我们的信念。对上帝的信念。对美国的信念。对我们正义之城的信念。因为只有那时……”
雷默惊动,突然警觉,立刻停止了遐想。是他在热浪里突然失去了平衡,还是他脚下的土地真的在颤动?很明显是后者,因为所有聚集在敞开的坟墓前的吊唁者们都摆出了冲浪的典型姿势,两只胳膊保持着平衡。甚至连那长袍牧师,刚刚还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凡事干扰的样子,突然也敏捷地从墓坑边跳开,好像他被告知那口他以为为另一个人敲响的丧钟其实是在召唤他一样。
雷默第一个内疚的想法是,如果是大地震动的话,他就是罪魁祸首。他默默地诅咒了神灵,而上帝偷听到了,表达了他的不悦。他急着想避免引起进一步的不满,正要进行无声、诚心的道歉时,他听到有人说,“地震。”总的来说,相较于神灵的惩罚,雷默更愿意相信是自然灾害,但他怀疑这只震了最多一秒钟的现象能称之为地震吗?与其说是地质结构的移动,不如说是震动了一下,就像附近某个地方的地面被什么东西撞击了。难道是他之前看到的飞机坠毁了吗?难道是他玩弄的那个车库钥匙导致的吗?他把遥控器从口袋里拿出来,困惑地研究着。他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
很快,警察局局长道格拉斯·雷默开始激动起来,难道这不就是他之前一直想讲清楚的警察工作的核心吗?责任、正义、爱、公正、遗产……那些词就和飞机的尾迹云一样缥缈。那穿着丝绸刺绣长袍、华而不实的人光动动嘴皮子,用花哨的辞藻就能假装对这些无所不知。可当大地在你脚下震动,人们转向寻求答案的却是警察。就好像解释这个世界的动荡是警察的工作。只有警察才知道如何拯救。
格斯·莫伊尼汉市长用手肘推推他。“雷默?”他显然对雷默手里的设备感到迷惑,这儿离最近的车库也得有超过一英里远。“这该死的地面刚才抖得像廉价的震动棒一样。你就站这儿啥也不做?”
实际上,这听起来还不错。如果是地震的话,他真想不出来哪里还有比这广袤、平坦的山谷区更好的地方,这方圆百码内没有任何高到可以砸着他们的东西。但至少目前为止,他还是警察局局长,要做点什么才符合常理。要做的事儿,他决定,是打电话给夏莉丝。她那儿总会有答案,或者有足够的建议,如果这些最终都没效果,至少还有同情,尽管即便是同情也经常掺和着讽刺。雷默把对讲机从他腰带的金属扣上取下来,按了通话键,愣了半拍,心想格斯·莫伊尼汉拿着便宜或者贵的震动棒会有怎样的体验,然后开口说,“夏莉丝?你在吗?”
没有回应。
吊唁的人都在七嘴八舌地讲话,这次雷默好像听到有人说,“流星。”是流星击中了警局吗?正好砸死了总机那儿的夏莉丝?
市长开始用他的食指敲雷默的对讲机。“如果你把它打开的话,也许它能更好地工作。”
啊,没错。他在仪式开始的时候把对讲机关了,不想让这该死的玩意儿在布道时朝他嚣叫。他把对讲机打开,夏莉丝的声音立马响起,“头儿?”
“我在。”他说,尽管实际上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在了。他的四肢末端都在发麻,好像那让地面动起来的东西正在从脚趾钻进他的身体,想要通过他的指尖和耳朵再出来。他转身避开刺耳的嘈杂声,好能听得更清楚些。
“你最好马上回城,”她说,“你不会相信发生了啥事。”
“是流星吗?”他试探着问,身体试着动了动,但他的两条腿感觉像树干一样沉重,难以移动。
“什么?”夏莉丝问。
“道格?”市长朝他叫,他扬扬手。难道这人没看到他正在忙吗?
“是流星吗?”他重复道。
“道格!”他的声音听上去很紧急。虽然雷默才移动了几步,但市长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几英里远。
“你还好吗,头儿?”夏莉丝问道。
实际上,雷默的视野好像令人费解地变窄了。前景是他正在讲话的对讲机,在模糊的远处是闪闪发光的挖土机。其他东西都蒙着薄纱。
接着,他又移动了一步,地面突然不见了,就在他意识到地面不见时,它又回来了,伴着他脑子里“砰”的一声巨响。难道他又开枪了,就像那天他对沙利那样?这一次,他好奇,子弹会落在哪儿?
你知道我对给白痴配枪的看法的,弗拉特法官在附近的棺材里窃笑着。
接着,他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