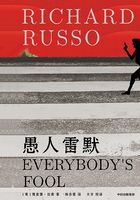
愿望
在那条把山丘区和山谷区分开的路的路肩上,罗布·斯奎尔斯正坐在挖土机的阴影里。这天早上早些时候,他就是用这台机器挖出了老法官的坟墓。如果是他说了算的话,罗布肯定会把机子停在墓边,但他的老板——德拉克洛瓦先生,认为吊唁的人是不会乐意看到它杵在一个新挖的坟墓旁的,更不用说意识到坟墓是由这样一个丑陋的、冷冰冰的家伙挖出来的。当然,他们也会愿意看到一个像罗布·斯奎尔斯这样的人坐在车里,带着一脸不耐烦,就等着死者入穴,好完事回家。所以罗布——碰巧那天真的很不耐烦——只能把挖土机开到一百好几码外,在挖土机投下的阴影里坐着。
“你知道我希—希—希望什么吗?”他大声说。还是个孩子时,罗布就深受结巴之苦。过了青春期,结巴消失了,但现在不知咋的,又回来了。也许是没人在附近听他讲话时,结巴就没那么明显,所以他最近开始自言自语,或者假装跟他的朋友沙利讲话。
什么?你到底希—希—希望什么?他知道,如果沙利真在的话,他肯定会这么问。罗布希望他最好的朋友——哦,好吧,是唯一的朋友——做出的改变并不大,他只是有时希望沙利不要这么爱开他的玩笑,特别是不要拿他的结巴开玩笑。罗布知道开玩笑是沙利跟每个人相处的方式,他并无恶意。但他真的厌倦了被取笑。
“我希—希—希望那家伙别再说下去了。”那个穿着松垂的白长袍的人已经唠叨了很久,至少有半个多小时了,这一点罗布很确定。周五都是干半天的。德拉克洛瓦先生说过的,只要把法官这事弄完,把挖土机停回维修库里,锁上,他就能离开了。“那样大家都能回家,我们也就能完工了。”仿佛这里只有他和沙利两个人,仿佛又回到了过往美好的时光一样,只要一起把土堆推到棺材的上方,就完工了。
沙利的声音又出现在他脑子里。不要空想,空耗生命,傻瓜。
罗布并不介意沙利叫他“傻瓜”,他觉得这是一个爱称。沙利叫绝大多数人傻瓜,而把绝大多数的女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唤作“宝贝”。
“你知道我真的希望的是什么吗?”罗布继续说着他的希望,忽视了沙利的建议。
左手是希望,右手是失望,我倒要看看谁强谁弱。
“我希望你别那么健忘。”罗布说,因为最近沙利有两次都没如期出现,他不确定能否受得了今天再一次被遗忘。
我不会忘的。我已经把梯子放在卡车车斗里了。
他答应过要帮罗布修整一下他和他老婆布茨房子旁的那棵大树。每次一起风,就有根树枝剐蹭她的卧室窗户,这要把她逼疯了。
你这是啥意思,她的窗户?
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时,罗布就厌倦了那婚床。为了逃避那硬邦邦的床,他跟布茨说她睡觉打呼——其实这不是事实——然后住到了楼下那个狭小、布满灰尘、没有暖气的房间。他睡在一张陈旧的军用简易床上,那床又窄又晃,可支撑不了布茨这硕大的身躯。罗布在很多场合都解释过无数次了,但沙利还是就此嘲弄他。不管怎样,丈夫住进了空房间,布茨很快就用俗艳的爱情小说取代了他。所以一有风,她就会觉得这严重干扰了她看小说。对她来说,那根树枝剐蹭玻璃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孩子——那个她一直期望却永远不可能有的孩子——想要努力地爬进来发出的声音。
一个孩子怎么会在她卧室外离地三十英尺的树上?沙利反对道。罗布对此也很困惑,但他知道最好还是别问。要修剪这恼人的树枝其实花不了十五分钟。但这些日子以来,罗布见到沙利的时间没之前多了,所以他希望能拖一整个下午。当然,沙利首先得记得这事。
“你知道我还希望什—什—什么吗?”罗布问。
什么?
“我希望我们能回到以前那样。”这当然是白日梦。罗布也知道空想是没意义的,但他情不自禁。
事情不是这样的,傻瓜。并不是你想回到过去就能回到过去的。如果那样的话,岂不人人都越活越年轻啦。
这话当然没错啦。但不管怎么样,这些年沙利是已经转运了。他不需要再工作。在过去,是工作或者说经济上的需要而非友谊,让他俩这么久以来都密不可分。罗布可以没完没了地希望下去,尽情地渴望下去,可那都不重要。总之,别傻了。你在这儿的这份工作挺好的。干吗想回到过去给卡尔·罗巴克打工呢?
他并没那想法,真的没有。卡尔经常把最冷、最湿、最臭、最危险的活儿留给他和沙利干。而且他是私下付工资的,这样他们就没法投诉了。尽管干的活儿都很糟糕,但罗布热爱那时的每一分每一秒。膝盖在污水里一浸好几个小时,冷得他手指都没了知觉,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沙利就在他身边,指示他该怎么弄,怎么忍受,有时甚至告诉他怎么战胜这些困境。罗布经历的沙利也要经历,这一点真是令人欣慰。就好像他们是在旅行,而他的朋友知道最佳路线一样。如果罗布觉得又冷又饿,又沮丧又迷茫,那也没什么大不了。沙利会告诉他怎么做,会听他唠叨自己的担忧和梦想:如果有一天生活大变样,芝士汉堡免费供应,那该有多美好……
难不成你更喜欢我那倒霉透顶的过去?即使那膝盖肿得像葡萄柚,也不得不工作十二个小时的过去?难道那时候更适合你?
罗布想要沙利改变的另外一点是:他总有本事让罗布责怪自己。比如沙利掉下梯子、摔破膝盖是罗布的错。再比如过去三十年来,沙利投注的赛马三重彩从来没赢过一次,也怪罗布。
“不是,我只是希望……”罗布底气不足,安静了下来。对希望这事——尽管他极不情愿,也开始明白,生活会骗你去期望最糟糕的事,然后再满足你的愿望。沙利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们还在给卡尔·罗巴克打工的时候,沙利总是期望他那霉运能有好转,而罗布从没有怀疑过好友的智慧,也总跟他一起许同样的愿望,同时加入些自己的想法。当沙利真的中了三重彩,反应迟钝的罗布还没感觉到出了问题,他只是想着,很好,他们不用再给卡尔打工了。如果事情就此打住的话,是很不错。
但事情不会就此打住,不是吗?它们还在发展变化呢。所以许愿时要小心。
“是你开始许的愿呀,”罗布认为这告诫对他不公平,“我只不过跟着你许了同样的愿望。”
那效果怎么样呢?
不好,他不得不承认。真让人难以置信,那个三重彩只是个开始。沙利经常抱怨卡尔的运气好到爆,结果这好运气竟然也降落到沙利自己的头上。他好运连连,终于,一个可怕的、难以想象的事实开始显现了:沙利不但不用为卡尔·罗巴克工作,他再也不用工作了。
这还不是罗布唯一没有预见到的事。沙利发达了,而罗布没跟着他一起发达,这也是罗布没有预想到的。他怎么能想到这一点?十多年来,每个周五的下午,都是他和沙利两个人一起围堵卡尔——当卡尔欠你钱时,他有本事凭空消失——去讨他们的工钱。沙利会把罗布那份当场分给他。情况好的话,两人收入都不错;不好的话,都很差。这就好像他俩参加了野餐时玩的“两人三足”游戏一样,虽尴尬笨拙但密不可分,他俩的财政命运紧密相连。沙利的女房东死后,把房子留给了沙利,那时罗布还存有一丝希望,希望他也能有一份,但事实并非如此。之后,沙利父亲的那栋位于鲍登街的房子被征用,市政厅给了他一大笔钱,沙利也没有分他半点儿意外之财。很明显,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伙伴。
嗨,傻瓜。是谁给你找的这份山谷公墓的工作?
罗布耸耸肩,又变乖了。“是你,”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
好吧。那么,表示出点小小的谢意好不好?
罗布叹了口气,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他知道自己更应该感激才对。在墓园的工作远没有给卡尔打工时那么脏、那么累,也更加稳定。但——
你就是不愿意交税。
这指责竟来自沙利(算是吧),这种一生都在打不交税的黑工的人,真是让人无法接受。但他的指控也并非没有道理。罗布的确很憎恶合法用工的约束。为市政厅工作意味着他不仅要付联邦税、州税、地方税,另外还要交社会保险,鬼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税要交。更糟糕的是,政府这么久以来都对他的存在毫不关心,现在突然想知道这些年来他都在哪儿,他应该跟他们怎么说?要支付这么一笔本可以用来买芝士汉堡的钱还没那么糟糕,更糟的是,这种被政府偷了的钱竟然还被冠冕堂皇地记在了他工资单的存根上。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让他假装把自己挣的钱全带回家了呢?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每周提醒他,他们没经他同意就拿走了他多少钱呢?虽然如此,罗布还是觉得得抗议一下沙利的说法。“不是因为税。”他说。
那是因为什么?
“我想念……”
什么?
罗布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什么,傻瓜?
“你—你—你。”罗布困难地吐了出来,如果沙利真的在的话,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你啥意思,想念我?
无法解释,罗布把目光移开。山下,那个穿白长袍的人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到现在,他讲了有多久?罗布看了看手表,感觉情绪愈加低落。当初他和沙利还是伙伴时,他根本不需要戴手表。沙利总是在他身边,告诉他时间,什么时候收工。这份新的工作,除了星期五,其他几天都是下午五点收工,他得知道时间,以便准时把挖土机锁进维修库。他现在管着好几把钥匙,其实他根本不想保管,但沙利已经不在了,不可能把钥匙交给他了。
看到没?
什么?
你过得更好了。现在不用问别人,你也知道时间了。
沙利总是这么说——没有他,罗布过得更好了——好像他在等着罗布哪天能赞同他这观点。罗布才不会赞同呢。“我更喜欢你知道时间的日子。”
嘿,傻瓜,看着我。
但罗布不能。他怎么受得了去看这已判若两人的旧友?他又怎么受得了那人说他过得更好了?而实际上,正因为他的缺席,罗布才变得那么悲惨吧。
好吧,就那样吧。
他还记得新工作开工的第一天很糟糕。他是多么孤单。时间过得多么慢。那天收工时,他锁上了维修库,按沙利教他的方法——
用你自己的钥匙……
然后,他走到墓园的大门口等着沙利来接他,他们就能像往常一样,一起赶往白马酒吧。但四十五分钟后,还是没有沙利的人影,于是,他搭了便车进城去找他。乔可正在锁瑞克苏尔药店的门。“嘿,伙计。”他注意到失魂落魄、一副被遗弃模样的罗布正在路边徘徊,于是打了个招呼,“你咋看起来像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开了个玩笑。而对于罗布来说,这根本就是事实。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他问道。
乔可看了看手表,“六点半了?哦,如果让我猜的话,在这个点,他肯定在老地方。事实上,我敢打赌他坐在哪个凳子上。”
罗布正打算告诉乔可他猜错了,沙利不可能在酒吧,原因很简单,如果他在那,罗布也会在,而罗布不在,所以他也不可能在。毕竟,他们没讨论过沙利不来接他这件事。他以为沙利肯定会来的,要不然他们跟以前一样的夜生活怎么开展?但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错了。又一次错了。其他事上他已经错了,现在这事儿他也错了。他本来的结论是,日子跟以前唯一不同的是,沙利不需要再工作了,但事实更糟糕,要糟糕得多。如果他想要晚上去白马酒吧和沙利在一起的话,他就得自个儿赶到那儿。而当他赶到那儿时,沙利已经坐在了吧台前,他来前淋过浴,身上散发着须后水的香味,就像往常他在周末出现的那样。之前他俩一起出现,看起来、闻起来都像是那些为谋生挣扎的人时,没人会介意。但现在,如果罗布一个人那样出现,他们就会介意了。
站在路边,罗布完全明白了被遗弃的全部含义,这不只是几小时、几天、几个星期不见面,也不只是没有肢体接触。他和沙利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周四十多个小时肩并肩,那时罗布最享受的就是能时时刻刻分享彼此对生活以及如何改善生活的最深刻、最亲密的思考。他能承受得住这份缺席吗?也许吧。但那只在他相信沙利也同样怀念他们的友情的前提下,哪怕沙利的怀念要比他少得多。但如果沙利一点都不想他呢?他刚想到这个可能性,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更阴暗的想法——如果沙利给他介绍这个墓园的工作是为了摆脱他的话,他又该怎么办?
“我正要去那边,要不我顺路带上你。”乔可主动说。但罗布感觉难受极了,他转身走了,否则对方就能看到他喷涌而出的泪水。这是他不想面对的可怕事实:他只剩自己了。
我们每个人都只有自己,傻瓜。绝无例外。
“但……”罗布开口。
而且,你太夸张了。我并没有遗弃你。
是没有完全遗弃,没有。当沙利的运气刚刚好转时,罗布最怕的就是沙利会搬家,搬去一个更好、更温暖,一个罗布无法跟去的地方。但到目前为止,沙利还没有显露出这方面的想法。有时,罗布在周五下午锁门时,沙利会把卡车停在山谷公墓的维修库外,然后,他们就会像往常一样到白马酒吧喝酒。有时,他也会开到他和布茨住的地方,第二天再一起开回城里,在海蒂之家吃个早饭,之后再去赌马场。但这些还不够。罗布需要知道沙利什么时候会来,否则,他会一整天都心神不定地想着他会不会来。只有每分每秒都能见到他才行。
终于,沙利注意到了罗布竟变得那么沮丧萎靡,他试图解释,现在他得多在家里待些时间,不能再浪费那么多时间喝酒了。他想给孙子树立个好榜样。让孩子看到他每天晚上喝到酒吧关门才醉醺醺地回家,或是因为这样那样愚蠢的原因,名字总出现在警察日志上,那样对孩子影响不好。罗布想要相信他。其实,他真的相信了。但从沙利留下的蛛丝马迹来看,他似乎仍然是白马酒吧的常客。有时,罗布会试探性地打电话过去找沙利。但博蒂——酒吧里那个经常值班的服务员,能听得出他的结巴。她经常跟他说沙利不在,自己好多日子没见过他了。但罗布见过她向那些坐在她对面的男人们的妻子说类似的话,因此他很容易就能想象,她向沙利坐的方向抬抬眉,沙利向她摇头,暗示她说不在,就像其他男人一样。
“我只希望你不总是那么急匆匆的。”罗布支吾着说。他痛恨沙利以沉默回答。诚然,沙利说假话和过分的话已经够糟糕了,可沉默更糟糕,因为对于罗布而言,那意味着要么沙利对他失去了兴趣,要么他认为罗布努力解释的事情不值得回应。这些日子以来,沙利似乎总是来去匆匆,着急赶往下一个地方,好像他正被一个他俩都难以名状的东西追赶着。今天下午是不是也是如此?如果可能的话,罗布可不想那样。修剪那恼人的树枝花不了半个小时,但他下定决心要搞上一下午。不用担心布茨,她在工作,沙利的儿子、孙子也不在,他俩可以拉两张草坪椅躺着,罗布可以向他倾诉他积累着的心事,一个想法接着一个想法地说,直到他把所有的话都吐光。但如果他感觉到沙利很匆忙的话,那么所有的话就都会卡在喉咙里。
做沙利的朋友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不得不跟人分享他。不管是在海蒂之家、赛马场,还是白马酒吧,他俩之间的友谊永远是道残忍的算术题——沙利是罗布唯一的朋友,而罗布仅是沙利众多朋友中的一个。除了沙利的儿子和孙子——这两个人罗布都深深憎恶,尽管他知道他不该这样——还有那个卡尔·罗巴克,这个人他就更深恶痛绝了。作为前雇主,他根本没有任何资格获得沙利丝毫的喜爱,但不知怎的,沙利似乎就是喜欢他。还有海蒂之家的露丝,沙利说他们的关系没再继续了。可如果是真的,她为什么还是他的朋友?名单越来越长。白马酒吧的博蒂、乔可,还有其他的常客。还有上主街上的女人们,那些住在破败的维多利亚式的旧房子里的老寡妇们,就指着沙利带她们去美发店,修她们坏了的管道,但从不付钱给他。为什么这些人要插进来分享他的沙利?
这看上去真的就是道算术题,有一段时间,罗布只能指望用减法解决。沙利的女房东死时,罗布觉得自己会是占用他朋友的时间和喜爱的第一继承人,但不知为啥,那并没有发生。一年之后,维尔夫——沙利的律师、他快乐的酒友也去世了,罗布曾重燃起希望,但那次还是破灭了。真的,每次他的朋友圈里有人死了或搬走了,沙利好像也随之减少了似的,从来就没有过新增。今年秋天威尔要去上大学了,彼得说如果那样的话,他也会离开巴斯,照平常的话,罗布肯定会精神大振,但现在他不会了。
你该听你妈的话。
“你从—从—从——”
我从—从—从——?
“你从—从没见过她。”
她告诉过你会发生什么。你只是不相信她。
即使是过了这么多年,罗布还是不愿意想起他的母亲,那个为他尽心尽力的女人。还是个孩子时,他很晚才会说话,到三岁才吐出第一个字。他父亲给他起名叫罗伯特,但他母亲想叫他罗勃,因为她老公叫鲍勃。
但罗布发这个音很是挣扎,事实上,他发很多音都很困难。不久之后,就发现他有严重的语言障碍。要花很久才能吐出R的音,这让他筋疲力尽。而他发出的听上去更像是“布”而不是“勃”,所以他母亲决定就这么叫吧。后来,她看到儿子在学校十分孤单、不合群,因为结巴成为无穷无尽的笑柄,她便向儿子推荐了耶稣。她说耶稣会是最重要的朋友,她并没有预见到沙利的存在。有时,她会把罗布带到那个她礼拜日去做礼拜的那座摇摇欲坠的教堂。在那儿,他们会谈论耶稣和世界末日的狂欢。但有一周有个人带了条蛇过来,罗布受了极大的惊吓,在那之后,他母亲就只能把他留在家里,让他跟他父亲一起了。于是,对于他,耶稣就只是那个日历上的人。
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耶稣——一月耶稣、六月耶稣、十二月耶稣——这些耶稣就如一年四季般恒常可靠,又如时间一样无处不在。但随着岁月流逝,罗布的境况越来越悲惨,日历耶稣却还是一如既往的一副幸福表情。虽然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头上戴着参差的荆棘冠冕,掌心刺穿(每只掌心都分别有一滴鲜红的血),但耶稣仍然平静安详;而罗布,这个忧虑的孩子也希望等长大后面对困顿时能拥有这份洒脱,或是那长期的不甘心或多或少可以转为平静地接受。当然现实并非如此,二十年后,当他有次不小心用钉枪戳中自己的左掌心时,他发现,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子(或者至少是远房堂兄弟)的话,要在那种疼痛中保持平静安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他可怜的母亲,绝大多数时候都神情和善、恍惚,这让罗布一直怀疑她是不是能预知未来,以及是不是因为这个她才一直这么担心他。但也许她沉思的是自己的未来和孤单,而不是他的。尽管他和他父亲都在,罗布还是感到她和自己一样,从头到尾都孤苦伶仃。因为这个,他深感自责。虽然他知道自己只是个孩子,不是成年妇女合适的同伴,但他仍然深感愧疚。除了去教堂,她从不离开房子,而他父亲经常嘲笑她的宗教信仰。你还是去相信你的复活节兔吧,他喜欢这么嘲弄她,罗布这才知道原来世上并没有复活节兔。罗布曾尝试向日历耶稣祷告,因为他爱他母亲,他也知道母亲希望他这么做。她教过他怎么祷告,但显然,他并没做对,因为当他说完祷告词后,他并没有浑身涌动着如母亲所说的救世主的爱,相反,他感到更加空虚、更加孤单了。他的父亲呢?真是罪过,罗布对他爱憎交加,因为他那令人生厌的笑,也因为他从不跟任何人好言好语。但最终,有关耶稣,罗布竟然改变了立场,赞同了他父亲的观点——上帝之子的地位跟那个和他分享了复活假期的兔子没多少不同。
令罗布百思不解的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他父亲去世时他还会这么悲痛?难道是因为这是男孩子失去父亲时应该有的情绪吗?还是因为他母亲,那个本该因为这男人的逝去而有充分理由高兴的女人,却在可怜地啜泣?她怎么会去想念一个像呼吸空气一样肆意贬低她的男人?同样,罗布又怎能去想念这样的父亲?在他最鲜活的记忆里,一个周日的早晨,他母亲离开家去教堂,留下他俩在家。他仿佛仍能看到老头坐在那个别人都不能坐的灯芯绒扶手椅里。当时罗布正在挣扎着跟他说个重要的事(他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了),他盯着他,脸上带着嘲弄好奇的表情。只要父亲在附近,他的结巴就会更严重,话语在他嘴里变成了一片片碎片。他现在回想起来,他之所以要继续挣扎着说下去的部分原因是,当时他已经说出了他要表达的一部分内容,进而误以为他父亲的好奇表情是对他说的话有兴趣。但紧接着他明白了,那表情根本就不是好奇,而是厌恶。“你怎么就不放弃?”这才是他父亲想让他回答的。
“你怎么敢这么对他?”突然传来一声怒吼。罗布和他父亲都没听到他母亲回来的声音。她就那样突然出现在了门口,如此盛怒,以至于她不但听起来而且看起来也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之前他从没有见过母亲跟他父亲抬高过嗓门,但那会儿,她怒目圆睁,浑身发抖,手里拿着一把闪亮的厨刀。那时,他的母亲——那个经常将凉爽干燥的手覆在他手上来安抚他结巴的人,看上去真会杀了这个男人,而平时,她日复一日逆来顺受地忍受着他的口头侮辱,仿佛那是她应得的一样。
“你,”她接着叫道,刀尖指着他父亲,语气坚定,全然不见平时嗓音里的颤抖,“就是因为你,他才变成现在这样子。”
而罗布的父亲,嘴巴大张着,像张开的合页一般,比起尖刀挥舞的恐怖景象带来的恐惧,他更像是因为她的话而目瞪口呆。罗布同样也大受震惊,他拼命地想要弄明白母亲在说什么。他非常清楚,父亲在时,他的结巴会更严重。但这病症怎么能怪到他父亲头上?如果罗布的嘴巴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怎么会是别人的错,错不应该在他自己吗?他母亲不是也一直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吗?还有那位母亲带他去见的大学里的女士——一个言语治疗师,别人是这么称呼她的——不也这么说吗?罗布一直觉得她们这么说只是让他好受些,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错。他不反对宠溺,但这是不同的。他母亲疯了吗?他这愚蠢的口吃怎么会是他父亲的错?
“你这可恨的男人,太可恨了,”罗布惊恐地看着她,她接着喊道,“你唯一的乐趣就是折磨爱你的人。”
他父亲开始想说什么,但没有声音从他嘴里发出,因为他母亲还没结束。现在她把锋利的刀尖对着罗布了。
“那孩子却仰慕着你,你这个可恨的男人。他不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取悦你这回事。他不明白你在享受他正在遭受的折磨。你知道吗?我也不明白。现在你倒说说看。这个孩子,你的儿子,醒着的每一刻都这么恐惧以至于晚上尿床,你怎么还能享受?”
罗布听到这,眼睛盯着地板,羞耻得恨不能钻进地板缝里。他还不知道他父亲知道他尿床的事。他母亲曾跟他说这是他俩之间的秘密,但很明显,她没有遵守承诺。她之前说就是因为你,他才变成现在这样子,她这么说是啥意思现在终于清楚了。她不只是说他结巴这事,而是指所有他不对劲的地方——他整个人都变得令人失望。
此外,他也明白了其他事情。母亲之所以如此愤怒——不但维护他而且还把他的失败归咎于他父亲身上——正是对他父亲的那句“你为什么还不放弃”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回应。一开始,他还以为他父亲是在指点他停顿一下、平静一下、调整一下,然后可以从一个更平和的状态重新开始说。毕竟,他母亲和那个语言治疗师经常鼓励他那么做。然而现在,亏得他母亲的盛怒,才让他明白了他父亲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在经历了种种事情后他还不彻底放弃,为什么还会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失去这样一个男人又有什么可悲伤的?
你来告诉我。
但罗布说不清,正如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年后,他还在浪费这么多时间沉迷于那些愚蠢、不可能的幻想。沙利是对的。你不可能让时光倒流。这意味着他和沙利再也不是最好的朋友了。“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吗?”他问。
但沙利又一次沉默了。
也许,罗布想,这世上就是有你不知为何非得要的东西。也许他对沙利的需要和他母亲对他父亲的需要没什么大的不同。那男人从未厌倦对她的毁谤,但罗布确定她曾需要过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久,她就不再去教堂了。没有征兆,也没有解释,日历耶稣就突然从厨房的墙上消失了。就好像现在房子里只剩他俩了,再也没必要标记岁月的流逝了。到罗布上了中学时,她开始走丢,人们把她送回来时,她看着茫然而迷失。更糟糕的是,她好像不知该拿那个她曾经持着明晃晃的刀子维护的罗布怎么办。沙利最近也经常对他做出同样的表情。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沙利身上吗?他新出现的健忘、坐不住,是不是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兆?沙利,会和罗布的母亲一样,心不在焉,然后开始走丢吗?如果那样的话,谁来把他送回家?如果他忘了,谁来提醒他,他的朋友们是谁?他也会忘记罗布吗?
嘿,傻瓜。
“什么?”
别那样。
是的,罗布开始大哭起来,沙利最恨他这样了。他在错误的时间看向了那些参加葬礼的人们。那个穿长袍的人朝着那明晃晃的棺材大大地挥了一下手。在那一瞬间,太阳光反射在棺材的表面,亮得让人目眩。罗布突然明确了刚刚还在困扰他的事情。她母亲丧失心智时还相对年轻,但沙利老了,他不会走丢的,他会直接死去。最糟糕的是,当那一天到来,将是罗布去挖他最好的朋友的墓穴。
你听到了没?别哭了。
“我控制不住。”罗布号啕大哭。
听我说。
“什么?”
你在听吗?
罗布点点头。
我还哪儿都不会去呢。明白吗?
“你发誓?”
除非你一切就绪,否则我哪儿都不去,好不?这样总行了吧?
罗布点点头。这样很好。正如他母亲之前确信的那样,他很肯定——他永远也不会一切就绪的。
永远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