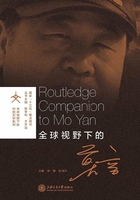
本土性、民族性的世界写作
——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莫言是中国最富活力、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国内数量不算很多的当代作家海外传播研究的文章中,关于莫言的研究相对较多。海外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莫言无疑是一个重镇。本文以莫言的海外传播为研究重心,围绕着莫言作品的海外翻译出版、接受与研究状况展开,希望通过对这一案例的整理与研究,揭示和探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可能问题。
一、作品翻译
一般认为,莫言在国内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1986年《红高粱家族》的出版则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根据对莫言作品翻译的整理,《红高粱》也是他在海外最先翻译并获得声誉的作品。这部作品于1990年推出法语版,1993年同时推出英语、德语版。莫言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并先后获得过法国“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等国外奖项。作品被广泛地翻译出版并且屡获国外文学奖,客观地显示了莫言的海外传播影响以及接受程度。为了更详细准确地了解莫言作品的海外出版状况,笔者综合各类信息来源,对莫言海外出版进行列表综述(见表1)。
表1 莫言作品翻译统计列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列表显然并不全面,仅以德语作品为例,除表中《酒国》外(2005年再版),莫言的德译作品还有《红高粱家族》(Das rote Kornfeld,Peter Weber-Schäfer译,Rowohlt,1993、1995,Unionsverlag,2007)、《天堂蒜薹之歌》(Die Knoblauchrevolte,Andreas Donath译,Rowohlt,1997、1998、2009)、《生死疲劳》(Der Überdruss,Martina Hasse译,Horlemann,2009)、《檀香刑》(Die Sandelholzstrafe,Karin Betz译,Insel Verlag,2009)和中短篇小说集《枯河》(Trockener Fluβ,Bochum,1997),以及短篇小说合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包括莫言、阿来、叶兆言、李冯,Chinabooks,2009)。莫言的意大利语作品除了表中收录外,经查还包括:《红高粱》(Sorgo rosso,Einaudi,2005)、《丰乳肥臀》(Grande seno,fianchi larghi,Einaudi,2002、2006)、《檀香刑》(Ⅱsupplizio del legno di sandalo, Einaudi,2005、2007)、《生死疲劳》(Le sei reincarnazioni di Ximen Nao,Einaudi,2009)。莫言的越南语作品数量很多,但早期代表作品《透明的红萝卜》(cǔ cài  trong suô t)、《红高粱家族》(Cao luong
trong suô t)、《红高粱家族》(Cao luong  ,译者黎辉肖(Lê Huy Tiêu),劳动出版社(Nhà xuât bào Lao
,译者黎辉肖(Lê Huy Tiêu),劳动出版社(Nhà xuât bào Lao  ),2006)已有越语翻译。除了个人作品外,莫言也有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一起翻译的作品集,这里不再列出。
),2006)已有越语翻译。除了个人作品外,莫言也有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一起翻译的作品集,这里不再列出。
可以看出,莫言作品翻译较多的语种有法语、英语、德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其作品海外传播地域的分布和余华及苏童具有相似性:即呈现出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受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亚洲国家为中心的特点。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关联程度是制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最基本的两个要素。从莫言的主要传播地域来看,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方接受和以日韩越为代表的东方接受会有哪些异同?这里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究竟有哪些主要的因素在制约着文化的交流方向和影响程度?我们知道文化和政治、经济并不总是平衡发展的事实,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并且可以与之抗衡的独立文化体系,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洲文化圈。当它的国力发生变化时,它会对文化传播的方向、规模、速度产生哪些影响?这些都值得以后更深入地探讨。
中国当代文学的西译往往是由法语、德语或英语开始,并且相互之间有着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其中一个语种获得了成功,其他西方语种就会很快跟进,有些作品甚至并不是从中文译过去,而是在这些外文版之间相互翻译。就笔者查阅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而言,一般来说法语作品出现得最早。莫言的西方语种翻译也符合这个特点,如《红高粱家族》法语版最早于1990年推出,1993年又推出《透明的红萝卜》;德语和英语版《红高粱》则都于1993年推出并多次再版,反映了这部作品的受欢迎程度。相对于西方语种,东方国家如越南和韩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高潮一般出现在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越南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非常出乎笔者的意料。许多当代作家翻译最多的语种往往是法语或越南语,并不是想象中的英语。如本表中显示莫言翻译作品最多的是法语,其作品在法国的影响力也很大。莫言在一次访谈中曾表示:除了《丰乳肥臀》《藏宝图》《爆炸》《铁孩》四本新译介的作品,过去的《十三步》《酒国》《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又都出版了简装本,书展上同时有八九本书在卖 。另外,《丰乳肥臀》在法国出版以后,确实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正面的评价比较多。莫言在法国期间,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人道报》《新观察家》《视点》等重要的报刊都对他做了采访或者评论,使得他在书展期间看起来比较引人注目。
。另外,《丰乳肥臀》在法国出版以后,确实在读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正面的评价比较多。莫言在法国期间,法国《世界报》《费加罗报》《人道报》《新观察家》《视点》等重要的报刊都对他做了采访或者评论,使得他在书展期间看起来比较引人注目。
从以上统计来看,日本不但是亚洲,也是世界上最早译介莫言作品的国家。如1989年就有井口晃翻译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莫言》,并很快再版;之后有1991年藤井省三、长堀祐造翻译的《莫言短篇小说集》。日本汉学家谷川毅表示:“莫言几乎可以说是在日本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百姓,莫言都是他们最熟悉的中国作家之一。”据谷川毅讲,是电影把莫言带进了日本,“根据莫言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日本很受欢迎,他的小说也随之开始引起注意,所以,他进入日本比较早” 。莫言的韩语译作除一部外,其余的都集中在了新世纪,而越语作品在2004年以来竟然出版多达十本以上,其出版速度和规模都是惊人的。有越南学者指出:“在一些书店,中国文学书籍甚至长期在畅销书排行榜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莫言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在中国作家中是较早被翻译成越南语的,并很受越南读者的欢迎,在越南国内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被称作越南的‘莫言效应’”。“根据越南文化部出版局的资料显示,越文版的《丰乳肥臀》是2001年最走红的书,仅仅是位于河内市阮太学路一百七十五号的前锋书店一天就能卖三百多本,营业额达0.25亿越南盾,创造了越南近几年来图书印数的最高纪录。”
。莫言的韩语译作除一部外,其余的都集中在了新世纪,而越语作品在2004年以来竟然出版多达十本以上,其出版速度和规模都是惊人的。有越南学者指出:“在一些书店,中国文学书籍甚至长期在畅销书排行榜占据重要位置。而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莫言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在中国作家中是较早被翻译成越南语的,并很受越南读者的欢迎,在越南国内引起过很大的反响,被称作越南的‘莫言效应’”。“根据越南文化部出版局的资料显示,越文版的《丰乳肥臀》是2001年最走红的书,仅仅是位于河内市阮太学路一百七十五号的前锋书店一天就能卖三百多本,营业额达0.25亿越南盾,创造了越南近几年来图书印数的最高纪录。” 越南著名诗人、批评家陈登科的评论:“我特别喜欢莫言的作品,尤其是《丰乳肥臀》与《檀香刑》两部小说。莫言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对于莫言及其他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在越南走红的原因,笔者很赞同陶文琉的分析。首先,莫言作品具有高贵的艺术品质。通过《丰乳肥臀》与越南当代小说的比较,他指出中越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倾向,突出地体现在思想与审美趋向,以及文学艺术的建构与发展方面。其次,莫言作品能够在越南风行还跟中越两国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越不但历史上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相近的文化情趣与历史情结,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都进入了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多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莫言作品在越南能够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越南著名诗人、批评家陈登科的评论:“我特别喜欢莫言的作品,尤其是《丰乳肥臀》与《檀香刑》两部小说。莫言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对于莫言及其他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作品在越南走红的原因,笔者很赞同陶文琉的分析。首先,莫言作品具有高贵的艺术品质。通过《丰乳肥臀》与越南当代小说的比较,他指出中越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存在着某种相同的倾向,突出地体现在思想与审美趋向,以及文学艺术的建构与发展方面。其次,莫言作品能够在越南风行还跟中越两国共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越不但历史上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相近的文化情趣与历史情结,20世纪80年代后两国都进入了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社会多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莫言作品在越南能够产生广泛影响,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二、莫言的海外研究
以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规模和影响力,很自然地,莫言研究会成为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之一。笔者在查阅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基本规律: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翻译语种多、作品数量多、再版次数多,必然会产生研究成果多的效应,这些作家往往也是在国内被经典化的作家。在英、法、德、日几个语种间,都有大量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限于语言能力,笔者这里只对部分有代表性的英语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
和中国一样,海外学术期刊是研究莫言最重要的阵地之一,海外涉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学术期刊几乎都有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如《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曾专门出版过莫言评论专辑,发表了包括Chan,Shelley W《从父性到母性:莫言的<红高粱>与<丰乳肥臀>》(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 On Mo Yan's “Red Sorghum” and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禁食》(Forbidden Food: “The Saturnicon” of Mo Yan);托马斯·英奇(Inge,Thomas M)《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王德威《莫言的文学世界》(The Literary World of Mo Yan)四篇文章 。另一个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前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也先后发表过周英雄(Chou,Ying-hsiung)《红高粱家族的浪漫》(Romance of the Red Sorghum Family);危令敦(Ngai Lingtun)《肛门无政府:读莫言的<红蝗>》(Anal Anarchy: A Reading of Mo Yan's “The Plagues of Red Locusts”);陈建国《幻象逻辑:中国当代文学想象中的幽灵》(The Logic of the Phantasm: 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Imagination,该文同时分析莫言、陈村、余华的作品);Stuckey,G. Andrew《回忆或幻想?红高粱的叙述者》(Memory or Fantasy? Honggaoliang's Narrator)
。另一个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期刊《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前名为《中国现代文学》)也先后发表过周英雄(Chou,Ying-hsiung)《红高粱家族的浪漫》(Romance of the Red Sorghum Family);危令敦(Ngai Lingtun)《肛门无政府:读莫言的<红蝗>》(Anal Anarchy: A Reading of Mo Yan's “The Plagues of Red Locusts”);陈建国《幻象逻辑:中国当代文学想象中的幽灵》(The Logic of the Phantasm: Haunting and Spect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Imagination,该文同时分析莫言、陈村、余华的作品);Stuckey,G. Andrew《回忆或幻想?红高粱的叙述者》(Memory or Fantasy? Honggaoliang's Narrator) 。其他期刊上研究莫言的文章还有刘毅然(Liu,Yiran)《我所知道的作家莫言》;蔡荣(Cai,Rong)《外来者的问题化: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父亲、母亲与私生子》;Guptak,Suman《李锐、莫言、阎连科和林白:中国当代四作家访谈》;Inge,Thomas M《莫言与福克纳:影响与融合》;孔海立(Kong,Haili)《端木蕻良与莫言虚构世界中的“母语土壤”精神》;Ng,Kenny K. K.《批判现实主义和农民思想:莫言的大蒜之歌》和《超小说,同类相残与政治寓言:莫言的酒国》;杨小滨《酒国:盛大的衰落》等
。其他期刊上研究莫言的文章还有刘毅然(Liu,Yiran)《我所知道的作家莫言》;蔡荣(Cai,Rong)《外来者的问题化:莫言<丰乳肥臀>中的父亲、母亲与私生子》;Guptak,Suman《李锐、莫言、阎连科和林白:中国当代四作家访谈》;Inge,Thomas M《莫言与福克纳:影响与融合》;孔海立(Kong,Haili)《端木蕻良与莫言虚构世界中的“母语土壤”精神》;Ng,Kenny K. K.《批判现实主义和农民思想:莫言的大蒜之歌》和《超小说,同类相残与政治寓言:莫言的酒国》;杨小滨《酒国:盛大的衰落》等 。
。
除了学术期刊外,在各类研究论文集中也有不少文章涉及莫言。如著名的《哥伦比亚东亚文学史》中国文学部分有伯佑铭(Braester,Yomi)《莫言与<红高粱>》(Mo Yan and “Red Sorghum”) 。其他还有Feuerwerker和梅仪慈(Yi-tsi Mei)合作的《韩少功、莫言、王安忆的“后现代寻根”》(The Post-Modern “Search for Roots” in Han Shaogong, Mo Yan, and Wang Anyi)
。其他还有Feuerwerker和梅仪慈(Yi-tsi Mei)合作的《韩少功、莫言、王安忆的“后现代寻根”》(The Post-Modern “Search for Roots” in Han Shaogong, Mo Yan, and Wang Anyi) ;杜迈克(Michael Duke)《莫言1980年代小说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
;杜迈克(Michael Duke)《莫言1980年代小说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 ;吕彤邻(Lu Tonglin)《红蝗:逾越限制》(Red Sorghum: Limits of Transgression)
;吕彤邻(Lu Tonglin)《红蝗:逾越限制》(Red Sorghum: Limits of Transgression) ;王德威(Wang David Derwei)《想象的怀乡:沈从文,宋泽莱,莫言和李永平》(Imaginary Nostalgia: Shen Congwen, Song Zelai, Mo Yan, and Li Yongping)
;王德威(Wang David Derwei)《想象的怀乡:沈从文,宋泽莱,莫言和李永平》(Imaginary Nostalgia: Shen Congwen, Song Zelai, Mo Yan, and Li Yongping) ;岳刚(Yue,Gang)《从同类相残到食肉主义:莫言的<酒国>》(From Cannibalism to Carnivorism: Mo Yan's Liquorland)
;岳刚(Yue,Gang)《从同类相残到食肉主义:莫言的<酒国>》(From Cannibalism to Carnivorism: Mo Yan's Liquorland) ;钟雪萍(Zhong Xueping)《杂种高粱和寻找男性阳刚气概》(Zazhong gaoliang and the Male Search for Masculinity)
;钟雪萍(Zhong Xueping)《杂种高粱和寻找男性阳刚气概》(Zazhong gaoliang and the Male Search for Masculinity) ;朱玲(Zhu Ling)《一个勇敢的世界?红高粱家族中的“男子气概”和“女性化”的构建》(A Brave New Worl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 Red Sorghum Family)等
;朱玲(Zhu Ling)《一个勇敢的世界?红高粱家族中的“男子气概”和“女性化”的构建》(A Brave New Worl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in The Red Sorghum Family)等 。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一般来说,很少有单独研究某一当代作家的文章,多数是选择某一主题和几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04年博士毕业的方津才(Fang Jincai),其论文题目为《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小说中父系社会的衰落危机与修补》
。海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论文,一般来说,很少有单独研究某一当代作家的文章,多数是选择某一主题和几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如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2004年博士毕业的方津才(Fang Jincai),其论文题目为《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小说中父系社会的衰落危机与修补》 。当然,除了英语外,法语、德语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如执教于巴黎七大的法国诗人、翻译家、汉学家尚德兰(Chen-Andro,Chantal)女士,主要负责20世纪中国文学和翻译课程,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法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也对莫言的小说颇有研究兴趣,曾撰写有《莫言“红高粱”》(Le Sorgho rouge de Mo Yan)一文
。当然,除了英语外,法语、德语也有许多研究成果,如执教于巴黎七大的法国诗人、翻译家、汉学家尚德兰(Chen-Andro,Chantal)女士,主要负责20世纪中国文学和翻译课程,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法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也对莫言的小说颇有研究兴趣,曾撰写有《莫言“红高粱”》(Le Sorgho rouge de Mo Yan)一文 。
。
莫言的英译作品目前有《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师傅越来越幽默》和《爆炸》,译者主要是被称为现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对莫言文学作品的研究发表在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前身是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 Today, Moder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Positions等著名期刊上。当然,在各类报纸媒介上也有许多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评论。海外对莫言的研究角度各异,从题目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作品研究,如对《红高粱》《酒国》等的分析,这类研究数量最多,往往是从作品中提炼出一个主题进行;比较研究,如Guptak,Suman对莫言和李锐、孔海立对莫言和端木蕻良、王德威《想象的怀乡》以及方津才的文章等。还有一类可以大致归为综合或整体研究,如王德威《莫言的文学世界》,刘毅然、杜迈克等人的文章。作品研究里,目前以对《红高粱》《丰乳肥臀》《酒国》的评论最多。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王德威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一文中认为 :莫言的作品多数喜欢讨论三个领域里的问题,一是关于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二是关于叙述、时间、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重新定义政治和性的主体性。文章以莫言的五部长篇小说和其著名的中篇为基础展开了论证,认为莫言完成了三个方向的转变,它们分别是:从天堂到茅房,从官方历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莫言塑造的人物没有一个符合毛式话语那种光荣正确的“红色”人物形象,这些有着俗人欲望、俗人情感的普通人正是对于毛式教条的挑战。在谈到《红高粱》时他说:“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文章最后指出,之所以总是提及“历史”这一词汇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推动莫言小说世界的基本力量,也客观上证明了他一直试图通过小说和想象来替代的努力。莫言不遗余力地混杂着他的叙述风格和形式,这也正是他参与构建历史对话最有力的武器。
:莫言的作品多数喜欢讨论三个领域里的问题,一是关于历史想象空间的可能性;二是关于叙述、时间、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是重新定义政治和性的主体性。文章以莫言的五部长篇小说和其著名的中篇为基础展开了论证,认为莫言完成了三个方向的转变,它们分别是:从天堂到茅房,从官方历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莫言塑造的人物没有一个符合毛式话语那种光荣正确的“红色”人物形象,这些有着俗人欲望、俗人情感的普通人正是对于毛式教条的挑战。在谈到《红高粱》时他说:“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文章最后指出,之所以总是提及“历史”这一词汇是因为他相信这是推动莫言小说世界的基本力量,也客观上证明了他一直试图通过小说和想象来替代的努力。莫言不遗余力地混杂着他的叙述风格和形式,这也正是他参与构建历史对话最有力的武器。
时任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学院英文系教授的托马斯·英奇(Thomas M. Inge)对莫言作品大为赞赏,他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一文开篇即讲:“莫言有望作为一个世界级的作家迈入二十一世纪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舞台。”文章着重分析《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和《酒国》三部作品。如认为《红高粱》营造了一个神奇的故乡,整部小说具有史诗品质,其中创新性的叙事方式颠覆了官方的历史真实性,对日本侵略者也非简单地妖魔化处理,在创作中浸透着作者的观点,塑造了丰满、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等,这些都是这部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认为莫言已经创作出了一批独特有趣、既对中国当代文学有益又保持其自身美学原则的作品,莫言正以其创作积极地投身于将中国文学带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他说不止一个批评家同意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杜迈克(Michael Duke)教授的意见:即莫言“正越来越显示出他作为一个真正伟大作家的潜力”。杜迈克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欣赏,他认为:这部作品把技巧性和主题性的因素融为一体,创作了一部风格独特、感人至深、思想深刻的成熟艺术作品。这是莫言最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它支持改革,但是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因素。它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中,形象再现农民生活的复杂性,最具想象力和艺术造诣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莫言或许比任何一位写农村题材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更加系统深入地进入中国农民的内心,引导我们感受农民的感情,理解他们的生活 。
。
时任科罗拉多大学教授的葛浩文在《禁食》一文里,从东西方文学中人吃人现象谈到莫言对于吃人肉这个问题的处理。文章首先分析两种“人吃人”类型,一种是“生存吃人”,他举了美国1972年Andean失事飞机依靠吃死难者尸体生存下来的例子;另一种是“文化吃人”(learned cannibalism),这种“吃人”通常有文化或其他方面公开的理由,如爱、恨、忠诚、孝、利益、信仰、战争等。作者认为吃人尽管经常和“野蛮”文化联系在一起,却也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寓言、警醒、敏感、讽刺等效果常被作家描写。具体到《酒国》,他指出《酒国》是一部有多重意义的小说,它直面许多中国人的国民性,如贪吃、好酒、讳性等特征,探讨了各种古怪的人际关系,戳穿了靠一个好政府来治理文明国家的神话。他认为既然《酒国》中的吃人肉不是出于仇恨,不是出于饥荒导致的匮乏,而是纯粹寻求口腹之乐,那么作者这样写显然是一种寓言化表达:如中国由来已久对农民的剥夺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对人民的压迫,以及作家对于整个社会是否还有人性存在提出的强烈质疑。科罗拉多大学的W. Shelley Chan博士《从父性到母性》一文则对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进行了分析。认为《红高粱》中表现出对历史的不同书写,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肯定了莫言对毛式革命话语的颠覆和解构。她认为《丰乳肥臀》中父亲形象的缺失可以被看作是对毛式话语模式的挑战,因此这部作品可以视作对共产主义父权意识形态的一种叛离。不仅如此,作品中的性描写充满了对过去意识形态的反叛意味,作者通过这些手法在质疑历史的同时也审视了中国当下的国民性和文化。
对于《丰乳肥臀》,《华盛顿邮报》专职书评家乔纳森·亚德利(Jonathan Yardley)评价此书处理历史的手法,让人联想起不少盛名之作,如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们》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过它远未达到这些作品的高度。“此书的雄心值得赞美,其人道情怀亦不言而喻,却唯独少有文学的优雅与辉光。”亚德利盛赞莫言在处理重大戏剧场面,如战争、暴力和大自然的剧变时的高超技巧。“尽管二战在他出生前十年便已结束,但这部小说却把日本人对中国百姓和抗日游击队的残暴场面描绘得无比生动。”给亚德利印象最深的,是莫言在小说中呈现的“强烈的女权主义立场”,他对此感到很难理解。亚德利说,尽管葛浩文盛名在外,但他在翻译此书时,或许在信达雅之间搞了些平衡,其结果便是莫言的小说虽然易读,但行文平庸,结构松散。书中众多人物虽然有趣,但西方读者却因为不熟悉中文姓名的拼写而很难加以区别。提到《丰乳肥臀》的缺点,亚德利写道:“那多半是出于其远大雄心,超出了素材所能负担的限度,这没什么不对” 。他还认为此书也许是莫言的成功良机,或可令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他还认为此书也许是莫言的成功良机,或可令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
以上我们主要列举了海外专家对莫言作品的一些评论意见,海外普通读者对《生死疲劳》也有大量的阅读评论。其中,在英文版卓越网上我看到了八九个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意见,基本上都是正面、肯定的意见,但是理由各有不同。如一位叫wbjonesjr1的网友评论道:“《生死疲劳》是了解二战后中国社会内景的一种简捷方式。”他强调了这部小说的情节控制的速度、戏剧性和其中的幽默意味,尤其佩服、惊叹于莫言对小说长度的巧妙化解,每个轮回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这样读者就不会掉入漫长的阅读过程中了。网友Bradley Thomas JohnQPublic认为这部书对于西方人来说,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其他人的生活,同时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道德并不一定适用到其他国家区域。也有一些读者似乎对“长度”感到很困难,至少两位网友提到虽然这本书故事精彩,内容丰富,但却仍然让他们感到有点“疲劳”。一位叫Blind Willie的网友说:“我推荐这本书,但有时《生死疲劳》也确实让我感到很疲劳。”在其他的一些评论中,有些评论者则指出了《生死疲劳》中的民俗、人物性格刻画、叙述方面的高超技巧,当然也有人指出这部作品的不足之处,如认为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写得太松等。
三、莫言海外传播的原因分析
在讨论莫言作品海外传播原因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思考另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不断得到传播的原因有哪些?这显然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想指出:中国当代作家个人的海外传播除了他本人的艺术素质外,往往离不开这种更大的格局,并且有时候这种大格局甚至会从根本上影响作家个人的海外传播状况。比如当前世界似乎正在泛起的“中国热”的带动效应,再如当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时,作家作品的选择就会受到过滤和筛选;以及大型的国家、国际文化活动也会加速或扩大作品的译介速度和范围,更不用说国家整体实力的变化、国家间经济、文化关系方面出现重大变化带来的种种影响了。就整体而言,这些基础性的影响因素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的关系,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对抗,政府或民间交流的需要等。笔者曾就此问题做过一项海外学者的调查问卷,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伯佑铭(Yomi Braester)教授的观点正好印证了我的判断。他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政府文化活动、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和时代的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因素。在与王德威教授访谈时,他也明确承认文学永远是政治(politic)的,认为中国的强大确实与作家的海外传播有着微妙的关系。当然,在这一总体格局中,作家的海外传播又会形成自己的传播特点。
关于莫言海外传播的原因,一些学者也曾做出过自己的探讨。如张清华教授在德国讲学期间,曾问过包括德国人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他们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是谁?回答最多的是余华和莫言。问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位?回答是,因为余华与他们西方人的经验“最接近”,而莫言的小说则最富有“中国文化的色彩”。因此张清华认为:“很显然,无论在任何时代,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的获得,是靠了两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 张清华教授总结出来的这两个基本途径,其实也从文学本身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基本原因:即中国当代文学兼具世界文学的共通品质和本土文学的独特气质。共通的部分让西方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独异的本土气质又散发出迷人的异域特色,吸引着他们的阅读兴趣。而莫言显然在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地域性很强的本土经验能否被有效地翻译并且被海外读者感受和欣赏到?这就涉及莫言海外传播比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好的翻译。
张清华教授总结出来的这两个基本途径,其实也从文学本身揭示了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基本原因:即中国当代文学兼具世界文学的共通品质和本土文学的独特气质。共通的部分让西方读者容易感受和接受,独异的本土气质又散发出迷人的异域特色,吸引着他们的阅读兴趣。而莫言显然在本土经验和民族文化方面有着更为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值得怀疑的是:这种地域性很强的本土经验能否被有效地翻译并且被海外读者感受和欣赏到?这就涉及莫言海外传播比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好的翻译。
中国很多当代作家的写作中都充满了地域特色,如莫言和贾平凹就是两位地域色彩浓重的作家。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语言和贾平凹有着特殊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方言,都会给翻译带来极大的困难。贾平凹对此深有感触:他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翻不出来”。“比如我写的《秦腔》,翻出来就没有味道了,因为它没有故事,净是语言。”他还认为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一批专业、优秀的海外版权经纪人,“比如我的《高兴》,来过四五个谈海外版权的人,有的要卖给英国,有的要卖给美国,后来都见不到了。我以前所有在国外出版的十几种译本,也都是别人断续零碎找上门来和我谈的,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他们”。最后他认为要培养一批中国自己的在职翻译家 。翻译人才的缺乏确实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障碍。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远未做到系统的译介,苦于合适的翻译人才太少,使得许多译介处于初级和凌乱的阶段。顾彬教授曾与笔者在一个访谈中提到过翻译问题,他讲到自己为什么更多地翻译中国当代诗歌而不是小说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诗人。他的潜话题是:诗歌的语言要求更高,他培养的学生可以很好地翻译小说,但未必能翻译诗歌。所以,优秀的翻译人才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涉及深刻的文化理解甚至切身的创作体验等。我们可以培养大量懂外语的人,但让这些人既能对本国的语言文化有着精深的掌握,又能对他国的语言和文化达到对等的程度,并且具备文学创作经验,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任务。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他总喜欢举现代名家如鲁迅、老舍、郁达夫等为证,许多著名国外作家往往也能同时用外语创作。不得不承认,从理论上讲兼具作家、学者、翻译家三重身份的人应该是最合适的翻译人才。莫言也许是幸运的,他的许多译者正好符合这一特点。如英语译者是号称为中国现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日语译者包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
。翻译人才的缺乏确实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障碍。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远未做到系统的译介,苦于合适的翻译人才太少,使得许多译介处于初级和凌乱的阶段。顾彬教授曾与笔者在一个访谈中提到过翻译问题,他讲到自己为什么更多地翻译中国当代诗歌而不是小说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自己也是诗人。他的潜话题是:诗歌的语言要求更高,他培养的学生可以很好地翻译小说,但未必能翻译诗歌。所以,优秀的翻译人才并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涉及深刻的文化理解甚至切身的创作体验等。我们可以培养大量懂外语的人,但让这些人既能对本国的语言文化有着精深的掌握,又能对他国的语言和文化达到对等的程度,并且具备文学创作经验,这的确不是一个简单任务。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外语,他总喜欢举现代名家如鲁迅、老舍、郁达夫等为证,许多著名国外作家往往也能同时用外语创作。不得不承认,从理论上讲兼具作家、学者、翻译家三重身份的人应该是最合适的翻译人才。莫言也许是幸运的,他的许多译者正好符合这一特点。如英语译者是号称为中国现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日语译者包括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等。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莫言在海外传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张艺谋电影的海外影响。这一点不但在日本如此,也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电影巨大的市场往往会起到极好的广告宣传效应,迅速推动海外对文学作品原著的翻译出版。莫言本人也承认:“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充满了互生互助的味道,这一方面说明优秀的文学脚本是电影成功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的电影运作会产生一种连锁效应,可以带动起一系列相关文化产业,其中的规律与利弊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知道,1988年《红高粱》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随后1989年再获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青年评委最佳影片奖。电影的成功改编和巨大影响迅速地推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止于莫言。张艺谋可以说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间接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他先后改编了莫言的《红高粱》(The Red Sorghum)、苏童的《妻妾成群》(Raise the Red Lanterns,译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活着》(To Live),这些电影在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的同时带动或扩大了海外对这些作家小说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海外传播同时也显示:电影对文学起到了聚光灯的效应,它提供了海外读者关注作家作品的机会,但能否得到持续的关注,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比如莫言就曾提到过,他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却要比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
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充满了互生互助的味道,这一方面说明优秀的文学脚本是电影成功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说明,成功的电影运作会产生一种连锁效应,可以带动起一系列相关文化产业,其中的规律与利弊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知道,1988年《红高粱》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随后1989年再获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青年评委最佳影片奖。电影的成功改编和巨大影响迅速地推动了文学作品的翻译,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止于莫言。张艺谋可以说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间接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他先后改编了莫言的《红高粱》(The Red Sorghum)、苏童的《妻妾成群》(Raise the Red Lanterns,译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的《活着》(To Live),这些电影在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的同时带动或扩大了海外对这些作家小说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莫言、苏童、余华等人的海外传播同时也显示:电影对文学起到了聚光灯的效应,它提供了海外读者关注作家作品的机会,但能否得到持续的关注,还得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比如莫言就曾提到过,他的作品《丰乳肥臀》《酒国》并没有被改编成电影,却要比被改编成电影的《红高粱》反响好很多。
当然,影响莫言海外传播的因素还有很多,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作家表现出来的艺术创新精神、作品中丰富的内容等因素外,国外对中国文学接受环境的变化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曾谈到海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和接受大体经历了一个由社会学材料向文学本身回归的趋势,这种变化使得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得以更多地彰显,这种基于文学性的接受与传播方式,对于像莫言这样的作家来说,更容易被人注意到他的创作才华。笔者有幸参加了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作家的一些讲演、谈话活动。不论是在法兰克福大学歌德学院会场,还是法兰克福文学馆的“中国文学之夜”,留下的直观的印象有以下几点:参加的听众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或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外国读者数量也会因为作家知名度的大小而产生明显变化,比如莫言、余华、苏童的讲演,会场往往爆满,而另一些作家、学者则并非那么火爆。提问的环节往往是文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混杂在一起,比如有国外记者问铁凝的方式很有策略性。他首先问一个文学性问题,紧接着拿出一个中国异议作家的照片,问铁凝作为同行,对那位异议作家被关入狱有何评论等。在“中国文学之夜”会场上,作家莫言、刘震云、李洱等以各种形式和海外同行、读者展开对话,对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在国外传播、接受的变化提出了个人观感。如莫言在和德国作家的对话中讲道 :20世纪80年代国外读者阅读中国小说,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从纯文学艺术角度欣赏的比较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德国的一些读者和作家同行开始抛开政治经济的视角,从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角度来品味作品。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就曾在读完《红高粱家族》之后评价说,这部作品与重视思辨的德国文学迥然不同,它更多的是在展示个人精神世界,展示一种广阔的、立体化的生活画面,以及人类本性的心理、生理感受等。莫言得到这些反馈信息时感到很欣慰。他说:这首先说明作品的翻译比较成功,其次国外的读者、同行能够抛开政治的色彩甚至偏见,用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的观点来品读、研究作品是件很让人开心的事。他希望国外读者能以文学本位的阅读来体会中国小说。
:20世纪80年代国外读者阅读中国小说,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情况,从纯文学艺术角度欣赏的比较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德国的一些读者和作家同行开始抛开政治经济的视角,从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角度来品味作品。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就曾在读完《红高粱家族》之后评价说,这部作品与重视思辨的德国文学迥然不同,它更多的是在展示个人精神世界,展示一种广阔的、立体化的生活画面,以及人类本性的心理、生理感受等。莫言得到这些反馈信息时感到很欣慰。他说:这首先说明作品的翻译比较成功,其次国外的读者、同行能够抛开政治的色彩甚至偏见,用文学艺术以及人文的观点来品读、研究作品是件很让人开心的事。他希望国外读者能以文学本位的阅读来体会中国小说。
必须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只是普遍性地分析了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的原因,但不同国家对同一作家作品的接受程度是有区别的,其中也包含了某些独特的原因。如莫言作品在法国、日本、越南,在接受程度、作品选择方面也会有差别。莫言在谈到自己作品在法国较受欢迎的原因时说:“法国是文化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西方的艺术之都,他们注重艺术上的创新。而创新也是我个人的艺术追求,总的来说我的每部小说都不是特别注重讲故事,而是希望能够在艺术形式上有新的探索。我被翻译过去的小说《天堂蒜薹之歌》是现实主义写法,而《十三步》是在形式探索上走得很远。这种不断变化可能符合了法国读者求新求变的艺术趣味,也使得不同的作品能够打动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读者,获得相对广阔的读者群。” 总的来说,在艺术形式上有探索,同时有深刻社会批判内涵的小说比较受欢迎,如《酒国》和《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描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家庭的纷争和变化,《酒国》则是一部寓言化的、象征化的小说,当然也有社会性的内容。小说艺术上的原创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独立的文学经验并不代表无法和世界文学很好地融合,笔者虽然并非莫言研究的专家,但也能感受到他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以莫言和贾平凹、苏童、格非、余华、王安忆为例,我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劳》《秦腔》《高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兄弟》《启蒙时代》时,感受各有不同。莫言、贾平凹之于苏童、格非,一个倾向于民间、乡土,有着粗粝、热闹、生气勃勃的语言特性,小说散发出强烈的北方世俗味道;另一个则精致、细腻、心平气和地叙述,充满了南方文人的气息。阅读《人面桃花》《碧奴》清静如林中饮茶,而阅读《生死疲劳》《秦腔》则热闹若台前观戏。莫言、贾平凹作品的画面感强,色彩浓重,声音响亮,气味熏人,与余华的简洁、明快、幽默,王安忆的优雅、华贵、绵长的叙述风格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莫言和贾平凹,虽然在文风上有相似性,但陕地和鲁地不同的风俗、语言特征也很明显地区分开了他们的作品。莫言显得比贾平凹更大开大合,汪洋恣肆,有一种百无禁忌、舍我其谁的叙述气概,鲁人的尚武、豪迈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总的来说,在艺术形式上有探索,同时有深刻社会批判内涵的小说比较受欢迎,如《酒国》和《丰乳肥臀》。《丰乳肥臀》描写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家庭的纷争和变化,《酒国》则是一部寓言化的、象征化的小说,当然也有社会性的内容。小说艺术上的原创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是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独立的文学经验并不代表无法和世界文学很好地融合,笔者虽然并非莫言研究的专家,但也能感受到他和其他中国当代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以莫言和贾平凹、苏童、格非、余华、王安忆为例,我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檀香刑》《生死疲劳》《秦腔》《高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兄弟》《启蒙时代》时,感受各有不同。莫言、贾平凹之于苏童、格非,一个倾向于民间、乡土,有着粗粝、热闹、生气勃勃的语言特性,小说散发出强烈的北方世俗味道;另一个则精致、细腻、心平气和地叙述,充满了南方文人的气息。阅读《人面桃花》《碧奴》清静如林中饮茶,而阅读《生死疲劳》《秦腔》则热闹若台前观戏。莫言、贾平凹作品的画面感强,色彩浓重,声音响亮,气味熏人,与余华的简洁、明快、幽默,王安忆的优雅、华贵、绵长的叙述风格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便莫言和贾平凹,虽然在文风上有相似性,但陕地和鲁地不同的风俗、语言特征也很明显地区分开了他们的作品。莫言显得比贾平凹更大开大合,汪洋恣肆,有一种百无禁忌、舍我其谁的叙述气概,鲁人的尚武、豪迈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1934年在《致陈烟桥》的信件中谈论中国木刻时曾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 ,后来被人们演绎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说法。鲁迅的原话在他的文章语境中是十分严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如果从合理的方向来理解这句话,也可以讲得通。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写作是如何从个人出发,走出地方、民族的局限,走向世界的?就本质来说,写作其实是完全个人化的。我们听说过有两人或集体合作的作品,有通过地方民谣等口头传唱形成的作品,也有某一民族流传形成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最终也总是通过多次的个人化写作固定下来;但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世界范围内的传唱并形成的作品。莫言或者其他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超越个人经验出发,沾染着地方色彩、民族性格,最终被世界接受的。包括王德威、伯佑铭等教授在内的许多海外学者也认可中国当代文学中,地方和民族风情会显示出中国文学独异的魅力,是构成世界文学的重要标志。虽然作家们都在利用地方和民族的特色,但莫言无疑是其中最为成功者之一。他以个人的才华、地方的生活、民族的情怀,有效地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后来被人们演绎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说法。鲁迅的原话在他的文章语境中是十分严谨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如果从合理的方向来理解这句话,也可以讲得通。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写作是如何从个人出发,走出地方、民族的局限,走向世界的?就本质来说,写作其实是完全个人化的。我们听说过有两人或集体合作的作品,有通过地方民谣等口头传唱形成的作品,也有某一民族流传形成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最终也总是通过多次的个人化写作固定下来;但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世界范围内的传唱并形成的作品。莫言或者其他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当代作家,他们的写作都是从超越个人经验出发,沾染着地方色彩、民族性格,最终被世界接受的。包括王德威、伯佑铭等教授在内的许多海外学者也认可中国当代文学中,地方和民族风情会显示出中国文学独异的魅力,是构成世界文学的重要标志。虽然作家们都在利用地方和民族的特色,但莫言无疑是其中最为成功者之一。他以个人的才华、地方的生活、民族的情怀,有效地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