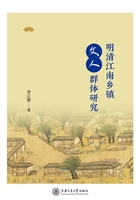
一、江南的城乡差别与不同生活方式
历代的江南地方志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这样叙述:江南社会自古富庶繁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社会都普遍崇尚奢侈、追求享受,而且人文教育发达,人们偏爱文化审美消费。这一叙述早在南宋范成大纂辑的《吴郡志》中就已出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二“风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与此相类的是,在无数乡邦文献中,人们往往对社会风俗急剧变迁的感叹最多。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一二十年间,乡村社会以往勤俭朴素、淳朴敦厚的风俗早已为奢靡骄伪的民情所取代。如清嘉庆年间纂修的上海《法华乡志》说:
与此相类的是,在无数乡邦文献中,人们往往对社会风俗急剧变迁的感叹最多。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一二十年间,乡村社会以往勤俭朴素、淳朴敦厚的风俗早已为奢靡骄伪的民情所取代。如清嘉庆年间纂修的上海《法华乡志》说:
法华人物朴茂,不事雕饰。士尚气节,农勤耕织,商贾务本安分,向称仁里。家居必具衣冠,亲友朝暮见必拱揖。时谓之法华喏嘲足恭也,然而君子称之。自清咸丰庚申之变后,礼俗趋于简略,服用习为侈靡,不若昔时之敦朴矣。![[清]王钟纂,[民国]胡人凤续辑,许新洪标点:《法华乡志》卷二“风俗”,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尤其明清时期,这种繁华奢靡确实是江南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源头则由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大都市发起,然后渐次向小城市以及乡镇和村落波及。如明人张瀚就曾说,三吴的消费风气对整个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力,因而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城市文化的消费性特征。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多数西方学者都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城市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在景观、组织和心态等方面都表现为高度同质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城乡分别也不是个人身份的标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文化特性。从江南社会的普遍风俗及其变迁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仔细考察分析,认真区分城市与乡镇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概念上来说,城市是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过去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纷杂的特征。而乡镇、市镇则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同时又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它既区别于普通村落和其他乡村社区,又与它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纯粹的乡村村落社会就更加不同了。
江南社会普遍崇尚奢侈,追求享受与审美性的消费习性,说明江南社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性和精神独立性,这也就是学者刘士林所提出的江南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于以经济-审美为核心,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与主体内在的审美需要的满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独立自由。江南以经济生产为基础的消费文化,依赖的是社会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造。例如,明清时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消费,人们更偏好于个体内在欲望的满足与精神的自由宣泄,而不是对外在的如礼仪性的、伦理性的、社会地位象征的重视。这与依赖政治中心维护的北方消费文化不同,北方文化生产的内在动力与创造理念主要根源于人们对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来自文化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要。
由此,是否说江南城乡社会之间就没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显然不是这样的。由于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毕竟存在巨大差距,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受到物质条件和发展空间制约的江南诗性文明就呈现出城市与乡镇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生产形态。这种在江南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不均衡”,是江南诗性文化再次裂变为“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
江南城市与江南乡镇的差异,主要是由它们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方面的不同决定的。 例如,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江南城乡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各不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基础”有直接关系。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乡镇、市镇原本是在政治都邑之外由于专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在性质上与州、县、都邑有很大差异,江南地区的城市大多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而乡镇则一般只担任较纯粹的经济商业身份,即使明清以来许多江南市镇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所属之县城,但在市场系统中的地位多半仍然屈居于县城之下。而在商业和手工业之外,传统江南市镇大多还包含着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从而呈现出一种“半市半乡”的色彩。这是乡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尚未与农村完全脱离关系的明显反映。
例如,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江南城乡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各不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基础”有直接关系。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乡镇、市镇原本是在政治都邑之外由于专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在性质上与州、县、都邑有很大差异,江南地区的城市大多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而乡镇则一般只担任较纯粹的经济商业身份,即使明清以来许多江南市镇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所属之县城,但在市场系统中的地位多半仍然屈居于县城之下。而在商业和手工业之外,传统江南市镇大多还包含着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从而呈现出一种“半市半乡”的色彩。这是乡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尚未与农村完全脱离关系的明显反映。
从城市与乡镇关系的角度看,由于在物质文明积累、制度文明建设,以及在城市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无论是对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系统的游离程度,还是经济生产的性质与规模,江南乡镇与江南城市的差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在“物质文明”层面上,“物质生产方式”是江南城市诗性文化进行自身再生产最重要的社会背景。传统江南社会的城乡差别不在于经济发达的程度,而主要在于城市的功能与经济组织方式。这一基础也决定了江南乡镇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纯粹以商业为基础的江南城市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
即使江南乡镇中存在许多超级乡镇,甚至有的已经在规模上超越了它的领属城市,如吴江县的震泽镇与盛泽镇、湖州的南浔镇等,在市场贸易上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规模,人口都在万户以上,远远超出县城的人口数量,但其城市功能则无法与县城匹敌,只是一个三级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专业市镇,而县城则是二级市场体系中的商业中心,此外县城还具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等功能。因此,江南乡镇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总是比城市更容易受到压制与限制,如康熙前期就颁布“机户不得逾百张”以限制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同时,“郊区市镇由于地域范围较小,因而似乎并未像府城那样形成专门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苏州、杭州等商业区分明、工业集中、城市空间规模大、人口数量巨大、消费水平领先的大都市,其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在经济功能上出现了显著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城市工业,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分配体制的相当成熟的市场交换系统,与一般的江南城镇相比,在生产结构与经济功能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都市的内涵与特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苏州、杭州等商业区分明、工业集中、城市空间规模大、人口数量巨大、消费水平领先的大都市,其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在经济功能上出现了显著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城市工业,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分配体制的相当成熟的市场交换系统,与一般的江南城镇相比,在生产结构与经济功能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都市的内涵与特征。
在江南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它们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不同。社会学家认为:“在实际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要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和表现出来的。这种形式即社会生活方式(简称生活方式),它表示的是人们以何种办法、手段与采取何种社会形式去过社会生活及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由此可知,一个时代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既直观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权力意志与政治需要,是其“政治文明”的客观化、现实化、感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看出江南城乡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即使在已相当富裕的江南乡镇,人们在生活观念上依然倾向于儒家哲学,如“耕读为本”“勤俭持家”等朴素生活方式。这一点与北方意识形态中重勤俭、礼仪、廉耻、耕读等社会政治伦理的生活观念恰恰非常一致,例如,万历二年,徽州吴氏的《茗洲吴氏家典记》中的“戒靡费”:
由此可知,一个时代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既直观地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物质文明”发展水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权力意志与政治需要,是其“政治文明”的客观化、现实化、感性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明显看出江南城乡在“文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即使在已相当富裕的江南乡镇,人们在生活观念上依然倾向于儒家哲学,如“耕读为本”“勤俭持家”等朴素生活方式。这一点与北方意识形态中重勤俭、礼仪、廉耻、耕读等社会政治伦理的生活观念恰恰非常一致,例如,万历二年,徽州吴氏的《茗洲吴氏家典记》中的“戒靡费”:
吾族喜搬演戏人,不免时屈举羸,诚为靡费,自今惟禁园笋,保禾苗,及酬愿等戏,则听演。余自寿诞戏尽革去。只照新例出银,以备常储,实为不赀。其视一晚之观艳,而无济于日用者,孰损孰益,必有能辨之。![[明]吴子玉纂:《休宁茗洲吴氏家记》卷七“戒靡费”条,家谱,明万历二年。](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又如明清时期江南乡村社会广为流传的家训或发蒙读物,其所宣扬的基本上也是“政治文明”的理念与话语。如家喻户晓的名言:“传家二字耕与读,防家二字盗与奸。倾家二字淫与赌,守家二字勤与俭。”(《重定增广贤文》)“人生在世,多见多闻,勤耕苦读,作古证今。”(《训蒙增广改本》)“念祖考创家基,不知栉风沐雨,受多少苦辛,才能足食足衣,以贻后世;为子孙长久计,除却读书耕田,恐别无生活,总期克勤克俭,毋负先人。”(《围炉夜话》)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南城市社会生活中那种昼夜喧闹、纸迷金醉、“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奢侈与糜烂,以及狂放、不顾一切只管眼前行乐的风尚。明代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中说:
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明]张瀚撰,盛冬铃点校:《松窗梦语》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而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广志绎》卷四中也对江南城市的奢侈有所描陈: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牢终日,夜则归市殽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则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明]王士性撰,周振鹤点校:《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在江南文化研究领域建树良多的刘士林先生还指出,“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明末一些士大夫发起的‘不入城’运动,他们不喜欢城市生活的奢华与糜烂,因而选择逃到乡镇去。又如清人颜元把自己少年时的轻薄不检归结为生活在城市里(《未坠集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江南城与乡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重要区别。从中可以见出,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同,江南乡镇对‘政治文明’的依附要比江南城市严重得多。”
在精神生活上,江南城市与乡镇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曾指出:
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美]R.E.帕克等著:《城市社会学》,宋峻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由此类推,我们知道乡镇社会也有自身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状态。乡镇社会所关心和延续的精神生活必然是以自我的物质基础及其生产方式为基础,是在自身社会心理与社会道德情感、共同趣味引导下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乡镇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基础有根本区别,其社会精神生活所关心的主旨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甚至截然对立。
在江南乡镇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人们把政治伦理功能看得比经济生产功能高得多。乡镇精神生活的核心是维护社会道德伦理的稳定,而不是个体自我的审美快乐。例如民国初年已被现代文明风尚撬动的南浔镇,人们仍然恪守着严格的伦理信念。著名诗人、报告文学家徐迟在《一个小镇的轮廓》中描绘的南浔的社会文化观念就是如此:
在这个镇上有着令人起敬的严峻的道德律。特别在男女关系上,当然婚姻是必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处女必需的束胸,不过已经不用裹脚了,还要善于女红和少不得要有一切处女应有的美德。除了迎神赛会,她们是不允许站到街头去的。自然她可以跟妈妈到绸缎店去,当绸庄里的伙计把印花的,闪光的,五色的料子取来给她挑选的时候,她才第一次看到世界上的美丽。然而这些女人虽然是被幽禁起来了,也不知道忧愁,她们都静静地等候命运允许她们每人一个好丈夫。男孩子和女人一样的受到礼教束缚,是不允许他们勾搭女人的。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江南乡镇是传统礼俗最忠实的信仰者与实践者,在维护风化与纲纪等方面,它们往往比北方的政治中心更加顽固不化。如江南乡镇对越轨男女的惩罚,其严厉与残酷是世人皆知的。再如,在素有“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之称的徽州棠樾,那里驰名于世的牌坊群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但在江南城市生活中,情形就大不一样。对此,刘士林先生的论文《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有所论述:
对同一件事情,不仅羡慕者有之,鼓励、纵容者有之,更有甚者还把它们美化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解放行为。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是古代色情小说,也最喜欢以苏州、扬州、杭州为生活场景。如《梧桐影》第三回写道:“话说从古到今,天子治世,……第一先正风化。风化一正,自然刑清讼简了。风化惟‘奢淫’二字,最为难治。奢淫又惟江南一路,最为多端。穷的奢不来,奢字尚不必禁,惟淫风太盛。苏松杭嘉湖一带地方,不减当年郑卫……”透过其道德说教的外衣,恰好说明江南城市生活的‘去道德’与‘去教化’本质。与江南乡镇诗性文化相比,江南城市诗性文化则呈现出更加自由、活泼的感性解放意义。
从伦理习俗的角度着眼,我们可以看出江南城乡社会在精神生活上泾渭分明的态度。
在日常生活、闲暇生活与文化消费方式上,江南城市与乡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上,江南城市社会的人们有更多从事工商业的机会,同时服务业的发达又可以吸纳大量闲散劳动力。明清时期作为苏州商业和手工业作坊聚集中心的虎丘和山塘一带即是如此,各种手工业作坊和手工艺制品店有好几百家,清人顾禄的《桐桥倚棹录》记述这里的酒楼、茶肆数量不下四五十家,因而,虎丘一带的多数居民可以完全以此为生计来源。明代后叶的小说《石点头》就形象地反映了当时苏州的这种都市社会的经济世态:
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少扯空砑光的人。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挨次铺排,倒也热闹齐整。![[明]天然痴叟撰:《石点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因而,江南城市市民的生产活动是直接为城市消费经济服务的,其日常生活消费也主要靠从市场购买来取得,而不需要自(半自)给自足。
江南乡镇的情形就不一样,仍然是一种“半市半乡”的社会。虽然这里工商业也很发达,但要使大多数人完全赖此生存则不可能。因而,江南乡镇的常态是“工农之间界线模糊”,绝大多数人是通过半工半耕的方式供给自己。江南经济史研究者认为:“由于农村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江南农村居民常常是农、工、商多种职业兼营,并非只是种田的‘专业农民’,相反,在市镇居民中,也有不少人把其全部或部分劳动时间用于农业生产劳动。” 如20世纪30年代,德清县新市镇的家庭以蜡烛生产为副业就是一个典型。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新市镇蜡烛灯芯之制造情形》记载:
如20世纪30年代,德清县新市镇的家庭以蜡烛生产为副业就是一个典型。民国时期的调查报告《新市镇蜡烛灯芯之制造情形》记载:
蜡烛芯之制造,皆以女工任之,女工散居四乡,或由烛芯店发给原料,限期交货,或由乡人自备原料,分批出卖,……制造烛芯一,为乡间妇女种副业,酬劳极微。若以之为家庭工业,则不足维持生计,大概最多每天可得大洋二角,普通只有五分至一角。
日常闲暇与文化消费的情形也与城乡之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直接相关。江南乡镇社会里,闲暇生活的状况受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社会关系的性质、个人思想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如民国时期吴兴双林镇上人们生活清闲:“耕田育蚕外,无所事事。男子徜徉廛市,出入茶酒各肆,女亦闲暇时多。”![[清]蔡荣升纂:《双林镇志》卷十七“商业”,见谭其骧,史念海,傅振伦等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2册下,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569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较为缓慢,市镇商业的顾客主要是农民,大多早市以后即可收市打烊,因而人们有相对稳定的闲暇娱乐时间,如光绪年间《慈溪县志》卷五五“风俗”说:“市肆晨开午闭。余时击鼓吹箫为乐……其市井之人午前开肆,午后闭肆。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无不为。”
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较为缓慢,市镇商业的顾客主要是农民,大多早市以后即可收市打烊,因而人们有相对稳定的闲暇娱乐时间,如光绪年间《慈溪县志》卷五五“风俗”说:“市肆晨开午闭。余时击鼓吹箫为乐……其市井之人午前开肆,午后闭肆。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无不为。”![[清]冯可镛等修,杨泰亨纂:《慈溪县志》卷五五“风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版,第1206—1207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由于社会可供消遣的文化资源相对有限,加上抵制消费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的闲暇生活和文化娱乐虽然相对稳定平缓,但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多为泡茶馆、酒肆、赶庙会,文化消费上多半是听乡村戏曲等。著名漫画家、文学家丰子恺在《中举人》一文中回忆自己的祖母时说:
镇上演戏文时,她总到场,先叫人搬一只高椅子去,大家都认识这是丰八娘娘的椅子。她又请了会吹弹的人,在家里教我的姑母和父亲学唱戏。
不过乡镇社会演戏的内容和形式一般都比较粗糙,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这恰如今人东君在《看戏琐记》里回忆的那样:
小时候在浙南乡间,大人们坐在戏台前看得如痴如醉,我们这些吊儿郎当的小孩子就喜欢往后台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那些戏子在上场之前总是使劲地往粗皮糙肉上草草涂抹一些庸脂劣粉;再走近一些,或许还能看到皇冠上爬着几只小虫子,凤披间留着几根稻草屑。
乡镇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都不够纯粹,往往掺杂着直接的功利目的与现实功效。它基本上都要与人们的经济生产活动和物质利益结合起来,具有更多的生产性或经济性。例如,江南乡镇的茶馆生意跟农民的活动节奏一致,如桐乡县乌青镇的“西栅茶店都为乡农出市叙集之所,故只乡航到时座中客满”![[民国]卢学溥修:《乌青镇志》卷二十一“工商·茶酒肆业”,见谭其骧,史念海,傅振伦等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3册,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第600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南浔镇的茶馆也是如此:
。南浔镇的茶馆也是如此:
又较大之乡村,多有小茶馆之设,在茶馆每人茶资七十文。乡间男子在农忙及养蚕时期外,每日生活大约须耗去半日光阴于此。晨起后,俟航班开行,即附船上镇。除在船上须耗去几许时间外,到镇后即步入茶馆,集相识者于一隅,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本地新闻、茧丝价格以及年成好坏,等等,均为主要谈话材料。在茧丝新米上市之时,乡人即以此地为探听市价之所,因而经营茧、丝、米或其他产品之掮客,亦往往出没于其间,从事撮合,赚取佣金。此外在不养蚕或农闲之季,乡民来此饮茶者尤多。在夏季昼长夜短,大约自晨至午,半日时间,皆消磨于此。临归时再买些油酒之类,回家午餐,餐后始下田工作。在冬日昼短,农家每日只有两餐,则早餐后上镇,晚餐前始归。此种情形,虽非人人皆然,多数要皆如此。一年四季除蚕忙田忙之时外,其余多日时间皆以此地为唯一消遣所,以是每日半日悠闲,半日工作,怠惰成性,荒废甚多。而其中不肖者遂相引作赌博,因此而丧财败名,往往有之。![[民国]刘大均著:《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版,第133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又如清人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中记载苏州乡镇二三月间的春台戏:“承平日久,乡民假报赛名,相习征歌舞。值春和景明,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俗谓之春台戏。抬神款待,以祈求农祥。台用芦席蔽风日,谓之草台。”![[清]袁景澜撰,甘兰经,吴琴校点:《吴郡岁华纪丽》卷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春台戏规模很大,非常热闹,但要以祁祥农事、敬奉神明为借口举办。
春台戏规模很大,非常热闹,但要以祁祥农事、敬奉神明为借口举办。
在江南城市,一般市民的文化娱乐消费则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多元文化审美消费活动,它以商业性与审美趣味为中心原则。如学者龙登高在《临安娱乐市场分析》中分析临安娱乐市场时指出:“中晚唐以后,娱乐作为一种消费服务,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在南宋临安,以谋生和营利为目的的文化娱乐活动已相当普遍,娱乐市场发育趋于成熟,并推动着娱乐业的成长,这在经济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阶段性的意义。” 再以日常游玩为例,尽管江南乡镇人也游玩,如士大夫赋闲或致仕以后在乡里游玩山水,但本质上是有节制的和高雅的,以不伤大雅,即不触及政治理想与伦理原则为前提。但江南城市市民的游玩与此不同,其最大特点是多元化与多样性,适宜不同人等的消费与享受。例如,明代文豪袁宏道在《虎丘》一文中所写的苏州虎丘中秋节景象:
再以日常游玩为例,尽管江南乡镇人也游玩,如士大夫赋闲或致仕以后在乡里游玩山水,但本质上是有节制的和高雅的,以不伤大雅,即不触及政治理想与伦理原则为前提。但江南城市市民的游玩与此不同,其最大特点是多元化与多样性,适宜不同人等的消费与享受。例如,明代文豪袁宏道在《虎丘》一文中所写的苏州虎丘中秋节景象:
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竞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头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而和者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明]袁宏道撰:《袁中郎游记全稿》,上海: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1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5D403B/165669936043561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34438748-eQ3od5aP1c1vCTKlSfFLEjo2ROL2QNOB-0-d123e931928d13ba7f1c4c9c1e2f9734)
这说明,江南城市以独特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基础,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江南乡镇的都市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