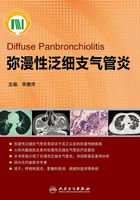
第三章 病因及发病机制
DPB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过去曾认为本病发生与吸入刺激性气体有关,但近年的资料表明,两者并无明显相关性,同时本病发生与吸烟也无密切关系。随着一系列分子基因及免疫学研究进展,目前普遍认为DPB是一种涉及多种因素的疾病,包括遗传、免疫异常及感染因素等。
从解剖结构上,终末细支气管移行至呼吸性细支气管,其长度只有数毫米,其内腔直径扩大十倍,气流于此处形成涡流,从而细菌和微粒易于沉积于该处黏膜上,引起炎症。最终可导致广泛的细支气管狭窄或阻塞而引起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
一、遗传因素
DPB可能是一种与遗传、人种和体质因素有关的疾病,其理由如下:①DPB带有人种特异性的可能性很强。据目前所知,DPB多见于日本、韩国及我国等东亚地区,直到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方有白种人患病的报道,但病例数总体较少;②鼻窦炎是一种遗传性因素较强的疾病。DPB与慢性鼻窦炎密切相关,研究发现80%以上DPB患者合并慢性鼻窦炎或有既往史,部分患者有慢性鼻窦炎家族史。有文献报告[1]父母鼻窦正常、父或母罹患鼻窦炎和父母均患鼻窦炎者,其子女患DPB的概率分别为10%~14%、50%~60%和60%~68%;③本病有一定的家族发病倾向,曾有文献报道6个家族同胞都患有DPB[2],上海市肺科医院近年也发现一些一个家族同时有2例以上DPB患者的家系。关于DPB的遗传学背景究竟有哪些异常目前尚未完全弄清楚,有些研究认为与以下几方面异常有关。
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系统即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位于人体第6号染色体短臂6p21.31区,全长约3600kb,包括224个基因座位,其中仅有128个为功能性基因(有产物表达),96个为非功能性基因,很多基因座位存在大量的复等位基因,具有高度的多态性,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最复杂的基因系统。
HLA参与抗原的处理及提呈、免疫应答的遗传控制及T细胞的活化。尽管HLA仅相当于基因组DNA的1/3000,却与部分疾病密切相关。HLA基因表达的多样性,群体中不同个体HLA等位基因拥有状态的不同,均可导致个体间免疫应答能力和对疾病的易感性出现差异。
根据编码产物的结构、组织分布及功能不同,HLA可分为HLA-Ⅰ、HLA-Ⅱ、HLA-Ⅲ三类。
HLA-Ⅰ类基因的多态性非常高,主要位于端粒端,其中经典HLA-Ⅰ类基因包括A、B、C三个位点,其产物称HLA-Ⅰ类分子;非经典Ⅰ类基因又称HLA-Ⅰb,包括HLA-E、HLA-F、HLA-G等。Ⅰ类分子广泛分布于机体有核细胞表面,其主要功能是参与提呈外来性抗原给CD8+的T细胞。
HLA-Ⅱ类基因主要包括DP、DQ、DR三个亚区,主要分布于B淋巴细胞、抗原提呈细胞和激活的T淋巴细胞表面,参与提呈外来抗原给CD4+的T细胞。
HLA-Ⅲ类基因位于Ⅰ类和Ⅱ类之间,主要有补体C2、C4A、C4B基因、肿瘤坏死因子基因等。
现有研究表明,与DPB疾病相关的主要是HLA-Ⅰ类抗原,HLA-Ⅱ类抗原的意义尚不能肯定,而与HLA-Ⅲ类抗原无明显联系。
1990年,Sugiyama等[3]运用血清学微量淋巴细胞毒实验的方法对38例DPB患者HLA抗原进行的研究发现,DPB与HLA-B54呈高度正相关性,B54抗原在患者组及对照组出现的频率分别为63.2%和11.4%(相对危险度RR = 13.3,P<0.001)。已知HLA-B54是除印第安人与大部分犹太人外,包括中国人在内的蒙古系人种的特有抗原,日本人约12.2%阳性[6],韩国人约12.6%阳性[6],中国人约5.66%阳性[8],而白种人极为少见。该结果支持DPB存在一定的人种特异性。此外,DPB患者组Cw1和MC1也有轻微的升高,分析可能是由于此两种抗原与HLA-B54共同形成了日本人典型的单倍型HLA-B54-Cw1-A11/24-DR4(DRB1* 0405)。
HLA-Ⅲ类抗原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及C4位于HLA-B位点附近,推测可能与DPB发病相关。Yasuyuki T[4]等运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法(polymo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PCR-RFLP)对32例DPB患者进行研究,发现DPB患者组B54较对照组明显增高(40.3% vs 13.0%,P<0.001),但DPB与TNFα/β及C4 A/B多态现象无明显相关性,从而推测DPB与HLA-Ⅲ类抗原无明显联系。
此后,Keicho等[5]分别检测76例日本DPB患者及110例健康对照者的HLA等位基因,结果显示,DPB与HLA-B54、A11、Cw1呈正相关性,与HLA-A33、B44呈负相关性,其中以HLA-B54相关性最为明显,患者组及正常对照组B54阳性率分别为36.8%和14.6%(P = 0.004)。已知编码HLA-B22家族的等位基因包括HLA-B54、B55和B56,进一步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ingle strand conformational polymorphism,PCR-SSCP)方法进行分析,血清型为B54者,B* 5401在DPB患者组及正常对照组出现频率分别为37%及15%(χ2=12.4,P=0.0004);血清型为B55者,DPB患者组几乎为B* 5504,对照组全部表现为B* 5502;血清型为B56者,DPB患者组及对照组B* 5601阳性率分别为8%及3%。提示DPB的发病与编码HLA-B54抗原的B* 5401基因及编码HLA-B55抗原的B* 5504基因具有高度相关性。
Keicho[5]等同时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方法检测Ⅱ类抗原HLA-DRB1,发现HLA-DRB1* 1302在患者组出现频率有所降低(P<0.02),但由于日本人中存在典型的单元型A33-B44-C blank-DR13(DRB1* 1302),其是否有原发关联意义尚不肯定。故Keicho等提出,HLA-Ⅰ类抗原较Ⅱ类抗原与DPB的关联性更强。
1999年,Park等[6]对30例韩国DPB患者HLA抗原及单倍型进行了研究,采取血清学方法对HLA-Ⅰ类抗原进行分型,顺序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分析(PCR-sequence specific oligonucleotide,PCR-SSO)方法对HLA-Ⅱ类抗原进行分型,结果显示DPB患者中高频率出现HLA-A11,其阳性率为53.3%,而对照组仅为17.5%(P= 1.2×10-4,OR=5.4)。同时B55(16.7% vs. 3.5%,P = 0.05,OR = 5.5)、B62(36.7% vs. 16%,P<0.01,OR=3.0)、Cw4(23.3% vs. 8.5%,P<0.05,OR=3.3)也显示了与DPB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此外,与对照组相比DPB患者组HLA-B44(6.7% vs. 22.0%,P<0.1)、DR13(5.0% vs. 25.5%,P= 0.05,OR= 0.15)出现的频率有所降低。与日本不同的是,韩国DPB患者与B54没有明显的关联,B54在韩国DPB患者组及对照组阳性率分别是13.3%和12.5%(P>0.05)。
Park等[6]对HLA单倍型的研究显示,与HLA-A11抗原相比,单倍型A11-Cw1(16.0% vs. 1.9%,P=6.3×10-7,OR = 12.1)、Cw1-B55(7.9% vs. 1.0%,P = 0.004,OR = 9.8)、A11-B62 (12.9% vs. 2.2%,P=5.5×10-4,OR=7.9)与DPB相关性更强。与DPB患者组B54抗原无明显升高不同,单倍型A11-B54和A11-Cw1-B54在患者组出现的频率有所升高。故Park等[8]认为,韩国DPB发病与HLA-A11有高度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提出,DPB易感基因可能位于HLA-A、B位点之间。
既往研究结果显示,日本人群中HLA-B54和韩国人群中HLAA11分别与DPB发病呈显著的相关性。日、韩两国人种在人类遗传学上有密切的相关性,日本人和韩国人的祖先具有共同的组织相容抗原系HLA-B54-Cw1-A11。根据以上结果,Keicho等[7]提出了DPB疾病易感基因(◆)的重要假说,该假说提出,在日、韩共同的祖先染色体(B54-Cw1-◇-A11)发生了对疾病感受性上的变异后(B54-Cw1-◆-A11),在日本人,基因重组主要发生在A位点侧;而在韩国人,基因重组主要发生在B位点侧,从而显示了目前DPB发病与HLA分型的相关性。根据以上假说,Keicho等[7]对HLA-A、B位点之间进行研究,发现7种标记等位基因与DPB明显相关,包括HLA-B54和HLA-A11。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相关的单倍型均是从Ⅰ类区域S和TFIIH位点之间分出,其中一个遗传标记delta值最高,表明与疾病相关性最强。由此推定DPB易感基因位于B位点约300kb处向A侧约200kb范围内。
2007年沈策等[8]采用顺序特异性寡核苷酸探针分析(PCR-sequence specific oligonucleotide probes,PCR-SSOP)法对24例DPB患者进行HLA分型,结果显示,HLA-A2与DPB呈负性相关,其在DPB患者组出现频率为20.83%,对照组为66.04% (χ2=13.52,P=0.001,OR= 0.12)。既往文献报道,日本(29.0% vs. 40.0%,P>0.05)、韩国(36.7% vs. 55.0%,P<0.1)两国DPB患者HLA-A2出现频率均有所减少,据此认为HLA-A2可能是DPB发病的一个保护因素。与韩国相似,HLA-A11与DPB的发病成一定正相关性,A11在患者组及对照组阳性率分别是58.33%和26.42%(P=0.007,OR=3.9)。B55在患者组也有所升高(16.67% vs. 3.78%),分析可能由于B55与A11构成典型单倍体HLA-A11-C blank-B55。HLA-DRB5* 010/020在DPB患者组阳性率较对照组稍高(37.5% vs. 16.98%,P =0.049),但尚不肯定其是否有意义。其DPB与HLA-B54没有明显的联系,患者组及正常对照组阳性率分别是12.5%和5.66%(P=0.37)。
但是,翟惠芬等[9]运用血清学的方法检测13例北方汉族DPB患者HLA-A、B抗原,结果却显示,DPB与HLA-B54呈一定相关性。由于HLA-B7和B54抗原具有部分相似的结构,属于相关抗原,将其作为整体计算,DPB患者组阳性率为53.8%,而对照组仅为16.7%(χ2= 4.524,P=0.03)。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提示我国DPB遗传背景的研究有待深入,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
HLA-Ⅰ类分子的主要作用是与抗原多肽结合形成复合物,并提呈内源性抗原给CD8+T细胞,诱发特异性免疫反应。
完整的抗原必须首先在胞浆中降解成多肽,而最主要的胞内蛋白酶解复合物是蛋白酶体,其核心是低分子量多肽(low molecular weight polypeptide,LMP),是MHC内的基因(LMP2、LMP3)编码的产物。而多肽必须从胞浆进入内质网(endocytoplasmic reticulum,ER)后才能与Ⅰ类分子结合,该过程需要在抗原加工相关转运体(transporter associated with antigen processing,or transporter of antigenic peptides,TAP)的帮助下实现。TAP是一个二聚体分子,双链分别由TAP1和TAP2两个座位的基因所编码。
Keicho[10]等认为,DPB与HLA-Ⅰ类基因相关,与HLA-Ⅰ类抗原提呈系统亦有一定的相关性。其对76例DPB患者运用DNA测序结果发现,TAP2外显子11内Ala-665和Gln-687的联合表达与DPB有显著的相关性(P=0.0028)。同时,如替换LMP2中的His60则显示了与DPB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
DPB的一个典型临床特征是大量脓痰,其中痰液的主要成分为黏液,而黏蛋白(MUC)基因与黏液分泌有关,故认为MUC基因可能在DPB发病过程中起作用。
目前已知的人类MUC基因有MUC1-4、MUC5AC、MUC5B、MUC6-9、MUC11-13,而气管和支气管上皮细胞仅表达MUC1-4、MUC5AC、MUC5B、MUC7、MUC8,其中MUC5AC是最主要的成分。
Yukihiro Kaneko等[11]通过蛋白印迹分析(western blot)法分别检测DPB患者及正常人群组、其他疾病对照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 fluid,BALF)中MUC5AC基因的表达,结果显示DPB患者BALF中MUC5AC基因的表达较其他疾病组、正常人群组均有升高,且在红霉素治疗后有所下降。Yukihiro Kaneko等[12]通过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模拟DPB小鼠模型,进一步检测发现小鼠肺组织中MUC5AC基因在mRNA、蛋白水平表达均有增加,应用克拉霉素后mRNA表达明显降低,进而提出MUC5AC基因在DPB发病过程中可能起一定作用。
但Koichiro Kamio等[13]提出,与DPB密切相关的不是MUC5AC基因而是MUC5B基因。他对92例日本DPB患者MUC基因启动子区域进行多态性分析,结果显示MUC5B基因多态性和DPB有高度的相关性(P = 0.0001)。MUC2、MUC4、MUC5AC、MUC7的启动子区域存在2~4种多态性,而MUC5B的启动子区域存在10种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s)和一种由双核苷酸插入/缺失引起的多态性,其中由双核苷酸CA插入/缺失造成的多态性与DPB发病最为相关。
在正常肺组织中,MUC5AC基因仅表达于支气管表面杯状细胞,而MUC5B基因主要在支气管黏膜下腺体细胞表达,在杯状细胞中仅有少量表达。某些气道疾病存在MUC5B异常表达于杯状细胞,从而造成黏液过度分泌。据此,Kamio等[13]进一步对DPB患者肺组织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后发现,黏膜下腺体细胞过度表达MUC5B,而杯状细胞除大量表达MUC5AC外,亦大量表达MUC5B,故提出MUC5B的异常及过度表达可能与DPB相关。
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CF)是一种白种人多发的遗传缺陷性疾病,其与DPB在鼻窦炎和支气管肺部的感染等诸多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均伴有铜绿假单胞菌等病原体感染及中性粒细胞占主导的气道炎症反应[14]。但是DPB患者并无胰腺功能不全、生殖功能障碍等表现,汗液中也无明显的电解质异常[15],而且CF患者中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常即位于7号染色体上CFTR基因中的delta-F508并未出现在DPB患者中[16],但目前尚不能排除CFTR基因突变在DPB发病机制中的作用[17]。
另一种遗传性疾病,所谓Ⅰ型裸淋巴细胞综合征(bare lymphocyte syndrome typeⅠ),其临床特征与DPB极其相似,与HLA的Ⅰ类抗原加工不完全有关,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效果很好[18]。而有趣的是,CFTR及抗原加工都是ATP结合转运超家族的成员[19],该病是否与DPB有关联尚需进一步研究。
既往曾有学者推测DPB与NADPH/NADH有关,但已被证实无明显关联[20]。
二、感染因素
DPB患者同时患有慢性鼻窦炎者占80%以上,且DPB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支气管黏膜病变或气道分泌物增多,部分DPB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以及白细胞介素-8(interleukin-8,IL-8)等升高,均提示本病呈慢性气道炎症改变。因此,有观点认为DPB发病与感染有关。
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又称绿脓杆菌,为革兰阴性杆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铜绿假单胞菌有多种毒力分子,包括外毒素A、内毒素、弹性蛋白酶(elastase)、黏附素及多糖荚膜等。
DPB患者几乎都有较多量的脓痰,痰中铜绿假单胞菌培养的阳性率为55%~82%,因此,推测DPB的发病可能是由于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支气管、肺慢性感染所致。1997年Yanagihara等[21]用铜绿假单胞菌包被的塑料管置入小鼠右侧支气管,成功建立了DPB小鼠模型。2005年沈策等[22]从DPB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并人工感染SD大鼠,成功建立了DPB动物模型。上述DPB动物模型的成功建立,进一步支持本病可能与铜绿假单胞菌感染有关。
有学者认为铜绿假单胞菌致病的最主要成分是弹性蛋白酶,其能降解肺组织的弹性蛋白,具有组织损伤活性,从而引起肺组织损伤及出血。Yanagihara等[23]用铜绿假单胞菌PAO1和PAO-E64两种菌株感染小鼠,建立DPB动物模型。其中PAO-E64是弹性蛋白酶突变菌株。研究发现,PAO-E64感染的小鼠肺组织中淋巴细胞数明显低于PAO1感染的鼠,PAO1感染的小鼠在细支气管周围有广泛的炎性细胞聚集,而PAO-E64感染的小鼠仅出现局部炎症。以上现象提示铜绿假单胞菌释放的弹性蛋白酶可促使DPB患者肺部发生明显的炎症改变。
尽管上述证据均提示DPB的发病与铜绿假单胞菌的感染有关,但铜绿假单胞菌感染与DPB之间的因果关系尚不清楚。
支原体(mycoplasma)是一类无细胞壁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已知对人致病的主要是肺炎支原体(M. pneumoniae)。机体感染肺炎支原体后,血清中可检出多种支原体抗体。病人血清中还可诱发一种非特异冷凝集素,其本质为IgM型的自身抗体。冷凝集素针对红细胞膜的Ⅰ型血型抗原,可与患者自身的红细胞或O型人红细胞在4℃条件下凝集,这种凝集在37℃条件下消失,即冷凝集试验(cold agglutination reaction)。肺炎支原体感染者冷凝集试验的阳性率为50%,可用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辅助诊断。但该反应为非特异性,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腮腺炎、流感等也可出现冷凝集素效价升高。
DPB部分患者出现血清冷凝集试验效价的升高,且红霉素治疗有效,进而有学者推测该病可能与支原体感染有关,但也有部分DPB患者血清支原体抗体为阴性[24],因此支原体感染与DPB的因果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人类嗜T细胞病毒(human T-cell lymphotropic viruses,HTLV)于1980年由美国学者Gallo首次分离出,是一种逆转录病毒。HTLV根据基因学及血清学反应可分为HTLV-1型和HTLV-2型,其中HTLV-1在体内主要感染CD4+T细胞,抑制T细胞功能及免疫应答反应,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皮肤、眼、肺、关节等多系统病变,如成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adult T-cell leukemia,ATL)、HTLV-1葡萄膜炎、HTLV-1相关的脊髓病/热带痉挛截瘫等;目前尚无HTLV-2与其他疾病明确的相关关系。
与HTLV-1感染相关的肺部疾病包括间质性肺炎、DPB、支气管扩张等。已有文献报道多例DPB患者合并HTLV-1抗体阳性[25]。Kimura等[26]报道,DPB患者HTLV-1抗体阳性比例为35%,较其他疾病及健康对照组增高。Kadota等[27]通过对15例HTLV-1相关性细支气管炎(HTLV-1 associated bronchopneumonopathy,HAB)患者及43例DPB患者的比较,指出虽然DPB与HTLV-1相关性细支气管炎在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表现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DPB不同的是,HTLV-1相关性细支气管炎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IL-2Rα(IL-2 receptor-α)、CD25+细胞比例明显升高,HTLV-1相关性细支气管炎患者组、DPB患者组、健康对照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CD3+CD25+细胞百分比分别为11.8%±1.7%、5.1%±0.7%及4.7%±3.4%。作者指出DPB可能与肺部HTLV-1慢性感染有关,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免疫异常
部分DPB患者可出现血清冷凝集试验效价增高,IgA、IgG升高,与正常人有显著差异,故推测DPB可能与免疫功能异常有关。
通过对DPB肺组织活检,可清楚地看到在炎症受累的气道内有活化的中性粒细胞聚集,造成气道的炎症和损伤迁延不愈,而大环内酯类的治疗可减少肺内这种中性粒细胞的聚集。
Ichikawa等[28]检测了11例DPB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结果显示DPB患者BALF中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其在DPB患者组为55.3%±24.4%,慢性支气管炎组为6.6%±6.4%,而健康对照组仅为1.8%±1.5%(P<0.001)。Kadota[29]等通过对7例DPB患者的随访观察发现,经红霉素小剂量(600mg/d)、长期(12.9个月±9.5个月)治疗后,DPB患者BALF中升高的中性粒细胞数逐渐降至正常,同时伴随临床症状和体征的改善,1秒钟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较用药前明显好转。提示中性粒细胞在气道中的聚集对DPB发病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DPB的组织形态学表现为以呼吸性细支气管为中心的细支气管炎及细支气管周围炎,在呼吸性细支气管区域中,淋巴细胞、浆细胞等细胞浸润使管壁增厚,常常伴有淋巴滤泡的增生。故淋巴细胞在DPB发病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
Mukae[30]等检测了33例DPB患者BALF中的T细胞亚群,对照组为9例支气管扩张患者及30例健康对照者,结果显示淋巴细胞百分比在三组人群中相似,但DPB患者组的淋巴细胞绝对数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CD8+HLA-DR+细胞百分比、总数及CD4+HLA-DR+细胞总数高于对照组,但CD4+/CD8+比值明显下降,相反,外周血中CD4+/CD8+比值升高。肺脏CD3+细胞表面的CD11a和CD18等黏附分子在DPB患者BALF中表达增高,而外周血中这些黏附分子的表达与正常对照组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在长期应用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后,淋巴细胞总数和CD8+细胞数下降,CD4+/CD8+比值上升。
细胞凋亡,又称程序性细胞死亡,是指在基因调控下,某种结构的部分细胞在预定的时期主动的死亡、消除。已有研究表明,DPB患者呼吸性细支气管周围淋巴细胞聚集,故有学者推测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与DPB病理变化相关。Kadota等[31]运用免疫染色的方法对5 例DPB患者的肺组织进行分析,分别是Bax(细胞凋亡的启动子),Bcl-2(细胞凋亡的抑制物),和caspase-3(细胞凋亡的终止物),正常肺组织表现为Bax染色阳性、caspase-3染色阳性,Bcl-2弱阳性或阴性。DPB患者细支气管周围及滤泡旁的淋巴细胞Bax染色、caspase-3染色阴性,而Bcl-2则表现为强染色。提示DPB患者肺部Bcl-2基因过度表达,Bcl-2家族蛋白通过抑制T细胞凋亡参与DPB发病过程。
抗原提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APC)是指能捕捉、加工、处理抗原,并将抗原提呈给特异性淋巴细胞的一类免疫细胞。APC可分为专职和非专职两种,前者包括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等,后者包括某些内皮细胞和上皮细胞等。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由美国学者Steinman于1973年发现的,是目前所知的机体内功能最强的抗原提呈细胞,广泛分布在除脑以外的所有器官的黏膜表面。有别于其他抗原提呈细胞,DC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启动T细胞初级免疫应答,因此DC是机体免疫应答的始动者。其中人树突状细胞的主要特征性标志为CD1a及CD83阳性。
Todate等[32]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11例DPB患者及7例健康对照者的肺脏组织进行研究后发现,DPB患者细支气管上皮和黏膜下组织中的CD1a+和CD83+DC数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其中黏膜下组织中DC数量的增加较细支气管上皮DC数量的增加明显。最为突出的差异是,患者组黏膜下组织表达CD83抗原的DC增多,而正常细支气管组织只有极少量的CD83+细胞。CD83+DC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抗原提呈细胞,表达高水平MHC-Ⅱ类抗原和黏附分子,有强大的抗原提呈能力。以上结果提示,DPB患者黏膜下组织高度聚集的CD83+DC通过其强大的抗原提呈能力,有效刺激黏膜下浸润的T细胞,导致细支气管的炎症。此外,DPB患者中细支气管细胞表达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明显增加,而GM-CSF已知与DC聚集、分化及其他功能相关,故DC的激活及增加在DPB黏膜免疫反应中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细胞因子是一类由免疫细胞(淋巴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和相关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及上皮细胞)产生的具有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多功能的低分子蛋白质,在机体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细胞因子可分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集落刺激因子、生长因子和趋化性细胞因子六类。
辅助性T细胞(help T cell,Th)可分为Th0、Th1和Th2三个亚群。Th1细胞亚群通过分泌干扰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IL-2、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alpha,TNF-α)及IL-1β等参与自限性的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反应;而Th2细胞亚群主要通过分泌IL-3、IL-4、IL-5、IL-6及IL-10等参与抗体介导的慢性、广泛的体液免疫应答反应。
Yanagihara等[33]通过对慢性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DPB动物模型的检测,发现铜绿假单胞菌感染60天以后,在试验小鼠的肺组织中,包括IL-1β、IL-2、IL-4、IL-5、IFN-γ和TNF-α等在内的炎症介质及淋巴细胞总数均有过量表达(P<0.01);而克拉霉素治疗后上述炎症介质均有所下降,以IL-1β和TNF-α最为明显(P<0.01);抗TNF-α抗体治疗后淋巴细胞总数及IL-1β明显下降(P<0.01),提示DPB发病过程中上述炎症介质可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相应的重要作用。
白细胞介素-8是α亚家族趋化性细胞因子的代表,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及少量淋巴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产生,其主要生物学功能是趋化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及T细胞等到达炎症部位。Koga T[34]在对DPB患者BALF研究后指出,DPB患者BALF中的中性粒细胞趋化活性(neutrophil chemotactic activity,NCA)及IL-8明显升高[71.6%±3.6%,(491.9± 48.0)pg/ml],而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组为[24.8%±2.8%,(54.1±13.9)pg/ml,P<0.001],正常对照组为[7.0%±0.9%,(14.2±3.9)pg/ml,P<0.001],提示IL-8与NCA明显相关。Kadota[29]等运用酶联免疫吸附反应(ELISA)证实DPB患者中性粒细胞和IL-1β、IL-1Rα及IL-8都明显增加,当长期应用红霉素治疗后,中性粒细胞数和上述细胞因子均下降至正常。IL-1β、IL-1Rα、IL-8与中性粒细胞的聚集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与BALF中肺泡巨噬细胞无相关性,提示IL-8可能在DPB患者气道中中性粒细胞介导的慢性炎症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脂类介质白三烯B4(leukotriene B4,LTB4)也是一种中性粒细胞强趋化因子。Oda[35]等研究发现,DPB患者LTB4含量和中性粒细胞趋化活性(NCA)明显升高,DPB患者BALF中LTB4平均含量为(3.5±1.1)ng/ml,健康非吸烟对照组LTB4平均含量为(0.1±0.0)ng/ml (P<0.001);而经红霉素治疗后,LTB4[(0.6±0.3)ng/ml,P<0.01]和NCA(26.4%±1.7%)水平显著下降,并且在红霉素治疗前后,LTB4含量的降低分别与NCA的降低(r= 0.832,P<0.01)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变化(r = 0.778,P<0.05)呈密切相关,提示LTB4也是引起DPB患者炎性损伤的一种重要介质。
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eptide-1α,MIP-1α)和RANTES (regulated on activation,normal T-cell expressed and secreted)均属于β亚家族趋化性细胞因子,与炎症细胞的趋化和激活活性有关。Kadota[36]等对23例DPB患者BALF中的β亚家族趋化性细胞因子及其与T细胞亚群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 DPB患者BALF中CD3+ HLA-DR+细胞百分比、CD8+细胞百分比、CD8+HLA-DR+细胞的百分比及绝对数均较健康对照组升高(P<0.0001); CD4+/CD8+比率下降; CD3+HLA-DR+细胞的百分比在DPB患者组及健康对照组分别为51.1%和39.1%; CD8+细胞百分比在患者组及对照组分别为54.1%和36.0%,而CD8+HLA-DR+细胞的百分比在患者组及对照组分别为33.5%和12.9%; CD4+/ CD8+比率在患者组及对照组分别为0.5和1.0;此外,MIP-1α和RANTES在DPB患者BALF中较对照组也有明显升高(P<0.05),并且CD8+T细胞绝对数或百分比分别与MIP-1α均呈明显的相关性(r=0.439,P<0.005; r=0.565,P<0.0001),而MIP-1α、RANTES与其他淋巴细胞之间无明显相关性。以上结果提示,MIP-1α可能通过招募或活化CD8+T细胞从而在DPB的发病过程中起一定作用,因此,MIP-1α和活化的CD8+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细胞黏附分子(cell adhesion molecules,CAM)是众多介导细胞与细胞间、或细胞与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间相互接触和结合的分子的统称,参与细胞的识别、活化和信号传导,细胞的增殖与分化、伸展与移动,是免疫应答、炎症反应等一系列重要生理、病理过程的分子基础。根据其结构特点,黏附分子可分为整合素家族、选择素家族、免疫球蛋白超家族、钙黏蛋白家族,及一些尚未归类的黏附分子。其中选择素家族包括主要分布在白细胞的L-选择素、主要分布在血管内皮细胞的E-选择素、主要分布在血小板的P-选择素。
Mukae等[37]测定了27例DPB者血清中可溶性黏附分子的水平,结果显示DPB患者血清中sL-选择素(soluble L-selectin)、sE-选择素(soluble E-selectin)、sP-选择素(soluble P-selectin)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5),其中血清sE-选择素的水平与DPB患者BALF中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有明显的相关性(n = 37,r = 0.50,P<0.01)。此外,DPB患者BALF 中IL-8和IL-1β水平也较健康对照组升高,血清sL-选择素和BALF中IL-8之间、血清sE-选择素和BALF中IL-1β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后,血清中sL-选择素、sE-选择素、sP-选择素等黏附分子和BALF中IL-8、IL-1β均下降。以上研究提示肺脏中产生的细胞因子等可能调节上述黏附分子的产生和释放,进而推测这些黏附分子,尤其是sE-选择素促进中性粒细胞在DPB患者气道中的聚集和浸润。
CD44属于尚未归类的黏附分子,其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细胞,在T细胞中主要存在于记忆T细胞。CD44可与透明质酸(hexadecenoic acid,HA)结合,促使淋巴细胞到达炎症相关部位。Katoh[38]等对19例DPB患者BALF进行检测,发现DPB患者BALF中可溶性CD44(soluble CD44,sCD44)聚集较健康对照组明显下降[(8.7±1.3)ng/ml vs. (14.2±0.9)ng/ml,P<0.005],肺泡巨噬细胞结合HA的能力下降,非HA结合的肺泡巨噬细胞百分比较健康对照组升高(32.5%±7.2% vs. 0.4%±0.1%,P<0.005)。经大环内酯类药物治疗后,患者BALF中可溶CD44聚集较前明显恢复[(15.9±1.8)ng/ml,P<0.001],非HA结合的肺泡巨噬细胞百分比较前下降(7.0%±1.7%,P<0.05),CD44的表达和巨噬细胞结合HA的能力恢复正常。提示DPB患者中CD44表达异常可引起肺泡巨噬细胞功能不良,从而促进DPB的发病。
气道中黏液的分泌与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有关。既往体内及体外研究证明,活化中性粒细胞产生的TNF-α可影响细支气管上皮表面EGFR的表达,EGFR的活动可导致黏液的过度分泌及杯状细胞化生。J H Kim等[39]对13例DPB患者及6例正常对照者的组织样本进行了AB/PAS染色及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DPB患者样本中,中性粒细胞引起的炎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2),细支气管上皮杯状细胞化生也较正常组明显增多,EGFR的表达也仅见于DPB患者细支气管上皮。由此可见杯状细胞化生引起的黏液过度分泌和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及EGFR的表达有关。
四、鼻部低浓度NO
鼻部高浓度NO(nitric oxide)在呼吸系统的病理生理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包括呼吸道黏膜纤毛转运清除能力、宿主防御反应等。
Taira等[40]检测了DPB患者的NCT(nasal clearance time),结果显示与健康对照人群相比,DPB患者呼出气体中NO浓度降低(P<0.05),NCT延长(P<0.01),提示NO浓度降低与DPB的发病相关。Nakano等[41]应用化学荧光技术检测了8例DPB患者鼻腔NO含量,结果显示,DPB患者组鼻腔NO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的88%(P<0.001),正常对照组鼻腔NO含量为556±87nl/min,而DPB患者组鼻腔NO含量仅为(69±70)nl/min。DPB成为第三个已知鼻部低NO的疾病,另两个鼻部低NO的疾病分别为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综合征(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syndrome,PCD)和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CF)。提示鼻部NO浓度下降可能DPB的发病有关。
已知鼻腔NO主要来自于鼻窦和鼻黏膜。对于鼻腔低NO的原因有几种可能的解释:①一种认为鼻腔表皮的NO合成酶(NO synthase,NOS)活性降低,NO合成减少,促使慢性气道感染。DPB患者上、下呼吸道黏液纤毛转运系统形态损害及功能损害已被证实。此外,DPB与PCD、CF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后两者均为基因缺陷性疾病,DPB也已被证实与基因相关,推测DPB患者鼻腔低NO可能与基因异常有关。②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DPB患者多并发慢性鼻窦炎,鼻窦反复发生炎症可导致广泛的上皮损伤,进而降低鼻部NO的聚集。已有文献报道慢性鼻窦炎患者鼻腔NO含量低于正常对照组的23%~59%。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DPB患者鼻腔NO下降88%。③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长期的红霉素治疗抑制鼻部NO产生。动物实验研究表明红霉素能抑制肺部炎症和阻止NO合成[42]。然而,Nakano[41]等的研究显示,2周的红霉素治疗对正常组鼻部NO的聚集并无影响。因此,DPB患者鼻部NO减少的原因还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五、刺激性有害气体吸入与大气污染
强酸烟雾、氯气、溶媒性气体、化学药品和各种粉尘等易导致本病,如二氧化硫严重污染区域(其浓度>0.04ppm) DPB发病率较一般地区为高。但目前DPB发病与环境有害气体吸入的相关性尚无定论。
(陈娴秋 何荷 李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