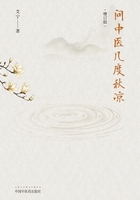
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母亲毕竟置身于科学时代,不可能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对中医,她按“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新中国中医方针,把她师傅传给她的东西按她能理解的和不能理解的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有一次,一个晚期癌症病人被她丈夫背到母亲这来了,母亲当然治不了,可这丈夫不肯接受妻子不治的现实,苦苦哀求母亲,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无奈,母亲给他开了一个古方,说是给病人吃老母猪肉。
这个男人从农村买来一头已丧失生育能力的老母猪,杀了给妻子吃肉。这女人十分想活,加之对母亲的迷信,就努力地吃。到了医生宣判的死期,她没死。一头猪吃完了,一个冬天过去了,女人的病竟好了!两口子来谢母亲时,母亲一脸茫然,她反复自言自语:“这糟粕不是糟粕?”
一位火车炉前工,由于生活不规律,得了很严重的胃病。由于带病坚持工作,吃药的效果也不好。母亲笑说,有一个“糟粕”方子治这病,说是备七口大缸,将稻草烧灰,填满大缸,用水浸泡,浸出物会有白色物质沉淀缸底,收集这七口大缸,可得一碗。将这一碗白色沉淀物服下,可治此病。
听了这个方子,我和鲁迅对中医的看法再一次统一,觉得中医有疗效的方子也是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方子中歪打正着地碰出来的。
有一次,这个炉前工在外地发病,疼得死去活来,遇到一个老太太将小苏打调和了一碗让他吃下,他吃惊于怎么可以服用这么大剂量的小苏打?但疼极了,老太太又一个劲地鼓动他,他就吃了,结果就不疼了。又吃了两次,竟全好了,再没犯过。母亲听了,就念念不忘老要泡七缸稻草灰看看那白色物质是什么东西。
我家的一个邻居是火车司机,刚40出头就得了很严重的哮喘。那时的火车司机总要探头看前面的信号灯,巨大的冷风灌得他根本受不了,只能在家休息。母亲给他治,告诉他要养,他这辈子不能再开火车了。有一次聊天时,说到中医的“吃啥补啥”,说人的肺功能弱可以用动物肺补,而在动物中肺功能强的非狗莫属,因为狗不出汗,狂奔后看它剧烈喘息就可知它的肺工作量很大。这个火车司机听了就与打狗队联系,要狗肺子吃。几十个狗肺子吃过之后,他重返工作岗位,又开上了火车,在冷风中一再探头,也没犯病。这令母亲十分惊异。母亲的惊异加深了我的印象。多年后,女儿的叔叔得了哮喘,一犯病得抢救,衣袋里装着激素,喘不上来气就得喷雾。我向狗肉馆要狗肺子,一天一只给他送,他就白水煮了吃。他病好了,我从未与他探讨过狗肺子到底起多大作用。
我想,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临床经验的丰富,她对“糟粕”的否定渐渐产生了动摇。我从母亲的学习过程中看到,人的学习也是分阶段的,不能从人的学习内容判断人的学习正确与否,决定学习效果的还有方式。年轻人学习时常轻易断言优劣、对错,造成学习上的留一半、扔一半现象,使学习走偏。上了年纪后,多观察少判断,结果从“愚昧”和“糟粕”中得到的启示往往要大于正统学术。由此可知,“愚昧”和“糟粕”不是没有价值,唯有上了年纪的人才能从中吸取营养,所以,对不理解的东西先行保全比彻底铲除要好。
有一个人找我母亲看病,他的病在西医做了全面检查,没查出问题。但他就是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的。母亲说他受了瘴气,不好治。我听了和病人一起感到奇怪,什么是瘴气,怎么是受了瘴气呢?母亲说,这个人去迁坟,开棺时他没躲开一下,让里面的瘴气散开后再捡遗骨,而是正冲着开棺的那股瘴气,他现在这种耷耷的、像摄了魂一般的症状,就是受了瘴气的原因。我和病人听了一起摇头,觉得这又是中医的一个谬论。
每当我埋头在旧书堆中时,母亲就把我拉到通风处、阳光下,说这些旧书有瘴气。这时,我就更认同父亲说中医是巫医的观点了。
最近看报道,说当初开启埃及法老墓穴的许多人受了病,曾被认为是遭到了法老诅咒。现经科学研究发现是墓穴中的一种特殊真菌对人的侵害。这使我不由得想到母亲的瘴气说。中医虽然不知瘴气中的真菌是什么,但知道瘴气能致病从而让人躲避,这是很重要的。
面对有人嘲笑中医是巫医,我现在不以为然。小时候我把母亲的许多认识或者当作人人皆知的常识,或者简单地归为中医的“糟粕”,有时直接斥为愚昧,所以根本没有在意。大半辈子活过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在中医之外并没有这种认识,母亲站在中医角度对精神的人和肉体的人的认识并不是落后的,有许多东西仍为当今科学解释不了。
我承认找巫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我一个同事得癌症从北京做手术回来对我说,癌症病人有三分之一真是被吓死的。我惋惜地想,如果这三分之一的人要是对癌症无知该有多好,要是有办法能消除这三分之一人的恐惧该有多好,哪怕是用中医或巫医的手段也行。如果真知的作用是把人吓死,那么在性命和真知之间,我看还是保命为上,绝大多数的人并不是爱真理超过生命的。而有的人天生具有自我保护机制。我一个朋友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昏死过去,把问题交给了我。另一个朋友对自己的重大错误失忆,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把错误那段全忘记。人的心理机制并不是让人无限制地承受严酷的真实,这虽有悖科学精神,却是大自然对人的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