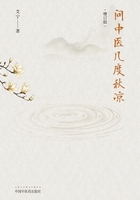
母亲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药味而难过。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即使是小时候,我也能看出母亲不适合在医院行医。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12岁时就给人做媒。一男一女分坐在我两边,拿逗我说着话。说着说着,两个人一起走了,把我扔下了。婚礼上,他们总说是自由恋爱,把我这个媒人给忘了。而后来,我把人家把我忘了视为做媒的最高境界。我父亲极力反对我和母亲“管闲事”,他说,做人有两大原则,一不保媒、二不荐医,保媒和荐医这两样都是落埋怨的事。但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一顿外,没有别的办法。她甚至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的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伙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肯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伙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她只好与这个男人结婚。婚后生活很艰难,再后来听说她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这些情况使我小时候不认可我母亲的诊所是医院,也觉得她做的许多事情不属于医学范围。便是在今天,这类情况在医院也很少见。
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处理问题。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世30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我在母亲诊所见到的好多现象西医并没有谈及,其解释并不比母亲解释的合理。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许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一般医院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有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当学徒工时,有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喊地。我们女工团结一致地同她丈夫作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却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里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经过几十年的琢磨,我也琢磨出其中的道理。我一个朋友患有不孕症,一辈子没生孩子。她与丈夫头半生相敬如宾,没红过脸。可到了更年期她却一反常态,对丈夫大打出手。她对我说:“我忍了一辈子,憋了一辈子,再装下去我就要疯了。”我遗憾地说:“你早打啊,早打把心中的垒块抚平还能生儿子,你打晚了。”所以,我也像我母亲一样,人家两口子打架我不轻易劝架。我曾做过妇联的权益部长,专管维护妇女权益。经常有妇女被打而来求助的,我总是详细了解情况,不轻易下判断,慎用法律武器。老百姓常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就是把清官的理性挡在了家门外。因为这里有很微妙的心理因素,有不为我们所知的东西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