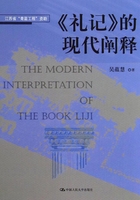
一、何为“礼”
《礼记》对礼有众多描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礼的内涵和功用。首先,礼是人类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人如果没有礼义,即使能说话,也只能算是禽兽之心性,因此,圣人制定礼法来教导人,使人有做人之规范,明确了自身和禽兽的本质区别,“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曲礼上》)。礼也是先代圣王用以顺承自然之道来治理人情的,丧失了礼就会灭亡,得到了礼方能生存,“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运》)。先代圣王顺应人情而拟定节制形式,用以隄防人民,使富有之人不至于骄纵,贫穷之人不至于困窘,尊贵之人不怨恨君上,以此使乱子日益减少以致消亡,即“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坊记》)。同时,礼又是用来防止人民淫纵、显明男女之别的,以此作为人民生活的纲纪,“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坊记》)。
对于国君而言,礼是其手中的权柄,用以区别嫌疑、辨明微隐、敬事鬼神、建立制度、分别仁义,进而治理国政、保君安位,所谓“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礼运》)。对于个人而言,礼是修身之器具,有礼而品行大备,品行大备即为盛德;礼能够消除邪恶,增益美质;礼措置于身,身就正;礼施用于事,事就通;礼于人身上如同竹箭之有丰润青皮,“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礼器》)。一言以蔽之,礼放之四海而皆准,“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曲礼上》)。
“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仲尼燕居》)而礼治的实行是由“亲亲”、“尊尊”推而广之、潜移默化的,从爱心出发事奉双亲,由亲情一级一级上推,从敬爱双亲到尊重祖先、敬重宗族、团结族人,再到尊奉宗庙、确保社稷,由亲亲而尊尊,进而为了确保社稷的威重而热爱百姓,自然而然做到刑罚公正,使民众安居乐业、财用充足、得以如愿以偿,从而形成良好的礼教风俗和和乐的社会氛围,即“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大传》)。统治者由敬重自身推及百姓之身,由敬重自己的儿子推及百姓的儿子,由敬重自己的配偶推及百姓的配偶,由这三敬教化进而推广到天下,如此则整个国家就和顺无疑了,即“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哀公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