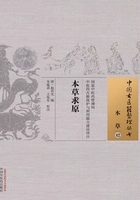
序
不晓症脉,不知病原;知病原,而不知物性,亦不知病之何以治。即知某药治某病,而不知其所以治,则用古人方,仅守古人之法,仍不知古人制方之意。 《神农本经》一书,从五形、五色、五臭、五气、五味,及生长收藏之时令,推测而得其所以治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故。故同治一症,而或从或逆,或反或正,各有其原。汉长沙 《伤寒》《金匮》诸方,悉从 《本经》精义而出,故一加减,而治症各异,效如桴鼓。自梁陶宏景作 《别录》,增 《本经》而倍之,其言气、言味与 《本经》多有异同。后之集本草者,遂不讲 《本经》,徒增药品,止录其当然,而不推求其所以然。其他 [1]者固无论矣。即李濒湖之《纲目》,亦徒多杂浅说,矜其博洽。虽以 《本经》冠众说之首,而其义蕴毫无发挥,是等之存羊[2]而已。汪讱庵之 《备要》,从《纲目》出,间出己见,亦有好处,而背经旨者亦复不少。惟前明仲淳缪子所著 《本草经疏》,颇能开凿经义,而拘泥尚多。刘潜江[3]又旁及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说,而汇以己意,为药四百九十种,其精深微妙,能发前人所未发。但词重意复,洋洋乎八万言,世之苟且图利以求捷径者,莫不厌其繁而置之高阁。至我朝名医,如徐灵胎、叶天士、陈修园等,皆仿张隐庵之法,句疏字解,而发挥其所以主治之故,其于《本经》一书,各有探本穷原之妙,修园尤参契于 《灵》 《素》《难经》,与仲景之书而详说之,彼四子者,真神农之功臣也。但各于 《本经》摘释,而各有未全,且于诸家治验,概置不录,则中人以下,犹恐其重视而畏远之。予乃采杂众说,从长弃短,而伸以己见。其间有各家主治难明之处,亦引 《内经》及长沙方法与名医方论,贯通而曲畅之。其诸家治验,有足与经义相发明,或为经旨所未及者,均系焉。又于 《本经》三百六十五品外,为世俗所常用,与食物生草便于采取,而确有专长殊效者,悉备列焉,以便查阅。计药九百余种,良方、单方不啻数万,较 《纲目》似约,而切于时用,大有加焉。至 《纲目》所载,为不常用,与乎不易得者,概删不录。稿凡几易,七越冬夏,而书始成,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而古人立方治病之义,凡所为顺逆反激,与乎升降互用、滑涩互用、寒热互用、补泻互用之法,灼然可据。而后杂病杂治,方可自制,庶不致专事坦夷,徒守不寒不热数十种,开口动言稳当,以为逢迎富贵之捷径,而为浅陋之庸医也。虽不敢自谓毫无遗义,而较于世之传书,颇为明备,号曰 《本草求原》,非夸也,道其实也。所以明刘、徐、叶、陈四家之注,一皆疏解 《本经》主治之原。予则求原于四家,为之增其类、补其义,以无失古圣前贤先后同揆之原,非敢专执一人之说以鸣高也,故又名之曰《增补四家本草原义》。古有云:“群言淆乱,当折衷于圣。”此则予之志也,四家先得我心也。岁在戊申孟秋,旸谷陈兄见此书于外海纫兰之馆,喜其详明且备,谓使人人得而阅之,亦足为日用养生之一助,因慨然助赀而付于梨梓。但古今土产各殊,如牛黄、首乌等,已非前时所产,气味不同,功效亦别,欲详考其实,而耳目所及无多,犹俟高明正之。倘有时下新出之品,果见殊能,堪采治者,亦望识者增予之所不逮焉。
[1]者固无论矣。即李濒湖之《纲目》,亦徒多杂浅说,矜其博洽。虽以 《本经》冠众说之首,而其义蕴毫无发挥,是等之存羊[2]而已。汪讱庵之 《备要》,从《纲目》出,间出己见,亦有好处,而背经旨者亦复不少。惟前明仲淳缪子所著 《本草经疏》,颇能开凿经义,而拘泥尚多。刘潜江[3]又旁及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诸说,而汇以己意,为药四百九十种,其精深微妙,能发前人所未发。但词重意复,洋洋乎八万言,世之苟且图利以求捷径者,莫不厌其繁而置之高阁。至我朝名医,如徐灵胎、叶天士、陈修园等,皆仿张隐庵之法,句疏字解,而发挥其所以主治之故,其于《本经》一书,各有探本穷原之妙,修园尤参契于 《灵》 《素》《难经》,与仲景之书而详说之,彼四子者,真神农之功臣也。但各于 《本经》摘释,而各有未全,且于诸家治验,概置不录,则中人以下,犹恐其重视而畏远之。予乃采杂众说,从长弃短,而伸以己见。其间有各家主治难明之处,亦引 《内经》及长沙方法与名医方论,贯通而曲畅之。其诸家治验,有足与经义相发明,或为经旨所未及者,均系焉。又于 《本经》三百六十五品外,为世俗所常用,与食物生草便于采取,而确有专长殊效者,悉备列焉,以便查阅。计药九百余种,良方、单方不啻数万,较 《纲目》似约,而切于时用,大有加焉。至 《纲目》所载,为不常用,与乎不易得者,概删不录。稿凡几易,七越冬夏,而书始成,使读者深识其所以然,因此悟彼,而古人立方治病之义,凡所为顺逆反激,与乎升降互用、滑涩互用、寒热互用、补泻互用之法,灼然可据。而后杂病杂治,方可自制,庶不致专事坦夷,徒守不寒不热数十种,开口动言稳当,以为逢迎富贵之捷径,而为浅陋之庸医也。虽不敢自谓毫无遗义,而较于世之传书,颇为明备,号曰 《本草求原》,非夸也,道其实也。所以明刘、徐、叶、陈四家之注,一皆疏解 《本经》主治之原。予则求原于四家,为之增其类、补其义,以无失古圣前贤先后同揆之原,非敢专执一人之说以鸣高也,故又名之曰《增补四家本草原义》。古有云:“群言淆乱,当折衷于圣。”此则予之志也,四家先得我心也。岁在戊申孟秋,旸谷陈兄见此书于外海纫兰之馆,喜其详明且备,谓使人人得而阅之,亦足为日用养生之一助,因慨然助赀而付于梨梓。但古今土产各殊,如牛黄、首乌等,已非前时所产,气味不同,功效亦别,欲详考其实,而耳目所及无多,犹俟高明正之。倘有时下新出之品,果见殊能,堪采治者,亦望识者增予之所不逮焉。
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季秋冈州寅谷氏赵其光自题于养和堂
[1] (suǒ索)
(suǒ索) :象声词,状贝类摩擦声。引申为细碎。《六书正讹》借为
:象声词,状贝类摩擦声。引申为细碎。《六书正讹》借为 屑字,即琐碎之意。
屑字,即琐碎之意。
[2]等之存羊:没改变,维系原样。
[3]刘潜江:即刘若金,潜江人,故称刘潜江。著 《本草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