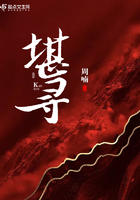
第44章 偷听鸟悄悄
昭枣例行公事地睡了几个小时,也是千奇百怪一大堆梦,却在醒来后什么都没记住。
她睡着了,小翠蛇就堆在她耳边的空地上,她醒了坐起来,小翠蛇就爬到她肩头,这蛇似乎特别喜欢离她的耳朵很近。
与往日一样,世间一切由黑直接硬切到阳光明媚。
天亮了,她迫不及待地去观察那些扶桑花朵:果然没令她失望,所有花朵一夜过后颜色都褪成了深深浅浅的透明。逆光下,花瓣的经络布局各异,成为证明这花朵确有的唯一存在。
她相信这还不算完,也就意味着时机尚未成熟,因为透明本是无色,还达不到“色与色归一”。
她眼睛都不眨一下,紧盯着那些花朵,生怕错过什么。可是只有在不停地变换观察的方位时,才能发觉这些花瓣颜色又渐渐加重了。
没有太阳就无法分辨时辰。在昭枣的感知里那应该是在午后某一个很特别的时刻……
因为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感觉到天气转凉了,也就在那一刻她看到了本以为盯着看反而会发现不了的一幕——所有扶桑花同时变成了金色!
那只是霎那的事情,所有的花无一例外同时达到了透明的巅峰,也就在达到极致的那一瞬间过渡到晃眼的纯金色,这个过程不过弹指,可是她没有错过,连眨眼都没有过!
如此良辰,纵然再也出不去又何妨!
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突然想到寸言哥哥。这样的人生际遇,日后自己恐怕没有那样的语言天赋去恰如其分地讲给他听。
一时间她忘了自己是要来干什么的,在这满目的金色里晃神很久,直到一束刺眼的光芒乍然出现,让她不得不回到现实。
天呐,万万没想到竟然是太阳光……
那束并非来源于天空正中的光线,刚直射在第一波金色花瓣上,立马就被挡住变成很多束,随即通通反射回对面树林里的金色花瓣上。
同样的方式,那些光线刚到达,就又变成更多束或宽或细的光,从不同角度再折返到不同方向的花瓣。
昭枣的眼睛飞速跟着这些光的轨迹在不同的方位间穿梭……就在光线借助金色花瓣充斥满整个林子的那一瞬,所有花瓣上的光都猛然抽离出一束同时直指同一个地方:那块卵形大石。
电光火石的一眼,那明晃晃的光芒险些让她失明,她本能地举袖遮住并使劲闭上眼。
若是她能敌过本能,那么她会选择死扛,因为什么她都不想错过。可就在刚紧闭上的那一瞬,眼睛周围一阵火辣辣的灼痛让她心底很快明白自己的眼睛被灼伤了。
庆幸本能快过思考!
顾不了痛,也只是那么一闭过后,她立马张开眼睛,眼前早已是另一番乾坤——
还是那大石头的形状,只不过已不再完全是原来的那个。她以为眼前会是光芒万丈,不想里面竟是一个不知深浅的墨蓝色世界。
一眼看到的就是:墨蓝色的波光摇曳里,一艘篷船在上面微微摇晃着,橘黄色的船灯光铺在粼粼的波光里。船灯旁坐着一个被黑色斗篷捂得严严实实的背影,看上去有些垂头丧气。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昭枣不敢贸然行动,哪怕只是动一动身体,更别说往前走,她深深探着腰用无比温婉的声音问道。
那背影并未作任何回答,过了良久才轻轻抬手,离昭枣最近的船尾立马出现一道旗帜,上面写着“犀渡”。
“哦,原来是条渡船啊,那请问船要开向哪里?”
昭枣以问完话后的姿势等待着,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回答,那个背影依旧是静默的背影。
她很是好奇,里面的世界好像是在深夜,单调到神秘,神秘到让人心里不安。
这时她才想起来回头看看身后的世界。
当你的眼前是黑夜,你可曾想过你的身后一片阳光灿烂,恐怕这很难想象!所以当昭枣回头的那一瞬间,她自己也被吓得不轻。
明明就是同一处,却如同以自己所在的面为分界线,被隔成了两个没有瓜葛的世界。
身后还是那片充满阳光的扶桑林,还是金色的花瓣,还是阳光裹挟在每一片树叶每一瓣花里。
那些光线也往这个方向照过来,可是却如同照不过来或如同被吞了那样,无法驱使黑暗照亮前方。
昭枣甚至留意到就以自己肩膀的中线为界,她整个人一半在阳光下一半在阴影里。
试着往后退一步,她便沐浴在暖烘烘的阳光里,就连肩头的翠蛇都欢愉起来。往前一步,她便身处黑暗之中,肩头的翠蛇连忙缩成更小的一团。
“你如果不走,我就要走了。”那个背影冷不丁地发出声响,昭枣被吓得心都骤停了一会儿。
好熟悉的声音,可是又不确定是不是听过。不敢花时间去思虑更多,她怕对方是个急性子,又怕显得失礼,所以赶紧问道:“可是这船去哪的?”
“你不知道去哪里的话为什么还来?”
“我……”这话真把昭枣给问住了,她知道再问也得不到更明确的信息,于是看向肩头的翠蛇。
这次她没有嘲笑自己竟然去找条蛇要主意,相反她渴望得到一个答案。或许她自己都不知道她只是需要一个声音来说出她心中那一早就有的想法。
这次翠蛇没有给她任何提示,而她终究是踏上了那条名叫“犀渡”的船。
那背影在船头始终没有回头,她在船尾一直注视。
“姑娘,想好了吗?这可是一条单向的船,回头万事休,所以才需要你三思其行!”在上船的时候,那个背影说道,可是没有谁比昭枣更明白自己的这点执拗了。
这是一条黑水河,黑暗中看不尽它的边缘。纵然那个背影也在摇着船桨,可是没有一丝水流声。
一片漆黑,所以无法找到可以参照的东西,她并不知道船走得快不快。
昭枣只知道在上船的那一刻,她回头时身后就已经没了那片扶桑林,取而代之的是如同前方那样无尽的漆黑和墨蓝。
说实话,尽管见过了太多的黑暗,可是这一路她内心的恐惧还是需要努力去压制的,那是一种对未知无法预测、能否应对的不自信。
似乎没有走多久前方就隐约有淡淡的荧光传来,那背影依旧很是淡定地划着船桨,似乎没看见那样。
一路上昭枣已经试过:不论你问他什么他都不会理睬,所以不如省点力气。
随着船渐渐逼近,一大团大红色也在那片荧光里显得格外耀眼。昭枣使劲睁大了眼睛意图去判断那究竟是何物,可是凭她有限的经历,实在是难做进一步的联想。
已经到那红色跟前,昭枣结合远处和近距离所看到的,这才在脑中拼成一个形象:这是一个巨大的树洞,大到光是树上的洞就把这片黑水河上的航道给截住了。
每一块都比自己还大的快掉落的树皮一半还贴在树干上,一半翘得如同岩石。
在远处所看到的这个黑幕里的影影绰绰十有八九就是这个树的树冠。黑暗中也无法判断这是什么树。
直到船头已经贴紧了树干,昭枣还是不知道树洞里那填充满了的大红色究竟是什么。
站在船中央,她试着用战刀刀背轻轻去戳——软软的,但也没戳出个所以然来。
她不禁使上了更大的力气,这次才刚一用力,那红色就往里缩了一下,紧接着整个身子在里面挪了又挪,竟换了一侧来对着树洞口。
那红色的东西转过来一动不动半天,正当昭枣以为它仅仅只是转个身时,它竟显得很急躁地在里面转得哗哗啦啦起来,费了很大劲儿才转过正面来。
原来是只鸟,一只红色巨大的鸟!
如此硕大的体形虽着实让昭枣觉得惊讶,但看它沉重的眼皮撑了半天才张开又爱搭不理地眯下去看了昭枣一眼,似乎毫不意外那样,昭枣的警惕性放松下来。
“真是烦,你说你要挠就多挠一会儿,就那么戳两下,现在反是搞得我全身都痒!”那鸟身子在里面蹭得“呱咂”直响。
“你你你,你怎么会说话?”昭枣惊得舌头都打结了。
“废话,作为一只偷听鸟,不多学几种语言,我怎么偷听!”
“啊……?”
借助船灯光,昭枣上下仔细打量这鸟:它虽是正面转过来了,但是整个儿依然被困在恰好能装住它身体的树洞里,根本不可能出来。但是这一望无际的大树挡住了前方的道路,船该往哪里去?
“那请问偷听鸟,我怎样才能过去?”
“谁叫偷听鸟啦,会不会说话?”那鸟真是易怒,这么简单的话就把它点着了。
它那长长的喙噼里啪啦上下拍打着吐出这些字儿,要不是被树洞禁锢着,它恐怕要一步跳到昭枣面前,啄着她的鼻子让她把刚刚这句话原封不动吃回去。
“呃,呵呵,抱歉啊!可,可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偷听鸟的吗?”昭枣和小翠蛇同时被吓得脖子都往身体里收回去一截。
“我是偷听鸟可我叫偷听鸟吗?啊!”这鸟不讲话则已,一讲话实在像破铜烂铁摔打在一块的声音,聒噪得紧。
“呵呵,呵呵,呵……那敢问这位矜持又稳重的鸟,你叫什么名字啊?”昭枣迅速摸准它的脾性,换了一种询问方式。
这句话果然很受用,那鸟的语气缓和下来,虽然调子依旧尖锐又刺耳,但显然它脾气好了很多。
“我叫悄悄!”
“哦,呵呵呵,悄悄啊,这名字果然很合您的气质!”昭枣违心地说完红着脸看了一眼小翠蛇,小翠蛇吐到一半的信就那样悬着,满眼的鄙视,看得昭枣悻悻地回正头。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说的都是假话,可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千年万年都在这个树洞里和它一起成长,在里面听到一件又一件的八卦、秘密、真话、假话、好听的、伤人的,最重要的是那些很想跟别人一吐为快的、或想去通风报信的话,却找不到人来说,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胖到对不起‘悄悄’这个两个字了!”
呃……这什么逻辑,“悄悄”二字和胖有交集么,胖和偷听多了有因果关系吗?昭枣觉得自己理不清。
“可是,悄悄,你既然那么苦恼偷听给你造成的困扰,为什么不试试不偷听呢?”
“什么!”它真的很易怒,而且讲话都是用吼的,一吼就地动山摇:“我是偷听鸟,这世上只有这一只,就像你肩上的那条绿蛟世上也只有一条那样,不偷听我会饿死的!”
“等等。”昭枣不在乎它那难听的声音了,撇了一眼翠蛇,问道:“你是说它是绿蛟,它分明就是绿蛇嘛,哈哈哈!”
“你到底会不会听重点?”那鸟的声音又大了好多倍:“我是告诉你我要靠偷听才能活着,那是我的食物,食物,懂不懂?”那鸟咆哮着,脸使劲往外挤着,不过这下它好像挤出来一些了。
“你,你……”
“没错,只要有人类听到一个我知道的事,我就会瘦点,你总算是把脑子带上了。”那鸟愤愤的,很是不爽又不耐烦,就像跟昭枣讲话它很跌档次那样。
昭枣思忖着悄悄的话,突然满脸堆笑:“既然说出你偷听到的事就能瘦,那我可以帮你呀!”
“狡猾的人类!”
悄悄歪扛着脖子满眼鄙夷,但又扛不住这个建议的诱惑。
因为这样肥胖的身躯刚好能挤在刚好合身的树洞里,着实不舒服,所以它的傲娇也只是意思一下,随后眼珠往下翻示意昭枣可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