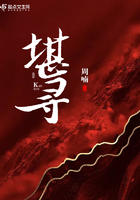
第36章 忆忧烟波之偷核桃
毛毛雨还真是不容小觑的,这一天一夜下来,到处湿漉漉的不说,就连气温也降了不少。
“七姊妹的事情已经了结,我们几个是不是要各回各家了呀?”卷堆往火炉边又挪了两下屁股把手伸到边上烘烤着,一只胳膊肘拐碰着正在翻阅一长卷书简的寸言。
“恐怕是的。”寸言并未抬头。
“那你本来打算去哪里的?”
“都可以。”
“你们呢?”光是烤火还不够,卷堆干脆把两只手放在旁边暖和得正昏昏欲睡的更云腿上手掌手背翻来覆去地捂着。
更云眯着眼把腿往自己方向收了一些,但卷堆的手像黏上了一般跟着挪过去,屁股也同样跟着挪。
“问你呢,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我听飘飘的。”更云翻了个身背对着卷堆,手肘撑在软席上,一手拄着头很快进入半睡状态。
“说到飘飘,她还没有出来?”
寸言听到这里,不由得集中所有的注意力,虽然眼睛还在书上,但脑子里也是很想知道眼前这两人对话的下文。
“是呀。昨天从陵园回来后直接进了自己屋就再也没出来过,连饭都戒了。哼,看来那个茱萸的死对她来讲影响很大。苏桂也留信说回家去了,连个打探消息的人都没有。”
烦躁又气愤的更云!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把他惹毛,卷堆识趣地撤回在他腿上摩擦取暖的手。
寸言一言不发低着眉眼又看了几排字,然后整整齐齐地把书简捆好,放在身边的矮几上,果断起身朝屋外走去。
“去哪儿呀?”卷堆扯着嗓子叫唤,然并无应答。
叶轻飘的屋子房门紧闭,门口那只小老虎紧贴着门槛缩成一团在微风中瑟瑟发抖,但不管怎么缩还是有些雨丝被风送到它身上。桑榆人民要是看到他们传说了几千年的神秘‘拥钓’现在被如此这般怠慢,恐怕会有一万个人跳出来不答应叶轻飘把它带走吧!
听见有响动,那小家伙埋在两腿之间头上的那两只小耳朵先抖了一下,然后抬头“咻”地朝着有声响的方位警觉地望去,眼睛精明又凶狠。
见是寸言,小老虎眼皮立马又慢慢垂下去一些,全身肌肉也放松下来,那些绒毛又在风中抖动着。
“……嗯……啊……”这真的还是一只奶老虎。
寸言双手搂起它,软绵绵的身体很是暖和。他把它放在一只手中,另一只手从袖中掏出一方手帕轻轻揩拭着它被毛雨打湿的地方。
“叶轻飘。”寸言把老虎抱在怀里,轻轻扣着门环,里面没有应答。
“谈谈吧。”
寸言等了一会儿,既没有应答也没有人开门。
“我数三声的时间给你准备一下,例如穿个衣服,擦个鼻涕眼泪什么的!”寸言这样的哄人方式真让人觉得生硬。
三声过后,寸言缓缓推门进去,在推门这个过程中随着视野的变化他把屋子里打探了一周——叶轻飘并不在房间里。
一颗心“咚”地往下掉了一截,走到屋子正中才看到门正对面的屏风处一截衣角露在外面,寸言这才缓了口气。
这屋的那头算是个檐廊,有门有窗,只不过平时都是用屏风隔开方便采光。叶轻飘整个人抱腿窝在竹椅中,眼光盯着走进来的寸言然后锁住他直到他在桌子的对面坐下。
雨丝从檐外斜飞进来,偶尔也会有那么三两滴拍打在脸上,让人愈加灵台清明。
坐定后,寸言扭头从栏杆外看出去:青瓦飞檐、木梁铜铃,风景倒是独好,繁华到喧嚣的桑榆竟也有如此斜风细雨的宁静时光!
跟想象的不一样,以为她至少是埋头不想见人,但是她却一直盯着他看,他已经坐下了还是依然紧盯着,整个人有一种少见的成熟。
本来是设定好了进来后自己对其察言观色的,这反转就反转吧,关键在于叶轻飘盯着自己看的时间太长了。这,哪有姑娘家这样毫不避讳一直盯着一个男人看的!
寸言以为凭自己对凡事的一贯漠然和淡定,掌控全局毫无悬念,于是心里略作思量收回目光也不言语笃定地接住她的眼神,但一种尴尬的感觉在胸中轰然膨胀又说不上来为何尴尬,所以很快败下阵来,目光不由得转向别处。
内心从未有过的慌乱,又不由得想要去对抗。再看她时,她已经低头去逗他怀中的小老虎。
白皙的脸庞,扑簌着的睫毛,侧影下挺拔的鼻梁以及微翘有些调皮的嘴唇。第一次目光如此长时间地停留在一个女孩子脸上,这种感觉很是微妙。
内心的波澜无法平静下来,他甚至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一颗心在使劲蹦跳。不是宠溺可就是有一种魔力让他想要好好看她,哪怕看到的就是这样口眼鼻唇零散的感官反馈。
他突然发现自己没有把她当成是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小姑娘,而是一直放在和自己一样的高度,而且很近,要不然也不会急匆匆赶过来。
掣荡不缺好看的姑娘,到了桑榆更是,可是“女孩子”这个词却第一次让他在心尖上有了明明白白的强调,毋庸置疑,她在自己眼中很特别。
“呸,寸言,你在干什么?”这样有失分寸让寸言一时间陷入恐慌,他在心里使劲啐了自己一口。
他为自己有这样龌蹉的想法而感到手足无措,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坦荡的人,可是这一刻……“不,不,她只是一个小姑娘,寸言,这是一个人生最美好无忧的年龄,你只是欣赏罢了!”寸言这样小心翼翼按捺住自己躁动的心,可是他突然间又想起昭枣,只比叶轻飘大一岁,可是怎么就没对她这样想过……
刚刚找到的还能凑合的理由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攻破,寸言的一颗心跳跃摇摆得毫无节奏感,额头上不由得急出了汗珠。
“你,怎么了?”
寸言回过神来,眼前叶轻飘一双纯净清澈的大眼。
“哦……”寸言抖抖衣袖,眼光闪烁了好几下:“你还好吗?”
叶轻飘咬住嘴唇低下眉眼轻轻摇头。
“是因为茱萸?”这话一出,寸言对自己真的感到失望,明明知道这不是主要原因,可还是脱口就出。
“不仅仅。”叶轻飘眉头紧蹙:“我想不通为什么死去那么多人,都是围绕她,她却一点都不动容,还有为什么她要用落瑛刺杀死凤尾,还有‘宿掩’,他们真的非死不可吗?”
“你是因为对唤蘅失望才有这样的想法?”一说到正事就变回心无旁骛的样子,寸言感到很放心。一辈子内心恐怕也再不会像刚才那样拧巴和纠结,这让从小就只有一种感情模式的他很是惶恐。
“在我长大的地方,篱酿带领大家生活得很艰难,省吃俭用,甚至常年隐匿在暗无天日的地方,只为大家可以好好的活着。从我记事开始,她和六四就一直很珍惜每一个人活着的时光,珍惜到哪怕有人生病她都会变得焦虑,害怕生病也会夺去人的性命。我一直笑话她肯定是过去遭遇过什么不测才会如此战战兢兢,可是直到在桑榆的陵园我才发现原来生命要失去真的可以如此简单。我很难过,明明他们都不用如此的……明明那些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我盼望的都不是只见这一次的……”叶轻飘说着,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眨眼时又被挂在眼皮之间,朦胧了双眼。
“你的问题或许我也无法乐观地来看待,只是有一件事或许你知道后会好过些。”寸言温暖的眼神看着叶轻飘。
她用左右手的食指交换着擦拭着眼泪,一瞬间那个小姑娘的模样又回来了。寸言心里更加踏实了,他在心底反复对自己强调:“没事,她只是和昭枣一样的小姑娘。”
“我听常集说了里面的情况。凤尾的死其实是个意外。落瑛刺是个钝器,且是木制的。它除了可以破‘顾盼流连’和伤到幻蝶外,无非就是材料很罕见炼制工序很复杂而已。我想事情的真相是唤蘅见母亲的秘密就要被发现,情急之下抛出了落瑛刺,那个落瑛刺即便穿过‘顾盼流连’砸到茱萸也最多是砸痛,唤蘅朝着茱萸的方向抛出,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多争取一点时间,但是她没有想到凤尾会去挡而且挡住了。”
“真的吗?”叶轻飘问这话时早已泪眼婆娑。
“其实你心里早已有数,只是需要另一个声音给你些肯定。以唤蘅的实力要杀凤尾机会很多,我想她早多次斟酌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即使不是落瑛刺,恐怕结局也不会美好。唤蘅她要捍卫桑榆,那么茱萸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该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况且你知道的,有一种不伤和气的方法是‘直说’,可是茱萸把事情搞复杂了。”
叶轻飘刚刚高兴一点,可马上又沮丧地垂下头。
“飘飘,其实唤蘅也有很多无奈。你说错了,这些人的死不是因为她,事实上她也是父辈的受害者。何况这些人的死,她要从心底里承受更多,桑榆的制度很多很森严,所以它能够被治理得很好,桑榆人民才能够有尊严地、从容地活着,从这点来说是值得的,你觉得呢?”
此刻的叶轻飘憋了很久的眼泪已成小溪顺流而下。寸言给她推过去一杯茶:“我根本不相信这些你没有想到,你只是不愿意去承认唤蘅的无奈,因为那意味着有一天你也必须去学会承受和权衡,而且不会有人理解这其中的残忍。”
叶轻飘使劲擤了一下鼻子,透过泪花看向正在奶声奶气哼叫着的小老虎:“给我的老虎取个名字吧!”
说收就收,让人一点防备都没有,寸言不禁莞尔。那小老虎刚被放在桌上,就自己爬到叶轻飘怀里去了。
“叫干净吧!”寸言知道她不是在征询意见,因为她本来就很有主见。果然她刚问完就立马自己回答。
“你嫌它脏啊?”
“不是,我希望我们的相处永远干净透明,没有杂质,没有试探和拐弯抹角。”
一种甜蜜悄然蒙上寸言的心头,只不过他没有发现而已。
“去吃好吃的吧。”尽管她已经试图把干净放在肚皮来挡一挡,但肚子里“叽里呱啦”的翻滚声穿透力还是太强。
这个声音乍一上来还是让寸言愣住了,因为防不胜防,而且,真的是很大声。然后接下来的反应是避免尴尬最好装不知道,不过所有的表现都太生硬。呃,与人相处从不像今天这样的别扭过,却又很回味这种别扭!
“嗯,好。”寸言真想侧过身去擦擦额头的汗珠。
“你给钱!”
“没问题。”
“叫上大家吧,热闹些。”
“好。”
两人前院后院找遍了都没有见其他两个人,诺大的宅子一片空寂,还真不免让人有些后背发麻。
“哎哎哎,又打下一个来了。”
“哪呢,哪呢?”
“草丛里,哎呀,笨死了!”
“草丛里你捡啊,那么深的草。”
两人正纳闷这恍若做梦的空院子时,后院围墙外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但听得出这是卷堆和更云的声音,而且好像是在干什么坏事。
叶轻飘给寸言递了个眼色,她以为很好懂,递完就蹑手蹑脚地顺着墙根角找到那两个声音的所在开始翻围墙。几番狗撒尿的姿势下来,拿那个墙壁真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任何可以踩或是攀的地方。
苦苦思索一番,叶轻飘以为自己机灵地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于是示意还站在原地的寸言过来蹲下驮她起来。
好容易才看懂她张牙舞爪的手势,寸言真是被她的想法所深深折服,苦笑着摇头轻撩衣服一提脚步便上了围墙,半点声响都没有发出,往围墙外一望,一脸的不可思议。
叶轻飘幡然领悟,一拍脑门,一字步一脚蹬在墙壁上如蜻蜓般落于围墙上。
吁,围墙的那头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
一墙之隔的外面是一农家的开放式院落,在与这个院子交界的地方有两棵核桃树,核桃结得并不多但是看上去个大皮薄。微雨里,一个个核桃一张张树叶都被一片湿润包裹,绿绿葱葱,一派生机。
大树下,更云提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竹竿正朝着那些够得到的个大的核桃一阵拍打,不远不近跟着他的是手提小水桶在草丛中一阵扒找的卷堆。更云每拍打几次核桃,树上就会噼里啪啦掉下一阵大的雨点,可他似乎浑然不觉。
好一对偷核桃的贼!
叶轻飘和寸言成排蹲在墙头,起初还只是想看个笑话,但看着看着,两双眼睛也开始满树地寻觅着那些大核桃,这一寻觅就开始忘我,就不再安安静静的,直到墙下两人目瞪口呆看着不知啥时候冒出来的两个比他们还上心的人。
“喂,我说你们俩是怎么知道这里有这个的?”发现被发现了,叶轻飘压着声音问道。
卷堆一头一脸的雨水,竖着指头往上指。
“哦,原来……”顺着他指的方向,叶轻飘和寸言看到他们刚刚休息的敞厅,从那里探个腰往下就可以看到这满树的硕果,也不知这两人是谁这么无聊先发现的。
“那你们为什么不到树上去摘,这么打很费力呀?”叶轻飘手作喇叭状。
“你蠢呀,人家都说打核桃,哪有说摘核桃的!”更云无限鄙视墙上那两人的没有常识。
是这样吗?叶轻飘挠着后脑勺向寸言求助。
“我也不知道,我家那里不种这个。”寸言也是觉得新鲜又好奇。
“那打下来和摘下来有什么区别?”叶轻飘又问道。
“啰嗦,被人发现……”
“啊,更云救我……”
“嘎儿嘎儿嘎……”
“啊,起开……”
“啊,我的小腿肚包……”
毫无预兆,围墙下面的混乱几乎始于突然间的大喊大叫,更云和卷堆嚎得都破音了,到处乱蹬乱跳不说,还有一群白色的东西在扑打着翅膀追着两人到处连飞带跑。
再仔细看,是不知哪里悄无声息钻出来的一群鹅,十来只的样子,一个个扑棱着雪白的翅膀对两人进行围追堵截。还有几只那橙色坚硬的嘴壳还叼在更云和卷堆的腿上,只见他俩以各种方式挣脱、甩开,不仅不管用,还撩拨起了其他鹅的兴致,一个个扇着翅膀跳起来往他们的屁股、腰上叮。
下面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上面干着急的两人也没折。
鸡飞狗跳间,一根细长的竹棍伸过来轻轻赶着这些鹅。墙上的两人先冷静下来,只见一挽着高低裤腿,脸上褶子深长的老者嘴里边唤边往回赶着鹅,很快那些在后面追的鹅就都回去了,可那些还紧紧咬住腿的鹅怎么也不愿意撒嘴。两人使劲甩着腿,可越使劲那些鹅叼得越卖命。
“抓住它的脖子。”老者声音洪亮吐字很快。
果然,手一把握住那些鹅的脖子,它们就松开了,老者这才用细竹棍作出赶的样子,它们立马“咕咕”叫唤着乖乖往家的方向伸缩着脖子一路摇摆着回去。
“你们俩回去换了衣服再来,要快。”老者用赶鹅的竹棍指着更云和卷堆。
“哦。”
“你们俩下来,跟我走。”
“哦。”
“哈哈哈……吓坏了吧?”寸言和叶轻飘都小心翼翼地跟在老者后面,直到听见一阵爽朗的笑声,两人才从老者背后闪出。
房舍的正门之外还套着两扇矮门,估计是用来挡挡外面的小动物,冬天用来遮遮寒气同时又不影响采光。笑声就是从扶着矮门立在门口的老妪那里传来的,小个子、慈眉善目,穿戴简单但浆洗得很是干净。
“老妈妈,我们……”做贼心虚,现在连想跟老人亲热些都怕被当成是在套近乎。
“不碍事儿,我们牙口都不行了,每年也等着核桃仔掉落下来,捡去给别人家的孩子吃。”老妇人拉住叶轻飘的手把她带进了屋,家里最吸引人眼的恐怕就是那几个用稻草新打的草墩,上面还用鲜艳的布料做了套子,成了这个家里最醒目的家什。
寸言和叶轻飘刚坐下,老妪就为他俩一人冲泡了一碗糖水,干净的土碗边氤氲着甜蜜的白气。正好叶轻飘饿了,一口气就把那碗糖水干完,又伸长眼珠子看着寸言的。
“啪。”进屋后就消失了一阵的老者从里间出来把一个竹簸箕扔在两人面前。
“哇!”看着簸箕里的,糖水什么的瞬间丧失了吸引力。
叶轻飘从草墩上滑蹲到地上捧起一大捧核桃嬉皮笑脸地仰头看向老者,他已一声不吭又回了里间。
“这样。”老妪勾腰到簸箕上方捡起一个已经褪去苦皮的核桃碰碰叶轻飘的手示意她看自己。
老妪一手拿核桃一手拿锤两下就把一个核桃壳砸裂,然后放在手心里碾捏几下再摊开掌心,核桃仁就已经被剥出来了。
叶轻飘吃着核桃,但还是对老妪的熟练钦佩不已。在寸言以前住的地方并不产核桃,更觉奇妙。
老人示范过后,两人就陷入了各种砸核桃吃核桃的乐趣,后来更多的就是砸核桃。鉴于只有一把锤子,但又都想尝试,叶轻飘很快发现利用门的开合掌握好力度也是可以夹出很完整的核桃仁来的。
当卷堆和更云磨蹭半天才来且看到叶轻飘和寸言砸好的那一大堆核桃仁,立马后悔自己没有硬着头皮赌一把:或许老人并不会责罚他们。
几个年轻人立马把欢乐和闹腾装满了整个屋子,老妪那满是褶子但饱满白皙充满光泽的脸上也是幸福满满。
刚刚忘忧,老者又从里间出来了,板着一张脸,脚步声铿锵有力,四人闻声立马端坐回草墩上。
老妪看看瞬间安静下来的孩子们再看看老伴板得僵了的脸,没憋住“噗哧”笑出声来。
老者从卷堆这头开始,从怀里的钵中拿出一个大鹅蛋递到卷堆面前。真是意外!
卷堆在边伸手试探着去接的同时也仰头看着老者那一脸的严肃,像犯错的孩子看大人是否真的消气了。
老人本是干脆利索地递过去,可是就在卷堆仰头的那一刻忽然顿住了,卷堆以为老者不给了,悻悻地欲将手抽回来,老者这时偏又往他手里塞。
卷堆长长舒了口气,总算……还以为要被抽打的!
“吃吧,吃了鹅蛋身体里干净!”
老者乍这么一说,四人又不免去琢磨这其中的意思。
刚刚进去里屋现在拿着几块青菜叶出来的老妪赶紧补充道:“鹅蛋可以吸附身体里的脏东西。你们可别多想呀,我家这倔老头只是不太会把心意表达清楚。我们家里没有孩子,但是都很喜欢小娃娃。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他只要见到别人家的孩子都会逗,但是那些孩子见了他立马盯着他哇哇大哭,有好几次都让人家误会是他吓唬或是打了人家孩子哩……哈哈哈……”这真是个爱笑的老妪,老者在一旁看着听着又不知道怎么说,直把胡子吹得呼啦啦的。
老妪说着笑着都忘记要事先说明了,直接就上手掀更云的裤腿要扒他的靴子,更云吓得一把摁住,老妪这才反应过来:“啊啊,瞧我这脑子不够用得,说着话就忘了。是你们俩被鹅叨了吧?”老妪看看更云又看看卷堆,两人使劲点点头。
“来,用青菜叶包着冷饭揉揉搓搓,可以去去毒气,会好得快些,如果是被叨破了皮就更要这样才不怕得病。”更云恍然大悟赶紧很是听话地脱靴搂起裤脚,卷堆更是把已经剥开的鹅蛋壳又包回去,立马脱鞋排队等候。
四人一直等待着人家跟他们算总账,可是一直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迹象。寸言看到屋外檐下有一大堆刚从地里拔回的红豆,于是主动提出帮忙剥豆子,然后一个下午的腰酸背痛换来一大簸箕红色新鲜的大豆子和老妪用这些豆子为他们炖的红豆汤。
吃饱喝足后,带上老人家送的核桃,四人才从围墙边准备绕到正门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