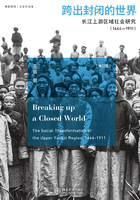
再版前言
《跨出封闭的世界》是1989年完成的,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重印)。本书从完成到现在已十六年有余,出版问世也近十三年了。这期间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已有长足的发展,我自己的学术生涯亦变化甚大。因此,在本书重新修订出版之际,兹就一些学术问题作一些交代。
本书出版后,立即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当年的《历史研究》第6期便发表长篇文章,肯定了该书在社会史研究上的“重要的创新意义”。文章认为,在中国学术界对长江上游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甚至可以说还未引起重视”之时,“本书开拓性地将这样一个空间范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在相应的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的情况下,选择这样的题目,是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的”。这篇评论指出,“史学工作者的智慧和识见,既不仅仅表现为对史实的精确的描述,也不单纯在对理论的精确理解,而在于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清晰地勾画出历史的表象,又能揭示隐藏在表象之后而又制约着表象变化的力量。王笛相当注意而且比较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本书不仅内容充实饱满,而且内涵也显得丰富深刻”[1]。
本书关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的研究很受学者重视。毫无疑问,本书的写作是受到了施坚雅研究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本书没有把研究局限在四川省而以整个长江上游区域作为对象,便是其影响的结果。有学者指出:“迄今为止,大陆学者依循‘施坚雅模式’从事市镇研究最为典型的例证,当推王笛所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指出本书“详尽分析了有清一代长江上游地区的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包括集市的作用与功能、市场密度与农民活动半径、高级市场与城镇发展问题”。认为本书关于农村和市场的研究之所以“令人瞩目”,还在于揭示了“在传统农业社会,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决定了需求圈和销售域的大小。场均人口表明了市场所拥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是市场发展的决定因素,它们制约了市场的商品流通和交易数额。经济距离(即换算为运输成本的地理距离)、生产成本以及平均购买力,是考察需求圈和销售域的三大要素”[2]。
2002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教授C.卡悌尔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上发表长文,评述巨区理论对中国研究的影响时,便指出:“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地区的专著,对一个巨区进行了宏观考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这个研究对清代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况,提供了一个非常深入的评估。与施坚雅的巨区原始表达不同,王笛的研究考察了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而文化和社会则揭示了空间的过程,并详细展示了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是怎样超越了巨区的界限。”[3]
这个研究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二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以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研究》使我获益匪浅[4]。在年鉴学派影响下,这本书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个贯穿全书的主线。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是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是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即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这项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
这样的构想使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5]。然而在本书的论述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证明即使是在中国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社会从未停止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当我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本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向现代演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本书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评价。换句话说,这项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本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话语霸权”。从晚清开始,各种精英出版物中充斥着对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批评。精英们对人民的思想、民俗和大众信仰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当我使用这些资料时,基本上是从精英的角度,并没有力图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理解历史和文化的持续性,以及他们自己传统生活方式存在的合理性。那些把大众宗教都简单地归之于“迷信”等论断,都是当时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
对一个社会进行全面的观察,必须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这本书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且也局限在从精英的角度观察他们。本书完成后,我学术兴趣和学术观念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把研究的眼光从精英移到一般特别是下层民众,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的。如果说本书我注重“变化”(changes),那么我现在的研究则更强调“持续性”(continuity)。我最近的研究和思考反映在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6]。
在本书写作上,我在资料上下了极大功夫[7],然在某些问题上,却未能基于资料在理论上予以充分的发挥。因此,在本书完成后,特别是我到美国以后,西方的有关研究使我对一些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对书中已经使用的有些资料进行了更深入地解释,其中之一便是我在《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上发表的《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该文发表后引起史学同行广泛兴趣,被称之为在国内“首次借用公共领域的概念”的专题研究文章[8]。这篇文章是受我在霍普金斯大学攻博时的导师罗威廉(WilliamT.Rowe)有关研究启发完成的,同时也深受冉玫烁(Marry B.Rankin)研究的影响。罗威廉和冉玫烁关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研究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太平天国后的社会重建极大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扩张[9],但我发现长江上游公共领域的发展却不同于这个模式,长江上游地区清初的社会重建便出现了我所说的“早期的公共领域”。当罗威廉和冉玫烁笔下的汉口和浙江公共领域在剧烈扩张之时,长江上游地区的公共领域却“程度不同地萎缩了”。长江上游模式的另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官”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在汉口,公共领域的扩张几乎完全是因为地方精英的积极活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地方政府发起新政之后,公共领域反而遭受到无可挽回的破坏。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大力扩张基本上是在20世纪初,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推动的结果”。这篇文章的完成主要是依据本书第六、七、八、九章的一些资料,但从新的角度进行分析。
关于“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使用已经引起了西方和中国学者的热烈讨论,对此提出批评者也不少。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学术讨论之关键是明确所讨论问题的概念,即首先必须确定大家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但不幸的是,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似乎从一开始便偏离了方向。我已接触到的有关文章和研究中,包括对西方有关研究的批评,几乎都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看作同一个概念,因而在论述中,总是频繁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因而我们不清楚它们要讨论的究竟是“市民社会”还是“公共领域”。罗威廉和冉玫烁等研究“公共领域”的代表人物对这个概念是十分清楚的,他们的整个研究都是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如果研究者仔细读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和冉玫烁的《精英活动和中国的政治转型:浙江,1865—1911》,以及他们的其他有关文章,就会发现他们从未交叉或含混使用“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这两个概念。他们在研究“公共领域”时,都小心地把其与“市民社会”区别开来。冉玫烁便指出:“从17世纪初以来市民社会便一直是西方政治理论的主题。……但另一方面,公共领域的概念在西方政治理论或历史典籍中却都影响较微,因而对非西方世界更适宜采用。”他们都指出他们的研究并非完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罗威廉便意识到:“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哈贝马斯概念的使用恐怕并不会得到他的认可。”冉玫烁也明确表示:“晚期中华帝国公共领域的产生不同于西欧。”不过他们也指出:“即使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的细节并不适宜于中国历史,但这种中间领域的概念……看来对理解官和民两者间的关系却是有用的。”他们以英文public sphere作为在中国社会中有很长的历史的“公”的领域的对应词,力图以此概念为契机从一个新角度解释中国近代的历史[10]。但评论者却把他们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作为“市民社会”来批评,因此整个讨论,都显得无的放矢。当然,这种无的放矢的情况也出现在美国学术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中。在一次亚洲研究年会上,冉玫烁告诉我,当她写作其关于浙江精英一书、第一次使用“public sphere”时,哈贝马斯的著作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对哈贝马斯及其公共领域的概念,她根本是一无所知。她在书中所使用的“public sphere”完全是中文“公”翻译而成。所以说“public sphere”不适合中国历史研究云云,完全是张冠李戴。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个概念的借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于给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研究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并非是说我们过去对有关问题完全缺乏研究,问题在于过去我们未能有意识地去揭示处于“私”和“官”之间的那个重要的社会领域。
在本书再版时,除了对个别原稿和排印的错误外,我并没有进行大的修改。我想,把本书与前面提到的《街头文化》,以及即将出版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11]进行比较阅读,可以看到最近十多年来,我自己关于中国社会史、城市史和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从对一个巨区全面的考察,到对一个城市街头文化的探索,最后到对一个城市的一种公共空间的分析,这样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不仅是我自己学术关注的转移,从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发展。
另外,本书在十多年前初版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书中的曲线图都是手绘的,这次再版采用了电脑图表。第一章中的若干交通图,也在原图基础上作了一定加工,以力求更加清晰。
王笛
2006年1月20日
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