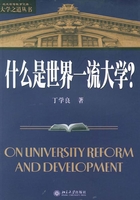
从世界看中国
今年(2004)春节刚过,北京的文化学者崔卫平女士到香港的几所大学从事学术交流,专门拨出宝贵的一个下午来香港科技大学做访谈。她问我1984年离开中国赴美国留学以来的二十年里,游学四方,所学到的东西中最主要的是哪些,我总结的两个要点之一,便是大学的素质与国家的竞争力血肉相关。我在回答她的问题时,心中正思考着修编本书的事,下面一部分言论,实在是针对着本书的未来读者而发的,用在这篇序言里,至为切合。[3]
丁学良:我和很多中国读书人一样,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是怀着一颗中国心,就是说你头等关注的事是中国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沉浸于“中国心、中国观”。什么叫“中国观”呢?就是仅仅就中国看中国,那种似乎是完全在关注中国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会产生非常狭隘偏颇的结论,很容易误导别人。所以我提倡的是“中国心、全球观”、“中国心、世界观”。你一定要把眼光尽可能地放得开。
崔卫平:在你的比较研究中,除了以上的,还有什么其他感受深刻的题目?
丁学良:我很关心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大学制度。这二十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综合评鉴中,亚洲能进入前五十名的大学一个也没有,中国内地能进入前一百五十名的大学一所也没有。进入大学排行榜前二百名最多的亚洲国家是日本,它的大学制度当年是从欧洲学来的,但后来没有迈出第二步——仿效美国之长的改造。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制度和日本的来源类似,后来却改造成了苏联式的,与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脱了节。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可以看出,等到新的产业部门越来越以知识创新为前提、国家的综合实力越来越依赖于“软力量要素”的时代,原来亚洲从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引进的大学制度就不够用了,更不要提苏联式的了,必须进行第二步的改革。
崔卫平:这第二步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丁学良:这方面美国对亚洲的启发极大。当今世界上,美国的大学数量最多,办大学的模式最多样化,效果相对而言也最好。美国当初在引进了英国、德国的大学制度之后,结合自己国家发展的需要和国际竞争的趋势,进行了长期的、多元的改革创新,1950年代起逐步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大学办得好,太得益于办学的多样性。它的大学不是一个以公立大学为主的体系,而是社会多元的财源办大学,因此葆有活力。美国也有公立大学,但大部分大学是私立的,最著名的几所都是私立大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1990年代更为突出),美国体制的大学日益成为研究的中心,这种模式对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式的大学提出了很大的挑战。[4]我在美国十年,经历的是美国制度,在香港和澳大利亚十年,经历的主要是英国制度和对它的改革尝试,所以体会非常深刻。美国大学的优势到1970年代都不是很明显,从1970年代之后越来越突出。美国的一流大学重视开创性的研究,而且研究不仅仅局限在象牙塔里,它还重视把研究成果进行“产学结合”,带动新的产业。它们的研究也不仅仅局限于应用技术,在基础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非常活跃。所以如果我们把“产学结合”的这个“产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扩展,那么可以说它对于行政现代化、国家的公共政策、发展战略、外交政策、国际竞争,都有巨大的助益。这个模式对亚洲来讲挑战太大了!一个国家的大学的创新力不够,就会坏事,因为大学在现时代,无论从科学角度、技术角度还是制度角度、观念角度、文化角度,都是整个社会创新的最重要的源头之一。
崔卫平:大学里的创新思路,如何对政府在制定政策方面起引导作用?
丁学良:一个大国的研究型大学所起到的作用,与政府或企业办的研究所不一样。不一样在于,政府自己办的那些研究所,研究的问题在政策层面上比较具体,偏向于执行的方面。但对于一个国家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是那些开放性(open-ended)问题的独立研究,这应该是在大学里进行的。比如美国社会里的种族关系,在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时代,大学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美国社会欠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的太多,因此应该大力扶持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但是那时候也有少部分大学里的研究成果不同意这样做,指出这样做的话,可能会有两个坏处。一是那些非常有能力的白人有可能被歧视,这会在整体上影响美国社会的发展,而且也不公正。第二,更有意思的观点是,少数民族中那些真有才能的人也不愿意这样做。他们认为,如果少数民族人士升得很快,这些成功不是基于他们能干,而是他们受到了特殊的照顾。这样可能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一种依赖思想,他们用不着非常努力,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特别照顾,这就无意识地鼓励了懒汉思想。这两种观点自1960年代以后一直在争辩,大部分时候是前一种补偿观占主导,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社会观念开始转变——越来越强调以后还是应该对所有的种族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我自己并不认为这两种政策哪一个是完美的、应该永远执行下去,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研究体制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它让多种观点都能够发出声音,虽然有的声音大,有的小,因此这个国家不会把一条路走绝,它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出现那种不顾一切代价、蛮干到底的状况。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国人重视。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无论是国内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还是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研究项目不是“一刀切”,没有统一的口径,没有预设的结论,所以走新路的机会不至于被封闭,出了差错能很快地改。
崔卫平:这样一种开放的大学研究体制,肯定需要同样是开放的人才引进制度?
丁学良:要想使大学为社会进步、为国家各领域的发展提供创新的源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开放地向世界招聘人才。全世界办得最好的大学都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好大学本身就应该是全球化的先锋,只要看看著名大学的背景就知道了。譬如早先的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吸引的师生决不仅仅是本国的,至少是欧洲各地的,后来又吸引了北美的好师生;德国的洪堡大学、海德堡大学是整个中欧人才的聚集地;美国那些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更是全球化的。亚洲的大学直到二十世纪快结束时,教员还没有全球化,学生全球化的也少,这样就严重限制了它们创新的机制。道理很简单,人只有来自五湖四海,才能把天下最有意思的观念和设想带来。人才是互相刺激的,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才会产生刺激。这是我最想在中国呼吁推动的事情,就是让中国资源最丰富的那些大学,在招聘教员的时候全球化。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在观念方面、公共政策方面、外交战略方面(这些也就是“软力量要素”),成为国家整体利益最好的代言人和推动者,这个角色对后发展的中国来讲更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些应用科学的成果还可以拿钱去买到,但是在开发那些软力量要素上、在给本国国民提供开放性的思路上,用金钱去买是买不到的。这是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发挥的公共服务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