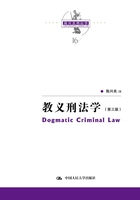
第二版前言
《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版自2010年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四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原作中有些表述需要纠正,有些内容需要调整,有些错别字需要改正。因此,利用修订之机,对本书进行了局部的修改,由此形成本书的第二版。《教义刑法学》一书是我近作中较为满意的一部作品,也反映了我近年来对刑法学的最新感受与领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义刑法学》一书是我在吸收德日刑法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将其融入我国刑法学,作为推进刑法学术发展的一种尝试。
《教义刑法学》的核心是“教义”,即德文Dogma。对于Dogma一词的中文译法,王世洲教授力主翻译为“信条”,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1]王世洲教授在论证Dogma应当翻译为“信条”而非“教义”时认为,除了历史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信条”是非宗教的,而“教义”一词来自日本的转译,本身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其实,“信条”与“教义”相同,也都具有宗教背景。例如,“百度知道”对“信条”的解释为:(1)宗教信仰的条文或体系;(2)可指普遍相信的任何原则或主张。[2]由此可见,“信条”一词在德文中也许与宗教无关或者如同王世洲教授所说的,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汉语中,“信条”一词的宗教色彩与“教义”一样,都是十分强烈的。即使“信条”一词没有宗教色彩,我也认为“教义”一词是更为合适的。因为,教义刑法学中的教义,是以对刑法法条先验地假设其正确为前提的,根据康德的话语,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3]而这恰恰就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因此,刑法教义学中包含了一种对待刑法法条的宗教信仰般的学术情怀。正如冯军教授指出的:
在传统上,刑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视为信仰的来源,现行刑法的规定既是刑法教义学者的解释对象,也是解释根据。在解释刑法时,不允许以非法律的东西为基础。对刑法教义学者而言,现行刑法就是《圣经》。因此,人民把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现行刑法进行阐释的学问,称为刑法教义学。[4]
在刑法教义学的语境中,刑法法条是解释的对象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对象。有教义的刑法学与无教义的刑法学之间的区分,恰如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区分。以往我国的刑法学是一种没有教义的刑法学,因此,这种刑法学缺乏内在逻辑的自洽性,缺乏整体知识的体系性,缺乏基本立场的一致性。
当然,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具有性质上的相同性。刑法教义学只是与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以及刑法沿革学之间具有区隔性,但与刑法解释学则是一词二义而已。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刑法解释学之外的刑法教义学。在这一点上,应当听取张明楷教授的忠告:
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5]
不过,我宁可将张明楷教授的这句话反过来说。这就是:
不要试图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解释学。
这就是我对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关系的态度。
此为第二版前言。
陈兴良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2014年4月18日
注释
[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主译,主译者后记,701~70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见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CW4QZBqk YpOV0KI2LwF0_WREqiNYn3bm-RWv Yh 4FsXsEfTx3Ro6sgeJP9bBJMji7jmlf-1REoJXh4f tvUQqh_,2014-04-18。
[3]转引自[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1)。
[5]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载《中外法学》,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