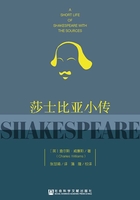
一 莎士比亚的出身

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
根据H. M.文书局主管批准绘制的《地形测量图》
注:版权所有牛津大学出版社。
威廉·莎士比亚出身于市民家庭。这种市民跟《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里的市民没有什么不同。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镇是一个外省集镇,与仅次于考文垂市阿登的亨利镇和沃里克自治市同属沃里克郡的商业中心。该镇位于埃文河北岸,一条古罗马小道曾在那里的浅水处穿河而过。中世纪时期,那条河上曾建有一座木桥,15世纪末被一座石桥取而代之,这座石桥至今犹存。西大路沿着通往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沃特林古道,穿过考文垂去往北方。然而,从伦敦来的两条小道却在斯特拉特福桥会合。一条经牛津,从克茨沃尔兹山下过来;另一条经由班伯里和埃奇希尔而来。过桥后,条条道路穿过斯特拉特福镇,向四面八方辐射,分别通向沃里克、伯明翰、奥尔斯特和伊夫舍姆。卡姆登[1]在《不列颠志》(Britannia,1586)中把这个地方描述成“相当不错的集镇”。约1540年到过该镇的利兰[2]记载,该镇房屋是“木头建造的,质量相当好,除了小巷,还有两三条大街”。地志学家把埃文河北岸的沃里克郡命名为“阿登”,并把它作为“林地”与埃文河南面费尔顿河一带的耕地区分开来。不过,在埃文河北岸,有开阔的农田,还有许多圈起来的牧场,而且,星罗棋布的小村显示了阿登林地边缘早期开垦的情况。13世纪,该地的领主在斯特拉特福镇拥有自己的“丛林”,后来变成林苑。然而,利兰说,在他那个时代,那里已看不到什么林地了。
斯特拉特福镇仅占同名大教区的一小部分。1546年,该镇方圆10英里内接受圣餐的教友有1500人。麦西亚[3]王给予伍斯特大主教的封赏优厚,主教们不受郡守制约,在帕思罗和斯特拉特福镇的吉尔普茨设立道旁法庭,对帕思罗特区“百户”拥有独立审判权。还为主教及其家室提供了一所修道院,以后才撤销支配权。主教的很多权限甚至是撒克逊时代的特权,通过转让和其他方式移交给豪绅。16世纪,在这个教区里有几处采邑。克罗普顿村就由同姓家族占有;勒丁顿村由阿罗的康韦家族拥有;德雷顿村由切斯特顿的皮托家族所有;毕晓普斯顿村原属拉普沃思的凯茨比家族,后来又转入坦沃思的阿切尔家族手中;肖特利村的部分地区是伍顿韦温的史密斯家族的地盘。然而,直到1549年大采邑仍归主教所有。市镇就坐落在大采邑里,这就是“老城”。“老城”与南郊的圣三一教区教堂分开。大采邑上还有老斯特拉特福、韦尔科姆村和肖特利村管区的一大片农田。在斯特拉特福镇的东方,主教还有“主教的汉普顿”这样一个特设城镇。河南岸的格洛斯特郡有夏尔科特村的露西采邑、米尔科特村的格雷维尔采邑和克利福德钱伯斯村的雷恩斯福德采邑。桥对面的布利奇敦村一部分归斯特拉特福镇管辖,一部分归阿尔维斯顿所有。斯特拉特福镇的东北和西北是斯尼特菲尔德和阿斯顿康特罗两个村庄。这两个村庄曾经是“沃里克领地”,即比彻姆和奈维尔两大世家的领地,已经收归王室所有。对于这些地方来说,斯特拉特福镇是天然的城市中心。
这个自治城镇是在约翰·德·库唐斯主教任职期间(1195~1198)形成的。这位主教把他的一部分领地划分成许多大小1/4英亩的正方形地块。这些地块作为租地被人占有。实际上,每块地交过1先令基本地租后就可以自由支配,有权划分、出售或按遗嘱转让给他人。主教的总管另外主持一个采邑法庭,不过市民们可以自行选举镇长和副镇长作为行政官员。采邑法庭一年开庭两次,配合复活节和米迦勒节[4]前的“民事法庭”或“法律日”。在这种场合委任官员、记录土地保有权的转让、听取关于债务之类的琐碎民事诉讼,制定维持良好秩序的细则,惩罚违反上述规定、饮食“法定标准”和其他货物质量标准的行为。“圣十字公会”这个组织是跟采邑法权一道形成的,它以各种方式主管城镇的福利。这个组织创建于13世纪。在15世纪,该组织合并了一些较小的行会,此后,兄弟、姊妹入会,悼念死者的花销之类的记录就从未中断。死者的弥撒是由小教堂的教士们做的,这些记录都保存下来了。会员之间必须建立兄弟般的友爱关系,并且必须戴奥古斯丁头巾参加会员的葬礼。定期的联谊宴会促进了更加世俗的交往。在斯特拉特福和斯特拉特福附近,公会从供品和遗赠中积累了大量财产,它帮助贫穷的会员,并开办了一所贫民院。早在1295年就以某种形式存在的一所学校也是公会的建树之一。托马斯·乔利夫对这所学校有过一项捐赠,就是聘请一位教士教授文法。公会大楼就建在城区内,最后是由伦敦市长休·克罗普顿爵士于1492年修建完整的。他也建造了斯特拉特福镇的那座石桥。15世纪中叶,公会处于鼎盛时期,吸引了斯特拉特福镇外的名流入会。后来它逐渐衰微,部分原因是商会兴起,镇上的工匠出于商业目的不得不同商会挂钩。也许在该镇的宗教生活中,公会的小教堂比较远的一所大教堂还要重要。这个较远的教堂属于教区委员管辖下的一所教士学院,它不但拥有不少地产,还征收了大教区大量的什一税。
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斯特拉特福变化甚大。公会和学院按1547年的《附属礼拜堂条例》均被解散,其收入上交王室。临时指令允许学院继续办学。1549年,尼古拉·希思主教显然由于补偿不足而迫不得已将他的采邑连同主教的汉普顿地区一起移交给沃里克伯爵,即后来的诺森伯兰公爵约翰·达德利,此人迫切希望恢复比彻姆和奈维尔两大世家在该郡的旧治。1553年,达德利被褫夺公权,玛丽[5]将采邑赐给公爵夫人,1555年公爵夫人死后又赐给了萨沃伊医院。但是这笔赏赐差不多又被立即撤销,于是采邑直到1562年还在王室手中。1562年,伊丽莎白将它赐给诺森伯兰的儿子安布罗斯·达德利,当时恰值他承袭沃里克伯爵。1590年伯爵死后采邑又被上交给王室,但在出售时由米尔科特的爱德华·格雷维尔爵士购得。然而,在1553年又发生了一件事,减弱了采邑及其法院在地方事务中的重要性。居民们也许对自己城市生活中种种重要因素的丧失深感不安,于是上书请愿,要求合并为一个王属自由镇。也许是由于当时掌权的诺森伯兰施加影响,这次请愿被1553年6月28日的一项特许状批准了。自由镇政府由1名镇长、14名参事以及14名显要市民组成的议会管理。权限是维护良好秩序,管理公共财产,填补议员空缺,每年选举镇长、治安官、保安官和其他必要的官员。议会必须汇报王诏在市区范围内落实的情况,不受郡守制约。镇长负责归公财产管理、验尸、发放救济品、管理市场,以此效忠于王室。作为被选举出的参事,他还要参与维持治安工作。镇长受权跟巡回贸易法院一道管理每周一次的市场和每年两次的集市。镇长手下还有一个登记法院,裁判民事案件,解决不超过30镑的财产争端。为了支付市政开支,特许状转让了原公会46镑左右的财产,同意归还学院批准出租的教区什一税,以及保留下来的34镑租金,学院的其余财产仍归王室所有。拨给的款项用来维持贫民院运转,给校长、牧师、副牧师发放薪金。一个笼统的附加条款后来造成了麻烦。因为这一附加条款是为维护领主的权利而制定的,尤其是镇长的选举要征得领主同意,校长和牧师也须由领主任命。1553年以后,若干年内的档案让人难以分清镇长及其同事的事务与民事法庭的活动。然而,1560年伊丽莎白批准特许状后,议会很快就正常工作了。议会每月在“市政厅”或原公会会馆开会,制定法令,审理财产,通过租让,整顿市场、集市和贫民院,为公共和慈善目的征收小额税款以贴补它的固定资金。
在登记法庭上协助镇长办事的起初是镇公所干事,后来是一名财务管理人员。除了处理民事纠纷(主要是债务方面的),就是处罚违反法令或商品规定的案例。吵架也许由治安法官处理。民事法庭虽然被削去了不少职能,但仍然在继续开庭。它也许处理采邑上特有的事务,诸如土地权转让之类。保安官虽然和其他官员一起在米迦勒节由议会挑选,但在民事法庭上宣誓就职。在税务、平民权利、镇长的认可等问题上,领主之间常有争议,内部纪律也常产生麻烦。参事和市民显贵并不总是定期参加镇务会议,其中有一些人在该他们负责时往往逃避责任。到16世纪末,议会多参与伦敦的事务。斯特拉特福镇的产业凋敝,还发生过火灾。于是,上奏王上,请求免除给王室的特支费,并请求增订特许状。1610年,詹姆士王确实进行了增订。这份特许状扩大了该镇的地界,把“老城”也包括进去了。
斯特拉特福镇一直被描绘成一个肮脏不堪、孤陋寡闻的城镇,不配做一个诗歌摇篮。这种说法缺乏历史眼光。无疑,当时的卫生学还在初创阶段,对违法乱纪行为的惩罚,一方面说明法纪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也说明法规得到了贯彻。同时代伦敦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小狗在舰队街乱跑,穆尔迪奇地区无人清扫。斯特拉特福镇的街道是铺过的,住宅周围有不少花园,整个市镇被榆树环绕。1582年的一次调查记载,院落中间、租地后面的榆树数目十分可观。城镇周围是优美的开阔地,那里有林苑,有绿树成荫的幽谷,还有一条波光潋滟的河流。城乡交流非常频繁。城镇工业、编织、印染、鞣革、制鞋、制造手套、铁器、拧绳、木器等都是为农业服务,或者是由农业提供原料的,不少市民在本教区或邻村占有土地。人们大量收购大麦,以满足麦芽酒的酿造和销售,这是许多家庭的一项副业。牛、羊、鸭和戴项圈的猪在被称为“河滨牧场”的公共牧场上跑来跑去。虽然偏远,这个城镇并未与较大的文明世界隔绝,到牛津轻而易举,去伦敦亦非难事,条条大路上都有脚夫定期往返。这个城镇里也不是完全无书可读。显要的市民能够引用拉丁文,如有必要,还可用拉丁文写信,文法学校也颇有声望。校长的薪金乔利夫原定为10镑,特许状把它增为20镑。这就比沃里克的12镑与先令高得多了,也比除威斯敏斯特、伊顿、温彻斯特和施鲁斯伯里之外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文法学校高出许多,而且还胜过牛津或剑桥研究员的酬金。这所学校的具体课程不得而知,也许是根据科里特[6]1518年为圣保罗公学、沃尔西1529年为伊普斯维奇公学定的课程安排的。科里特要求入学新生能够“胜任拉丁文和英文的阅读、写作,以便能够读、写自己的功课”。不过,伦敦有对小学程度的要求,斯特拉特福镇的标准较宽,如果孩子“有资格进文法学校,或者起码懂得,或即将懂得文法中的词态和原理”也就心满意足了。就连课程预修好像最初也由文法学校的临时助理教员来辅导,会计付给助理教员“教学费”。到1604年,一位独立执教的教师已经教授了一段时间的阅读,他的妻子教刺绣。“因而,我们的青少年阅读能力大大提高,公费学校大大减轻了那种烦恼。”在这所文法学校除了拉丁文外没有多少东西可学。科里特和威廉·李利所著的文法,经过修改,成为历届君王钦定的学校教材:有伦哈特·卡尔曼的《儿童箴言》或伊瓦尔达斯·加拉斯的《儿童学话》之类的简易成语集;有伊索的《寓言》和加图的《论风习》;有西塞罗、萨卢斯提乌斯或恺撒的著述;有奥维德的大量著作;有维吉尔的作品;也许还有贺拉斯或泰伦斯的撰述,或者某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像巴普蒂斯塔·斯帕格诺罗·曼图安纳斯的《牧歌》或者马赛拉斯·帕林吉尼乌斯的《诗人传》。但多半不会有希腊作品。男孩在16岁左右就发育成熟,可以上大学了。休·克罗普顿爵士曾给牛津和剑桥留下6项奖学金,镇务委员会是否继续拨款维持它们则不得而知。
这就是青年时代的莎士比亚的生活环境。他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不是斯特拉特福镇本地人,公会登记册上没有莎士比亚这个姓氏。在1552年4月29日的民事法庭上,约翰才在斯特拉特福镇初次露面。当时,他未经许可就在亨利街堆了一个粪堆,被罚款1先令。人们认出他就是斯尼特菲尔德村的一个名叫约翰·莎士比亚的人。这可能是有一定根据的,此人在1561年管理他父亲理查德的田产。理查德在斯尼特菲尔德村的两家采邑上拥有土地。在某种程度上是阿斯顿·康特罗村里威尔姆科特的罗伯特·阿登的佃户。1528~1529年,他就在那里留下了踪迹,可能是来自巴德布鲁克的汉普顿·科莱,其本源无从考查。在申请授予约翰·莎士比亚纹章时,纹章官声称约翰的祖先曾为亨利七世效力,还宣布赏赐他沃里克郡的几块土地。不过,找不到更进一步的记载。16世纪,在沃里克郡姓莎士比亚的大有人在,尤其是在斯特拉特福北面弗罗克萨尔和罗温顿四周的林地上更多。约翰·莎士比亚,身为他父亲的管家,被人称作农民或农夫。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弟弟亨利在斯尼特菲尔德拥有土地,此人债台高筑,于1596年死于该地。其他文件把约翰称为自耕农。按法律规定,自耕农就是完全保有年收获量价值50先令的土地的人,但是这一描述也往往用到还够不上绅士的小康人士身上。更加确切的称号就是“手套匠”或“白盐硝皮匠”。白盐硝皮匠处理、漂白制造手套的原料软革。毋庸置疑,约翰·莎士比亚把这几种职业合为一体了。他是一个手套匠、白盐硝皮匠及衣领匠同业公会的会员。这种公会也是斯特拉特福形形色色的商会中的一种。这和下面一些同时代的说法出入不大。1681年约翰·奥布雷[7]称他为屠夫;1709年,第一次尝试写了一本诗人的系统传记的尼古拉·罗称他为羊毛商。他很可能还有副业,有人提到他出售大麦和木材。或许他就是1570年前后在主教的汉普顿因贡牧场上当佃农的约翰·莎士比亚。显然,他不是克利福德·钱伯斯的某个约翰·莎士比亚,这个约翰·莎士比亚从1560年到1610年死时在该地都有迹可循。他也不是斯特拉特福的又一个约翰·莎士比亚,那个莎士比亚是一个鞋匠,从1586年到1595年前后住在该镇。早期的传记作者把此人的后裔同诗人父亲的子孙混为一谈。诗人的父亲娶的是玛丽·阿登。玛丽是罗伯特的女儿,诗人的祖父正是从他那里获得土地的。罗伯特出生于位于帕克·霍尔的阿登家族的古宅里,不过精确的亲属关系无法肯定。玛丽是个并不富有的女共同继承人。罗伯特在1556年的遗嘱中给她留下了一些在威尔姆科特的土地,这块土地被称为“阿斯比斯”,也可能他早就把那里的其他财产留给她了。她也有资格分享罗伯特的斯尼特菲尔德田产的一份将来应得的利息。玛丽·阿登一定是在立遗嘱的日期和1558年9月15日之间结婚的。因为1558年9月15日有一个女儿琼在斯特拉特福受洗,她一定是早夭了。威廉出生的确切日期不得而知,据信是4月23日,他于1616年的同一天逝世。这一认识似乎是由18世纪的一个差错造成的。1556年,约翰·莎士比亚买了两座房子。一座在亨利街,一座在格林希尔街。1575年,他又买了两座住宅,但地点无法确定。1590年,他在亨利街拥有两座毗邻的住宅。这两座住宅中,靠西边的一座现在被说成“出生地”,靠东面的一座被称为“羊毛铺”。这种传说追根溯源不会超过18世纪中叶。“羊毛铺”肯定是在1556年购置的。可是,约翰是在1552年就住在“出生地”呢,还是当时以房客的身份住在“羊毛铺”,在1575年才买下“出生地”呢,这还是个疑案。
然而,购置房产却说明约翰·莎士比亚生意兴隆是有可能的,而且他在市政生活中也出人头地。1557~1561年,他当过陪审员、保安官,在民事法庭里当过罚款员,他本人因阴沟不卫生及身为品酒员却未向登记法庭提供实物而被再度罚款。1561年和1562年,他被选为财务管理员之一,之后两年,他破格行使财务管理员代表职责,这大概就是他理财有方的证据。到1561年,可能他已经是一位显达的市民了,不过他的名字在1564年的名册里才首次出现。在鼠疫流行的那一年,他慷慨解囊,救助贫民。1565年,他被选为参事,而在1568年到达了市民抱负的顶巅——当了镇长。他常常用画押的方式批阅文件,有时打一个叉,有时画个钩。考虑到当时的习惯,这并不足以说明他不会写字。然而,十分不幸的是,这种做法使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如何拼写自己的姓名的。镇公所干事也就是常务文书,经常把他的姓写成“Shakspeyr”。但在斯特拉特福的文件上还可以发现二十几个不同的拼写形式。经过一段合乎习惯的间断后,1571年,约翰作为首席参事再次出任治安法官。几年以后,约翰出现了时运衰微的迹象。在登记法庭上,为了一笔数额很小的款项他既当原告又当被告,不过这些似乎是斯特拉特福商务老套的组成部分。他在高级法院偶然出过一次庭,这次牵涉大宗款项。1571年,约翰为了50英镑对一个老同事艾德里安·昆尼的儿子理查德·昆尼进行起诉。1573年,他本人却要偿付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前任会计亨利·希格福提出的30英镑赔偿。他未曾出庭,于是拘捕状发出了。如找不到他,则下令剥夺其公权。1575年,他仍可在房产上开销40镑。然而,在1577年,他突然中止参加镇务委员会会议,除了一两次特殊场合,再没有露过面。翌年,他被免除了一笔济贫税款,却被摊派了极少的集会花销,而这一笔钱到1579年仍未缴纳。他妻子继承的财产被处理掉了,斯尼特菲尔德的这一笔小小的继承权卖了4英镑。阿斯比斯以极低廉的地租租了出去。也许考虑到现款支付的缘故,威尔姆科特的其他财物向玛丽的妹夫埃德蒙·兰伯特抵押了40镑,定于1580年米迦勒节偿还,其实并未偿还。约翰·莎士比亚后来声称他曾经提出偿还,但遭到拒绝,因为他还欠兰伯特另外几笔账。这件事他好像并未证实。他还坚持说,兰伯特的儿子约翰由于在1587年继承了财产,答应立即购买莎士比亚夫妇及其儿子威廉的财产,但未曾恪守诺言。这种种说法遭到约翰·兰伯特的否认。1589年有过讼争,1597年再度发生讼争。但事实证明这笔财产已无法收回了。1580年的一件奇事仍然弄不明白。约翰·莎士比亚和诺丁汉一个名叫约翰·奥德利的帽匠在英国高级法院具结保证不妨害治安。他们言而无信,于是招致了巨额罚款。约翰·莎士比亚也因本人爽约而被罚款20镑,另有20镑是为奥德利作保而罚的。1587年他又与弟弟亨利的事务产生纠葛,这使他的处境更为尴尬。同年,镇务委员会失去了耐心,委任1名新参事取代约翰,“因为莎士比亚先生接到会议通知后,不参加会议,而且长期如此”。登记法庭上的另外一些诉讼说明他仍在经商。1592年9月25日,因“违犯每月去教堂做礼拜的王法”,约翰·莎士比亚与斯特拉特福的一些人一起被列入名单。在他和另外8个人的名字后面还加上了这么一条说明:“据说这9个人不去教堂是因为害怕收到债务传票。”16世纪,可以在星期日拘捕欠债人。按约翰·莎士比亚1557年以后的经历,这一解释似乎言之有理。然而,事实证明,传记作者们对一个城镇参事单调生活中的宗教传奇想得太多了,在解释约翰个人生活和官场生活中的隐秘时过于别出心裁,其实他是个不从国教者。到底他是个天主教徒,还是个清教徒,理论家们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1592年不从国教的复兴而言,这种立场是一目了然的。从日期的混乱来看,这种复兴跟1593年的反清教法规毫无瓜葛。1591年,英国正等待着西班牙卷土重来的入侵,郡守委任状由10月18日的公告颁布,对地方官的指令也公之于众。地方官员要收集不做礼拜的人的名单,不能“强迫任何人回答有关宗教的良心问题”。然而,如果发现这些人是任性的不从国教分子,那就要审查他们是否忠于女王,是否信仰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是否信仰耶稣会或神学院教士的主张。显然处境危险的只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清教徒。除去复兴本身,唯一与约翰·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有关的文件就是18世纪在亨利街他的一所住宅房顶上发现的那份虔诚的遗嘱或“testamentum animae”(灵魂遗嘱),这不可能是伪造的。但如果立遗嘱的约翰·莎士比亚就是诗人的父亲,这份遗嘱大概是他早年写的,对他在伊丽莎白统治下的宗教立场提供不出什么证据。17世纪曾有过这样一篇记述,一个来访者(至于他是何人,一定存在严重差错)在他的铺子里发现“一个笑脸迎人的老头儿”,他说:“威尔是一个诚实的小伙子,但他竟敢随时跟老子开玩笑”,这篇记述倒使人真正联想到他的性格。约翰虽然不再是镇务委员会的成员了,但1601年人们与领主发生纠纷时,还是会向他请教。1601年9月8日他被埋葬。人们不知道有遗嘱或遗产管理之类的事,然而从他手里传下来的所有财产中,人们发现只有亨利街的两座住宅归诗人所有。
关于威廉·莎士比亚本人的早年生活,有案可查的记录寥寥无几。罗根据大概是托马斯·贝特顿[8]在斯特拉特福做的调查研究告诉我们:威廉·莎士比亚的父亲送他上了一所公费学校,但由于“家境困难,而且家里需要他帮忙”,他只好中途辍学。没有理由反驳这种说法,因为它完全符合我们所知道的约翰的经济状况,而且约翰也没有理由在斯特拉特福镇的学校之外去找一所公费学校。不幸的是,那里没有把早期的学生名册保存下来。罗的话暗示,莎士比亚的退学未免过早了一些。从斯特拉特福还传出一个姓道德尔的人的更早的记述(1693),说诗人给一个屠夫当徒弟时逃跑了,但没有说明师傅也就是他的父亲。不过,这个记述说明,涉及约翰·莎士比亚的职业时,奥布雷的想法并不是一家之见。奥布雷提出威廉继承了父业,“他一边宰牛,一边高谈阔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他对约翰职业的见解,这种说法大概表明威廉·莎士比亚早就在训练模仿才能。“宰牛”似乎是江湖艺人的拿手好戏之一。[9]罗也风闻莎士比亚结婚很早,因为偷鹿离开斯特拉特福镇。有关这门亲事的文件使人迷惑不解。结婚的时间接近1582年年底,地点却不在斯特拉特福的教区教堂,也不是人们根据推测而去寻找注册簿的许许多多教堂中的任何一个。或许是在勒丁顿村的小教堂,在登记簿被毁之前,据说有人在上面看见过这么一项记载。婚书是11月27日在伍斯特主教登记处领的。第二天,两个保证人交了婚约,使主教无懈可击,结婚程序完全正规,没有家庭反对的迹象。但是婚书登记册上的新娘姓名是坦普尔·格拉夫顿的安·惠特利,而婚约上写的是斯特拉特福的安·哈思维。于是,传奇式的传记又一次嗅出了神秘的气息。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作为原始文件,婚约是正确的,负责登记的文书写错了名字。至于从来没有听说过婚约的罗,只知道哈思维这个姓。在斯特拉特福教区有好几个姓哈思维的人,所以安的父母究竟是谁就不十分清楚了。她也许是勒丁顿人,但是肖特利人的可能性更大,因为那里有一个名叫理查德·哈思维的人,他家的别名是加德纳。理查德·哈思维拥有休兰田庄的房屋,现在叫作安·哈思维村舍。他于1581年把钱留给了一个当时尚未婚配的女儿艾格尼丝。艾格尼丝和安虽然在严格的法律用语中不可等同,但在普通用法上,被看作一个名字的不同形式是毫无异议的。如果这门亲事还有什么仓促或秘密成分的话,也许就是安有孕在身。一种豁达的见解辩护说,可能存在一种相当于世俗婚姻的约前活动。女儿苏珊娜于1583年5月26日受洗,后面的一对孪生兄妹哈姆奈特和朱迪丝受洗于1585年2月2日。既然莎士比亚本人的姓氏普普通通,那么猜测谁是教父、教母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这对孪生兄妹的名字却是大有来头的,它们与斯特拉特福的一个面包师哈姆奈特或哈姆莱特·萨德勒及他的妻子朱迪丝有关。
偷鹿的传说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罗的记述独自确认了1695年当了格罗斯特郡萨坡顿教区长的理查德·戴维斯某些更早的札记。也许同罗一样,他把地方上的流言蜚语信手拈来了。罗说这件事发生在夏尔科特的托马斯·露西爵士的林苑里,还说为了对露西的起诉进行报复,莎士比亚给他写了一首歌谣。由于进一步起诉,他只好离开斯特拉特福镇。戴维斯说莎士比亚受到露西的鞭挞和监禁,于是他把露西描写成一个“纹章上有三个用后脚立起的虱子”的法官作为报复。这显然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一幕第一场有关。在这场戏里,夏禄法官抱怨福斯塔夫打了他的人,杀了他的鹿,砸开了小屋,并威胁要把这事作为暴乱告上法院。据说,他的外套上绣着“十二条白棱子鱼”,而休·爱文斯爵士开玩笑说成“白虱子”。从12世纪起,露西家族就一直占有夏尔科特,纹章是“蓝白相间的条纹构成的钟形空白,上有三条头部跃出水面的银色棱子鱼”。莎士比亚时代的托马斯爵士是一位杰出的治安法官,1571年、1584~1585年在议会里代表沃里克郡。据信,整个故事只不过是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段文字里演绎出来的。但就本质而言,我们不应把这一段传说置之不顾。偷鹿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被当作区区玩笑对待。即使对地位比莎士比亚高的青少年,也不足挂齿,但细节又另当别论。露西不会鞭挞莎士比亚,如果他按1563年通行的狩猎法办事的话。狩猎法中规定的唯一处罚就是监禁。如果事情被看作是暴行,可能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从法律的意义上讲,露西似乎不会在夏尔科特拥有一座“林苑”。他在1600年去世时,只有一个自由小猎物养殖场。诚然,博闻广记的律师爱德华·柯克爵士把獐算在小猎物养殖场的动物之内,但不包括鹿。虽然好像其他权威人士持不同看法,但1339年就是这样规定的。1563年的条例似乎对当时任何围场中的鹿都加以保护,不管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林苑,夏尔科特的自由小猎物养殖场当然也在此列。如果鹿不在狩猎法所保护的围场内,对它的任何劫掠只不过是一种侵害,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既不可能也不需要鞭挞或监禁偷猎者。然而,罗仅仅谈及告发,提到一首歌谣,这也许相当于诽谤罪。有一节诗,据称是那首歌谣的开头一节,说的是对多虱现象所开的一个玩笑。这节诗在18世纪传到威廉·奥尔迪斯[10]和爱德华·卡佩尔[11]的手中,据说关于这一情况的信息来自斯特拉特福的居民,是由一位死于1703年的琼斯先生提供的。果真如此的话,这就代表了第三种传说,它同戴维斯和罗的传说一样陈腐。1790年,斯特拉特福镇的一个潦倒诗人兼导游约翰·乔丹提供的一首完整的诗可能只不过是显示他的杜撰本领而已。但是,还有用另一种格律写的所谓这首歌谣的片段,据说是由剑桥大学的教授乔舒亚·巴恩斯1690年前后在斯特拉特福镇捡到的,证据实在贫乏得可怜。这首歌谣拿鹿角开玩笑,用伊丽莎白时代司空见惯的手法影射露西当了“乌龟”,而露西却在夏尔科特为亡妻立碑赞美她的贞节。显然这两种歌谣片段有很大出入,都不会是真的。但值得重视的是,通过戴维斯、罗、琼斯和巴恩斯的四重证据,证实偷鹿的传说在17世纪末的斯特拉特福十分风行。后来还有添枝加叶的传闻,但都不可以认真对待。一位作家在《英国人物传记》(1763)中,把莎士比亚的获释归因于伊丽莎白的干预;另一位作家在1862年声称,根据夏尔科特的档案,应把此事归因于1588年死去的莱斯特伯爵,但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灵感说成由莱斯特伯爵对露西的不满而生。到18世纪末,也许是发现夏尔科特没有林苑的缘故吧,故事又转移到邻近的富尔布鲁克林苑。然而,这个林苑到1557年已经开放。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代,这个林苑不在露西家族手中,1615年露西家族买下它,随后重新开放。某种对托马斯爵士的讽刺也许包含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一段文字中。但有人认为,总体来讲,特别是在《亨利四世》中,夏禄法官的形象是一个清官“画像”,这种推论未必恰当。那种肖像画似乎同莎士比亚的艺术手法格格不入。人们还一度相信斯特拉特福镇的显要公民欣赏有点儿撒野的小伙子,这种信念就引出了后来关于莎士比亚酗酒的故事。这种故事除了酒店老板的杜撰,根本无源可寻。
我们无法确定“逃亡”的确切日期。1818年,斯特拉特福镇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鹿肉是偷来给婚宴加餐的,这恐怕是一部分添枝加叶的内容。没有父亲仍可以给孩子施洗礼,但没有父亲生不下孩子。说莎士比亚1584年还在斯特拉特福镇,还比较合乎情理。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否在什么时候陪他出过门,没有她到过伦敦的记载,在买下“新居”以前,也没有她在斯特拉特福的记载。可是男孩哈姆奈特于1596年8月11日葬在斯特拉特福镇。另外,这并不足以证明莎士比亚仍住在斯特拉特福镇,因为按照他父亲的主张,他同意把威尔姆科特的地产在1587年前后卖给约翰·兰伯特,这好像仅仅是个君子协定。不管威廉人在何处,我们没有理由推断他同家人不通音讯。罗的偷鹿故事和道德尔关于当学徒时逃跑的类似传说含有直走伦敦的意思。然而这些说法都经不起进一步推敲。我们不能确定莎士比亚1592年以前就在伦敦,1592年罗伯特·格林[12]的一份言辞轻蔑的海报说明他已经当了演员,并开始写戏剧,这无疑与某次更早的逗留相符,因为这次逗留可能时间不长。有人估计更早的斯宾塞[13]的《缪斯的眼泪》(1591)中的“威利”指的就是他,这种说法现在遭到一致否定。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在他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一段中断,从1584年到1592年,有8年之久。显然,这一段时间里会有许多事情发生,只是我们一无所知。除了关于他步入剧坛的种种说法外,传说在填补这一段空白上是无济于事的。正是演员威廉·比斯顿告诉奥布雷,莎士比亚曾在乡下当过校长。比斯顿的回忆可以追溯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这种说法本身并不是不可信的。不过,他在斯特拉特福学的功课即便不是半途而废,也难以使他具备管理一所文法学校的资格。他的职业充其量可能只是一个助理教员或是一个启蒙先生,我们也不必假设他的学业,甚至是对古典语文的学习,随着学校生活的结束而结束。最直接的同时代证据是本·琼生提供的。琼生说他“不大懂拉丁文,更不通希腊文”,这自然是从作者自己学识渊博的角度来讲的。自从理查德·法默[14]的《论莎士比亚的学识》(1767)问世以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议颇多。人们列举了大量图书,古代的和现代的,学术的和通俗的,这些图书也许直接或间接地为他的剧本提供了素材。然而,这些推论未必总是严谨的,人们有理由假定莎士比亚一直在阅读到手的任何图书,有原文,也有译文。我们不知道他自己的藏书情况,不少图书上有他的签名,但大都是伪造的。有人说他有一本1502年阿尔丁版的《变形记》[15],有一本蒙田作品1603年的译本,还有一本1612年翻译的普卢塔克的著作。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莎士比亚在遗嘱中未提图书。他为什么不提?似乎没有任何道理,除非他要把图书从其他动产中清出来。同他的一般学识一样,莎士比亚对于法律的认知也是博而不精。他的作品中法律术语比比皆是,都天衣无缝地织进他的比喻结构里,但博而不精。其他的戏剧家也是如此。我们善于诉讼的祖先对法律程序了如指掌,幸而我们没有那么喜好讼诉。可是许多人认为,莎士比亚一定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里受过专业训练,虽然这不是经常被人援引的坎贝尔勋爵的定论。还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莎士比亚被斯特拉特福镇某律师雇用过。凡是无案可查的地方,总有人喜欢妄加揣测,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出于类似的根据,莎士比亚被说成药剂师,曾学过医等。他当过兵的说法是把他跟罗温顿的许多威廉·莎士比亚混为一谈造成的。又有人说他当过印刷工,依据是发行莎士比亚诗作的理查德·菲尔德是斯特拉特福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彼此矛盾的理论也进行了相互批驳。人类经历的范围非常广阔,莎士比亚都能应付自如,不管他是如何获得这种本领的,这本身就表现了莎士比亚的特色。对于他的某些经历,我们只消考察斯特拉特福镇就行了:早年会打猎、钓鱼、捕鸟;对田园生活洞察秋毫,这种洞察中还零零星星掺杂着寓言式的博物史,这是当时的文学从中世纪动物寓言集中继承下来的。至于其余的从何而来,我们也无法说清。然而,我们有资格假定一个神游八方、洞察万物的心灵,以某种方式熟知各色人等和多样风习,善于选择和应用五花八门的知识,这就是天才的秘诀之一。使读者最为大惑不解的也许是莎士比亚的文雅气质。在上流显贵的社交场合他待人接物从容 、温文尔雅。我们切不可把斯特拉特福的小康人家想成乡巴佬,不过地方城镇的文雅不是波细霞[16]的那种文雅,或许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一种统觉能力、一种活跃的气质的作用,它不仅善于把握事实,而且善于领会人的价值。
克茨沃尔兹山南部有为数不多的姓莎士比亚的人。引自1848年的一个“传说”,说诗人曾在德斯里居住,这一传说导致了这样一种推测:他也许在那里找了一个临时避难处。有人要求夏禄法官怂恿温科特的威廉·维索对抗山上的克莱门特·珀克斯;有人指出有个叫维沙德的人1612年在德斯里当镇长,而且温科特或伍德曼科特的维沙德和斯廷奇科姆山的珀克斯的几家邻居长期以来都繁衍下来。姓氏的关联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不过,珀克斯本身不仅在格罗斯特郡,而且在沃里克郡和伍斯特郡都是一个普通姓氏。事实上,1568年一个名叫克莱门特·珀克斯的人就出生在伍斯特郡的弗拉德伯里。在斯特拉特福镇的文件中,莎士比亚的姓氏出现过多次,但大多都没什么意义。使人感兴趣的是,有莎士比亚父亲名字的同一张不从国教者名单上,还有一个弗卢伦和一个巴道尔夫的姓名,不过莎士比亚知道巴道尔夫是一个贵族的头衔。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叫斯蒂芬·斯莱的人与《驯悍记》中的克利斯朵夫和斯蒂芬·斯莱相对应。虽然“斯莱”(Slie)和“唐·克利斯朵·瓦里”在《伏悍记》这一源本剧中已经有了。不过,克利斯朵夫·斯莱自称“伯顿·希思”,也许就是希思河上的巴顿,这正是兰伯特家族居住的地方;而温科特村酿制麦芽酒的胖老板娘玛丽安·哈克特一定就是一半位于克利福德·钱伯斯、一半位于昆顿的温科特的人。就在这个温科特,一个名叫萨拉·哈克特的人于1591年受洗。也许有人异想天开,认为克莱门特·斯沃罗在1559年控告约翰·莎士比亚欠债不还,所以他就跟托马斯·露西爵士一起被写成克莱门斯酒店的夏禄法官。埃文河畔蒂丁顿的一个名叫凯瑟琳·哈姆莱特的人在1579年淹死,这也许给奥菲丽亚的结局提供了暗示,但这些都不足以说明问题。不管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沃里克郡人在他的想象中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都无法知道。他早期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依然是那段未曾探明的中断。谁能说清万事云集的伊丽莎白时代的6年或8年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经历?揣测无济于事。经过如此繁多的历史调查,仔细探讨了条条线索,耐心掂量了种种可能之后,一个尊重自己的学者的结论只能是不可知论。
啊,当我们热切盼望肯定的时候,
灵魂得到的却是布满灰尘的答案![17]
[1]威廉·卡姆登(1551~162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2]约翰·利兰(1506?~1552),英国古物专家。——译者注
[3]英格兰中部一古国名。——译者注
[4]复活节在春分满月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米迦勒节在9月29日,英国的四大结账日之一。——译者注
[5]玛丽(1518~1558),英国女王(1553~1558)。——译者注
[6]约翰·科里特(1467?~1519),英国人文主义者,圣保罗教堂副主教,创办了圣保罗公学,与该校校长威廉·李利(1468?~1522)合著拉丁文法。——译者注
[7]约翰·奥布雷(1626~1697),英国文物专家,著有《莎士比亚传略》。——译者注
[8]托马斯·贝特顿(约1635~1710),演员,戏剧家。——译者注
[9]1521年圣诞节玛丽公主的《账目》记载:“一个温莎人当着公主的面在幕布后宰牛,款已付讫。”J.雷恩的《芬契尔修道院》(瑟蒂斯社)441号援引了一种名叫“宰牛”的18世纪艺人的“滑稽表演”。
[10]威廉·奥尔迪斯(1696~1761),文物专家,写过多种传记,声称写过一本《莎士比亚传》,现失传。但莎士比亚学者斯蒂文斯177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中显然利用了奥尔迪斯的《莎士比亚传》。斯蒂文斯还印过出自奥尔迪斯之手的《轶事补》。——译者注
[11]爱德华·卡佩尔(1713~1781),莎剧的第七位编者,被称为大学者之首。——译者注
[12]罗伯特·格林(1558~1592),“大学才子”之一,剧作家。——译者注
[13]埃德蒙·斯宾塞(约1552~1599),诗人。——译者注
[14]理查德·法默(1735~1797),教育工作者,曾任剑桥大学副校长等职。——译者注
[15]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代表作。阿尔丁版是15~16世纪威尼斯人Aldus Manutius或其家人印行的精装古籍版本。——译者注
[16]《威尼斯商人》中的女角。——译者注
[17]引自乔治·梅瑞狄斯(1828~1909)的《现代爱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