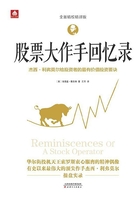
第5章 痛定思痛,再战华尔街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回到我的故乡。不过,就在我刚到家的那一瞬间,我就明白了:自己这辈子的追求只有一个——筹集本金重返华尔街,因为那里是美国唯一能让我大展拳脚的地方。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交易之路会走上正轨,到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假如你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切早晚都会向你靠拢,证明你是正确的。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不过当然的,我力图再一次深入对赌行。那时候,对赌行已经减少了许多,而且其中有一部分还是陌生人开办的。那些对我还有印象的人必定不会给我交易的机会,不会想知道我从纽约铩羽而归后,是否还够格成为一名交易员。
我已经如实告诉了他们我自己的经历,我在纽约输光了所有,无论我曾经在家乡赢了多少,如今,对他们而言,倘若他们允许我交易,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客户。但是,他们怎么不肯答应。另外那些新开的对赌行也不靠谱,老板们觉得,一位绅士在有把握赌对的情况下,最多也就买进20股。
现在的我最需要的就是钱,而那些规模比较大的对赌行正从他们的老主顾身上大把大把地捞钱。于是,我找到一位朋友,请他代替我去一家对赌行的营业厅进行交易。而我就假装闲逛,进去看看。我再一次央求接单柜员接我的一笔小单子,哪怕只接50股也好啊。当然,他还是拒绝了。
之后,我跟我的这位朋友约定了一些暗号,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准确又及时地执行我的指令——买哪个品种,多少钱买进,多少钱卖出,以及什么时候交易。但是,这样只能帮我赢一点零花钱而已。没过多久,我这位朋友下的单子也开始遭到了营业厅的抱怨。终于有一天,当他要卖出100股圣保罗的时候,柜员给他打了一个回票。
后来我们得知,我俩在外面交谈的时候被一位客户撞见了,是他告诉营业厅的,当我的朋友进去找柜员卖出那100股圣保罗时,那家伙却告诉他:
“我们绝不受理圣保罗的任何卖单,所以也不接你的单子。”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样呢,乔?”我的朋友问。
“没有为什么,就是这样,”乔回答。
“那是我的钱有问题吗?都在这儿呢,你再好好看看。”我的朋友将我事先给他的100美元——都是10美元一张的纸币——递了过去。他尽量显得很恼火,而我则好像漠不关心地看热闹,然后其他大部分客户都围了过来,观看双方的争执。
通常,营业厅里若是有人说话声音大了,或者店方与客户之间出现了什么细微的摩擦,他们一直都是非常关注的。他们希望将事情经过以及是非曲直打听清楚,目的就是弄明白,对赌行有没有足够的偿付能力和信用。
这位乔,大概是什么经理助理,他从里面走出来,朝着我的朋友走过来,瞪了他一眼,然后又撇了我一眼。
“哈哈,笑话,”他一字一顿地说,“真是天大的笑话,如果你的朋友利文斯顿不在这儿闲晃,你就一动不动。你就只是干坐着,不声不响地盯着报价板,一看就是半天。他一旦进来,你突然就像换了个人似地忙活一通。可能你的确是为自己交易的,不过,我们营业厅再也不接你的单子了。我们知道,是利文斯顿在背后指使着你,我们绝不上当!”
唉,我的生活费来源就这样断了。不过,除去花销,我的净资本已经有好几百元了,于是,我开始琢磨怎么将这笔钱用得更好,以便最终赢得足够多的钱再回纽约。现在,我的心情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急切。我相信,下一次我能做得更好。
如今,我有充足的时间平静地反省以前的一些愚蠢做法,而且我发现,往往站得远一点来观察,反而对看清全貌更有利,但我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筹集到一笔本钱。
有一天,我正在一家饭店的大堂和几位熟人闲聊,他们都是业绩非常稳定的股市老手。所有人都在谈论着股票市场。我告诉大家,没有人可以赢得这场游戏,因为他们从经纪商那儿得到的执行价低得吓人,尤其是像我这样总是按照市价指令方式进行交易的。
这时,一位老兄问我究竟说的是哪家经纪行。
我对他说:“就是当地最好的一家。”他再一次问究竟是哪一家。我看得出来,他对我曾经在第一流经纪行交易过的事情根本就不相信。
我回答说:“我说的是任何一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并不是由于他们是骗子,或者太过粗心,而是由于当你发出交易指令以市价买进时,你根本没办法知道股票实际上是以什么价格成交的,必须得等到从经纪行拿到成交回报后才能知道。你看,市场上1~2点的小波动是不是比10~15点的大波动多得多,这也是因为执行的问题,所以场外交易者要想捕捉到小幅上涨或下跌实在是太难了,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如果对赌行允许我在他们那进行大笔交易的话,不管是哪天,我都甘愿在对赌行里交易。”
跟我说话的这个人,我之前从未遇到过。他叫罗伯茨,看上去十分和善。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我是否在其他交易所交易过,我摇了摇头。他跟我说,他认识几家经纪行,是棉花、农产品和其他一些比较小的股票交易所的会员,这些经纪行对执行客户指令特别负责。他还向我透露,他们跟纽约股票交易所最大和最精明的经纪行都很有交情,通过他们特殊的影响力,以及保证每个月都可以接到成千上万股的生意,他们可以得到比个别客户更好的服务。
“他们对小主顾真的非常关照,”他说,“他们擅长做外地生意,而且对待一笔10股的生意与一笔1000股的生意同样尽心尽力。他们不仅很专业,还很诚实。”
“嗯。但是,如果他们按常规要付给股票交易所经纪行1/8美元的佣金,他们挣钱的来源又是什么呢?”我问道。
是的,他们按例应付1/8美元的佣金。但是——你懂得!”他冲我挤了挤眼。
“是,这样没错,”我说,“不过,削减佣金是股票交易所会员公司最不愿接受的事情。要知道,交易所的头头们宁愿他们的会员犯谋杀罪、纵火罪和重婚罪,也不愿意圈外人的交易佣金比1/8少一分一厘。只有会员们严守这条规则,才能保证股票交易所的生存。”
他此时必定已经看出我以前跟股票交易所的人聊过,于是接着说,“听着!每过一段时间,在这众多虚伪的经纪行中,总有那么一家由于违背规则而被吊销一年的执照,对吧?返还佣金的路子五花八门,没有人会告发的。”或许,他从我脸上看出我对他的话不怎么相信,所以他继续说:
“其实,在某些业务类别上,那些电话经纪公司除了要收1/8美元的佣金之外,还要收额外费用1/32美元。不过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很好说话。他们从来都不是真的收取这项额外费用,除非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客户的账户交易活跃度很低。你知道,对他们而言,实际上,额外收费是划不来的。他们做这生意可不是闲着没事找事玩的”。
这下我明白了,他这是在为某些冒牌的经纪行招揽生意呢。
“那么,你所知道的那些经纪行中哪家能靠得住呢?”我问道。
“我知道一家经纪公司,它是美国最大的,我自己就在那里交易。”他说,“它们的分店遍及美国与加拿大的78个城市,生意做得极大。如果它们不是一丝不苟地诚实经营,绝不可能每年都能把生意做得这么好,是吧?”
“肯定是的,”我表示赞同,“它们所提供的是不是纽约股票交易所里交易的那些股票呢?”
“当然了,不仅如此,还包括场外的、美国的或者欧洲其他任何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而且还有小麦、棉花、粮食,只要你想得到,就能买得到。他们到处都安排了市场信息员,是所有交易所的会员,只不过有的身份是公开的,有的身份是秘密的。”
这时我算是全都明白了,但我还是想逗他继续吹嘘下去。
“嗯,对的。”我说,“但是,总得有个人替他执行客户指令吧,说得再多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啊。市场如何变化,或报价机的价格与交易所场内的实际市场价格有多少偏差,是没有哪个人敢保证的。顾客从报价机上看到报价,然后发出交易指令、再通过电报传达到纽约,时间就这么溜走了,钱也这样流走了。可能回纽约才是我最好的选择,在正规经纪公司交易,至少亏也亏得甘心一些。”
“亏钱?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客户从来不会这样。他们在我们的关照下总是挣钱的。”他说。
“你们的客户?”我问。
“啊,是这样,我也是公司里的一个小股东。因为他们待我一向真诚,通过他们,我也的确赚了不少钱。如果我能给他们介绍生意,我定会尽心尽力。要是阁下愿意,我可以向经理介绍你。”
“那这家公司的名字是?”我问。
他告诉了我那个名字。对于这家公司,我曾经听说过。他们的广告多到所有报纸上都有,大肆宣扬某些客户因为听从了他们关于某只热门股票的内部信息而发大财的消息。该公司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此——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对赌行,而是对赌行中不折不扣的骗子。实际上,他们截留客户的单子与客户进行对赌,表面上却打着经纪行的幌子;他们通过精心设计的伪装给全世界留下正规经纪商的印象,让人们相信他们从事的是合法业务。在这类公司中,这一家是资格最老的一家。
今年,有很多同类型的“经纪商”倒闭了,它们应该算是这类经纪商的鼻祖吧,以至于还在经营。这一行全都是一样的门道和伎俩,但是,敲诈大众的具体花样却与时俱进,因为那些老把戏实在漏洞百出,所以,这些人不得不随时改变某些细节。
这些人习惯于广泛散布买进或者卖出某只股票的内幕消息,比如,这几百封电报建议马上买进这只股票,又比如,那几百封电报建议马上卖出同一只股票——与老式赛马内幕消息的骗局其实是一个套路——不明真相的群众往往会轻信这类消息,此时,买入与卖出的交易单会蜂拥而至。
举个例子来说,那家对赌行可能会通过一家正规的股票交易所经纪公司买入、卖出1000股,以便获得一份正规的成交单。如果哪位客户起了疑心,严词质疑他们截留客户交易指令的话,那他们就拿出这份成交单堵住他的嘴。
此外,他们还习惯于在营业部组建代理投资的集合资产管理池,然后,作为一项特大恩惠送给客户,从而让其以书面形式授权他们进行代理投资,也就是用客户的资金、在客户的名下、根据他们看来最合适的方式做交易。如此一来,当客户的钱蒸发以后,即便是最执着的客户也没法得到任何合法的赔偿。
他们会在账面上做多一只股票,将客户放到这个集合资产管理池中,然后,他们便开始施展对赌行的老伎俩之一——驱使股价暴跌,以洗掉几百位客户那微薄的保证金。他们不会对任何人手下留情,妇女、老人、教师等,是他们最中意的掠夺对象。
“我对所有经纪商都没了信心,”我告诉他,“再让我好好想一想。”说完转身走开了,以免他再喋喋不休下去。
之后,我跟很多人打听过这家公司。了解到他们的客户大概有数百个,虽然通常也有不少他们的种种传闻,不过,我没发现一个赚了钱却没能从他们那里拿到钱的客户。这事儿难就难在,你很难找到哪位客户的确曾经在他们那里赚到过钱,但是,还真的被我找到了。就在那一段时间,市场行情看上去对他们非常有利,这意味着,假如某一笔交易不利于他们的话,他们或许不会赖账。
当然,绝大部分此类公司最终都关门大吉了。每过一些日子,便会有一阵骗子经纪行的倒闭风潮出现,就如同之前一家银行破产之后,人们争先挤兑其他银行那样。但话说回来,美国的一些骗子经纪行的老板一直安然混到退休的,也着实有不少。
关于那位先生推荐的公司,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发现有什么令人忧虑的蛛丝马迹,除了他们自始至终专心追名逐利的习惯,以及并不总是像说的那样诚实之外。他们擅长骗取那些企图一夜暴富的肥羊。不过,他们总是先让客户签好书面委托书,“授权”他们名正言顺地将自己的钱财卷走。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在某一天,确实曾经亲眼看见他们发出过600封电报给客户,建议其买进一只股票;与此同时,他们还给其他客户发出另外600封电报,强烈建议把同一只股票卖出。
“是的,这种把戏我曾经见识过。”我对那位朋友说。
“没错,”他接着说,“不过,这还没完,次日,他们又给同一批人发电报,建议他们将手上所有的股票一律平仓,再买进另一只股票。我当时问了一位正在营业部的高级合伙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你们起初的做法我还能够理解,你们的部分客户有一段时间在账面上必定是获利的,尽管他们最后与其他客户一样会亏损。然而,现在你们又发给他们这样的电报,岂不是谋害所有客户的命。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那人回答说,“客户嘛,无论如何都注定是要赔钱的,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何种价格买进任何品种,结果都是一样的。当他们赔光了,我的客户也就跟着没了。反正都一样,因此,在他们身上能捞多少最好就捞多少,之后,再寻找下一群肥羊。”
好吧,我承认,我并不在意那家公司的商业道德如何。你应该记得,我对泰勒公司一直耿耿于怀,直到从他们那里赚回了一笔才解了气。然而,对于这家公司,我并没有这样的感受。可能他们的确是骗子,可能他们并没有别人传言的那样糟糕透顶。但我根本就没有让他们替我做任何交易,或听从他们的内幕消息,或听信他们的谎言的打算。
我唯一想的,就是抓紧筹一笔本钱好杀回纽约,好在那里的正规营业部里大展拳脚。在那儿,我既不担心警察什么时候会突然上门查抄店面(当时,警察会突然查抄对赌行),也不用担心邮政管理局会突然神兵天降一般把你的资金冻结。如果你比较走运的话,等一年半载之后,每1美元就能赚回8美分。
不管怎样,我决定要去看看,比起那些可能被称为合法经纪商,这家公司究竟会为客户提供哪些交易上的优势。我可以用来充当保证金的钱并不多,而且,截留客户指令的公司在这方面自然也没什么严苛的要求,所以,在他们的营业部里,几百美元就可以玩得很爽。
我来到他们的营业厅,先找到经理谈了谈我的情况。当他得知我是一个曾经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经纪公司拥有正式户头的交易老手,而且输光了自己带去的每一分钱之后,才没有继续拍着胸脯说大话。他还跟我说,假如我愿意将存款交给他们,让他们替我操作的话,保证一分钟内就给我变成一百万美元。
他觉得我应该是一只无可救药的迷途肥羊,属于那种对投机上瘾,却死不回头的赌徒。所以,不管是在截留客户指令的冒牌经纪商那儿,还是在满足于赚取佣金的本分经纪商那儿,我都是稳定的赚钱来源。
我告诉经理,我只求指令得到合理的执行结果,因为我习惯于按照市价指令方式交易,我不想看到成交回报的价格与报价机显示的价格差0.5点,甚至是1个点,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于是,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他们将尽一切努力达成我的愿望。他们很乐意接我的单子,因为他们要让我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高级经纪商。当然,他们的确招揽了这一行数一数二的优秀人才。实际上,他们所擅长的正是执行交易指令,并因此种卓绝的才能而著称。如果报价机上的价格与成交回报的价格有所差异的话,那必定总是有利于客户的,虽然这一点他们并不能向客户保证。要是我在他们这儿开户,我便可以按照电报发来的价格进行买卖交易,对于他们的经纪人,他们非常有信心。
当然,这便意味着,在这里,我可以和在对赌行时一样随心所欲地交易——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愿意让我按照当时的最新报价进行交易。我打算不那么快就显露出我心中过分的热切,于是摇了摇头,跟他说,当天暂时还不想开户,但是,我考虑一下会给他回话的。他再三劝说我马上开始交易,抓住当下还算不错的的行情,正好可以赚一笔。
对他们而言,现在的行情确实挺好——市场一片死气沉沉,处于上下微幅拉锯的震荡状态——这正是他们赚钱的好时机,他们先劝说客户根据他们提供的“内幕消息”交易某只股票,然后驱使股价急剧波动一阵子,然后一举吞没客户的资金。经过一番好说歹说,我好不容易才得以脱身。
自然,我把我的名字和地址留给了他。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不断地接到他们发来的预付邮资的电报与信函,敦促我不要错过这只或那只股票,还义正言辞地声称,他们已经知道某个资金合伙的内部庄家,正在策动一轮高达50个点的上涨行情。
此时的我正忙着到处走动,尽可能地遍访其他几家同类型的冒牌经纪行。我认为,假如我的确可以从他们攥牢的掌心里拿到钱的话,那么,我筹集一大笔本金的唯一途径,就是去附近的这些冒牌经纪行交易。
通过了解,我觉得,我可以同时在三家公司开户,于是我就这么做了。我自己还租了一小间办公室,而且架设了直连三家冒牌经纪行的电报线,以方便交易。
为了避免一开始就把他们吓跑,我打算还是从小笔交易开始。整体上,我是盈利的,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告诉我,他们希望同与他们直连电报线的客户做像模像样的生意,他们不待见那些散户的小打小闹。自然,他们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客户的单子越大,亏得就越多,就越快被他们洗光,他们挣得也就越多。
他们的想法的确有几分道理,要知道,这些人往常对付的都是普通的客户,从理财的角度讲,普通客户绝不会撑得太久。客户破产之后,就不能再继续交易了。而赔了钱却还没有破产的客户便会四处抱怨,指桑骂槐,甚至变着法子找他们的茬儿,其实更不利于他们的生意。
我另外还跟当地一家和纽约合作方直接连线的经纪公司建立了联系,它的合作方也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会员之一。我先安装了一台报价机,然后开始保守地进行交易。就像我之前说的,除了节奏稍微慢一点儿之外,这跟在对赌行交易差不多。
这个玩法我有把握赢,并且也确实赢了。我绝对没有达到百发百中的完美境界,不过,整体上是获利的,而且是一周接一周地获利。这样一来,我又活得非常舒心了,但现在必须得先把一部分盈利另存起来,逐步增加我的本金,好带回华尔街。之后,我又架了两条电报线连到其他两家冒牌经纪行,如今,我一共拥有5条直连电报线路——当然,我跟我的正规经纪行也有单独的直连线路。
有时候,我的交易计划也会出现差错,我选中的股票后来的表现与价格模式不符,甚至是背道而驰,没有按照我预测的方式变动。然而,这种情况是伤害不了我的——它们做不到,因为我的保证金是如此微薄。我跟这些经纪商们相处得还算不错,他们的账目与交易记录并不总是跟我的一致,当然,出现偏差的时候都是对我不利的。
你以为真是奇妙的巧合吗——错,不是巧合!但是,通过我的据理力争,最后总是可以按照我的方式结算。他们一直都心存侥幸,希望再拿回我从他们那里挣到的钱。在他们的眼里,我赢得的只不过是一笔临时贷款,我感觉他们就是这样想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公平交易精神,一点儿都没有。他们绝不会满足于固定比例的佣金,为了赚钱,这伙人不择手段地出尽法宝,坑蒙拐骗无所不为。由于肥羊们在股票市场赌博时始终是赔钱的——他们根本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投机者——或许你会觉得,这些家伙从事的这个行当虽然不合法,不过可能还算合情合理。
但是,并非如此。有这样一句古老而正确的真理——“在客户中间一买一卖地赚差价,一份耕耘即有一份收获”,对他们而言就是耳旁风,他们并不满足于与客户真刀真枪地对赌。
有好几次,他们对我耍出老把式,试图欺骗我的钱。由于我的一时疏忽,让他们得逞了几次,他们总是趁着我的盘子比一般规模小的时候糊弄我。我之后指责他们交易不公或行径卑劣,不过他们怎么会认账呢,最终,我还得继续像往常那样交易。
其实,跟骗子做交易也是有好处的,想要你继续跟他做生意,他们总是能够原谅你曾经当场揭穿他那骗人的把戏。对他而言,这种事情本无所谓。他非常乐意屈就和配合,脸皮多么厚,心胸多么宽广啊!
他们竟然施展骗子手段阻碍我正常筹集本金的速度,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我打定主意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看看。我先精心选择了一只股票——曾经,它是投机热门股,如今已经归于沉寂,就好像毫无生机了。如果我选择一只从未活跃过的股票,他们有可能会怀疑我的作为。然后,我给这五家冒牌经纪行全都发出买入这只股票的指令。当他们收到我的指令之后,他们就等着纸带机打出的下一个报价;此时,我通过股票交易所的经纪行发出以市价卖出100股该股票的指令,又催促他们尽可能快地成交。
当我这笔卖出指令传到交易所场内时,场内发生的情景你完全能够想象得出来,向来交易清淡的冷门股,某家与外地连线的佣金经纪行突然之间一起卖出,有人捡到了便宜股。然而,这笔交易会在报价机纸带上出现,它的价格就是我发出的那五份买入指令应该付给五家公司的价格。总体来说,我是以一个较低的成本价格做多400股该股票的。和交易所连线的公司向我打听,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告诉他们说,听到了一点内幕消息。
就在收市之前,我又给正规经纪行发出马上买回100股该股票的指令,不要耽搁一点儿时间。不管怎样,我并没有做空的打算。他们以什么价格成交我也不在乎。于是,他们给纽约发电报传达尽快买进100股的指令,导致其行情猛然上涨。当然,我也给那五家冒牌经纪行发出卖出指令,轧平被那五家截留的500股。可以说,整个过程中间没有漏洞。
他们依然死不悔改,继续跟我耍花招,于是我便如法炮制,继续了几回之前的套路。现在,我还不能跟他们撕破脸,所以,我的交易量一般不会超过100股1~2个点的限度。不过,对我的小金库来说,这些进账还是不小的。要知道,我正在为重返华尔街冒险而积攒本金。我有时候会变变花样,将某个股票卖空,但不过量。我每次出击,都可以收到600到800美元的净利,我已经很满足了。
有一次,我这手绝活玩得实在是太漂亮了,以至于股票价格竟然上涨了足足10个点之多,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没想到有这等好事会被我遇到。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在其中的一家冒牌经纪商那里买进了200股,而并非像通常每家买进100股,但是在另外四家则每家只买进了100股。对他们而言,这事好得简直是太离谱了。
终于,他们这次愤怒了,开始在与我往来的电报中对我进行语言攻击。因此,我过去拜访了经理,就是那位刚开始急于邀请我开户的那位老兄,之后,每当我捉住他正企图算计我时,他总是不“斤斤计较”。以他所处的位置来说,他的话实在是有些装腔作势。
“那只股票的行情竟然是假的,你他妈的别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他骂得很难听。
“你们收我单子买入的时候,行情并不是假的。既然那个时候你允许我进场了,那么,现在你就得允许我出场。如果你们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就不能这样耍赖,我说的没错吧?”
“不,我完全可以那样做!”他咆哮道,“我能够证明,有人在搞鬼操纵股票价格。”
“这个人是谁?”
“你自己心里明白!”
“究竟是谁在搞鬼?”我质问他道。
“我确信,肯定是你的同伙搞的鬼。”他气愤地说。
我严肃地告诉他:“你清楚得很,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而且,这一点本地所有人都知道。甚至从我开始做股票交易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知道了。我现在要善意地劝告你:你最好赶紧派人取钱给我,我没有把事儿闹大的意思,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
“要钱没有!有人给我设了圈套!”他叫嚷道。
我懒得再跟他浪费时间,干脆地告诉他:“赶快付钱,就在这里,立刻!”
接下来,他又跟我吵闹了好一会儿,还断然指责我是个骗子,不过最后,还是很不情愿地拿出了钱。其他几家倒是没有像这样吵吵闹闹。其中一家的经理对我炒作的那些不活跃的股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当他接到我的买入指令时,的确进场替我买进了那些股票,而且,同时也给自己买入了一些,因此,他也跟着赚了一点儿钱。这帮家伙对客户起诉他们欺诈的行为根本不在乎——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事先采取法律手段,给自己编织一张安全的保护网。
不过,他们害怕我起诉查封他们营业部的家具及设备——我没有办法把他们在银行的资金冻结,因为他们一向很谨慎,不允许任何资金冒一丁点儿这种风险。假如人们知道他们做生意是如此精明刻薄,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什么大事;然而,如果人们知道他们多么擅长坑蒙拐骗,那对他们可是致命的打击——顾客在经纪商那里赔钱,并非大不了的事儿。但是,如果客户挣了钱却没能拿到手,那么,在“投机圣经”里,这个罪行是最不可恕的。
好在,我从所有的经纪商那里都拿回了钱,不过,那次10个点的跳跃式上升,给这段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愉快消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们自己惯于用这种小把戏欺诈那不计其数的可怜顾客,如今,他们是严加防范、风声鹤唳。我再次回到常规的交易轨道,然而,市场状况并不总与我的交易套路相适应——也就是说,他们愿意接受的交易指令的规模是有限的,这一点便束缚住了我的手脚,使我不能痛下杀手,一次就狠狠地赚上一大笔。
这样的交易生涯,我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期间我想了很多办法,尽可能地在这些电报经纪公司交易赚钱。我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不但能放开手脚消费,还买了一辆不错的车。我的确得积攒一笔本金,但是与此同时,也得把日子过好。
假如我的市场头寸做得比较合理,那么,我挣的钱根本就花不完,所以可以存起来一些。如果头寸做错了,我就无法挣到钱,也就没有钱可花了。我之前说过,我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一笔本钱了,再者,在这五家骗子经纪行也没多少钱好让我赚了。我认为,是时候重返纽约了。
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于是,邀请了我的一位交易员朋友一同启程。他答应了,我们立刻就动身了。我们途经纽黑文,在那里我们停下来吃了晚饭,还在饭店里碰巧遇到一位旧相识,于是大家聊了起来。从他那里得知,本地有一家有电报连线的对赌行,生意做得相当红火。
我们离开饭店之后,继续朝着目的地纽约赶路,然而,当我开车经过那条街时,忍不住想看一看那家对赌行有着什么样的外表。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我实在是抵不住诱惑,于是便停下车走了进去。大厅里不算多么奢华,不过,我的老伙计——报价板——就在那里,还有一群客户,一场好戏正在上演。
经理是个年轻小伙儿,看着好像曾经是个演员,又像个政治演说家,他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早上好”的模样,就仿佛他曾经花了十年时间,每天用显微镜仔细观察后终于发现了早上的好处,现在正式向其他人宣布他的重大发现。他见我俩从跑车款的汽车里走出来,而且又都是冒失跳脱的年轻人——我感觉自己看上去还不满20岁——他自然猜测,我们是耶鲁大学的两个学生,我没有反驳他。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根本没有给我们丝毫说话的机会。
他说,见到我们很高兴,还问我们,是否愿意在这里舒服地小坐一下。他还说,股票市场马上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早晨的市场行情,如大家所愿是上涨的;市场前景是如此红火,正有助于替大学生活所需的零花钱增值。当然,一直以来,聪明的大学生从来都不用担心零花钱不够花。而且,此时此刻,只须一小笔初始的投入,就可以借助这个好心的报价机赚个几千美元。股票市场慷慨地把好机会留给了我们——这可是一笔谁都花不完的零花钱啊。他的这番话的确很有诱惑力。
那好,既然这位对赌行的经理这么热心,假如我们不领情遵命,岂非太不给他面子了?于是,我跟他说,就按他说的办,因为我听说很多人都是通过炒股发家致富的。
于是,我开始十分保守地交易,不过,随着不断获利,我也逐步增加了头寸。当然,我的朋友跟我保持同样的步调。
我们当天在纽黑文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差不多九点五十的时候,再次光临了这家热情好客的对赌行。那位杰出的演说家看到我俩来了,依然很高兴,似乎感觉今天他的机会到了。然而,数了数我当天净赚的,只差几美元就达到1500美元了。第三天早上,我们又一次顺便去拜访那位演说家,同时递给他卖出500股糖业的单子,虽然他有片刻迟疑,不过,最终还是一声不吭地接下了!
这只股票下跌了1个点,我打算平仓了结,于是,就把成交单交给了他。正好,我当初的500美元保证金加上500美元的利润,一共是1000美元。他从保险柜里拿出了20张面额50美元的钞票,认真地数了三遍,每一遍数得都很慢,然后转身走到我面前,又数了起来。
此时,他指头上的汗水仿佛变成了胶水,那沓钞票就像粘在了他手上,但他最终还是将钱递给了我。他两只胳膊交叉抱在胸前,一直紧紧咬着下嘴唇,两只眼睛直直瞪着我身后那扇窗户的上端。
我告诉他,我想卖出200股钢铁。他却装作什么都没听到,一动不动。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不过,这次将卖出股票的数量增加到了300股。这时,他回过头来,我正准备听他的长篇大论。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仅仅只是看着我,然后咂咂嘴,喉结滚动着——好像要对反对党50年来罄竹难书的贪腐暴政展开攻击一般。
最后,他冲着我手上的那沓黄色钞票摆了摆手,说:“拿开那堆东西!”
“什么?”我问。我不太清楚他要赶走的是什么。
“你俩要去哪儿?”他用令人难忘的声音说道。
“去纽约!”我说。
“这就对了。”他一边不断地点头,一边说着,“很好,你们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现在我已经认得你们俩了!不,我知道,你们并不真的是学生,你们是什么人我很清楚。没错!”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我十分礼貌地问他。
“没错!你们两个——”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撕掉他那正人君子的面具,大声尖叫起来,“你们两个就是全美利坚合众国最大、最可恶的鲨鱼!什么学生!啊?什么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啊!”
我们俩随即离开了,留下他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可能他并没有多么心疼那些钱,因为职业赌徒都不会这样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游戏本身所注定的,而且,总会遇到这样一天的。其实,最伤他自尊的是,他觉得自己被我们愚弄了。
就这样,我第三次返回华尔街,从头开始做起。当然,我一直没有间断过研究,力求找到我的交易体系所存在的缺陷,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我在A·R·富勒顿公司营业部的一败涂地。
当我20岁的时候,我赚到第一个1万美元,后来又输光了。但是,至于我为什么赔钱、怎么赔的钱,我都很清楚——因为我一直都是不顾市场状况不停地交易;因为我的交易背离了自己的系统——我的系统是以扎实研究和实践经验为根基的,然而,我进场只是为了单纯的赌博。
我渴望赢,而不知道按照一定的模式交易就能赢。当我大概22岁的时候,曾经将本金攒到了5万美元,然而,在5月9日又全部亏掉了。但是,至于为什么赔钱、怎样赔的钱,我清楚得很。因为纸带报价比市场实时行情滞后,而且,在某些可怕的日子里,市场波动异常惨烈。
但是,对于从圣路易斯回来以后,或者在5月9日大恐慌之后,我为什么会亏损,我就真的不知道了。对此,我有几点想法——我觉得,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做法中的问题,而且针对这些问题我已经做出了一些补救,但我还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下正确与否。
以丧失你所拥有的一切为代价,来教导你绝对不可以去做什么——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教育效果更好呢。那么,当你学会绝对不可以做什么才不会赔钱时,也恰恰是你开始学习应该做什么才会获利的时候。懂了吗?你才刚刚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