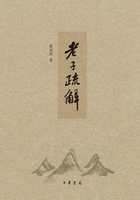
十二章
五色使人目盲,
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
五味使人之口爽,
五音使人之耳[聋]。①
是以社(圣)人之治也,
为腹而不为目,
故去彼而取此。②
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目盲,
驰射狩猎使人气躁心狂,
难得的财货使人行为邪妄,
美味佳肴使人味败口伤,
悦耳的音乐使人听觉失常。
所以圣人对国家天下的治理,
只在于满足肚腹的淳朴之需,而不去滋长眩目惑心的种种欲望,
因此他鄙弃那样而选取这样。
【校释】
①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
帛书乙本“耳”下残损一字,据甲本当为“聋”;补损阙后,其字句如上。甲本“盲”作“明”,或为抄写之误;“难”上残损三字,据乙本当为“心发狂”;“货”作“筕”,“仿(妨)”作“方”,“爽”作“窡”。甲、乙本虽用字有异,但句脉、文义从同。
郭店楚简本未见此章文字。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帛书本“使”王本作“令”,帛书本“田”王本作“畋”,帛书三、四、五句“使人”下多一“之”字;此外,帛书第二、三句为王本之四、五句,帛书第四句为王本之第三句,帛书第五句为王本之第二句。从句序看,王本似更合理些,但整节文字的义理并无异致。
※诸传世本多同于王弼本,其略异者则有:易州景龙碑本、易州开元幢本、邢州开元幢本、易州景福碑本、庆阳景祐幢本、周至至元碑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北京延祐石刻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河上公(影宋、道藏)本、敦煌写本之乙、丙本、《群书治要》本、傅奕本、李约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张君相本、强思齐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司马光本、苏辙本、陈象古本、宋《御解》本、邵若愚本、李霖本、白玉蟾本、彭耜本、董思靖本、宋李荣本、林希逸本、范应元本、文如海本、无名氏本、寇才质本、赵秉文本、时雍本、李道纯本、邓锜本、杜道坚本、吴澄本、林志坚本、张嗣成本、明《御注》本、危大有本、释德清本、薛蕙本、周如砥本、潘静观本,“畋”作“田”,“驰骋畋猎”为“驰骋田猎”。
“五色”,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古人以此为五正色。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释《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云:“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出于黑,故六者有黄无玄为五也。”“五色”,在本章泛指多种色彩。“五色使人目盲”,谓缤纷的色彩令人眼花目盲。
“驰骋”,指驰射、田猎;高诱注《吕氏春秋·任数》“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云:“驰骋,田猎也。”“田腊”即田猎;《风俗通义·祀典》云:“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也。”“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谓驰射狩猎会令人气躁心狂。
“仿”为“妨”之借字,害、妨害之意;韦昭注《国语·越语下》“将妨于国家”云:“妨,害也。”“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谓珍贵难得的财货会使人的行为邪妄。
“五味”,指酸、甜、苦、辣、咸五种味道;郑玄注《礼记·礼运》“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云:“五味,酸、苦、辛、咸、甘也。”这里,“五味”泛指多种美味。“爽”,指伤或伤害;李善注《文选·张衡〈南都赋〉》“其甘不爽”引《广雅·释诂四》云:“爽,伤也。”“爽”而“伤”,乃味败之意,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注《楚辞·招魂》“厉而不爽些”云:“爽,味败也。”“五味使人之口爽”,谓美味佳肴会使人味败口伤。
“五音”,指古代五声音阶中的五个音级,即宫、商、角、徵、羽;赵岐注《孟子·离娄上》“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云:“五音,宫、商、角、徵、羽。”这里,“五音”泛指多种乐音。“五音使人之耳聋”,谓动情的音乐会使人听觉失灵。
②是以 (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圣)人之治也,为腹而不为目,故去彼而取此。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社(圣)”作“声”,“为腹”下少一“而”字;“不”字下残损二字,据乙本当为“为目”;“故去彼而取此”为“故去罢(彼)耳(取)此”,“耳”为“取”之误书。甲、乙本用字有出入,但句脉、文义大致无异。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勘校以帛书本,王本“圣人”下少“之治也”三字,“为腹”下少一“而”字,帛书本义胜。
※诸传世本悉皆同于王弼本。
以“为腹”与“为目”对举而说“圣人之治”所作的“去彼而取此”的选择,其意略相当于三章所谓“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为腹”,是就满足生命自然之所需而言;“为目”——“目者,心之符也”(《韩诗外传》卷四)——则必致为“文敝”所陷,以至于目迷于“五色”,耳惑于“五音”,口败于“五味”,心狂于“驰骋田腊(猎)”,行妨于“难得之货”。王弼注云:“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所谓“以物役己”,是指纵“心”、“志”之欲以逐物——人既以逐物为标的,则势必为外物所牵羁。王氏此解,颇得老子之谛趣。
【疏解】
此章再度申衍祈愿中的“圣人之治”,其大旨与三章相应和。全章之措思略可分两层:一是对“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所可能造成伤生后果的警示,一则是“为腹不为目”这一“圣人之治”方略的提出。
“五色”、“五音”、“五味”以至“驰骋田猎”而贵“难得之货”,皆可一言以蔽之谓人为之“文”,其无一不关联着已见崩坏的“礼”、“乐”而俱在以克除“文敝”为宗归的老子之学的贬斥之列。老子不像比其略晚的孔子那样,在礼坏乐崩的春秋之末力图重新厘定“礼”、“乐”的当有分际以求“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而是在终极意义上不再信从“礼”、“乐”。在儒者所认可的传统视野中,礼是天经地义的,这用春秋时郑国大夫子大叔的话说则略如下:“吉(子大叔之名——引者注)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混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老子却不同,他视“礼”(“乐”)为“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崩坏后的“礼”、“乐”如何依从某一标准再度予以制订,而在于这无论怎样制订都必至于崩坏的“礼”、“乐”终当予以摈弃。换句话说,在老子这里,不存在无“敝”之“文”,凡“文”不可能不“敝”,因此消除“文敝”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乃在于扫“文”以“复朴”或所谓“见素抱朴”。老子将其义理之根追溯到“生”,而“法自然”以“复朴”则被认定为“长生久视”的不二法门。“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之耳聋”、“五味使人之口爽(伤)”皆对人之生有伤,“驰骋田腊(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仿(妨)”亦皆于人之生有伤;一切于生机有伤害的所作所为自当去除,“五色”、“五音”、“五味”的讲求以及对“驰骋田猎”、“难得之货”的推尚遂并在弃绝之列。
借用三章的话说,见诱于“五色”、“五音”、“五味”,纵欲于“驰骋田猎”、“难得之货”即是“见可欲”。三章申释“圣人之治”是从“不见可欲”——“不上贤”、“不贵难得之货”——说起的,与之相应,本章则转换了一个角度,告诫人们如果“见可欲”便可能使人“目盲”、“耳聋”、“口爽(伤)”、“心狂”、“行仿(妨)”而伤身害生。于是,由此引出的“圣人之治”遂颇可与三章的说法相比拟:三章将其归结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本章则谓之为“为腹而不为目”。其实,“为腹”与“为目”的对举,正相当于“实”与“虚”、“强”与“弱”的对举。“为腹”即是“实其腹”、“强其骨”,“为目”即是放纵而非“虚”、“弱”其“心”、“志”;前者乃顺应自然之需求而不失人生之浑朴,后者则使心志孜孜于攫取而逞其巧智与诡诈。老子如此称述“圣人之治”或被后世注者视为愚民的策略,然而,可予分辨的是,其由“腹”、“目”之别而说“愚”,这“愚”原只是“朴”的同义语,而且,这“朴”而“愚”的教化的践履正在于求取“圣人之治”者的“我欲不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