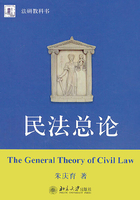
第八节 中国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缘起
“法律行为”并非我实证法上的法定术语,与之相当的,是“民事法律行为”。
(一)前《民法通则》的民事法律行为
1949年以后的新政府在《民法通则》之前曾有过三次民法典起草经历,但“民事法律行为”概念在历次草案中均未出现。立法者所考虑的问题,是究竟在“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两概念中作出选择,还是直接废弃“法律行为”概念。
据张俊浩教授考证,立法文件中,“民事法律行为”一语始见于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稿)。 就笔者所掌握的原始资料而言,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1985年4月13日的《民法总则(内部讨论稿)》,该稿第四章名为“民事法律行为”,计8条(第48—55条)。其中,第48条为立法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设定、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不过,学术著作中,“民事法律行为”之出现远早于此。
就笔者所掌握的原始资料而言,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1985年4月13日的《民法总则(内部讨论稿)》,该稿第四章名为“民事法律行为”,计8条(第48—55条)。其中,第48条为立法定义:“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设定、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不过,学术著作中,“民事法律行为”之出现远早于此。
1958年,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民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基本问题》一书出版,此亦新政权下的第一部民法教科书。在论及法律事实的分类时,该书指出,行为可以区别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两类,最主要的合法行为便是民事法律行为。所谓“民事法律行为”,“可以简称为法律行为。它是公民或法人自觉地以发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术文献。在此,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同义概念出现。
这是笔者所见最早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术文献。在此,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同义概念出现。
之后,作为“全称”的民事法律行为术语虽未获青睐——通行的是法律行为这一“简称”,但仍不时出现于教科书。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定:民事法律行为简称法律行为。 问题是,为何法律行为能够被当作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而具有相同含义?对此,张佩霖先生的说法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他认为,“法律行为这个命题,准确的说,应该是指民事法律行为,你不加上民事两个字加以限制,那么包不包括刑事上的法律后果呢?其他法律部门管的法律后果很多,是不是全叫法律行为?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刑法只有叫犯罪行为,而没有叫法律行为的。所以我认为准确的说,应该叫它为民事法律行为。”
问题是,为何法律行为能够被当作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而具有相同含义?对此,张佩霖先生的说法或许能够提供一种解释。他认为,“法律行为这个命题,准确的说,应该是指民事法律行为,你不加上民事两个字加以限制,那么包不包括刑事上的法律后果呢?其他法律部门管的法律后果很多,是不是全叫法律行为?我认为不是的。因为刑法只有叫犯罪行为,而没有叫法律行为的。所以我认为准确的说,应该叫它为民事法律行为。” 显然,在张先生看来,所谓法律行为,只能发生民法上的法律效果,其他法域的行为则不得以法律行为相称。换言之,民法之外无法律行为。因此,前缀“民事”二字,意在表明法律行为的专属法律领域。
显然,在张先生看来,所谓法律行为,只能发生民法上的法律效果,其他法域的行为则不得以法律行为相称。换言之,民法之外无法律行为。因此,前缀“民事”二字,意在表明法律行为的专属法律领域。 如此即可理解,为何民事法律行为能够简称为法律行为。就法域的把握而言,张先生的见解可谓相当准确。可惜,这一语用逻辑不仅未必见赏于彼时学界,其后发展更是与之渐行渐远。
如此即可理解,为何民事法律行为能够简称为法律行为。就法域的把握而言,张先生的见解可谓相当准确。可惜,这一语用逻辑不仅未必见赏于彼时学界,其后发展更是与之渐行渐远。
(二)《民法通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令“民事法律行为”成为法定术语,“法律行为”随之正式退隐幕后。《民法通则》第54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这一概念创造,一度被盛赞为“世界民法立法史上的一个独创”,原因在于,“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上更加完善的概念体系”。 假若民事法律行为仅仅是法律行为的“全称”,如此高调颂扬显然师出无名。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了何种语用变化,以至于能够承载中国立法者的光荣与梦想?
假若民事法律行为仅仅是法律行为的“全称”,如此高调颂扬显然师出无名。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了何种语用变化,以至于能够承载中国立法者的光荣与梦想?
二、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语用逻辑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赋值考量
关于《民法通则》创造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重要意义,佟柔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一书曾作如下概括:“它能使人们避开以往法学界对法律行为一词所持多种理解而造成的歧义。在民法通则里的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体系中,如果是要在本来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行为’概念,可将其称之为‘民事法律行为’,这样,民事法律行为就同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如行政行为、刑事行为等)区分开了;如果是要在扩大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行为’的概念,则可将其称之为‘民事行为’,这样,民事行为概念就成为统率民法中所有行为的总概念。” 就其文意理解,所谓“本来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似乎意指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而“扩大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则是指囊括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的一切民法上的行为。概念使用的逻辑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民事法律行为”之术语,一方面通过“民事”二字划定行为所属法域,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二字界定合法性特征。于是,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不再是同一概念的简称与全称关系,或者说,法律行为已不能被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因为二者已非等值概念。
就其文意理解,所谓“本来意义”上的法律行为,似乎意指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而“扩大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则是指囊括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的一切民法上的行为。概念使用的逻辑虽然不是很清晰,但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理解:“民事法律行为”之术语,一方面通过“民事”二字划定行为所属法域,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二字界定合法性特征。于是,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间,不再是同一概念的简称与全称关系,或者说,法律行为已不能被视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简称,因为二者已非等值概念。
上述概括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毋宁说,它近乎忠实地记录了立法者的考量。
首先,关于合法性。早在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之时,立法者曾对“法律行为”概念存有疑虑。1956年11月28日提出的《总则部分讨论题》中,即有“法律行为是否包括不合法的?‘无效法律行为’的提法是否妥当?”之问题。而主张弃用法律行为概念的理由之一亦在于:“如果规定的象苏俄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一样的东西,没有办法解决法律行为是指合法的,但又产生法律行为无效的矛盾问题,而按照‘民事行为’来规定则不发生这一矛盾。” 不过,直到第三次民法典起草结束,立法者似乎仍未就此问题形成确信,而安于在立法定义中保持沉默。
不过,直到第三次民法典起草结束,立法者似乎仍未就此问题形成确信,而安于在立法定义中保持沉默。
打破沉默的,是1985年7月10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讨论稿)》。该稿第6章以12个条文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并将其定义为:“民事权利主体以设定、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为目的,符合法律规定和要求的行为。”对此,讨论稿所附《“民事法律行为”说明》表示:“民事行为多反映当事人的自主权利和自由意志,因而易流于放任,故第一条强调‘合法’为其特征,借以树立行为标准,防止非法行为。”
其次,关于法域区分。上述《“民事法律行为”说明》同时指出:“‘法律行为’始见于德国民法,原有‘民事’的含意,后为各国采用时多不加‘民事’二字。现在法律部门标立,法律行为一词渐有泛指一切有法律后果和法律意义的行为的趋势。本章定为‘民事法律行为’,以示区别。”这意味着,“民事”二字不再如张佩霖先生般用以强调法律行为之民法专属性质,毋宁说,它已被当作限制成分。所表达的语用逻辑是,“法律行为”在所有法律领域均有其意义,为民法所规制者,不过是民事领域的“法律行为”而已。“民事法律行为”构词依旧,用法却已判然有别。
然而,法域区分之考量虽可为“民事”二字的出现提供说明,仅仅是为了区分法域,却又似乎难以承受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作为“世界民法立法史上的一个独创”之重。在《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看来,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意义,“体现在创造了‘民事行为’这一概念上”。 为此,尚需对民事行为的含义略作考察。
为此,尚需对民事行为的含义略作考察。
(二)民事行为的含义
“民事行为”术语其实并非始创于《民法通则》,早在新政权第一次起草民法典之时即曾与“法律行为”互较长短,并在第三与第四草案中胜出,成为正选概念。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民法通则》创造了民事行为的独特用法。
因此,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民法通则》创造了民事行为的独特用法。
第一次民法典起草时的民事行为概念虽被用以取代法律行为,但它不是法律行为之同义表达。第四草案民事行为章备有三种写法,均将民事行为定义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根据写法二之另案表述,民事行为具体可分两类:一是“以设定、变更、废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二是“虽不是以上述为目的,但由于其行为而引起民事法律后果”。 显然,前者相当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后者则涵盖除法律行为之外其他一切“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不法行为亦在其列。换言之,彼时所谓民事行为,对应于德国法之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
显然,前者相当于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后者则涵盖除法律行为之外其他一切“引起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不法行为亦在其列。换言之,彼时所谓民事行为,对应于德国法之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
民事行为在第一次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回避“无效法律行为”表述之矛盾。这一“优势”在第三次民法典起草期间再次引起学者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述,当属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民法教程》。该书出版于《民法通则》之前,却未如其他教科书般使用法律行为概念,而直接把民事行为作为固定术语,并明确指出:“用民事行为,可以避免法律行为理论上的缺陷。传统的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与违法行为相并列。同时又将法律行为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两种。这种传统的分类,其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为什么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又是无效的?我们用民事行为这个概念也是为了避免上述缺陷。” 惟值注意者,较之以往,民事行为概念的用法已发生变化。依《民法教程》之见,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为达到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
惟值注意者,较之以往,民事行为概念的用法已发生变化。依《民法教程》之见,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为达到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以意思表示为基本要素。 显然,此处所称民事行为,系表示行为之谓,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均被排除于外。这一别出心裁的用法为《民法通则》所接受。
显然,此处所称民事行为,系表示行为之谓,事实行为与侵权行为均被排除于外。这一别出心裁的用法为《民法通则》所接受。
《民法通则》第58—61条及66条使用民事行为概念,却未作定义,其所对应者,则均属存在效力瑕疵之行为。不过,这不表示,民事行为仅指存在效力瑕疵之行为。依曾经担任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的顾昂然先生之解释,“合法的民事行为,叫做民事法律行为。这就是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区别,民事行为比民事法律行为要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可见,《民法通则》所使用的民事行为语词虽早在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之时即曾出现,但用法已相去甚远,它不再是一切产生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的总称,而仅仅对应于表示行为。
可见,《民法通则》所使用的民事行为语词虽早在第一次民法典起草之时即曾出现,但用法已相去甚远,它不再是一切产生民事法律后果之行为的总称,而仅仅对应于表示行为。
以民事行为表达传统法律行为之概念,此等语用逻辑尚未见之于其他立法例,在此意义上,称民事行为概念为《民法通则》所创,自不为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何民事法律行为概念之意义,“体现在创造了‘民事行为’这一概念上”。因为,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配套使用之后,在维持法律行为之合法性特征的前提下,诸如“无效法律行为”之类的概念得以回避,长期存在于德国学术中的合法性矛盾就此一举得到解决。如此重大的学术贡献,似乎没有理由不在世界立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法律行为概念的“合法性矛盾”
处理法律行为“合法性矛盾”之前,须先就其合法性问题作一考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如果法律行为其实本不具有合法性特征,所谓合法性矛盾,即属虚假。
(一)合法性挑战
《民法通则》颁行后,几乎所有民法教科书在论及民事法律行为时,皆自觉地与制定法保持一致,以合法性为其基本特征。对此表示异议者极为鲜见。
张文显教授对法律行为概念的检讨与建构
对《民法通则》的定义,挑战首先来自于法理学者。
据黄金荣教授考察,1949年以来的新中国法理学中,“法律行为概念的地位一直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局面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 而法律行为概念的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93年张文显教授所著之《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出版”。
而法律行为概念的地位上升,“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993年张文显教授所著之《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的出版”。 在该书中,张教授将“法律行为”视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要论题”,并为之单辟一章。
在该书中,张教授将“法律行为”视为“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要论题”,并为之单辟一章。 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法律行为”,“为各部门法学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
目的在于,通过深入系统地研究“法律行为”,“为各部门法学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原理”。
法律行为概念首出民法,讨论起点当然亦在于此。《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行为。这显然是构建适用于所有法域之一般“法律行为”理论的障碍,不能不予以清除。张文显教授正是循此思路展开论述。在他看来,源自德国的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原初含义虽然是“合法的表意行为”,“但是,在苏联的法学理论体系中,‘法律行为’是一个涵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属性的行为的广义概念和统语,而不限于狭义的合法的表意行为”。受其影响,“从50年代开始,我国的法学家,尤其是法理学家都是在广义上使用法律行为概念”。“法律行为作为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的统语本来是没有多少异议的,但自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以来,争论就发生了。” 张教授由此认为,《民法通则》不值得认可。法律行为作为“最能科学地概括和反映人们在法律领域全部活动的概念”,应该得到坚守,主要理由是:第一,在汉语中,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用来修饰“行为”的中性定语,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或“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而不是指“公平的”、“合法的”、“违法的”。因此,“法律行为”指称具有法律意义的或能够引起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第二,在逻辑上,“法律行为”的对应概念应是“非法律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这一点可以借鉴伦理学的概念方法。在伦理学中,道德行为(伦理行为)是与非道德行为(非伦理行为)相对的。第三,仅仅因为《民法通则》把“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同时用“民事行为”概念与之并行,就要改变一个学理概念的内涵以及采用了这一内涵的其他法律文件,也是不可取的。
张教授由此认为,《民法通则》不值得认可。法律行为作为“最能科学地概括和反映人们在法律领域全部活动的概念”,应该得到坚守,主要理由是:第一,在汉语中,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用来修饰“行为”的中性定语,指“具有法律意义的”或“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而不是指“公平的”、“合法的”、“违法的”。因此,“法律行为”指称具有法律意义的或能够引起一定法律效果的行为。第二,在逻辑上,“法律行为”的对应概念应是“非法律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这一点可以借鉴伦理学的概念方法。在伦理学中,道德行为(伦理行为)是与非道德行为(非伦理行为)相对的。第三,仅仅因为《民法通则》把“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同时用“民事行为”概念与之并行,就要改变一个学理概念的内涵以及采用了这一内涵的其他法律文件,也是不可取的。
张文显教授的立意虽然高远,论述亦雄辩,却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不仅关于苏联法学的概念使用张教授的认识不见得正确,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存在明显的望文生训现象。如果把“法律行为”作为德文 Rechtsgeschäft的对译语词,在通过汉语理解法律行为概念之用法时,就不能简单地在自身既有语境下作语词拆分,而必须同时置入他者的语用逻辑中。否则,概念之意义脉络可能变得面目全非。在语词构成上,“法律”与“行为”二词的结合固然无法显示行为的合法性,德国法通过这一概念所表达的私法自治理念更是难觅其踪。若据此断定,所谓“法律行为”,无非是具有法律意义之行为 ,那么,这种论证进路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如下局面:“法律行为”系 Rechtsgeschäft的汉译概念,但以汉语解释“法律行为”时,表达的却是juristische Handlung(法律上的行为)或 Handlung im Rechtssinne(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而在德国法,后者乃是 Rechtsgeschäft 的上位概念。如此转换之后,不仅 juristische Handlung与 Handlung im Rechtssinne再难汉译,与 Rechtsgeschäft 用法相同的汉语概念亦消失不见。最终,概念体系将因此需要全盘重构。
,那么,这种论证进路将无可避免地造成如下局面:“法律行为”系 Rechtsgeschäft的汉译概念,但以汉语解释“法律行为”时,表达的却是juristische Handlung(法律上的行为)或 Handlung im Rechtssinne(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而在德国法,后者乃是 Rechtsgeschäft 的上位概念。如此转换之后,不仅 juristische Handlung与 Handlung im Rechtssinne再难汉译,与 Rechtsgeschäft 用法相同的汉语概念亦消失不见。最终,概念体系将因此需要全盘重构。
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法学者开始对《民法通则》的概念定义展开反思。其中最称系统全面者,当属董安生教授。
董安生教授认为,关于法律行为概念之理解,基本上可划分为两种立场:一是主张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质,惟有效法律行为始得称为法律行为;二是不以合法性为特征,只强调法律行为中的设权意图,故而无效法律行为与可撤销法律行为皆列其中。《民法通则》代表前者,包括德国、苏联(尤其是苏联立法)在内的传统民法理论则持后一立场。 为董教授所接受的,是“传统民法理论”。理由略谓:以法律行为为合法行为,首先,难以解释为何却又存在无效、可撤销或效力待定法律行为之现象;其次,难以解释为何其下位概念合同及遗嘱却又存在合法与不合法之别的现象;再次,既造成我国民法概念体系的混乱,且不利于对外交流;最后,这一背离概念传统的做法并无充分的根据。
为董教授所接受的,是“传统民法理论”。理由略谓:以法律行为为合法行为,首先,难以解释为何却又存在无效、可撤销或效力待定法律行为之现象;其次,难以解释为何其下位概念合同及遗嘱却又存在合法与不合法之别的现象;再次,既造成我国民法概念体系的混乱,且不利于对外交流;最后,这一背离概念传统的做法并无充分的根据。
此后,越来越多学者加入到质疑者行列。 不过就理由而论,似乎皆未超出董安生教授之框架。
不过就理由而论,似乎皆未超出董安生教授之框架。
董安生教授所列理由中,前两项涉及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矛盾,后两项则事关如何对待法学传统问题。为此,关于合法性,本书尚需就法律行为概念之传统理解再作考察,尤其是当学者对于传统理解本身即持有异议之时 ,此种考察更显必要。构成学者所称传统理论者,包括德国法学与苏联法学。
,此种考察更显必要。构成学者所称传统理论者,包括德国法学与苏联法学。
(二)德国法学的用法
以董安生教授为代表的《民法通则》质疑者多认为,作为法律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未尝予法律行为以合法性特征。该项判断恐怕值得商榷。
18世纪,内特尔布拉特首先将 actus juridicus 对译为德语的 rechtliches Geschäft时,即已指出,这一概念指称“人的合法行为”——尽管他本人并未严格遵守这一用法。18世纪末,哈勒大学教授与法学院董事达贝洛(Christoph Christian von Dabelow)亦以 rechtliche Handlungen或 rechtliche Geschäfte 为拉丁文 actus juridici 或 negotia juridica的德译名,并将其定义为“以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erlaubte menschliche Handlungen)。 同一时期的巴伐利亚州埃尔兰根大学教授格林德勒(Carl August Gründler)对 rechtliche Geschäfte所作定义与达贝洛基本一致:“以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
同一时期的巴伐利亚州埃尔兰根大学教授格林德勒(Carl August Gründler)对 rechtliche Geschäfte所作定义与达贝洛基本一致:“以权利义务为标的之合法的人的行为。”
现代法律行为概念为萨维尼以降的潘德克顿法学系统阐发。在此阶段,包括萨维尼本人在内的潘德克顿法学家未再刻意突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而致力于发掘其意志决定性质。不过,无论是海泽 ,还是普赫塔
,还是普赫塔 、温德沙伊德
、温德沙伊德 、德恩堡
、德恩堡 ,在概念的分类体系中,法律行为均和不法(违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gen, rechtswidrige Handlungen, unerlaubte Verhalten)处于同一位阶,共同构成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之下位概念。法律行为与不法(违法)行为对立,这一逻辑结构表明,法律行为非属不法(违法)行为。
,在概念的分类体系中,法律行为均和不法(违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gen, rechtswidrige Handlungen, unerlaubte Verhalten)处于同一位阶,共同构成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之下位概念。法律行为与不法(违法)行为对立,这一逻辑结构表明,法律行为非属不法(违法)行为。
19世纪晚期,经过潘德克顿法学的努力,法律行为概念已趋定型。其时,法律行为之意志决定性虽得到普遍强调,但同时以合法性特征定义法律行为者,殊非罕见。波恩大学教授巴龙(Julius Baron)即其著例。巴龙首先将法律行为定义为“当事人直接指向法律效果(权利之产生、移转、终止、变更与维持)之合法(erlaubte)意思表示”。 随即又指出,法律行为之首要特征为“合法的意思表示”:“它永远都必须是合法的(合乎法律的)意思表示,否则,即便具备了与合法意思表示相同的外部特征(如抢匪对遗物的占据), (不法行为,违法行为)亦不属于法律行为。”
随即又指出,法律行为之首要特征为“合法的意思表示”:“它永远都必须是合法的(合乎法律的)意思表示,否则,即便具备了与合法意思表示相同的外部特征(如抢匪对遗物的占据), (不法行为,违法行为)亦不属于法律行为。” 更具意义的是施洛斯曼(Siegmund Schlossmann)著作。波恩大学教授施洛斯曼对于法律行为概念持批判态度。
更具意义的是施洛斯曼(Siegmund Schlossmann)著作。波恩大学教授施洛斯曼对于法律行为概念持批判态度。 但由其论述可以推知,至迟到19世纪晚期,法律行为系合法行为之观念已经得到大范围的认可。施洛斯曼认为,通说将法律行为列作不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en)的对立概念,该分类并未穷尽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当中存在既非属法律行为、又不能归入不法行为的情况,例如,驶过或走过他人土地,且因之时效取得地役权。因此,真正符合逻辑的分类应该拆列两组:(1)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2)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其中,第二组第一类(法律行为)系第一组第一类(合法行为)之一种,第一组第二类(不法行为)则为第二组第二类(非法律行为)之一种。
但由其论述可以推知,至迟到19世纪晚期,法律行为系合法行为之观念已经得到大范围的认可。施洛斯曼认为,通说将法律行为列作不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en)的对立概念,该分类并未穷尽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当中存在既非属法律行为、又不能归入不法行为的情况,例如,驶过或走过他人土地,且因之时效取得地役权。因此,真正符合逻辑的分类应该拆列两组:(1)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2)法律行为与非法律行为。其中,第二组第一类(法律行为)系第一组第一类(合法行为)之一种,第一组第二类(不法行为)则为第二组第二类(非法律行为)之一种。 由此可见,即便是批评激烈如施洛斯曼者,亦未对“法律行为系合法行为”表示怀疑。
由此可见,即便是批评激烈如施洛斯曼者,亦未对“法律行为系合法行为”表示怀疑。
《德国民法典》颁行前后的教科书中,以合法性界定法律行为之举仍随处可见。例如,罗斯托克大学教授马蒂亚斯(Bernhard Matthiass)指出,法律上的行为有不法行为(unerlaubte Handlungen)与合法行为(erlaubte Handlungen)之别。若是合法行为之法律效果系行为人意欲所致,则称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 德国枢密院法律顾问与柏林大学教授科勒(Josef Kohler)则将行为(Verkehr)分为三类:适法行为(Rechtshandlungen)、不法行为(Unrechtshandlungen)与中性行为(neutrale Tätigkeiten),其中,适法行为是指“人的意志合乎法律逻辑本质(der logischen Natur des Rechts)之行为”
德国枢密院法律顾问与柏林大学教授科勒(Josef Kohler)则将行为(Verkehr)分为三类:适法行为(Rechtshandlungen)、不法行为(Unrechtshandlungen)与中性行为(neutrale Tätigkeiten),其中,适法行为是指“人的意志合乎法律逻辑本质(der logischen Natur des Rechts)之行为” ,而私法适法行为(Privatrechtshandlungen)又包括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与附随适法行为(abhängige Rechtshandlungen)两类。
,而私法适法行为(Privatrechtshandlungen)又包括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与附随适法行为(abhängige Rechtshandlungen)两类。
所有这些,似乎都意味着,无论如何划分法律上的行为,只要有合法行为类型,之下的亚分类就必定包括法律行为。恩内克策鲁斯与冯·图尔进一步为该判断提供了佐证。
恩内克策鲁斯指出,能够依法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称“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rechtswirksame Handlungen)或“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对于法律上的行为,二分为合法或不合法(rechtmäßige oder unrechtmäßige)不尽妥当,但若非得作此划分,其中两类最属重要:“作为合法行为的意思表示,即,指向并因此决定法律效果的意思表达,以及违法行为,多属为行为人招致不利后果(基本上都是损害赔偿义务)的可归责行为。”意思表示的核心部分是法律行为,违法行为则包括侵权行为与债务不履行。 冯·图尔将法律上的行为称作“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rechtliche bedeutsame Handlungen)。与恩内克策鲁斯不同的是,在冯·图尔看来,合法与不法之划分不仅必要,而且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之最高层级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合法行为,即是法律行为。
冯·图尔将法律上的行为称作“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rechtliche bedeutsame Handlungen)。与恩内克策鲁斯不同的是,在冯·图尔看来,合法与不法之划分不仅必要,而且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之最高层级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合法行为,即是法律行为。 至于不法行为,冯·图尔指出,包括对特定关系义务之违反及对一般性义务之违反两类。
至于不法行为,冯·图尔指出,包括对特定关系义务之违反及对一般性义务之违反两类。
如今,德国法学家在阐述法律行为概念时,多从功能角度凸显其作为私法自治工具之意义,淡化甚至搁置合法性问题,相应的,合法行为与不法行为之分类亦常隐而不现。 然而,这恐怕只能说明,合法性讨论在当代文献中的重要性降低了,却似乎不能据此认为,德国法学已不再将法律行为归入合法行为之列。实际上,但凡有合法行为类型,之下的亚分类就必定包含法律行为,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许布纳(Heinz Hübner)指出,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即是与法律相关、具有法律效力之行为,包括合法行为(rechtmäßiges Verhalten oder erlaubtes Verhalten)与违法行为(Rechtswidriges Verhalten)两类。合法行为可进一步划分为法律行为型(rechtsgeschäftlicher Art)与非法律行为型(nicht rechtsgeschäftlicher Art),违法行为则包括违反法定义务(侵权行为)、违反意定义务(违约)以及违反特定结合关系中的法律义务(如缔约上过失)诸情形。
然而,这恐怕只能说明,合法性讨论在当代文献中的重要性降低了,却似乎不能据此认为,德国法学已不再将法律行为归入合法行为之列。实际上,但凡有合法行为类型,之下的亚分类就必定包含法律行为,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例如,许布纳(Heinz Hübner)指出,法律上的行为(juristische Handlungen)即是与法律相关、具有法律效力之行为,包括合法行为(rechtmäßiges Verhalten oder erlaubtes Verhalten)与违法行为(Rechtswidriges Verhalten)两类。合法行为可进一步划分为法律行为型(rechtsgeschäftlicher Art)与非法律行为型(nicht rechtsgeschäftlicher Art),违法行为则包括违反法定义务(侵权行为)、违反意定义务(违约)以及违反特定结合关系中的法律义务(如缔约上过失)诸情形。 博尔克(Reinhard Bork)亦保留了合法行为(rechtmäßige Rechtshandlungen)与违法行为(rechtswidrige Rechtshandlungen)之分类,并将侵权行为、积极侵害契约(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等归入后者,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归入前者。
博尔克(Reinhard Bork)亦保留了合法行为(rechtmäßige Rechtshandlungen)与违法行为(rechtswidrige Rechtshandlungen)之分类,并将侵权行为、积极侵害契约(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等归入后者,将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归入前者。
综上所述,情况似乎是,德国法学传统中,法律行为之合法性自始即为众多法学著述所肯定,甚至不妨认为,这一认识其实构成了德国法学主流。
(三)苏联法学的影响
德国传统对新中国未必有足够的影响力。影响新中国法律知识之形成的,主要是苏联法学。
苏联法理学译著中的法律行为
上文曾指出张文显教授对于法律行为的理解有望文生训之嫌。论者或不以为然,因为,将法律行为理解为一切能够产生法律效果之行为,此为几乎所有新中国法理学者所共举,其来源,则在苏联法理学。的确,新中国法理学家有关“法律行为”之认识,系来自于苏联法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来自于苏联法理学译著。 据黄金荣教授判断,在众多译著中,玛·巴·卡列娃等著《国家和法的理论》当属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它“对法律事实、法律行为、法律事件和事实构成含义的理解和表述,日后都似乎成了许多中国法理学教材的标准蓝本”。
据黄金荣教授判断,在众多译著中,玛·巴·卡列娃等著《国家和法的理论》当属影响最大的教科书,它“对法律事实、法律行为、法律事件和事实构成含义的理解和表述,日后都似乎成了许多中国法理学教材的标准蓝本”。 该书认为,法律事实包括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其中,如果“苏维埃法律规范把个别人本身的行为看作是这些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改变或消灭的根据,”即称“法律行为”,包括“合法的法律行为”与“违法的法律行为”两类,对于前者,该书仅举劳动法律关系与产品供应关系两例予以说明,未作进一步逻辑划分,后者则又包括犯罪、违反民法的行为、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以及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等等。
该书认为,法律事实包括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其中,如果“苏维埃法律规范把个别人本身的行为看作是这些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改变或消灭的根据,”即称“法律行为”,包括“合法的法律行为”与“违法的法律行为”两类,对于前者,该书仅举劳动法律关系与产品供应关系两例予以说明,未作进一步逻辑划分,后者则又包括犯罪、违反民法的行为、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以及违反行政法的行为等等。 看起来,苏联法学上,“法律行为”确实是所有能够产生法律效果之行为的总称,而不限于合法行为。不过,在接受这一结论之前,不妨稍作追问:苏联法理学译著中的“法律行为”,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是否同其所指?
看起来,苏联法学上,“法律行为”确实是所有能够产生法律效果之行为的总称,而不限于合法行为。不过,在接受这一结论之前,不妨稍作追问:苏联法理学译著中的“法律行为”,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是否同其所指?
限于语言能力,笔者无力考证苏联法理学著作中被汉译为“法律行为”的俄文语词。但就用法而论,卡列娃等著《国家和法的理论》中,与事件并列的“法律行为”显然指称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若质之以潘德克顿法学,与其对应的概念理当是juristische Handlung(法律上的行为),而非 Rechtsgeschäft。果若如此,新中国法理学家从苏联译著中习得的“法律行为”,即非属民法语境下的 Rechtsgeschäft,而是另外一个概念“法律上的行为”。对此,另外一部苏联法理学译著也许可为之提供佐证。
汉译阿列克谢耶夫著《法的一般理论》同样将法律事实划分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其中,“法律行为是人们的意志行为,是公民的意志和意识、组织和社会构成的意志的外在表现”。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 但在该书所列法律事实分类表上,与事件相对应的概念是“行为”,而行为之下“合法行为”的亚分类中,“法律行为(契约)”赫然在列,位阶与之相同者,是国家法行为、行政行为、诉讼行为、劳动法行为以及家庭法行为等。
但在该书所列法律事实分类表上,与事件相对应的概念是“行为”,而行为之下“合法行为”的亚分类中,“法律行为(契约)”赫然在列,位阶与之相同者,是国家法行为、行政行为、诉讼行为、劳动法行为以及家庭法行为等。 显然,和“法律事件”并列的所谓“法律行为”(行为)与分类表中以契约标注的“法律行为”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用法上,前者相当于 juristische Handlung,后者则为 Rechtsgeschäft。依笔者所信,当我国法理学者以苏联法理学译著为根据,主张“法律行为”应作“广义”理解时,实际上是用 juristische Handlung 来批评Rechtsgeschäft。张冠李戴式的望文生训在苏联法理学译著的掩护下,就此轻而易举地正当化为中国法理学者的共识。
显然,和“法律事件”并列的所谓“法律行为”(行为)与分类表中以契约标注的“法律行为”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用法上,前者相当于 juristische Handlung,后者则为 Rechtsgeschäft。依笔者所信,当我国法理学者以苏联法理学译著为根据,主张“法律行为”应作“广义”理解时,实际上是用 juristische Handlung 来批评Rechtsgeschäft。张冠李戴式的望文生训在苏联法理学译著的掩护下,就此轻而易举地正当化为中国法理学者的共识。
实际上,在苏联民法译著中,法律事实概念体系极其清晰,根本不存在法理学译著中的混乱。例如,布拉都西主编《苏维埃民法》:“法律事实可以分为:(一)事件;(二)行为。行为又分为:(甲)行政行为;(乙)法律行为——即旨在发生、变更或消灭法权关系的意思表示;(丙)没有产生法权后果的意图、但直接由法律本身而引起法权后果的合法行为;(丁)依权利形成之诉所为的法院判决;(戊)不法行为(不合法行为)。” 再如,坚金主编《苏维埃民法》:“可以把作为发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据的法律事实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国家管理机关的文件;(二)事件——不依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实;(三)人们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而行为本身又可以分为下面几种:预期达到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并无引起法律后果的目的、但由于法律有直接规定而引起这种后果的单方的行为;由于侵权而引起法律后果的非法的作为(或不作为)。”
再如,坚金主编《苏维埃民法》:“可以把作为发生、变更和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根据的法律事实分为以下几大类:(一)国家管理机关的文件;(二)事件——不依法律关系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事实;(三)人们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而行为本身又可以分为下面几种:预期达到法律后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并无引起法律后果的目的、但由于法律有直接规定而引起这种后果的单方的行为;由于侵权而引起法律后果的非法的作为(或不作为)。”
因此,除非苏联如同我国,法理学与民法学在概念使用上各行其是,否则,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苏联法学中,法律行为是与事件相并列的“广义”概念。而法理学译著中出现的概念混乱,或可归因于翻译本身。
早在1950年,新政权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即组织翻译了《苏俄民法典》。《法典》第26条系法律行为的定义:“法律行为,即设定,变更或废止民事权利关系之行为,得为单方者及双务者(契约)。”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各稿草案定义的原型。它与《民法通则》的最大不同是,未透过立法定义显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特征。但这不表示,苏联不存在相关讨论。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民法典起草各稿草案定义的原型。它与《民法通则》的最大不同是,未透过立法定义显示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特征。但这不表示,苏联不存在相关讨论。
阿加尔柯夫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讨论
学者常以为,《民法通则》之所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合法行为,是受苏联学者阿加尔柯夫的影响。其说略谓:阿加尔柯夫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法律行为必属合法行为,并进而主张,“无效法律行为”之概念是自相矛盾的,这一遭到包括诺维茨基、布拉都西、坚金等众多苏联学者批评的“不成熟观点”,却为《民法通则》所接受。 依笔者管见,这一说法恐怕值得推敲。
依笔者管见,这一说法恐怕值得推敲。
据诺维茨基介绍,阿加尔柯夫确实认为法律行为具有合法性特征,亦确实主张,“作为合法行为的法律行为有时可能是无效的这种看法,是不合逻辑的”,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法律行为不可能是无效的,无效的只可能是人们借以从事法律行为的那个意思表示”。 不过,诺维茨基所批评的,不是阿加尔柯夫奉法律行为必合法之立场,而是其“无效法律行为”概念自相矛盾、需质以“意思表示无效”之观点。诺维茨基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实际存在,当中并无矛盾。
不过,诺维茨基所批评的,不是阿加尔柯夫奉法律行为必合法之立场,而是其“无效法律行为”概念自相矛盾、需质以“意思表示无效”之观点。诺维茨基认为,无效法律行为实际存在,当中并无矛盾。 至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诺维茨基本人有如阿加尔柯夫,亦持肯定态度。他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民法书籍中有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合法或不合法并不是法律行为这一法律事实的必要特征,而只决定着法律行为的这些或那些后果。这种论断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法律行为是合法的行为,这一点乃是法律行为所特有的本质的要素之一”。
至于法律行为的合法性问题,诺维茨基本人有如阿加尔柯夫,亦持肯定态度。他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民法书籍中有这样一种见解,即认为合法或不合法并不是法律行为这一法律事实的必要特征,而只决定着法律行为的这些或那些后果。这种论断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法律行为是合法的行为,这一点乃是法律行为所特有的本质的要素之一”。 相应的,在诺维茨基看来,“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一个或几个有行为能力并作为财产权利(民事权利)主体的人所办理的旨在设定、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的、法律性质的行为”。
相应的,在诺维茨基看来,“所谓法律行为,就是一个或几个有行为能力并作为财产权利(民事权利)主体的人所办理的旨在设定、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的、法律性质的行为”。
苏联民法译著显示,以合法性定义法律行为者,非在少数。如布拉都西主编《苏维埃民法》对于法律行为的定义虽未明确显示合法性特征 ,但在论及法律事实的分类时却指出:“行为,如其不受法律禁止者,便是合法的行为。法律行为,即具有引起一定法权后果的意图而为的行为(立遗嘱、缔结买卖契约等),便是合法的法律上的行为中的主要一种。”
,但在论及法律事实的分类时却指出:“行为,如其不受法律禁止者,便是合法的行为。法律行为,即具有引起一定法权后果的意图而为的行为(立遗嘱、缔结买卖契约等),便是合法的法律上的行为中的主要一种。” 再如谢列布洛夫斯基:“法律行为属于具有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目的底合法行为。为法律行为的人是希图达成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为法律行为的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特征。但是为了那个意思表示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就要意思表示是根据了法律并是依照法定方式表现出来底。”
再如谢列布洛夫斯基:“法律行为属于具有发生一定法律效果目的底合法行为。为法律行为的人是希图达成一定的法律效果。所以为法律行为的人的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特征。但是为了那个意思表示具有法律上的效果,就要意思表示是根据了法律并是依照法定方式表现出来底。”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民法译著显示,彼邦民法理论依然持合法性立场。如格里巴诺夫与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称:“法律行为、有法律后果的行为以及包括计划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等等,都是合法行为。”
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民法译著显示,彼邦民法理论依然持合法性立场。如格里巴诺夫与科尔涅耶夫主编《苏联民法》称:“法律行为、有法律后果的行为以及包括计划行为在内的行政行为等等,都是合法行为。” 不仅如此,该书还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指的只是合法行为。”“根据多数人的见解,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同时,也有一种见解认为,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但不构成法律行为的要素。应当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于法律行为的实质。”
不仅如此,该书还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指的只是合法行为。”“根据多数人的见解,合法性是法律行为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同时,也有一种见解认为,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但不构成法律行为的要素。应当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于法律行为的实质。”
如果能够相信,上述民法译著足以代表相应时期的苏联主流,那么,就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学者对于苏联的认识也许就有调整之必要。因为,在此传统中,恰恰是支持法律行为具合法性特征的见解占有主导地位。实际上,直至今日,俄罗斯民法理论依然将法律行为划归合法行为之列。
(四)所谓合法性矛盾
阿加尔柯夫主张以“无效意思表示”取代“无效法律行为”概念,《民法通则》创造出“民事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独特用法。两种策略进路不同,想要解决的问题却无二致:法律行为既具合法性特征,无效法律行为概念便与之矛盾。《民法通则》的批评者则认为,所谓合法性矛盾其实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按照传统理解,法律行为不必是合法行为。换言之,正是因为《民法通则》无谓改变法律行为概念的既定用法,矛盾始得出现。这一釜底抽薪式的批评若能成立,给对手的打击必定是致命的。然而,本书显示,无论是德国传统,抑或苏联传统,其主流观念均与批评者的判断大相径庭。
局势似乎因此变得峰回路转:既然《民法通则》并未改变传统语用逻辑,以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有效之法律行为、其他则归诸民事行为之策略,便无可非议;非但如此,由于即使德国亦未避免无效法律行为这一矛盾概念,誉之为“世界民法立法史上的一个独创”,自不为过。
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民法通则》的解决之道,虽然曾备受赞誉,但亦非全然未遭批评。例如,寇志新教授指出,即使将无效行为以民事行为相称,问题依然未能得到解决,因为,部分无效的行为,以及可撤销(可变更)但超过除斥期间却未作撤销(变更)的行为,究竟是属于“民事法律行为”,抑或“民事行为”,令人困惑。 张俊浩教授的批评则独辟蹊径,他表示,无效法律行为和可撤销法律行为“这两个被非议的语词,具有储藏特别信息的修辞价值,而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其实,在我们的语言中,类似的修辞用法并非罕见,例如‘假革命’、‘假党员’、‘未婚妻’就是。如均目为语义矛盾,岂不等于放弃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修辞手段?”
张俊浩教授的批评则独辟蹊径,他表示,无效法律行为和可撤销法律行为“这两个被非议的语词,具有储藏特别信息的修辞价值,而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其实,在我们的语言中,类似的修辞用法并非罕见,例如‘假革命’、‘假党员’、‘未婚妻’就是。如均目为语义矛盾,岂不等于放弃了一种颇有价值的修辞手段?” 将众多学者眼中的法学难题化之以“修辞手段”,这一举重若轻的处理虽然难免予人过度简化之感
将众多学者眼中的法学难题化之以“修辞手段”,这一举重若轻的处理虽然难免予人过度简化之感 ,但它同时启示了另外一条思维进路: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无效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逻辑矛盾?
,但它同时启示了另外一条思维进路:法律行为的合法与无效之间是否真的存在逻辑矛盾?
法律领域,概念定义有以立法作出者——称立法定义(Legaldefinition),亦有学术性的本质定义(Wesensdefinition)。二者目标不同,定义方法亦各异。立法定义属于描述性规范(umschreibende Rechtssätze),意义在于,通过构成要素之描述为法律规范中的概念作出界定,以便寻找可供适用的法律规则。例如,《合同法》第21条系关于承诺的立法定义:“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据此,构成一项承诺需要具备的要素是:第一,须为意思表示;第二,意思表示的内容须对要约表示同意。两项要素缺乏其一,即不构成第21条所称承诺,法律适用时,亦不得适用有关承诺的各项规则。本质定义旨在揭示概念的逻辑本质,与立法定义判然有别。本质定义所指向的,是被定义事物之“共相”。 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系本质定义。其意义在于指明,在抽象的层面,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理性,而不是说,构成一个具体人,必须具备理性要素。因而,“非理性人是人”命题不与“人是理性动物”之定义相抵触。虽然均在使用“人”这一概念,但论域不同,概念所指其实并不相同。其中,“非理性人”之“人”对应具体的个人,而“人是理性的动物”之“人”,则为人之共相,系抽象之人。
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系本质定义。其意义在于指明,在抽象的层面,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拥有理性,而不是说,构成一个具体人,必须具备理性要素。因而,“非理性人是人”命题不与“人是理性动物”之定义相抵触。虽然均在使用“人”这一概念,但论域不同,概念所指其实并不相同。其中,“非理性人”之“人”对应具体的个人,而“人是理性的动物”之“人”,则为人之共相,系抽象之人。
以此返观法律行为的定义。学术上,称“法律行为是根据意思表示内容发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合法行为”,系本质定义。此时所谓“法律行为”,乃是法律行为的抽象共相。这一命题与“无效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之命题并不抵触,因为,“无效法律行为”指称的是具体的法律行为。这一观念,实际上早在《德国民法典》制定之初,即已为齐特尔曼(Ernst Zitelmann)所揭示:“概念定义,乃是针对正常的法律行为而论,各种非正常状态对之不构成影响。” 所谓“正常的法律行为”,表达的正是共相之谓。然而,立法定义法律行为时,任务不在于揭示抽象法律行为的共相本质,而是描述判断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以便法律适用。若将法律行为合法性之逻辑共相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立法定义,“合法”便成为鉴别概念的构成要素。不具备该要素者,即不得称此概念,亦不得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因而,《民法通则》第54条将合法性纳入定义之时,“无效法律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之两难追问即已生成:一方面,既然每一项法律行为都必须具备合法之要素,因为违法而无效的法律行为怎么可能是法律行为?另一方面,行为之所以无效,恰恰是适用法律行为规则(如行为能力欠缺、意思表示瑕疵等)的结果。能够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则,又怎么可能不是法律行为?
所谓“正常的法律行为”,表达的正是共相之谓。然而,立法定义法律行为时,任务不在于揭示抽象法律行为的共相本质,而是描述判断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以便法律适用。若将法律行为合法性之逻辑共相以立法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立法定义,“合法”便成为鉴别概念的构成要素。不具备该要素者,即不得称此概念,亦不得适用相应的法律规则。因而,《民法通则》第54条将合法性纳入定义之时,“无效法律行为是否属于法律行为”之两难追问即已生成:一方面,既然每一项法律行为都必须具备合法之要素,因为违法而无效的法律行为怎么可能是法律行为?另一方面,行为之所以无效,恰恰是适用法律行为规则(如行为能力欠缺、意思表示瑕疵等)的结果。能够适用法律行为的规则,又怎么可能不是法律行为?
可见,所谓“合法性矛盾”,其实是立法者误以学术定义的方法进行立法定义所导致的。如果立法者能够分清学术与立法的界限,不将本质定义与立法定义强行并轨,也就不会存在需要解决的“旷世难题”。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德国学界普遍认为法律行为系合法行为,立法却未作此等定义。实际上,《德国民法典》对于法律行为甚至根本未作定义。虽然立法定义能够界定概念的构成要素,从而有助于法官适用法律,但法典的制定者面对法律行为这一如此核心的概念时,却选择了沉默。立法者的考虑是,“司法裁判也许会(因为缺乏明确的立法定义而)犹疑不定,甚至将法律行为之关键性原则适用于本不具有法律行为性质的行为之上,或者对真正的法律行为发生错认,但尽管如此,比之僵硬的概念定义,它所带来的误导危险当较为微小。” 在某种程度上,概念越是重要,立法者就越是需要谨慎克制。《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对其权力行使的节制意识,也许值得我国立法者三思。
在某种程度上,概念越是重要,立法者就越是需要谨慎克制。《德国民法典》立法者对其权力行使的节制意识,也许值得我国立法者三思。
四、“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域区分价值
(一)潘德克顿法学中的法域界定
除解决合法性矛盾之外,《民法通则》创造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另外一项贡献被归结为,“民事”二字把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从其他法域中区分出来。显然,想要印证此项贡献,就必须回答:法律行为是否同样存在于其他法域?为寻找答案,首先需要考察法律行为概念出现之初的使用情况。对此,温德沙伊德与德恩堡等潘德克顿法学家有过明确阐述。
依温德沙伊德之见,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类,是指向权利设立、消灭与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与裁判意思表示(die richtlichen Willenserklärungen)相对立。 温氏进而认为,普赫塔等人仅以“根据意思表示而变动权利”定义法律行为,颇有不当,“因为这样一来,法院裁判也是法律行为了”。
温氏进而认为,普赫塔等人仅以“根据意思表示而变动权利”定义法律行为,颇有不当,“因为这样一来,法院裁判也是法律行为了”。 在《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第1卷第6版中,温德沙伊德更是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实施者并非根据国家权威而行为。”
在《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第1卷第6版中,温德沙伊德更是特别强调:“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实施者并非根据国家权威而行为。” “因此,尤其是法院裁判,虽然也包含一项处分,但它并非法律行为。”
“因此,尤其是法院裁判,虽然也包含一项处分,但它并非法律行为。” 德恩堡与温德沙伊德见解相似,他指出:“公权处分(尤其是裁判)不是法律行为”,虽然时有将法律行为概念扩展至其他领域者,但其所谓“法律行为”既呆板(farblos)又不准确(unpräzis),因而不足为训。
德恩堡与温德沙伊德见解相似,他指出:“公权处分(尤其是裁判)不是法律行为”,虽然时有将法律行为概念扩展至其他领域者,但其所谓“法律行为”既呆板(farblos)又不准确(unpräzis),因而不足为训。 温德沙伊德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民法典》总则编预案的起草者格布哈特所接受,后者在撰写预案的立法理由时,明确表示:“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机关为国家事务所为之处分,尤其是司法处分,不在此概念之列。”
温德沙伊德等人的研究成果为《德国民法典》总则编预案的起草者格布哈特所接受,后者在撰写预案的立法理由时,明确表示:“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机关为国家事务所为之处分,尤其是司法处分,不在此概念之列。”
不过,上述考察结果尚无充分的说明价值,因为,法律行为概念原本专属于民法,论者多不予否认,批评者所要表达的是,随着法学理论的发展,法律行为逐渐扩及至其他法域。为此,下文尚需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潘德克顿法学家基于何种考虑将法律行为当作私法专属概念?二是公法领域是否有法律行为的容身之地?
(二)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
德国法学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的工具。不过,新中国的语用逻辑与之相去甚远。
在苏俄的影响下,新中国从启动民法典编纂之始,即将法律行为简单地作“设定,变更或废止民事权利关系之行为”理解,德国传统理论一直强调的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未引起立法者太多关注 ,借助法律行为而彰显的私法自治理念当然更是无从谈起。非但如此,学者亦往往遵从意识形态话语,为配合社会主义的管制需要,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
,借助法律行为而彰显的私法自治理念当然更是无从谈起。非但如此,学者亦往往遵从意识形态话语,为配合社会主义的管制需要,猛烈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 直至20世纪90年代,正面张扬此等理念者方始偶见于学者著述。
直至20世纪90年代,正面张扬此等理念者方始偶见于学者著述。 但旋即又遭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衰落”论的强力阻击。
但旋即又遭遇“意思自治(契约自由)衰落”论的强力阻击。 私法自治理念命运之多舛,良有以也。
私法自治理念命运之多舛,良有以也。
意志决定性抽出之后,合法性问题随即被推到了概念讨论的前台。于此可以理解,为何新政权以来,法律行为合法性问题一直盘踞着概念讨论的中心,历经数十年而不堕。
法律行为的合法性当然值得讨论。问题在于,新中国对于法律行为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偏离应有的航道,在抽空意志决定性的背景之下,合法性讨论往往在加剧偏离的同时更使问题变得隐蔽难察,从而导致真正的关键之点反被忽略。实际上,于德国法学而言,法律行为概念的核心根本不是所谓的合法性,而是行为人意志与法律效果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惟有如此,它才能够成为私法自治的工具。前文对于德国法律行为概念的梳理谅已表明,这一观念至少自萨维尼开始,即根深蒂固地贯穿于法律行为概念的整个历史脉络。在此意义上,新中国继受法律行为概念,却又剔除蕴含其间的私法自治理念,此举实与买椟还珠无异。
温德沙伊德论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
埃森哈特(Ulrich Eisenhardt)指出,温德沙伊德有关法律行为之见解代表了19世纪德国通说,从而为民法典采信。 而关于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的内在关联,在其《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的历次修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关于法律行为与私法自治的内在关联,在其《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的历次修订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1862年,温德沙伊德《学说汇纂法学教科书》第1卷首版问世,其中,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种,已被明确界定为“指向”权利设立、消灭与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 ,其私法属性彰显无遗。不过,在正式定义法律行为时,温德沙伊德的表述是:“法律行为是以权利设立、消灭或发生变更为内容的私人意思表示。”(Rechtsgeschäft ist die Willenserklärung einer Privatperson des Inhalts, das ein Recht entstehen, untergehen, oder eine Veränderung erleiden solle.)
,其私法属性彰显无遗。不过,在正式定义法律行为时,温德沙伊德的表述是:“法律行为是以权利设立、消灭或发生变更为内容的私人意思表示。”(Rechtsgeschäft ist die Willenserklärung einer Privatperson des Inhalts, das ein Recht entstehen, untergehen, oder eine Veränderung erleiden solle.) 法律效果与意思表示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得到足够明白的表达。
法律效果与意思表示之间的内在关联,尚未得到足够明白的表达。
1879年教科书出至第5版时,法律行为的界定方式发生变化:“法律行为是指向权利设立、消灭或变更的私人意思表示。”(Rechtsgeschäft ist die auf die Entstehung, den Untergang oder die Veränderung von Rechten gerichtete Privatwillenserklärung.) 此时,法律行为被明确定义为“指向”权利变动的意思表示。通过法律行为实现私法自治的观念已是呼之欲出。
此时,法律行为被明确定义为“指向”权利变动的意思表示。通过法律行为实现私法自治的观念已是呼之欲出。
1887年的第6版不仅继续突出意思表示对于法律效果的“指向”性,更详细说明法律行为概念之私法属性:
“法律行为是指向法律效果之创设的私人意思表示(Rechtsgeschäft ist eine auf die Hervorbringung einer rechtlichen Wirkung gerichtete Privatwillenserklärung)。
1.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它表达法律效果应得实现之意思,而法律制度亦因此听其实现,原因在于,它为法律行为的实施者所欲求。
2.法律行为是私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的实施者并非根据国家权威而行为。
3.法律行为指向的是法律效果之创设。法律行为的最终目的总在权利(或权利集合)的设立、消灭或变更,不过,它无需直接指明权利的设立等效果。
4.法律行为只是指向法律效果之创设。所欲求的法律效果是否确实通过法律行为得到实现,以及是否得到立即实现,不属于法律行为的概念范围。”
如果能够了解,法律行为概念之创造,系用以指称私法领域中法律效果为意志所规定的自治行为,那么,以之为私法专有概念,实属理所当然。因为,私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公法)领域中,当事人行为并不奉行自治原则。就此而言,无论法学理论如何发展,只要公法与私法的界分仍属必要,法律行为就不可能扩及至私法之外的其他法域。再者,若是认为,法律行为不仅存乎私法领域,诸如“行政法律行为”等概念亦能成立,因此需要另创“民事法律行为”术语以示区别,除非论者一并声称自治理念已扩及至公法领域,否则,此等见解即意味着,“法律行为”作为“行政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等的上位概念,不再用以指称效果为意志所决定的自治行为,而仅仅是一切具有法律意义之行为的通称。
(三)法律行为与行政行为
前述论证似乎不过是单纯的理念推衍,实际情况是,许多学者主张,至少在行政法领域,法律行为概念亦有其容身之所。 为此,尚需对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略作观察。
为此,尚需对行政法中的“法律行为”略作观察。
德国行政法上所谓 Verwaltungsakt 概念,系法语 acte administratif之德译。
概念,系法语 acte administratif之德译。 其含义为,国家公权力者为形成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而实施的单方行为。
其含义为,国家公权力者为形成公法上的法律关系而实施的单方行为。 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理论为19世纪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Otto Mayer)首创,以服务于法治国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之目的。
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理论为19世纪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Otto Mayer)首创,以服务于法治国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之目的。 许宗力教授指出,行政行为概念指涉极为广泛,兼跨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与救济法领域,并且在不同的领域有其不同的功能。例如,行政行为在实体法上具有明确界定国家与人民权利义务关系,以提升法安定性的功能,在执行法上充当执行名义,在救济法上则是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
许宗力教授指出,行政行为概念指涉极为广泛,兼跨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与救济法领域,并且在不同的领域有其不同的功能。例如,行政行为在实体法上具有明确界定国家与人民权利义务关系,以提升法安定性的功能,在执行法上充当执行名义,在救济法上则是提请救济的前提要件。
在能够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方面,诸如警察命令及形成性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授予许可证、任命公务员)等行政行为与法律行为类似。 就此而言,行政行为无妨以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相称。
就此而言,行政行为无妨以行政法上的意思表示相称。 然而,行政行为终究不是法律行为,即便存在法律行为式的行政行为(rechtsgeschäftlicher Verwaltungsakt)之语词,一般观念仍然认为,行政行为与私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迥然有别。
然而,行政行为终究不是法律行为,即便存在法律行为式的行政行为(rechtsgeschäftlicher Verwaltungsakt)之语词,一般观念仍然认为,行政行为与私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迥然有别。
法律行为包括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契约),行政行为则必为单方行为 ,除此之外,依弗卢梅概括,二者尚有如下差别:第一,行政行为不适用私法自治,而适用依法行政原则;法律行为则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第二,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自决;行政行为则在内容的法定性。第三,对于行政行为而言,需要考察的是,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以及行为是否依法律的指示而实施,当中并不存在公职人员的创造性意志形成空间,甚至,只要“依法作出并且合乎事理”,即便是精神病公职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亦属有效;相反,意志因素对于法律行为至关重要,精神病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第四,行政行为中,意志因素亦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表现为行政“裁量”。不过,行政裁量必须受制于义务思想(Pflichtgedanken),换言之,公职人员在作出裁量行为时,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否则,即存在裁量瑕疵(Ermessensfehler)或裁量权滥用(Ermessensmißbrauch),该行政行为亦相应变得有瑕疵。第五,行政行为是公权力行使行为,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法律行为则必须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取得强制执行力。第六,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是,行政行为的内容原则上为法律所确定;法律行为、尤其是债权契约,则奉行内容形成自由原则。
,除此之外,依弗卢梅概括,二者尚有如下差别:第一,行政行为不适用私法自治,而适用依法行政原则;法律行为则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第二,法律行为的核心在于自决;行政行为则在内容的法定性。第三,对于行政行为而言,需要考察的是,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以及行为是否依法律的指示而实施,当中并不存在公职人员的创造性意志形成空间,甚至,只要“依法作出并且合乎事理”,即便是精神病公职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亦属有效;相反,意志因素对于法律行为至关重要,精神病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第四,行政行为中,意志因素亦具有一定的活动空间,表现为行政“裁量”。不过,行政裁量必须受制于义务思想(Pflichtgedanken),换言之,公职人员在作出裁量行为时,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导向,否则,即存在裁量瑕疵(Ermessensfehler)或裁量权滥用(Ermessensmißbrauch),该行政行为亦相应变得有瑕疵。第五,行政行为是公权力行使行为,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法律行为则必须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取得强制执行力。第六,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是,行政行为的内容原则上为法律所确定;法律行为、尤其是债权契约,则奉行内容形成自由原则。
可见,虽然行政行为理论系借鉴法律行为而来,但不过是技术模仿(如有关行为之分类、行为之无效或可撤销规则等)之产物,其间理念不可同日而语。行政行为并非法律行为扩及至行政法领域的结果,不是“行政法律行为”(Verwaltungsrechtsgeschäft或 verwaltungsrechtliches Rechtsgeschäft),而仅仅是行政行为(Verwaltungsakt)。
Rechtsgeschäft的翻译
在某种意义上,依西方学术范式而建立的中国法学乃是翻译学术。这不仅表现在几乎所有法律术语皆自翻译而来,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对于现代法学思维脉络的想象,基本上都是在翻译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法律行为”的不同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因为翻译所致。“法律”与“行为”两个平淡无奇的汉语词汇组合,在字面上,既难以传达合法性的信息,更无法让人将其与私法自治理念建立联系,而望文生义的“具有法律意义之行为”理解,倒显得自然顺畅。问题是,是否有更合适的对译语词?
用“法律行为”表达德文 Rechtsgeschäft,并不是中国学者的创造,而来自于日本。 与日本翻译 Rechtsgeschäft 时有过激烈争论不同
与日本翻译 Rechtsgeschäft 时有过激烈争论不同 ,我国也许是因为有成例可循,在接受法律行为之译名过程中,未曾表现出太多踯躅。这一局面,直至近年方始有所改观。例如,米健教授认为,以“法律行为”对译 Rechtsgeschäft,其实是概念错译。因为,另外一个德文概念 Rechtshandlung才是真正的“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直接为法律所设定,而 Rechtsgeschäft的正确译法应该是“法律交易”。
,我国也许是因为有成例可循,在接受法律行为之译名过程中,未曾表现出太多踯躅。这一局面,直至近年方始有所改观。例如,米健教授认为,以“法律行为”对译 Rechtsgeschäft,其实是概念错译。因为,另外一个德文概念 Rechtshandlung才是真正的“法律行为”,其法律效果直接为法律所设定,而 Rechtsgeschäft的正确译法应该是“法律交易”。
Handlung一词的汉语直译是“行为”, Geschäft在日常用法上则有“交易”之含义。因而,以“法律行为”对译 Rechtshandlung、“法律交易”对译 Rechtsgeschäft,系语词直译。需要讨论的问题因而在于,是否有必要依此直译改造既有翻译?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首先,将 Rechtshandlung直译为“法律行为”未必准确。
德国法律用语上,Rechtshandlung 不是一个有固定用法的语词。依使用者的偏好,至少有四种用法。各种用法的涵盖范围有所不同。首先,在最广义上,Rechtshandlung指称一切能够产生法律效果之行为,包括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其中,合法行为又包括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违法行为则包括侵权行为与契约法上的违法行为。 此时,Rechtshandlung 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与juristische Handlung同义,可译作“法律上的行为”。其次,法律上的行为可能被二分为Rechtsgeschäft与Rechtshandlung。除Rechtsgeschäft外,其他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都属于 Rechtshandlung,包括违法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三类。
此时,Rechtshandlung 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与juristische Handlung同义,可译作“法律上的行为”。其次,法律上的行为可能被二分为Rechtsgeschäft与Rechtshandlung。除Rechtsgeschäft外,其他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都属于 Rechtshandlung,包括违法行为、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三类。 显然,此处所遵从的区分标准是法律效果是否根据行为人意志而产生。Rechtshandlung 被用以指称“效果法定行为”,与 Rechtsgeschäft并峙而立。再次,Rechtshandlung 可能被用作所有合法行为的共同上位概念,包括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
显然,此处所遵从的区分标准是法律效果是否根据行为人意志而产生。Rechtshandlung 被用以指称“效果法定行为”,与 Rechtsgeschäft并峙而立。再次,Rechtshandlung 可能被用作所有合法行为的共同上位概念,包括法律行为(Rechtsgeschäft)、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 此时,Rechtshandlung与 rechtmäßige Handlung或 erlaubte Handlung同义,可译作“合法行为”或“适法行为”。最后,合法行为可能被二分为 Rechtsgeschäft 与 Rechtshandlung。除 Rechtsgeschäft外,其他一切合法行为均归为 Rechtshandlung,包括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这一用法为较多学者所采。
此时,Rechtshandlung与 rechtmäßige Handlung或 erlaubte Handlung同义,可译作“合法行为”或“适法行为”。最后,合法行为可能被二分为 Rechtsgeschäft 与 Rechtshandlung。除 Rechtsgeschäft外,其他一切合法行为均归为 Rechtshandlung,包括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这一用法为较多学者所采。 在此用法下,由于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共同特点在于效果法定,故可将 Rechtshandlung译作“合法的效果法定行为”。
在此用法下,由于准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共同特点在于效果法定,故可将 Rechtshandlung译作“合法的效果法定行为”。
Rechtshandlung存在如此之多相去甚远的用法,简单的概以“法律行为”直译,对于语词含义之理解,显然无所助益。更为务实的做法是,根据使用者的不同用法,分别选择对译语词。同时,如论何种用法,Rechtshandlung 的意义均极为有限,因为,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各行为类型相去甚远,难以抽象出一般性的法律规则适用于所有的Rechtshandlung ,况且,用法如此漂移不定,以至于内涵外延均不确定,不可能是法学上的重要概念,《德国民法典》甚至根本未出现这一概念即其明证。
,况且,用法如此漂移不定,以至于内涵外延均不确定,不可能是法学上的重要概念,《德国民法典》甚至根本未出现这一概念即其明证。
其次,以“法律交易”直译 Rechtsgeschäft未必能够清除概念理解障碍。
在传达合法性与私法自治理念方面,“法律交易”并不比“法律行为”更有优势。不仅如此,“法律交易”之译法,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在汉语语境之下,将抛弃等单方行为称为“单方法律交易”,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称身份法领域亦存在“法律交易”,同样令人费解;法律行为最重要的分类负担行为(Verpflichtungsgeschäft)与处分行为(Verfügungsgeschäft),若分别更名为“负担交易”与“处分交易”,所带来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理解上的困难,更有汉语构词法的变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实际上,若要诉诸构词法,Geschäft的原初含义其实并非“交易”。Geschäft来自于Schaffen,因而,更为彻底的语义分析亦当追溯至此。就此问题,早有学者指出, Rechtsgeschäft从 Schaffen中提取的不是字面上的“劳作”(Arbeiten)之义,更多的指向“创造”(Produziren)。就此而言,所谓 Rechtsgeschäft,是指“创造法律意义之行动”(eine Thätigkeit, die rechtlich Bedeutsames schafft)。 不仅如此,其间关键尚在于,“该法律意义或称效果能够被理解为行为人欲求的结果:行为的法律效果之发生,系行为人欲求所致”。
不仅如此,其间关键尚在于,“该法律意义或称效果能够被理解为行为人欲求的结果:行为的法律效果之发生,系行为人欲求所致”。 这意味着,强调作为日常用语的 Geschäft 之“交易”含义,对于理解Rechtsgeschäft的语用逻辑,意义实在有限。
这意味着,强调作为日常用语的 Geschäft 之“交易”含义,对于理解Rechtsgeschäft的语用逻辑,意义实在有限。
再次,对于概念的理解,了解用法比单纯的语义分析更重要。
以“法律行为”对译 Rechtsgeschäft 确实难如人意,但这一缺憾,实际上亦存在于德文语词自身。以 Recht与 Geschäft组合而成新词,将其作为专业术语使用,这在德国亦曾有过疑虑。阿福尔特即指出:“日常语言中亦常见 Rechtsgeschäft 一词,证据显示,该语词组合似乎易于理解,其含义即为:法律上的交易(rechtliches Geschäft),与法律相关的交易(Geschäft, welches Beziehungen zum Rechte hat)。” 实际上,将Rechtsgeschäft根据惯常用法进行拆分以求理解,此望文生训现象并不罕见,尤见之于新概念出现之初。
实际上,将Rechtsgeschäft根据惯常用法进行拆分以求理解,此望文生训现象并不罕见,尤见之于新概念出现之初。 原因是,新创概念往往不得不借助既有语词加以表述,而既有语词已然存在相对稳定的用法。在使用惯性的驱使下,理解者往往倾向于遵从语词的既定使用逻辑,从而导致新概念涵义之传达受阻。一般情况下,越是对新概念所依托的意义脉络感到陌生,理解者受语词既定用法牵引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新概念的理解也就越发困难。然而,无论如何容易引起误解,Rechtsgeschäft一旦成为特定的专业术语,就需要明了,其用法不再是简单的语义叠合所能说明者,毋宁说,通过构词法的运用,Rechtsgeschäft被附加了难以从字面看出的新含义。惟有在语词的实际使用中,其所表达的自治观念才能得到理解。换言之,静态的构词法分析固然有助于理解语词含义,但更具意义的,是概念的特定语用逻辑。
原因是,新创概念往往不得不借助既有语词加以表述,而既有语词已然存在相对稳定的用法。在使用惯性的驱使下,理解者往往倾向于遵从语词的既定使用逻辑,从而导致新概念涵义之传达受阻。一般情况下,越是对新概念所依托的意义脉络感到陌生,理解者受语词既定用法牵引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新概念的理解也就越发困难。然而,无论如何容易引起误解,Rechtsgeschäft一旦成为特定的专业术语,就需要明了,其用法不再是简单的语义叠合所能说明者,毋宁说,通过构词法的运用,Rechtsgeschäft被附加了难以从字面看出的新含义。惟有在语词的实际使用中,其所表达的自治观念才能得到理解。换言之,静态的构词法分析固然有助于理解语词含义,但更具意义的,是概念的特定语用逻辑。
最后,关于 Rechtsgeschäft,“法律行为”诚非信译,但新创译法似乎未能表现出实质的优势。既然如此,较为稳妥的做法也许就是因袭旧译。毕竟,“法律行为”之表述通行已逾百年,在未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之前,强行改变这一传统,不见得是明智的选择。时至今日,与其念念不忘译名的“拨乱反正”,不如致力于阐发法律行为的语用逻辑,后者对于理解概念及其背后的学术脉络或许更具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