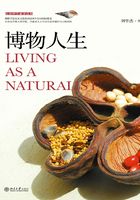
1.2 博物学:是什么?展现了什么?
博物学已经不见于课程表,多数现代人对此极为陌生。我们可以通过多种角度大致描述博物学。从知识论的角度看,博物学是指与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立的对大自然事物的分类、宏观描述,以及对系统内在关联的研究,包括思想观念也包含实用技术。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昆虫学来源于博物学,最近较为时尚的生态学也是从博物学中产生出来的。
何谓博物学?博物学为何似乎消失了?我这里先引用梅里厄姆(Clinton Hart Merriam, 1855—1942)于19世纪末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的描述:
随着生理学、组织学和胚胎学的研究日渐盛行,系统的博物学逐渐被忽视,甚至从大学课堂中销声匿迹,博物学家也几近绝迹。以往通常认为博物学包括地质学、动物学和植物学三门学科,精于此类学科的人被称为博物学家。地质学逐渐独立出来,现在各个大学都把它作为一门学科单独讲授;现在看来,地质课似乎可以取消,但要注意的是如果一个博物学家对地质学一无所知的话,是很难开展其研究的。剩下的两个生物学分支(动物学和植物学)对博物学家来讲似乎已经足矣,但这两门学科的教学已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博物学家”这个词也逐渐被“生物学家”取而代之,有人甚至觉得“生物学”这个词的意义也今非昔比。动物系统学已经不复存在了,即使在鲜有的几个大学还有这门课,也是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植物系统学似乎幸运一些,虽然也明显在走向衰落,但好歹在很多大学还占有一席之地。
这段话发表于1893年,还没到20世纪。读了这段话,也就容易理解20世纪博物学为何衰落了。衰落是事实,反思这种衰落则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迟迟未能启动。
1.2.1 谁是博物学家?
“什么是物理学?物理学家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物理学。”面对物理学的飞速发展和扩张,人们已经很难简单定义什么是物理学了,于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最宽泛的描述方式。
类似地,我们可以用博物学家所做的事情来大致描述什么是博物学。通过若干人物间接界定博物学是个好办法,可回避描述不精确的问题;了解到这些人物的所做所著,也就容易领会什么是博物学。
亚里士多德、达尔文、孟德尔、摩尔根是博物学家 ,其实在当前的文化下,人们早就忘记了这几个人曾是博物学家。
,其实在当前的文化下,人们早就忘记了这几个人曾是博物学家。
更典型的西方博物学家有老普林尼、布龙菲尔斯(Otto Brunfels,1488—1534)、格斯纳、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1522—1605)、约翰·雷、林奈、布丰、华莱士、普里什文、法布尔、梭罗、缪尔、利奥波德、林德利、J. D.胡克、古尔德、劳伦兹、J.古道尔、E. O.威尔逊等,他们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博物学。他们与数理科学家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卢瑟福、爱因斯坦、克里克、奥本海默、杨振宁、格拉肖、盖尔曼、威腾等非常不同。《山海经》、《救荒本草》、《神在造物中展示的智慧》、《物种起源》、《昆虫记》、《沙乡年鉴》、《夏日走过山间》、“博物学沉思录”系列、《蚂蚁》等都是著名的博物学作品。
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博物学实践和顺畅的博物学传承体系,也保留下来大量文献,无论是《十三经》、《通志》、《二十五史》、《古今图书集成》这样的巨著,还是《幼学琼林》这样的蒙学读物,都包含大量的博物学内容;反过来,读者如果有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也能更好地理解《诗经》 、唐诗宋词以及齐白石的艺术作品。李约瑟也称赞中国古代的“本草”著作构成一个伟大的传统(李约瑟,2006:187—189),按李的解释“本草”不是“具根的植物”而是“基本的草药”的意思。中国古代博物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特定植物或者某类植物的专著,“这种现象是西方世界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文献有的论述了整个自然亚科,如竹类;有的论述两个明显相似的野生的属”(李约瑟,2006: 302),比如《竹谱》、《桐谱》、《扬州芍药谱》、《南方草木状》、《滇中茶花记》、《菊谱》、《荔枝谱》、《梅谱》、《金漳兰谱》等。中国古代自然也有大量优秀的博物学家,如司马迁、张仲景、贾思勰、郦道元、沈括、郑樵、唐慎微、寇宗
、唐诗宋词以及齐白石的艺术作品。李约瑟也称赞中国古代的“本草”著作构成一个伟大的传统(李约瑟,2006:187—189),按李的解释“本草”不是“具根的植物”而是“基本的草药”的意思。中国古代博物学家撰写了大量关于特定植物或者某类植物的专著,“这种现象是西方世界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文献有的论述了整个自然亚科,如竹类;有的论述两个明显相似的野生的属”(李约瑟,2006: 302),比如《竹谱》、《桐谱》、《扬州芍药谱》、《南方草木状》、《滇中茶花记》、《菊谱》、《荔枝谱》、《梅谱》、《金漳兰谱》等。中国古代自然也有大量优秀的博物学家,如司马迁、张仲景、贾思勰、郦道元、沈括、郑樵、唐慎微、寇宗 、徐霞客、朱
、徐霞客、朱 、李时珍、曹雪芹、吴其
、李时珍、曹雪芹、吴其 等,甚至包括李善兰
等,甚至包括李善兰 。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博物情怀,但近代的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进程。如今分科之学一统天下,现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自己的传统学术,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博物学。现代教育体系几乎剥夺了青少年从事一阶博物学(上山采野菜、下水捉泥鳅等)的权利。二阶博物学研究在学者中仍然存在,目前分散在多个分支学科当中,如科技史、农史、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研究、知识社会学、文化史研究、民族植物学等。
。中国古代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博物情怀,但近代的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进程。如今分科之学一统天下,现代中国人已经遗忘了自己的传统学术,绝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博物学。现代教育体系几乎剥夺了青少年从事一阶博物学(上山采野菜、下水捉泥鳅等)的权利。二阶博物学研究在学者中仍然存在,目前分散在多个分支学科当中,如科技史、农史、历史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研究、知识社会学、文化史研究、民族植物学等。
不过,并非只有上述大人物才掌握着博物学。在无数普通农民身上,也传承着非常多的博物学。 在传统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博物学家,那时人们对土地、对“天”是有感情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也许无法生存,就像现在如果不晓得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在城市里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一样。
在传统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是博物学家,那时人们对土地、对“天”是有感情的,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也许无法生存,就像现在如果不晓得一点现代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在城市里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一样。
即使不考虑一阶工作与二阶工作的区分,实践博物学也有层次之分,有专业博物学,也有平民博物学。前者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后者则与普罗大众有关。有趣的是,与数理科学很不一样,对于博物学,专业与业余之间始终存在交流的通道,“界面”是可以自由穿行的。
1.2.2 博物学的自然性
博物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近现代科技只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博物学是自然而然的学术、知识、技术和技能,是在有限的好奇心、欲望观照下的产物。博物学产生于远古以来百姓日常生活的正常欲望、自然需要,而不是现代“高端”人群试图获得超额利润、竞争优势的过分需求。
近现代西方科技从一开始就讨论理想情况、非自然的人工环境,所谓的“自然定律”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定律,它们表述的是“反事实条件”关系。自然科学的定律及其导出结果,看起来如此简洁、完美,并不表明大自然本身如此,只是人造的那些“反事实条件”事先规定了情况如此这般。我们实际上始终生活在一个斑杂的世界(the dappled world)、博物学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丰富多彩,是秩序与浑沌的混合物,而不是由简明美丽的几条“规律”控制的世界。所谓“简明规律”通常是想象、建构出来用以规驯自然和人类的。简明自然定律的想法,与机械论自然观的思路是一致的。现代社会中科技工作者操纵“律则机器”(nomological machine),展示修辞上的说服艺术并实现实践中的技术效应(卡特莱特,2006: 58—59)。科学哲学家纽拉特说,数理科学家描述的那个伟大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科学谎言(卡特莱特,2006: 7)。在逻辑经验主义盛行的年代纽拉特能认识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依据自然科学定律开发的现代技术,并不是大自然的技术,它根本上是僭越的、人为操控的技术;它所声称的一系列完美效用,只在特定的人工可控体系中才可实现。
20世纪的科学哲学从石里克、费格尔、卡尔纳普到哈雷、哈丁、哈金、卡特莱特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回归到博物学的世界观、知识观。可以说,严格的科学哲学,努力一番后终于承认了博物学对世界的看法是自然的、不说谎的。博物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我们处在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博物学家或许也产生过把大自然缤纷的面貌、复杂的演化概括为几条简单定律的冲动,但博物的结果不得不使其诚实、谦虚、谦卑一些。现代的教育体制,让人类的后代重点学习的不是自然的知识,而是非自然的知识。教育变得不自然,科学技术变得不自然,社会生活也随之不自然。
1.2.3 博物学的本土性
环境保护运动、科学技术哲学早就从阐释人类学中借用了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的概念(Brosius,1997),对本土知识概念的讨论有大量文献(张永宏,2009)。现在人们多从人类学角度谈本土知识或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也可以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谈局部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这一表述的魅力在于,它并非宣布知识因地理位置其有效性要大打折扣,而是说知识相对于产生该知识的环境而成立。
地方性知识强调如下几个方面:知识的表述可能是附魅的、非自然主义的;产生知识的环境通常是自然演化的人地环境,而非在短时间内特意制作出来的人工环境、实验室环境;知识在人地系统中适应着环境而缓慢演化,知识通常是环境友好的,不会引起环境灾难;由于此知识依赖于特定的环境,脱离其环境后此知识的影响力有限,不会快速扩散到局部环境以外而成为侵略性的全球知识。
博物学知识和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均有地方性、本土性,只是后者喜欢装扮、粉饰,并强行到处“克隆”。现代中小学和大学讲授的知识,基本上是普适的非本土知识,它们主要来源于西方,并且在精神气质上大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从根本上讲,它们原来也是地方性知识,但已去本土化,变成了“普适知识”。当今的科学实验室,每天都在制造本来只适用于实验条件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其地方性非常强。但是,它们通过标准化,通过科学方法和科学体制的装扮,通过发表、技术标准甚至贸易规则、政治交易等,被建构成普适知识。普适性成了知识的一种“美德”。通过强化、正反馈,人们渐渐认定只有普适性的知识才是好知识或者才可以被称为知识。其他的,只配称作意见或者不靠谱的常识、偏见。
博物学知识通常表现为地方性知识、本土知识,不具有普适性,也不冒充普适性。它也没有知识产权的观念(有时也会保密),不喜欢像“输出革命”一样进行智力输出。这并非总是表现为某种缺陷。决定其地方性的原因在于,它是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文化的知识,是环境兼容的知识。借用进化生物学的词语,这种知识与环境是“适应”的。本地人掌握的本土知识是久经考验的,拥有了田松博士所说“历史依据”(田松,2007:93)。这种有“历时性”观察根基的知识有着重要的价值,至少可以补充西方科学由“共时性”观察而来的知识(Gadgil et al.,1993:151)。
我们承认博物学“肤浅”,但博物学、地方性也并非必然意味着十足的肤浅、无用,有时恰恰相反。爱斯基摩人虽然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转基因的秘密,但他们对雪有特别的研究,对于雪的颜色有一系列称谓,能分出许多类型。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雪的变化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和法国在饮食、厨艺上都很讲究,有大量这方面的词汇,比较而言英国就差多了。
本土知识相比于现代科技知识处于弱势,即使一些国家有关部门有意识地强调了本土知识存在的合理性,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本土知识仍然未能恰如其分地整合到决策过程当中,因为在制度层面一些受西方科学训练的人掌握着该考虑哪些“有用的”本土知识,该抛弃哪些“没用的”本土知识(Spak, 2005)。
1.2.4 博物学知识的意向性与价值非中立性
任何知识都是一定世界观、世界图景下的知识。人们创造、完善某种博物学是基于某种目的,所生产出的知识是主客体整合的产物,不能单纯还原为某种客观的知识。
博物学关注的对象和内容多种多样,如牡丹、红木、岩须、辣椒、咖啡、可可、兰、罂粟、香荚兰、凤、龙、浑沌、独角兽、盅毒、五行、气、家燕、熊猫的拇指、贝壳和植物的手性,等等,显然它们未必都是朴素实在论意义上直接存在的。但相对于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它们是有意义的或者有指称的。也可以说单纯的客观“对象”是不存在的,当我们言说“宇宙”时,就是指我们的宇宙,我们已知的宇宙或者能够想象的宇宙。某事物成为认识的“对象”的那一刻,也就失去了对象性的属性,变成了主客观统一的产物。
关于罂粟的知识,在博物学的范畴中,是指你、我、他或某个小群体具体的与罂粟相互作用展现出的多种可能性,不存在脱离语境的客观的罂粟知识,因而也无所谓罂粟是天生的毒品之类的现代人想象。罂粟并不必然与毒品、恶相联系;在我的记忆中它是美丽的(罂粟花十分漂亮)、实用的(罂粟可治病,罂粟籽油可食用)。但如今,法律剥夺了我们种植、欣赏和使用罂粟的权利(在有些国家仍然允许个人极少量种植) 。事实上,正是现代科技的提纯技术以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才使得罂粟变得罪恶。传统博物学知识的意象性范围从来都是受约束的,不可僭越的,人不能妄图拥有神的知识、智慧。这使得博物学的野心是受限制的,从后果论看也是如此。即使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掠夺性的博物学采集,其破坏性也是极有限的。
。事实上,正是现代科技的提纯技术以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才使得罂粟变得罪恶。传统博物学知识的意象性范围从来都是受约束的,不可僭越的,人不能妄图拥有神的知识、智慧。这使得博物学的野心是受限制的,从后果论看也是如此。即使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掠夺性的博物学采集,其破坏性也是极有限的。

四川海螺沟冰川旁边非常美丽的锦绦花(Cassiope selaginoides)(《中国植物志》英文版), 《中国植物志》中文版和《高等植物图鉴》(Vol.3, p.167)称“岩须”,其他名字有:雪灵芝、长梗岩须、水麻黄、万年青、铁刷把。杜鹃花科植物,矮小半灌木,高5—25cm。这种植物的美是无可争议的,但也需要关注,因为多数游客视而不见,或许只觉得它太矮小吧。

二叶红门兰(Orchis diantha),摄于四川九寨沟。

鸡冠围柱兰(Encyclia cochleata),也叫章鱼兰。

香草兰(Vanilla planifolia),又称梵尼兰、香荚兰、香子兰、华尼拉,其蒴果可提取天然香精。
博物学也用于自卫、猎物和杀戮,但其意象性决定了此时它依然展现为某种自然而然的知识和技术。相对于别的科学,博物学虽然不够有力量,但它符合人类、大自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或者不太违背这些要求,幸运地不会成为“致毁知识”(刘益东,2000, 2002;刘钝,2000.03.01)。自古以来,知识生产与知识运用是同一系统的内部过程,而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共同体的“缺省配置”是,知识是客观而中立的,知识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与知识本身无关,那是人的问题、运用不当所造成的。“科学技术是帮助人类理解宇宙、改变物质世界的工具性智慧,本身不具有价值与责任属性。运用科学技术最终出现什么结局、造成什么后果,完全是人的责任。”(张开逊,2010:16)实际上,知识从其生产或意欲生产的那一瞬间就与目的性、意向性高度相关,就与最后的各种可能应用有瓜葛。目前,博物学的发展与资本增值的关联并不像在其他学科中那么明显,也许正好因为博物学的“无用”、低效率才使得它是一种值得真正追求、去玩味、去实践的学问。

爪唇兰(Gongora truncata),也叫飞凤兰。
1.2.5 博物学传统与博物学文化
即使在当下不看好博物学的人,也无法否定历史上博物学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法伯(P. L. Farber)写过一部科学史小书《发现大自然的秩序》,副标题就叫“从林奈到威尔逊的博物学传统”。现在每一门响当当的学问,在发展的过程中几乎都有着博物的发展阶段,以医学为甚。1989年美国马里兰专门举办过一次展览“医学与博物学传统”(Boyd, 1989)。类似地可以讲农业的博物学传统、地质学的博物学传统,甚至几何、概率论的博物学传统。
这里的“博物学传统”有多层含义:第一层是就历时性、发生学而言的,指如今成熟的大量学科,都曾有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博物发展过程。第二层是就共时性、知识特征而言的,比如医学实践仍然是一种艺术、手艺,其中相当多工作要靠经验而不是理论、演绎。医学、医疗不能简化为书本知识、标准化的诊治过程。第三层是就思维方式而言的,指整体论而非还原论。在医疗中,现在世界上仍然存在不同的体系和建制,中医和西医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不同传统是不可通约的,如陆广莘所说“用西医看似科学的方法来衡量中医,不具有现实意义”(陆广莘,2009:60)。中医有极强的博物学传统,重视调理生命节律和气血,辨证施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传统的不同表现为生命观、方法论取向上的差异,中医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中更关注的是机体的自我维生,而不是努力发现致病因子而进行人为干预。
博物学传统背后有着丰富、深厚的博物学文化,涉及神话、哲学、宗教、历史、经济、习俗、生活方式等等。博物学文化在最近十多年得到科学史、文化史、哲学、人类学界的关注,其中《英国博物学家》(D.E.Allen,1994)、《博物学文化》(Jardine,et al., 1996)和《致知方式》(Pickstone, 2001)等影响较大,国际科技史界也开始用更多的精力关注“博物学与科学革命”(J. M. Levine, 1983: 57-73)、牧师与博物学家(Patrick H. Armstrong, 2000)、西方殖民地中的博物学家(Fati Fan, 2004)等主题。英国出版的“柯林斯新博物学家文库”(Collins New Naturalist Library)有一批好书(持续60余年,已经出版100多部),非常值得引入中国。英国《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季刊2004年3月还出版了一期“博物学专号”(42卷第135期),刊发了4篇博物学史论文。从已经译成中文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中,也可以感受到博物学史、科学史、文化史的深度融合及其有趣性。海灵曼(Noah Heringman)主编的《浪漫的科学》、张嘉昕著《明人的旅游生活》也与博物学史有关。
就哲学而言,博物学文化展现了诸多不同于当下主流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比如在博物学文化中,人与自然不是对象性关系,大自然、生命具有灵性或神圣性,不可能仅以物质或比特的形式来充分把握。博物学文化尊重大自然的变化过程和巨大力量,不过分夸耀人类的征服能力 ,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在日常生活层面,博物学文化倡导过普通的安定平和的生活,用中国古人的话讲就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
,不会高喊“人定胜天”,也不会盲目崇拜强力与速度。“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谐共生、生生不息是博物学文化的终极旨趣。在日常生活层面,博物学文化倡导过普通的安定平和的生活,用中国古人的话讲就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