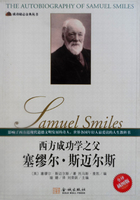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4章 青年时代的回忆
1820—1925年——马车夫节
在进一步讲述之前,我得提到几件孩提时代让我很感兴趣的事。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假期较少,除了8月的农忙时节,学校会放上四五周假。地方官员和学生父母会参加期末考试的成绩发布仪式,由于孩子们就要离校了,每人都能得到一袋糖果。哈代的学校就是这样,而在格雷厄姆的学校,除了糖果,最优秀的学生还能得到奖品。
马车夫节,也是我们的节日之一。镇上有许多货运马车,是用来在哈丁顿和爱丁堡之间往来运送粮食和货物的。马车夫们自己集资,每年夏天在镇礼堂举行一次舞会。他们会选一个人来主持活动,大家会向他欢呼,称他为“我的主人”。马车夫们用奇装异服将自己打扮起来,把帽子扔给情人,她们大多是女仆。她们把缎带戴在他们的帽沿或头顶上,跟许多缎带挂在一起。“我的主人”通常穿一件经过装饰了的棉绒夹克。马车夫们先集合成队,然后骑马在镇上游行。他们会在教区学校停下来,这时,“我的主人”走进学校,请校长放学生的假。这个请求总是能得到同意,于是,孩子们就会跑去看赛马。赛马在劳伦斯剧场和贝格比训练场之间的大街上举行。赛马结束后就是舞会,由头戴“我的主人”的帽子的女仆——“我的女主人”举办。我记得,在“我的女主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家的仆人。
这种奇特的风俗后来完全销声匿迹了。可怕的事故时有发生,因为货运马不宜在碎石路上奔跑,有时,这可怜的畜生会跌倒在地,受伤的马只能被枪毙。马主人有时也会受伤,摔坏胳膊腿儿。所以,马车夫节被废止了,更确切地说,是在镇上出现了铁路,使货运马车数量大减的时候被废止的。
1820—1825年——古老的习俗
我们的节日还有国王诞辰日、新年和斋戒日。在国王诞辰日那天,全体市民都会在十字架前集会,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夜晚时分,人们会在街上点燃篝火,与烟花爆竹和大炮小炮的轰鸣交相辉映。
我还要说一件让自己心惊胆战的事。那就是在马车厢里当众抽打小偷。毫无疑问,小偷们罪有应得,但这是在赶集日进行的,以便吸引最多的观众——男人、女人和孩子都要看。约6个或8个指定地点都会进行这种鞭刑,行刑的人用的是多节鞭,鞭刑结束后,犯人被送进监狱,继续受刑。
在镇礼拜堂里,还有另一种“示众”活动,跟在车厢里抽人一样暴戾,这就是让男人和女人坐在忏悔座[6]上,当众谴责他们。一般受惩罚的只有女人,男人受不了这种惩罚,就逃走了。幸好孩子们还不理解这种谴责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通常都被打发回家了。
当时,镇上有了自己的风笛手和鼓手。这是过去的古老习俗,在我很小的时候,地方官恢复了这种习俗。风笛手唐纳德·麦克格雷戈尔在环镇游行的时候,会奏起苏格兰高地小调。鼓手老贝尔德,会在拍卖和促销等诸如此类的活动上擂鼓叫卖,招揽大家的注意力。有时,他会喝得酩酊大醉,结结巴巴地胡言乱语,叫人们听不清他的叫卖。后来他被解雇了,“刽子手”汉奇被派去接替他的位置。汉奇是镇上的警察,因为欠了债,接受了10英镑的酬金,在车厢里抽打一个小偷,并沿街示众。后来人们就叫他“刽子手”了。星期天,他常常跟别的警察一起从镇礼堂巡逻到教堂,后面跟着地方官员。
尽管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本关于“节俭”的书,可我小时候一点儿也不节俭。我们小孩子都有零钱罐或储蓄罐,为的是培养自己把多余的钱存下来的观念。可我从来都不存钱,我认为钱主要就是用来花的。我偶尔会把几便士投进储蓄罐,可我很快就会用餐刀再把它们弄出来。我的兄弟杰克把他的罐子都存满了,这时候就得把罐子砸碎才能拿到里面的钱。而我的罐子常常都是空的。我估计,是岁月和理性带来了“节俭”的观念,不过,我还是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
我记得,在我很小时,第一次接触到的小说是沃尔特·司各特[7]的小说。我的一个妹妹还是婴儿时,被父母送到乡下抚养;星期六下午,我常常跟家里的仆人佩格·尼尔森一起去探望她。我们要路过克拉金顿公园,这是个迷人的地方,离镇子有一英里远,泰恩河从公园里蜿蜒流过。佩格是个优秀的故事家,她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古老的故事:核仁巧克力饼的故事、仙女的故事、幽灵的故事和女巫的故事,常常听得我们心痒痒的,而她也能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得到乐趣。有一次,我们在前往克拉金顿主城区的途中时,我要她讲个故事。她说,“好吧,给你讲一个吉普赛女郎和一个被偷渡者带上船的小男孩的故事。”然后,她就以一种很形象的方式,开始讲述名著《盖·曼纳令》中的哈里·伯特伦和梅格·梅里利斯的历险故事了。多年以后,我读到这本书时,才发现她没有省略这个故事的任何情节:她的记忆力太好了,讲述能力也十分出色。
1820—1825年——爱丁堡之行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爱丁堡参观了议会大厅。当时那里设立了法庭,在一次开庭期间,我看见了沃尔特·司各特先生。他是审判法庭的书记员,在另一个书记员对面坐着,法官就坐在他们的上方,而查理斯·霍普是审判长——一个长得英俊标致的男子,嗓音很好听。我看见沃尔特·司各特站起来,一瘸一拐地绕过桌子向他的书记员同事走去;接着,他离开了法庭,向议会大厅走去。我还在法庭上见到了弗朗西丝·杰弗里、亨利·科克本;前者是个机智敏锐的矮个儿男人,脸上经过仔细的修饰;后者以那双明察秋毫的深邃眼睛而著称。
还是回头来继续描述我的家乡吧。哈丁顿坐落在泰恩河谷,位于加勒顿山区的南坡脚下。在一座英国古老的土木工事不远处的山顶上向南眺望,能看见一片壮丽的景观。泰恩河从谷底蜿蜒流过,坐落在谷地空旷地带的古镇和古教堂,凸显出灯火辉煌的洛锡安和它雄伟的中心城堡。在那里,沉睡着祖祖辈辈的圣灵。
镇子以西,穿过萨尔顿森林,是树木葱茏、土地肥沃的山谷,那里曾是烈士安德鲁·弗勒切尔的故居,它面朝穆尔福特和绕春山。向正南方向眺望,视野可以延伸到种植园,它们环绕着古老的勒斯顿要塞,那里曾是梅特兰阁下(苏格兰玛丽女王手下那位狡猾的大臣兼顾问)的官邸。向南眺望,越过阿格勒斯卡尼、考尔斯顿和吉福德附近被林木环绕的村庄,视野可以一直延伸到拉莫缪尔斯山的最高点,它那蓝色的顶峰直插苍空。
沿着泰恩河谷向东下行,景色会越过阿密斯菲尔德、韦丁哈姆,向黑尔斯城堡延伸,这里是命途多舛的玛丽女王和她第三个丈夫的临时避难所,他们是在哈丁顿的波斯维尔[8]官邸中共度一夜之后逃到这里的。瓦普林·罗丘遮挡了东面的一部分视野。罗丘是一个大圆丘,是一块暗色岩[9],跟周围山地毫无牵连,在遥远的年代里,是它挡住了自西而来、涌向村子的激流和冰块。
尽管从加勒顿山南坡向下眺望,可以看到美景,但从北坡眺望,景致更美。从刹车山那边,一块辽阔的平原铺展开来,揽入了东洛锡安最肥沃的田野。它西起顿巴前方,东至穆塞尔区。福思河在这座美丽的村子四周流淌着,蓝色的费夫山远远地横在北方。在穆塞尔湾的那一边,亚瑟[10]的行宫就象一头休憩的卧象一样,国家纪念碑的柱子矗立在卡尔顿山上,远处就是烟雾缭绕的爱丁堡,景致气象万千。向北眺望,在5英里以外的地方,能看见古斯福德森林(那儿有威姆斯伯爵的官邸)、阿伯雷迪湾——拿破仑的登陆地、古雷恩山;再向东望去,是戴尔勒顿城堡遗址,然后是巴尔古尼、红屋、北伯维克·罗山(一座死火山)、巴斯岩、坦托隆遗址——道格拉斯家族最坚固的城堡之一,也是他们保留的最后一座城堡;在弗斯湾口很远的海面,是矗立着灯塔的梅岛。
1822年——国王乔治四世
在1822年8月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爬上加勒顿山,观看皇家舰队从福斯湾[11]到利斯[12]的巡航。在古雷恩山那一边,只见三艘军舰相互靠得很近;戴着望远镜的海军士兵告诉我们,乔治四世就在中间那艘军舰上,他要前往利斯和爱丁堡。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镇上的人们就已经处于兴奋的状态了。当时,满载石南花的敞篷车和四轮马车从街上穿过,车上挂着国徽。每个人都必须去爱丁堡观看著名的游行和迎驾仪式。但父母考虑到我太小了,不让我去,于是,大哥跟着父亲去观看这精彩的一幕了。
度完了八月假,我去达尔克斯拜访了很多亲戚了,这时,国王仍然下榻在布克雷奇公爵官邸。我看见从公爵府里出来的“纨绔子弟”穿过主街,去纽巴特尔教堂拜见洛锡安侯爵。我只晃眼瞟了国王一眼,因为他的马车走得太快了。苏格兰皇家骑兵队那时就在达尔克斯,他们的乐队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教区教堂前面奏乐。在护卫国王的时候,骑兵卫队会全力以赴、快马加鞭地在达尔克斯和爱丁堡之间往返。
在达尔克斯拜访了亲戚之后,我又去拉斯韦德、楼恩黑德、霍索德和罗斯利,拜访了另一些朋友。北埃斯卡一带的景色都很迷人;我徒步穿过普尔顿,在从霍索德到罗斯利的路上,都快被那里的河景迷倒了。罗斯利的古堡遗迹和精工修葺小教堂——建筑艺术上的一个奇迹——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1820—1825年——祖父去世
那时,我祖父还健在。他还是改革长老会里的元老。几年前,我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把我带到了圣会的讲道现场。人们千里迢迢地赶了过来,坐在草地上,或者躺在草地上;传道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上场讲道,他们不时会唱唱圣歌;圣会一直持续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在我放假期间,恐怕这些年长的人会觉得我是个十足的捣蛋鬼的。我有一把小枪,还有火药,几乎整天都在玩枪。邻居对我不满,可我还是继续玩;最后,火药炸了,烧伤了我的手,后来我的伤还是痊愈了。
祖父是一位相貌堂堂的老人,性格温和,长长的白发散落在肩上。我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陪我沿着小路走了半英里。显然,他越走越感到疲惫乏力。尽管他健康地活到了90岁,可年龄还是影响了他的身体状况。最后他说,“我累了,”说着就在里程碑上坐了下来。缓过气以后,他说,“我亲爱的小伙子,我再也见不到你啦。我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实在是太虚弱了。我不得不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死。你还年轻,可在我之后,你也一样会遇上这件事的。现在,你要做个好孩子,要读圣经,要听你父母的话,再见啦,塞缪尔。”
就这样,我满怀深情地告别了这位老人,在那里跟他分了手。回头的时候,我看见他正步履蹒跚地向山上走去。后来,我就再也没见到他了。我再次看到他平静的面容时,他正躺在棺材里。同年底,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被安葬在拉斯韦德墓地,就在埃斯卡的美丽谷地上的阿基戴尔·威尔逊将军(德里大捷)的纪念碑附近。